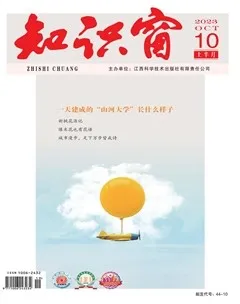躍入人海,做一朵奔騰的浪花
林木森

第一次覺得自己老了,是在校車上。當時是武漢的夏末,熱得讓人對一切都倦倦的。
我坐在窗邊,看著上來一個滿頭大汗、背著包,還拖著一個很大的黑色行李箱的男生。他滿眼迷茫,卻聲音洪亮地問司機:“師傅,到工學部嗎?”
因為我也到工學部,所以稍稍對這個男生多加了一些關注。
男生坐在離車門最近的位置,也是一個窗邊。一路上,他總是十分好奇地東張西望,有時還微微站起,探出身子往外四處張望。
我在心里笑了笑,但表面上還是不動聲色。
記得兩三年前的我也是這樣,或者更甚。
這趟校車叫“大循環”,是學校的環線,工學部是單程的最后一站。
那時候的校車還沒有安裝智能播報系統,校車司機的耐心似乎也被武漢的炙熱烤得所剩不多,不會每到一站都提醒學生下車。所以,車上很多新生除了睜著好奇的大眼睛,只剩下迷茫和擔心。迷茫的是不知道何處是何處,也不知道如何開口詢問,擔心的是會不會坐過了站,離目的地越來越遠。
而我為什么知道這些呢?因為這些新生讓我想起自己進學校的那天,太陽很大很大的那天。
那時,我背著大大的書包,拖著大大的箱子,汗流浹背地走在路上。我看著校車路牌,卻一頭霧水,在大小循環坐車點中間徘徊,最后看著身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對我來說完全陌生、充滿驚喜的校園建筑,終于毅然、決然地踏上被太陽炙烤著的水泥路。雖然手機可以導航,但七七八八的岔路口還是讓我迷失了方向。
但那個時候,我居然覺得往哪里走都是好的,因為可以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更快地揭開這個學校的神秘面紗。
后來長大了,我好像更害怕烈日,更害怕走錯路,覺得在一個錯誤的地方下車,是一件多么不應該的、不值得的事。
所以在還有兩站才到工學部的湖濱站,車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爭相下車,那個男生顧盼左右,然后正準備下車的時候,坐在不遠處的我想叫住他,甚至都沒意識到自己著急得已經從座位上微微起身了。
但看到那個男生雖然迷茫,卻無比堅定的眼神,以及扎進烈日里依舊燦爛的笑容,到嘴邊的提醒一時停住了,我重新坐回位置上,輕輕靠著椅背。那一瞬間,好像什么都沒發生,又好像什么都發生了。
我第一次鮮明而深刻地覺得,自己“老了”。
在后來的很多個夜晚,我都會想到那個瞬間,說不上來的情緒像失眠時窗外暗綠色的光,看似微弱,實則有吞噬一切的力量。有時我會慶幸,慶幸自己沒有叫住那個男生;有時我又會暗暗地想,如果叫住他,結果會是怎樣的不一樣。偶爾我甚至會有一些難過和內疚,問自己:“怎么會有叫住他的想法呢?”尤其是想到他下車時眼里的憧憬和向往,我就越覺得,如果當時告訴他下錯了站,那才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和這件事里的自己和解,是在參加完畢業典禮、快要離開學校的那幾天。那時,我終于從故事里那個準備叫住別人的學姐,又一次變成不知去路、選擇胡亂嘗試的新生。我記得我騎著共享電單車,漫無目的地在校園里穿梭,有時走進了沒有出口的巷子,有時明明可以直達的目的地,我卻繞了很遠的路;有時會因為路邊一朵不合時宜的花而突然停下,有時會因為前方的某個背影仿佛和記憶重疊,而加速前行……好像在一次又一次地探索和嘗試里,我看到了曾經那個滿眼懵懂卻勇敢熱情的自己,也好像在一種故地重游的情緒里,獲取了一種叫作時光倒流的錯覺。
在正式告別母校的時候,我在心里對自己說:“不可以哭,在武漢大學的最后一堂課,應該是笑著離開,帶著眷戀,但已然成長為一個可以欣然告別的大人。”但最后一次刷開校園門禁,走過出校通道的時候,我感受到一陣被酸澀包裹的情緒,我轉過身看著這個過去四年走過無數次的路,水泥地面還是被午后陽光炙烤著,瀝青反射著刺眼的光。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故意,我總覺得,母校在提醒我想起當初那個橫沖直撞的自己,晃眼的光也好像在催促我回頭,去迎接新的方向。
“未來躍入人海,也要做一朵奔騰的浪花啊。”我聽見,母校對我說。
我含著淚回頭,在心底感念母校過去四年的包容、照顧和培育,她看似把所有問題都直接置于什么都不懂的我面前,實則用最小心的守護陪伴著我,她從不催促我成為一個優秀的大人,而只是鼓勵我不要遺失勇于探索的、擁抱未知的初心。她像夜里皎潔的月光,在一切光芒褪去的時候,也讓我知道有一束光還在這里,還停在我身上。當有一天,我以為自己已經足夠了解她、可以脫離她的懷抱的時候,卻從未想過這也是她精心設計的、留給我的最后一份禮物——堅定地告別,再去奔赴下一場山海。
“好。” 我回答道。轉身離開的瞬間,隔著車水馬龍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又一次看見了,2019年初秋的自己、18歲的自己,以及那個勇敢、熱情、堅定、對世界充滿好奇的自己。
“未來躍入人海,也要做一朵奔騰的浪花啊。”我對自己說。
(作者系武漢大學英語專業2019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