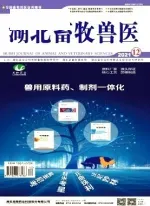制造業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及其影響因素
——來自浙江省的調查
劉云茹,謝夢婷,王晨羽,鄔柯皓,戚迪明
(衢州學院,浙江 衢州 324000)
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在城鎮化進程中,有2 個問題不容忽視,一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緩慢,城市內新二元社會結構凸顯[1,2]。城鎮常住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是真正意義的市民,他們既不具有市民的身份,也不具備市民的權利,并不能享受城市政府為市民在就業、居住、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所提供的各種公共產品和服務。二是較之以城區面積擴大為內容的土地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嚴重滯后。雖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逐漸打破,但區域公共服務享用的準入門檻仍在。農業轉移人口雖能在城市獲得工作,但城市公共服務供給卻沒有與他們的就業掛鉤,在很大程度阻礙了中國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實質就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3]。城鄉二元戶籍改革已經啟動,而戶籍改革的本質是能否實現城市公共服務的均等化[4]。因此,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實現無差別的公共服務是各級政府在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浙江省自20 世紀90 年代提出加快城市化進程重大決策以來,城市化列車駛入了快車道,全省城市化率從1998 年的35.0%提高到2015 年的65.8%,特別是2006 年提出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以來,城市化發展更加注重質量提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協調性明顯提高。但實踐中仍存在一些問題,突出表現在人口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土地城市化,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還不能平等享受城鎮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基本服務均等化的提出為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的問題提供了基本原則、標準及行為框架[5]。以“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切入點借鑒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需要轉變政府職能[5],增強農業轉移人口的維權能力。李梅香[6]從就業、社會保障、子女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等方面建立指標體系,采用直接賦分法評估新生代農民工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偏低。孫德超等[7]認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應從社會保障服務、公共就業服務、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服務、公共衛生服務及基本醫療等方面入手,具體要加強社會保障立法、建立分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拓寬社保資金的籌資途徑,加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培訓、建立城鄉統一的用工管理制度,改善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服務,建立門診費用報銷制度、完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丁會明[8]針對公共服務中的教育問題提出了均等化對策,創新流動兒童的服務管理制度、創新區域內教育服務、改革課程和考試制度、加強服務監督和管理等。李璐[9]認為需要多渠道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完善公共服務的資源配置方式,改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快推進社會融合組織建設。邱雯雯[10]在借鑒美國、加拿大、日本和韓國公共服務均等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針對新生代農民工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提出要運用法律手段保護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力、完善財政制度,并提升新生代農民工享受公共服務的能力等措施。胡艷輝[11]認為針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要注重各項制度間的銜接和配套,兼顧公平和效率。
關于政府對農業轉移人口公共服務供給問題的研究主要從政府供給不足的角度展開[10]。政府對農業轉移人口提供的社會保障服務、公共就業服務、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服務、公共衛生服務及基本醫療等都存在不足。申兵[12]進一步將政府細分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指出地方政府在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公共服務問題上的意愿不強、能力不足。梁滿艷[13]對地方政府供給公共服務的能力進行了研究,認為地方政府普遍存在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在基本能力不足的同時,還存在供給效率低下的問題[7,14]。本研究基于浙江省紹興市、臺州市制造業農民工的抽樣調查,分析其城市公共服務獲得情況與主體需求,構建計量模型實證分析影響其公共服務選擇的關鍵因素,以期為城市政府提供更優的公共服務提供政策建議。
1 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研究所用數據來源于2019 年8 月對浙江省臺州市、紹興市制造業農民工的抽樣調查,調查采用訪談法進行,在征得被調查對象同意后,由調查員進行一對一調查,累計獲得191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180份,問卷有效率為94.2%。其中,男性占比57.1%,高于女性農民工比例。被調查對象年齡主要集中于30~39 歲,占比35.0%,與其他行業農民工相比,制造業農民工相對較年輕,50 歲以上的受訪者占11.1%。受訪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占比達58.9%,32.2%的受訪者受教育程度為高中(中專)等,與其他行業農民工相比,制造業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76.1%的受訪者為已婚,23.9%的受訪者為未婚。制造業農民工平均外出務工年限為5.6 年,其中10 年以下占93.9%。
2 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獲得分析
2.1 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獲得情況
2.1.1 就業公共服務獲得 就業是民生之本,農民工進入城市首要的是解決就業問題,研究從工作獲得途徑、技能培訓及就業幫扶3 個方面分析農民工城市就業公共服務獲得情況,58.3%的受訪者通過親朋好友的介紹獲得工作,有27.8%的制造業農民工自已找工作,只有13.9%受訪者通過政府部門提供幫助,說明多數農民工在尋找工作過程中沒有獲得過城市政府的相關服務。此外,只有23.3%的受訪者獲得過城市相關部門提供的技能培訓,22.2%的受訪者獲得過城市相關部門的就業幫扶。大多數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并未獲得過相關部門的就業公共服務,原因是城鄉二元就業制度,大多數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只能以非正規就業的方式獲得工作,很難進入城市正規就業渠道。這意味著隱含在城市正規就業渠道下的就業培訓、就業幫扶等就業公共服務很難覆蓋到農民工群體。18.2%的受訪者曾遇招工歧視,6.7%的受訪者反映經常遇到這種情況。此外,11.7%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與同樣工作的本地人相比,工資存在一定差異。
2.1.2 住房公共服務獲得 安居才能樂業,居住問題也是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后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從受訪者的住所來看,67.8%受訪者在私人出租房居住,15.5%受訪者居住在單位宿舍,16.7%的受訪者已在務工地購買了住房。大部分農民工未享受到城市住房相關服務,由于戶籍制度的原因,農民工并不能享受城市廉租房的相關服務,大多數農民工通過自己租房或務工所在單位的員工宿舍解決住房問題。進一步考察農民工對自身居住狀況的主觀評價情況,14.4%的受訪者認為房子質量較好,17.8%的受訪者對居住狀況表示滿意,但有23.3%的受訪者認為房子質量不好,17.8%的對居住狀況不滿意。制造業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多數只是解決了“住”的問題,遠沒有到解決“安”的程度。
2.1.3 教育公共服務獲得 農民工在城市教育公共服務的獲得從2 個方面來體現,一是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情況,二是農民工本人在城市獲得的繼續教育服務。180 個樣本中有110 個受訪者家中至少有一個初中及以下的孩子,其中36.7%的農民工孩子就讀于城市公辦學校,為免借讀費,只有6.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相關學校借讀要支付子女的借讀費。這表明在勞務輸入地政府已經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提供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公共服務,但只是在義務教育階段,中考就必須回到生源地。從農民工本人在城市接受繼續教育服務來看,參加過城市相關部門提供的繼續教育服務的僅占6.3%,受訪者中有19.4%擁有各類職業資格證書,但其中大部分農民工外出務工前在老家所在地就考取了相關證書,也有少部分通過所在單位獲得職業資格證書,通過城市提供的繼續教育服務進而獲得職業資格證書的比例極低。
2.1.4 社保公共服務獲得 農民工社保公共服務主要從2 個層面分析,一是參加社會保險的情況,從調研數據分析來看,180 個樣本中有137 人擁有除合作醫療、新農保外的保險。從參加社會保險的類別來看,參加人數最多的為醫療保險,有131人,占比95.6%,其次是工傷保險,有102 位受訪者,占比74.5%。最少的是養老保險,僅22 人參加,占比12.2%。制造業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比例相對較高,其原因在于制造業農民工就業相對穩定,同時,單位的勞動保障較其他行業而言相對到位,使得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比例較高。另外,從農民工因病就醫選擇來看,研究設置了“如果生病了(常見疾病感冒、發燒),選擇到哪里看病時”的問題,統計后發現92.8%的樣本對象會選擇去正規醫院看病或去藥店買藥,只有7.2%的人會去個體診所看病或熬著等病好。說明農民工對城市醫療水平較為信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使用城市醫療資源,也從另一個層面表明制造業農民工較好地享受了城市醫療服務。
2.1.5 文化公共服務獲得 農民工在城市文化公共服務獲得主要通過其使用城市公共文化設施來體現,數據表明,77.2%的受訪者居住地周邊有廣場、健身器材等公共設施,并且大部分受訪者使用過這些公共文化設施。另外,從農民工下班后的休閑娛樂活動來看,看電視和上網占比較高,分別為76.67% 和52.22%,看電影和逛街的占比分別為33.33%和28.89%。從休閑活動的特性及與城市文化設施緊密度來看,看電影和逛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農民工對城市文化公共服務的獲得。從農民工城市文化公共服務獲得的總體情況來看,農民工對于外置的公共文化設施使用相對較多,但對于圖書館、藝術中心等文化場所的使用很少。
2.2 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滿意程度
在分析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獲得情況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其對城市公共服務的滿意程度,研究主要從2 個層面分析,一是對城市公共服務的總體滿意程度,主要是在總量指標上體現農民工對城市公共服務的滿意程度;二是對具體公共服務類型的滿意程度。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滿意度見表1,由表1 可知,從農民工對城市公共服務總體滿意度來看,27.2%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有12.3%的受訪者對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表示不太滿意或不滿意,有60.5%的受訪者認為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一般,說明農民工對城市公共服務的總體滿意程度不高。滿意程度最高的是教育服務,有56.1%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這主要是對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齡兒童而言,所在城市多數能夠接納他們入學,并且大多數都不需要借讀費,至少在義務教育階段解決了農民工子女就讀入學問題,使得受訪者的獲得感較深。滿意程度最低的是就業服務,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占比20.6%,不太滿意和不滿意占比59.5%。農民工進入城市首先要解決的是就業問題,只有就業問題解決了才有可能在城市穩定下來,所以就業信息服務、就業培訓、職業介紹等公共服務尤為重要,農民工對城市提供的這些服務獲得感也會比一般公共服務要強得多。
3 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分析
3.1 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描述
3.1.1 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總體需求狀況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體是農民工,從農民工視角出發,考察其對城市公共服務的需求具有重要意義。結合對城市公共服務類型的分析,研究細化成具體8 個方面的公共服務需求。調查發現,農民工對教育條件的公共服務需求比例最高,31.1%的受訪者最想要獲得新知識,參加培訓得到職業資格證,其更深層次的目的在于通過繼續教育提升就業能力以便獲得更高質量的就業,進而獲得更高的收入,提升其定居城市的能力。有21.1%的受訪者希望國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帶來收入的增加,而對權益的保障、工作環境改善的需求相對較少,分別占4.4%和5.6%。
為了更好地體現公共服務需求內容的層次性,將公共服務劃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滿足個人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務內容,主要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和改善社會保險;第二類是滿足家庭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務內容,主要包括提供保障住房或廉租房、改善子女教育條件和改善醫療條件;第三類是滿足個人進一步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內容,主要包括改善工作或生活環境、加強權益保障和提高職業技能。上述三類公共服務需求存在一定的等級性,首先滿足個人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務是最基礎的需求,其次是在滿足個人生活需要基礎上的家庭生活需要,層次最高的則是進一步發展的需求。將需求內容進行分類后,進一步統計發現,公共服務需求中家庭生活方面比例最高,占比52.2%,農民工進入城市后工作生活等領域的決策都是從整個家庭層面出發。關注發展需要的比例為17.2%。30.6%的農民工選擇個人生活需要的滿足,說明了農民工公共服務獲得情況并不理想,較低層次的公共服務還存在大量需求,政府應當關注這一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
3.1.2 個體特征與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 為更深入地識別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特征,將農民工的個體特征與城市公共服務需求進行交互分析,結果見表2。由表2 可知,與女性農民工相比,男性農民工對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需求明顯更高,而對家庭生活需要類的公共服務需求明顯更低。這表明女性農民工更加側重于家庭,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也會更多從家庭、家庭成員的角度來考量,而男性農民工更側重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于發展的需求逐步降低,29 歲及以下的農民工選擇發展需要的比例為30.0%,而50 歲及以上的農民工選擇發展需要的比例僅為6.3%。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民工對家庭生活的需要選擇比例逐步上升,29 歲及以下的受訪者選擇家庭生活需要的比例為15.0%,而50 歲及以上受訪者的比例為77.8%。從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和公共服務需求選擇來看,受教育程度為9 年以上的農民工對家庭公共服務的需求更高,占比55.2%,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工更看重個人生活需要。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農民工對發展需求的選擇比例也逐步上升,這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層次也會越高,會更重視自身發展需要。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較高,獲得了更高質量的就業和更高的收入,轉化為農民工進一步提升個人能力,形成循環累積效應,促進農民工更重視自身發展需要。從婚姻狀況與公共服務需求的交互來看,已婚農民工更加重視家庭生活需要,而未婚農民工更加重視個人生活需要。

表2 個體特征與公共服務需求的交互分析 (單位:%)
3.1.3 就業、城市融入與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 比較不同就業、不同城市融入特征的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的差異,通過交互分析,發現隨著務工收入的增加,個人生活需要的比例逐步降低,而發展需要的選擇比例逐步提升,收入在5 萬元以下的農民工選擇發展需要的比例為4.8%,而收入在10 萬元以上的農民工選擇發展需要的比例達62.5%,務工收入與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的層次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關。原因在于收入較高的農民工更易感知到通過個人發展可以進一步獲得高質量就業(創業),進一步增加個人城市務工收入,他們會更關注城市提供的有利于其個人成長發展的公共服務。從就業時長與公共服務需求層次的交互分析來看,累計務工時間在10年以下的農民工選擇發展需要的比例要高于務工時間10 年以上的,對于個人生活需要的選擇呈相同的特征,原因在于累計務工時間跟農民工的年齡有一定的相關性,務工時間短的農民工,相對年輕,一方面注重個人生活需要,同時也會關注發展的需要,而務工時間長、年齡較大的農民工更關注家庭生活的需要。從城市定居意愿與公共服務需求的比較來看,對于個人生活需要的選擇,愿意定居與不愿意定居者選擇比例較為接近。
3.2 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的回歸分析
3.2.1 變量選擇 因變量,研究考察的因變量為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考慮到公共服務需求類型的多樣性及可測量性,將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劃分為3 類,即個人生活需要、家庭生活需要和個人進一步發展需要。同時,研究認為3 個層次的公共服務需求存在一定的序列等級,即滿足家庭生活需要高于個人生活需要,而滿足個人進一步發展需要又高于家庭生活需要,因此,將選擇個人生活需要、家庭生活需要和個人進一步發展需要分別賦值為1、2、3。
自變量,研究關注的自變量主要包括3 個方面,一是農民工的個體特征,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二是農民工就業特征,主要選取務工收入和累計就業時長;三是農民工城市融入特征,以定居意愿來衡量。
3.2.2 模型設定 研究要分析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選擇的影響因素,由于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選擇劃分為3 個層次,上述變量取值分別為1、2、3,屬于有序分類變量,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 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2.3 估計結果解釋 采用有序Logistic 模型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3。由表3 可知,從個體特征對公共服務需求的估計結果來看,性別通過5%水平顯著性檢驗,表明其對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具有顯著影響,回歸系數為正,說明與女性農民工相比,男性農民工選擇更高層次的公共服務需求的概率更高,這與一般預期相符。從家庭內部分工來看,男性農民工更需要通過個人進一步的發展、提升獲得更高的收入,從而使自己及家庭受益。年齡通過10%水平顯著性檢驗,表明該因素對農民工公共服務選擇有重要影響,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相對年輕的農民工選擇更高層次的公共服務需求的概率更高。受教育程度通過5%水平顯著性檢驗,表明該因素對于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其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選擇更高層次公共服務需求的概率越高。婚姻狀況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該因素對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選擇沒有顯著影響。

表3 估計結果解釋
從就業特征對公共服務需求的估計結果來看,務工收入通過5%水平顯著性檢驗,表明該因素對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選擇具有重要的解釋作用,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務工收入越高,農民工選擇更高層次公共服務需求的概率越大。累計就業時長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從定居意愿對公共服務需求選擇的影響來看,該變量通過1%水平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具有城市定居意愿的農民工,選擇較高層次公共服務需求的概率更高。可能是在城市定居需要農民工有更高質量、更穩定的就業,需要有更高的收入,從而驅動農民工在務工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使其更加關注能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公共服務供給。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研究通過對浙江省臺州市和紹興市制造業農民工的抽樣調查,運用描述性統計和回歸分析方法,重點對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獲得、公共服務需求及其不同需求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13.9%的受訪者在尋找工作過程中得到過城市政府部門提供的幫助,22.2%的受訪者獲得過城市相關部門的就業幫扶;大部分農民工未享受到城市住房相關服務,有36.7%的農民工孩子就讀于城市公辦學校,并且免借讀費;制造業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比例相對較高,獲得城市文化服務的內容不多,程度不深。
2)從農民工主體對城市公共服務的需求來看,對教育條件的公共服務需求比例最高,31.1%的受訪者最想要獲得新知識,參加培訓得到職業資格證,其次有21.1%的受訪者希望國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52.2%的受訪者選擇家庭生活需求,30.6%的農民工選擇個人生活需要的滿足,有17.2%的農民工則選擇個人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3)通過回歸分析檢驗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需求的影響因素,發現與女性農民工相比,男性農民工相對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累計務工收入更高,愿意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選擇更高層次公共服務需求的概率更高。農民工的婚姻狀況、累計就業時長對其公共服務需求的選擇影響不顯著。
4.2 政策建議
1)從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視角,加快形成覆蓋農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供給農民工一定的就業幫扶及定期進行就業培訓,幫助農民工學習以獲得職業資格證書,提高職業技能,加強權益保障;完善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保險政策,有效地改進他們的社會保障制度,提升參保積極性,保障參保農民工社會保險權益;為農民工及時提供人文關懷,促進農民工享有城市文化服務,防止農民工出現心理健康問題。
2)健全有效的農民工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機制。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公共服務需求偏好不同,且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及總收入都會對其產生一定影響,因此要加快落實農民工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表達機制。持續開展農民工政策宣傳,邀請農民工積極參與,表達自己的想法,發揮媒體、網絡的作用,讓大眾加以監督,以期實現農民工在公共服務需求表達上具體制度的透明度,提高供給有效性。
3)完善財稅制度,提高政府為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優化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有針對性地改變支出比重,減少經濟型支出,加強對就業、社保、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支出,提高政府財政支出有效率。要有效地做到完善政府轉移支付的制度,努力做到各級支付共同支出。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管,確保財政支出很好地應用于農民工公共服務的改善。
4)加強法制建設,確保農民工公共服務得到有效保障。政府必須盡快建立有效的法律加以保障,健全政府關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績效管理和評估系統,盡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建立起有關農民工公共服務的長期機制,強化各級政府的社會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