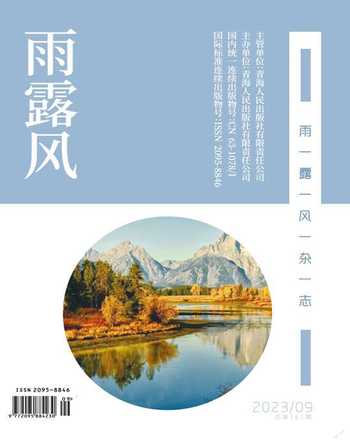張愛玲隱喻性小說藝術與中國文學傳統
邱海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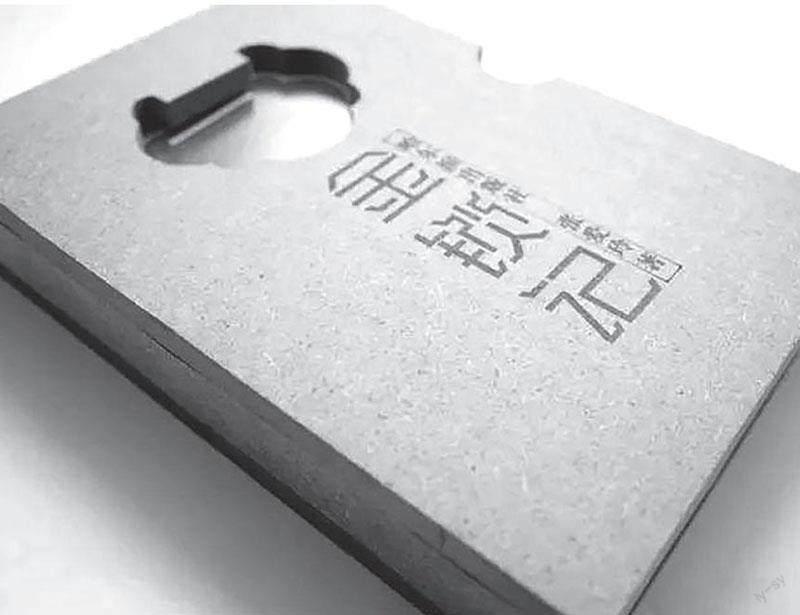
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她的小說受眾群體廣,流傳范圍廣,她創作出許多經典名著。張愛玲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特點就是隱喻,它與中國的文學傳統密不可分。文章從張愛玲的隱喻性小說創作入手,對中國文學的傳統進行了論述。
隱喻小說的主要特色是以詩性為邏輯,它的突出特點是想象力豐富,使它能把虛擬的世界與意圖結合起來,并以隱喻的形式起到提示和指導作用。從總體上講,張愛玲小說的隱喻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特點,這種特點與中國傳統對隱喻的強調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文章試圖從這兩個方面來討論兩者的關系,以期使人們對張愛玲的作品有一個更深刻的了解。
一、隱喻及其界說
在亞里士多德《詩學》中,隱喻被下了這樣的定義:“比喻就是將一個東西的名字轉移到另外一個東西上。或者從一個物種轉移到另一個物種。或者,按照相似的方式,從一個物種,變成一個物種。”束定芳認為,“隱喻”的界定其實是一種對隱喻本質的理解,具有哲學和方法上的含義。亞里士多德把所有的修辭現象都稱作“比喻”。亞氏把隱喻和明喻看作是一種區別于其他事物的修辭現象。在理論上,隱喻可以是詞語、詞組、句子、篇章,在功能上,它具有更大的認知和哲理意義。
耿占春認為,“比喻基于不同的存在或事物的相似,也就是基于人類與世界的相似”。隱喻,不管是詩歌的隱喻,宗教的象征,還是認知的形式,都是人類與世界的相似之處和統一的一種方法。通過隱喻,把本來更為復雜和隱蔽的存在呈現出來,把各種存在和事物連接在一起,這無疑會豐富語言的表現力,從而產生意義的傳遞和升華,從而擴展我們的知覺,提高我們的認知能力。
人的身體的弱點,以及人的各種矛盾,如精神與肉體的矛盾、生死的矛盾、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物質與精神的矛盾,都注定了人類的生存必然會面臨各種挑戰,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人類的多樣性、復雜性和不可復制性。人類的意志在各種矛盾的夾縫中掙扎著,我們需要變得更加強大,才能承受和擺脫人類文明發展帶來的各種痛苦。這一過程是人的生活經驗,而人的困境正是人生的真實存在。這就打開了一個更加寬廣、充滿無限可能性的視野,將無生命比喻為有生命。
二、張愛玲隱喻性小說詩學設想及其依據
(一)張愛玲隱喻性小說詩學設想
張愛玲的作品可以歸結為“隱喻”。它是張愛玲將小說與詩歌結合起來的一種特殊的創作形式,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嶄新的結果。總之,張愛玲從說書小說中吸取了“說和聽”的敘事手法和美學觀念,并吸取了“詩言志”的抒情詩性傳統,把二者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可以說,張愛玲對于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在于其創作的隱喻小說,由此也可以構成隱喻的詩學。而隱喻小說則是一種以詩化邏輯為基礎的小說。詩歌的邏輯學是從維柯《新科學》中產生的。維柯相信,人的智力其實是詩歌。原始人類沒有思想,但是他們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很強。原始人可以用詩一般的智慧來表現自己對大自然的理解,這就是原始人的天賦能力。而詩性邏輯則是詩歌智慧的必要前提。詩歌邏輯以意象為主要特征,把想象與意境所創造的世界當作喻衣,而喻衣與隱喻的含義構成了相似的聯系。“詩學”是指對張愛玲的比喻小說進行剖析。在對張愛玲的小說形式與特點的描寫的基礎上,對其故事特征、審美理想等各方面的理論總結與歸納,可以構成她的長篇小說詩學。
(二)張愛玲隱喻性小說的詩學學理依據
隱喻小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詩”為邏輯。詩性是從詩學角度來研究的,詩學是從張愛玲隱喻小說的特點和形式入手,從作家、敘述者、故事特征、美學理想等多個角度對其進行綜合的考察。張愛玲的隱喻性小說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探討。
1.小說是隱喻存在的形態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隱喻可以分為兩類:宏、微兩類。宏隱喻是小說隱喻的教育理論基礎,而微觀隱喻則僅限于修辭層面。就宏隱喻來說,它不僅關注其語法,而且越來越關注其所處的環境和意義。在宏隱喻的研究中,不僅限于特定的語言單元,而且還涉及大量的詞匯。從一個字到一部巨著,都可以透過比喻而存在。在整個小說中,隱喻的存在是必然的。
2.整體性意象和隱喻的關系
形象的存在形態是一種整體性的,它與作品中的藝術形象、構成要素、材料的時代相區分。就意象來說,是指文學作品中所有的藝術意象和語言。可以說,“藝術形象”“文學形象”的概念,都可以用“意象”來概括。而語象則是指語言的意象,它與離開了語言而存在于意識中的意象不同。意象的觀念可以是直觀的、過去的體驗的再現或記憶,也就是所謂的“知覺殘余”,作為一種心理活動,它可以與情感相融合,而這正是它最主要的作用。整體的形象是指“憂郁”,也就是能夠與總體含義形成類似關系的“憂郁”。本文從自身的一致性和可理解的角度來看,張愛玲的每部作品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它為作家的精神活動提供了支撐。張愛玲的作品中,意蘊與形象可以產生相似的聯系,因而產生了隱喻小說。
3.中國文學的詩性傳統
就中國文學來說,其詩性傳統表現為“詩言志”與“詩緣情”。這是中國詩學傳統的至高理想,也是我們古代文人的根本信念。可以說,“詩言志”與“詩緣情”都是我國所有的文學活動的正當性。同時,中國文學史上的詩性傳統也在美學中心論的修辭隱喻中得到了反映。“詩言志”“詩緣情”都是主觀意義上的,古人把文學看作是一門語言的藝術,可以用“言”來回答“意”。而這種意蘊又不斷地激發和滋養著歷代的文人創作“意”。同時,隱喻性的思考與言語也成為我國歷代文人表現自己的一個領域,而非僅限于詩詞。而“詩言志”“詩緣情”等中國詩學傳統也同樣影響著張愛玲。張愛玲可以說是將這二者創造性地融合到小說之中,從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隱喻小說,并以其特有的方法來延續中國文學的詩性傳統。由此可以看出,張愛玲的隱喻小說具有一定的詩學理論基礎。
三、張愛玲小說在敘事過程中的隱喻性
(一)我國古代小說的隱喻性傳統和白話小說特質
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發展經歷了神話傳說、散文、俗語、傳奇的演變,到了明清,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白話小說。而在其創作動機與創作目標上,文言與白話是一個獨立的體系,它們是并行發展的,在情節、表現形式上彼此滲透、融合,并最終形成了各自的風格。“說書”的敘述特征是我國傳統白話小說的基本特征。白話小說是要講故事的,而說書人的心態往往會發生很大的變動,所以要做到即興、半即興、隨機應變。因此,古代小說家們也把自己想象成一個說書人,把自己當成一個觀眾,而寫作的過程,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告訴給讀者。當代作家也對這種傳統進行了繼承和改造。如陳平原的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小說在敘述時間上采用了連續敘述,以故事為核心的敘事結構。20世紀初期,西方小說對這一敘述方式提出了嚴重的質疑。但我們的當代作家卻把西方的敘述方法積極地融入到傳統小說之中,使敘述方式發生了變化。從當代小說的角度來看,現代小說采用了許多敘述方法,如連貫、倒裝、交叉,以情節和背景為核心。而張愛玲則是完全繼承了中國傳統小說中的說書體,并且在融合說書體的傳統上進行了革新。
(二)多采用第三人稱
小說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閱讀,它通過說和聽來提出問題,并回答問題。就張愛玲的隱喻小說來說,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第三人稱的形式來講述,或者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出現,再由第三人稱人物來完成,在《第二爐香》《第一爐香》《茉莉香片》等作品中均有體現。很明顯,這些作品的開篇都采用了“說書”式的敘述方式。而且,這個方法可以讓讀者隨意地描述時間和人物。同時這種方法還可以與讀者或明或暗地溝通,以“看官聽說”的形式插入到文章中。在這種情況下,敘述者可以自由地談論、敘述,與小說中的角色、背景相結合,與讀者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在適當的時候,他也會主動跳出,與讀者進行直接的溝通,并且與小說中的角色、世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張愛玲的隱喻小說正是繼承了這種文學傳統。從與讀者的關系來看,這樣做是為了方便讀者對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的理解。張愛玲的隱喻小說中,作者與小說中的敘述者融為一體,敘述者繼承了張愛玲對這個世界和故事的理解,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生活對話的傳播者。而生活主題則是客觀地定義了作者的興趣,因而,在這個層次上,敘事者已將作者的訊息揭示出來。或者說,它是指從近代開始的書體小說審美趣味的變化,張愛玲在隱喻小說中創造性地融合了這種變化。
四、張愛玲隱喻性小說的特點
以上對張愛玲小說中的隱喻敘述與詩化特點進行了分析。通過對張愛玲小說中的豐富形象和比喻作用的分析,我們可以把握張愛玲的隱喻小說的特征。
(一)意象和故事的關系
張愛玲的隱喻小說最顯著的特征是其形象與整個故事具有相似性,甚至可以用形象來命名。從小說的觀點來看,這個特征與小說的含義和形象有關。因為意象具有形態和色彩的特性,所以它可以長期存在于讀者的腦海中。所以,當讀者的閱歷增加,它們就會在讀者的心中發酵,產生更多新的魅力。這種魅力,往往帶有玄學和哲學的特征,可以說是一種超脫于特定環境的特質,是一種可以持續理解的特質。從這一點來說,如果小說中的形象能在讀者的心目中久久不散,那就是經典之作。而這類小說,歷來被認為可以永久地存在于文學作品的話語結構之中并在美學的具體表現中,成為其美學本質的依據。在張愛玲看來,她的比喻作品中,形象與故事的總體結構具有相似之處。讀者只有真正理解張愛玲小說中的“形上質”,才可以到達最高層次,從而使張愛玲的隱喻小說具有藝術的全部價值。
(二)意象可輔佐整體性故事寓意的生成
張愛玲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形象。同時,在小說的敘事與描述中,也會出現一些分散的形象。它們在比喻的方法和層次上都不盡相同。比如《金鎖記》一書,就以“月”“金鎖”為隱喻。在創作中,作者運用了全詩的意境。《紅樓夢》中的月亮每次出現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義。月球能創造出三十年前的景象,給人一種很古老的感覺,而月球也能用來比喻人物的內在與個性。金鎖意象則是通過整個故事情節來進行體現的。所以,“金鎖”的形象更容易被人理解。此外,張愛玲的作品中也有很多的“太陽”形象,而運用“陌生化”的手法可以使“太陽”具有不同的情感色彩。
五、結語
總之,目前國內大部分的當代小說家的寫作都發生了敘述方式的變化,張愛玲則是為數不多的堅持以書寫體為主的作家。張愛玲的作品中形象豐富,并以形象的形式構成隱喻,把中國文學的詩歌傳統與說書體小說相結合,從而產生了“比喻”小說。可以說,張愛玲在作品中十分重視與讀者的對話與交流,把個人生活感悟具象化,開辟了一條隱喻的藝術之路。而以“形象”為主體的“小說”則具有“可讀性”和“讀者群體”的特點。同時,讀者在讀完小說之后,也會產生更深的哲學思考,具有很高的現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