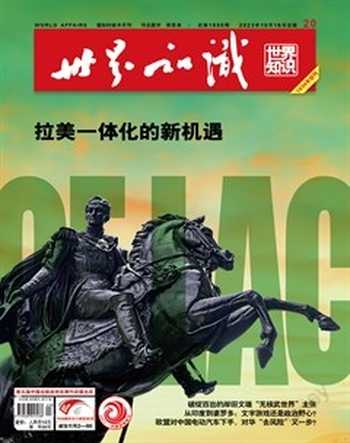文物盜竊丑聞后,大英博物館何去何從
郭莎莎

位于英國首都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正門。
大英博物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之一,但它的歷史卻并不光彩。據統計,大英博物館收藏了來自全球至少212個國家和地區的800多萬件藏品,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英國在殖民時期通過戰爭、掠奪、甚至欺詐的方式獲得的。長期以來,大英博物館能夠心安理得擁有這些文物的一個主要說辭是,“外國文物在這里得到了更好的保護”。
然而,近30年來,大英博物館發生過至少六起盜竊案件。近日,該博物館被曝約2000件館藏文物莫名其妙失蹤,其中還牽扯出博物館內部人員長期“順手牽羊”在eBay(美國在線購物與拍賣網站)上出售藏品的黑幕。該事件不僅震動英國,還牽動了所有不得不在大英博物館“保存”文物的國家的高度關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稱之為“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盜竊事件”。2023年8月16日,大英博物館發布公告稱此次丟失的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紀至公元19世紀的黃金首飾、寶石和玻璃制品。隨后,博物館館長哈特維希·菲舍爾引咎辭職。這些信息在令人震驚之余,也暴露出該博物館在文物保護、安全管理、內部監督等方面的嚴重漏洞,同時也戳破了其以安全為由拒絕歸還文物的虛偽立場,繼而引起國際各界群情激憤,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文物的呼聲空前高漲。
絕不是一個無辜的收藏者
大英博物館創建于1753年,當時的展品主要由私人收藏家捐贈的殖民地物品構成。18~19世紀,隨著英國在七年戰爭和拿破侖戰爭中獲得勝利,其在全球也建立了愈加龐大的殖民帝國,大英博物館的藏品也隨之迅速增加。英國利用軍事力量、外交手段或非法貿易,從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掠奪走大量藝術品和文物,并交給大英博物館保管。這些文物往往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和宗教價值,是被掠奪國家的國寶和精神象征。例如,希臘雅典衛城帕特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像是古希臘文明的代表作,1801~1812年間,英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托馬斯·布魯斯(即埃爾金勛爵)用盡心機獲得奧斯曼當局許可,將雕像拆下運回英國,并于1816年以3.5萬英鎊的天價出售給大英博物館,而在當時英國普通人的年收入不過幾英鎊而已。
“貝寧青銅器”是指西非貝寧王國(今尼日利亞南部地區)在15~19世紀期間制作的面具、雕像、牌匾等。1897年,英國為打開尼日利亞市場,發動了對貝寧王國的侵略戰爭,并在洗劫王宮后將青銅器運回國。此后,這些青銅器散落于各個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約有900件被送到大英博物館。這些青銅器被認為是非洲藝術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尼日利亞人民的珍貴文化遺產。
中國近代也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據估計,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中國有1000萬件文物被盜。其中,大英博物館是收藏中國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館,目前其收藏中國書畫、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銅器、雕刻品等珍稀國寶2.3萬件。由此可見,大英博物館在英國殖民史上絕不是一個無辜的收藏者。
展示帝國歷史“榮光”
作為大英帝國的“功勛”檔案館,大英博物館首先是展示帝國“輝煌成就”的場所。早在16世紀,歐洲便有一些殖民者喜歡在自己的住所設立“奇妙房間”,用來展示個人從海外帶回的寶物。這些“奇妙房間”本質上和后來的博物館一樣是殖民時代的產物,殖民者將占有文物視為征服其他國家的證據。大英博物館的創立便是歐洲殖民者收藏“戰利品”傳統不斷發展的產物,主要目的是展示帝國成就,希望帝國像這些文化瑰寶一樣與世長存。
同時,大英博物館也是建構大英帝國敘事的“宣講機”,不僅反映了其在當時的觀念和殖民策略,也影響著公眾的看法。例如,19世紀末,在英國和其他歐洲殖民者對貝寧王國進行圍攻時,當時的英國媒體在報道中提到貝寧正進行大規模活人祭祀活動,因為士兵們發現當地民居庭院中有幾處裝滿尸體的深坑。但尼日利亞方面稱,英國士兵在進入貝寧王國前就對其進行過數日遠程攻擊,死者被村民們匆忙掩埋在庭院中。在貝寧王國被夷為平地后的幾個月,大英博物館還專門舉辦了其獲得的用于宗教活動的貝寧青銅器展會。
由此可見,英國建造大英博物館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向并不熱衷殖民冒險的公眾宣揚帝國功績,讓他們看到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與金錢消耗的殖民活動可以帶來的切實好處;二是向英國人灌輸一種優越感和使命感,認為自己有責任通過推進對殖民地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去文明開化那些“野蠻”國家;三是讓公眾了解大英帝國的屐痕已遠至世界各個角落,強化人們的帝國情懷。同時,博物館的收藏和展示活動還是一種政治行為,使殖民活動披上了一層合理化甚至道德化的外衣。
文物歸還的法律與道義較量
在后殖民時代,大英博物館面臨藏品來源國歸還文物的強烈要求。例如,尼日利亞政府和民間團體多次向大英博物館要求歸還貝寧青銅器,但均遭拒,大英博物館曾表示愿將部分青銅器“借”給尼日利亞展出,但尼日利亞需承認前者對這些藏品的所有權。希臘政府和民眾一直主張大英博物館應歸還帕特農神廟雕塑,大英博物館則堅持認為,這些雕塑通過合法收購獲得,在其展廳中能得到更好的保護;埃塞俄比亞一直希望大英博物館歸還英國在1868年的軍事行動中奪取的該國北部的馬克達拉寶藏,盡管大英博物館網站承認馬克達拉文物到達英國的道路浸透著鮮血,但仍推諉說,“與埃塞俄比亞合作伙伴有關馬克達拉藏品的討論仍在繼續,博物館正在積極投資這些藏品。”
中國是近代史上英國殖民主義的最大受害國之一,大英博物館目前收藏的中國文物幾乎涵蓋所有藝術類別并跨越整個中國歷史。近年來,中國政府和民間機構一直致力于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大英博物館則聲稱,根據英國政府在1963年制定的《大英博物館法》,它作為公共機構無權“出售”藏品,因此拒絕歸還。
大英博物館聲稱拒絕歸還文物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它們,但隨著一起起文物盜竊案的發生,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腳。從最近這起盜竊案來看,被盜藏品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和學術價值,而根據既往先例,一些不法分子為迅速脫手文物“賺快錢”,很可能會將盜竊的黃金制品和寶石等文物熔化或切割再進行轉賣,而這將對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這也令人們對其他爭議藏品的安全性感到擔憂。正如英國下議院議員貝爾·里貝羅·阿迪所言,博物館以安全為由拒絕歸還別國文物的做法是“侮辱性的荒謬”,而援引《大英博物館法》拒絕歸還別國文物,則是“以自己制定的法律為借口,拒絕遵守國際道義、履行國際責任,非常虛偽可笑”。

大英博物館館藏的希臘帕特農神廟雕塑。
遺憾的是,目前國際上尚無針對殖民時期被掠奪文物追索問題的法律。國際上關于文物追索的法律文書主要有三種:一是1954年出臺的《關于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的海牙公約》;二是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口、出口和轉讓文化財產所有權公約》,旨在打擊文化物品的非法交易;三是1995年在意大利羅馬簽訂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它規定了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歸還或索賠準則。然而,這些國際公約都不具有溯及力,只能對文書頒布后發生的文物爭議提供行為依據,而對于發生在殖民時期的文物歸還問題卻無能為力。
但是,法律之外還有道義。從道義角度看,大英博物館是英國殖民擴張歷史的縮影,即便英國抹去了侵略者在文物上留下的指紋,也無法否定文物的真正所有權。歸還文物是一種道德責任,源于一種彌補歷史不公正的義務感,而出于道義和責任感選擇歸還文物的做法在西方國家并非沒有先例。例如,2017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訪問非洲時宣布,他在未來的五年任期內,會把歸還非洲文物作為“頭等大事”;2020年,法國正式通過國會投票,決定將尼日利亞的流失文物悉數歸還。2021年,荷蘭政府制定了新的指導方針以確認向前殖民地歸還殖民時代文物;2023年7月,荷蘭政府宣布將向印度尼西亞和斯里蘭卡歸還478件文物。
在倡導文明對話與文明多樣性的今天,大英博物館固守拒不歸還文物的態度與時代格格不入,本質上是殖民心態在后殖民時代不合時宜的延續。大規模歸還被劫掠文物需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這種“不舒適的剝離”不僅可為曾被掠奪的國家提供彌合創傷的可能性,也為帝國主義曾經的殖民罪責提供救贖途徑。在后殖民時代,大英博物館或需重新審視自己在全球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播中的角色和責任,并更多考慮道義上的合理性與正義性,積極回應文物來源國的正當聲索,為世界文明交流作出真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