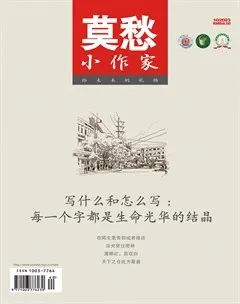一粒種子的傳承
1
周末下鄉看望媽媽,臨走前免不了帶點新鮮蔬菜回去。大姐和二姐不約而同地從菜地里割了一大堆韭菜放在院子里,大家圍坐到一起,七手八腳,一邊擇菜一邊閑聊。
韭菜好吃難擇,須一根根從手上過,摘除纏連在根莖上的枯爛老葉,掐掉葉梢的枯黃部分,搓去根莖部的泥皮。炒一盤韭菜要擇上數百根韭菜,實在考驗人的耐心細心。
有一次,姐姐們割了一堆韭菜讓我帶回家,愛人說他人老眼花,看不清小小葉子。我只好一個人坐在桌前,擇到半夜方才完工,不僅腰酸背痛眼花,指甲縫里的泥污、韭汁洗都洗不凈,真是自己挖坑自己填。媽媽知道后,叮囑姐姐們,再給我送韭菜一定要擇好。老家人多力量大,聊著天兒,這活兒就悄悄干完了。
大姐說,韭菜吃個頭和尾,春韭和秋韭最好吃。清明節后,她將韭菜老根或種子一簇簇、一行行種到菜地邊角上。彼時陽氣上升,小韭菜見風長,一陣春雨落下,長得更歡。韭菜葉子長到一指長,根部和葉邊還帶著娘胎紫,割一把回家,韭菜炒雞蛋、韭菜炒肉絲,哪怕就是韭菜炒韭菜,下鍋用鏟子一扒拉,鮮嫩流汁,清香撲鼻。夏天的韭菜瘋長,太陽烤得韭菜葉子老巴根筋的,吃起來不僅口感差,還容易塞牙縫。大姐在立秋時節便將夏天的老韭菜全部割了,重新施肥澆水拔草,秋天的第一茬韭菜重新蓄足水分,回歸鮮香水靈的本性,長得又高大又鮮嫩。
二姐也割了一堆韭菜,她沒舍得將上一茬韭菜割了,結果夏韭枯黃的老葉層層纏繞新葉根部,分享秋韭的養分,秋韭長得又瘦小又老氣。
我猜測,這大概是兩個不同的品種。大姐卻說,都是一個種,是她結婚的那一年媽媽送過去的。每年,她留下又高大又壯碩的韭菜株,開花收種留根,第二年又栽下去,年復一年,提純復壯,原汁原味。所以,這是保存了四五十年的純正本韭菜種子。
好種出好苗,人勤地不懶。怪不得老家的韭菜一直這么香,而在城里菜市場買的韭菜,始終吃不到那純正勁道的香味。
我偶爾去吃韓式烤肉,看到烤盤上寫有“身土不二”四個字,意即“生我養我的土地上生產的東西才是最適合我的”。韓國人將此語廣而告之,上升為只消費國貨的民族情感。用咱中國人的話,即“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生我養我的土地上出產的食物最適合我的腸胃,異域的山珍海味雖稀罕昂貴,卻于我水土不服。所以,古代游子出遠門時常帶一包家鄉的泥土和種子,以慰鄉愁,護佑平安。
土地和種子攜帶強大的基因密碼,決定著菜蔬的基本特征,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一方人的口味、性情。
2
韭菜種子的故事,將我的記憶拉回到小時候。
老家堂屋靠墻居中放著一張又寬又長的木頭老柜,兩頭堆放稻谷,中間一格上面是抽屜,放爸爸的工具和賬本;下面是對合門柜子,盛放著媽媽的寶貝——各類種子:烏溜溜的韭菜種,黃里透青的蘿卜種,小小的菜籽種,像癟谷一樣的藥芹種,還有茼蒿種、莧菜種、菠菜種……裝在花花綠綠、大大小小的瓷瓶里。
爸媽一共養育了六個女兒,家里人口多,媽媽精心侍弄菜地,盡可能地滿足一家人的日常食用。
媽媽在鴨棚下種過一種瓢瓠,許是鴨糞讓地力肥沃,結出的瓠瓜有斗盆大,像一個個可愛的胖娃娃伏在鴨棚頂上。摘一只嫩瓠,足夠一大家子飽餐一頓。瓠子老了,風干,一鋸兩半,掏去瓤,便是實用的水瓢。
南瓜易生長,粗藤大葉大花。媽媽每年在墻角、草垛、菜地種上幾顆南瓜種,秋天就能收獲一大堆大南瓜。黃澄澄的南瓜排成一長排,放在墻角,小院頓時充滿豐收的氣息。成熟的南瓜初始吃口感粉粉的,放置時間越長便越甜,南瓜所含的淀粉轉化為糖分了。南瓜是粗糧,當飽。農閑或下雨時,媽媽便剖開一只大南瓜,淘點糯米,一起放在大鍋里煮熟。又香又糯又甜的南瓜飯勾引著胃里的小饞蟲,我們一碗接著一碗,吃得心滿意足。而那南瓜種,隨瓜瓤一起被甩在泥墻上曬干,選出最飽滿最壯碩的種粒,又被收進媽媽的寶瓶中。
媽媽曾在我住的商品房后面的空地上點了幾顆扁豆種,待長開后又用竹竿將藤苗引到樹上。秋風吹開扁豆花,轉眼,一串串飽滿的扁豆掛上枝頭,來不及吃完,第二撥、第三撥扁豆又長開啦,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與鄰居、朋友們分享自己種的果蔬。
在物質貧乏的年代,媽媽種出的那些品種繁多的菜蔬,溫暖了童年的記憶,哺育著我們長大。
媽媽漸漸老了,種不了農田,她更加喜歡打理屋后的菜園,在適宜的季節里種菜點豆,在成熟的季節里又將種子收起。
土地和種子是有治愈力的。躬耕在菜園,媽媽忘記年老病痛,忘記生活的煩惱。在菜園里,媽媽充滿了喜悅,看果蔬生長的喜悅,收獲果蔬的喜悅,被兒女需要的喜悅。
3
人生是一粒種,落地就生根。兒女也是父母育出的種苗。憨厚勤勞善良的大姐最得媽媽的真傳。
大姐出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沒上過學,長大后進掃盲班識了些字,嫁給本莊一位憨實的瓦匠,生了一個兒子,一家子其樂融融。大姐勤儉持家,踏踏實實在家種田,大姐夫在外面工地上掙點活錢。眼看兒子長大,要買房結婚娶媳婦,家里那點積蓄哪夠?大姐聞說養豬掙錢,便買了村外場頭幾間廢棄倉庫,改造成豬舍,購買了上百頭苗豬,像侍候小祖宗一樣呵護著小豬,喂飼料、添水、挑豬糞、打掃豬舍、防病防疫……吃盡了辛苦。但這豬養到七八十斤時,怎么也催不肥、長不大了,不知是豬種的原因還是養豬技術不精,大姐的養豬事業以失敗告終。后來,大姐在聰明能干的四姐帶動下,回歸老本行——種田,規模種田,辦家庭農場!她在花甲之年打了翻身仗,手邊有了余錢,心情更加敞亮。
大姐視種田為主業,是安身立命的飯碗;種菜是副業,是可以自由發揮的自留地。村頭大路緊鄰大溝渠,一長溜的坎坡地鄰水向陽。大姐開發了一畦又一畦的菜地,種植各種時令蔬菜,不僅有老品種,還搜羅新品種,注意搭配品種和色彩,菜園更加豐盛、更加養眼。
老兩口能吃多少菜,她源源不斷地送菜給城里的兒子一家,還像年輕時的媽媽那樣,不時給妹妹們送點自產自種的果蔬禽蛋,春節前送點自家蒸的年糕、粉團,八月半送只老鵝……她常說,這一世做姊妹是緣分,應該互相幫襯著。
長姐如母,我們姊妹幾個也學著大姐的樣,勤儉持家,不多言,不做非分之想。雖然我們像韭菜一樣普通平凡,卻扎根腳下的土地,頑強生長,綻放芳華,傳播芬芳。
好的家風是一粒種子,會生根發芽,代代傳承。外甥女說,看著姨媽們的相處方式和生活態度,她們小姊妹一輩也深受感染,立志要吃苦耐勞、敬老愛幼、相互關心。聽說外婆愛上吃獼猴桃,她馬上表態,到網上買獼猴桃種苗的任務交給她了,爭取明年讓外婆吃上自家菜園里長的獼猴桃。
農家小院里一片歡聲笑語,有家人在,快樂就是這么簡單。
韓粉琴:江蘇省高郵市婦聯副主席,作品散見于多家報刊。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