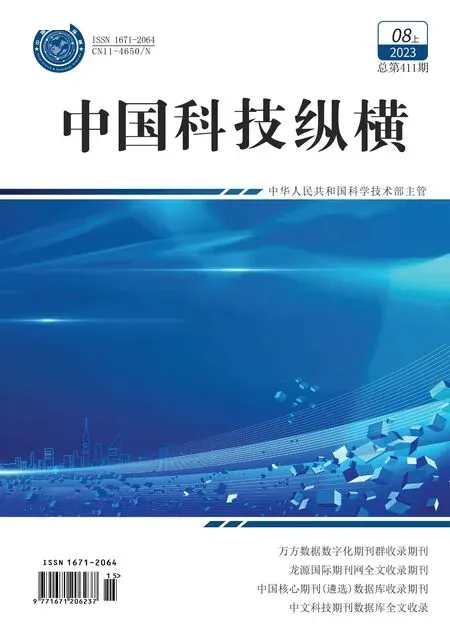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導彈控制系統
汪 敏 陳泓言 王 浩 張慶舟 李敬偉
(北京動力機械研究所,北京 100074)
0 引言
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軍事體系已經由機械化變革為信息化。未來戰爭是海、陸、空全方位的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作戰環境與作戰任務復雜多變,利用先進的軍事武器裝備實時、高效地處理戰場態勢,自適應地調整作戰策略,已經成為解放軍勝利的法寶。以導彈武器為代表的軍事武器裝備逐步轉向精準化和智能化,從而推動未來戰爭形式向著新形態演變[1]。
顯然,作為導彈武器裝備子系統的傳統導彈控制系統已經不能滿足未來智能化戰爭的需求。隨著人工智能領域的迅猛發展,人工智能技術[2]必將是未來提升軍事武器裝備的核心技術之一,它必將推動軍事武器裝備逐步向精準化、智能化、自主化和協同化的方向發展。
智能導彈武器的發展目前正處于實現導彈子系統智能化的起步階段。導彈控制系統作為導彈武器最重要的子系統之一,它的工作性能直接影響整個導彈的技術狀態和飛行姿態,甚至直接決定著導彈發射的成敗。導彈控制系統具有復雜性、時變性、非線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3],因此,難以建立精確的數學模型[4]。雖然傳統控制方法設計的導彈控制系統能夠滿足控制要求,但是傳統控制方法存在諸多局限性。例如,由于導彈控制系統模型參數的復雜性導致難以尋得最優參數;導彈控制系統缺乏自學習和自適應能力。
由此可見,構建智能化的導彈控制系統迫在眉睫。智能導彈控制系統是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到導彈控制系統中,使導彈控制系統具有學習、推理和決策的能力,甚至可以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自適應學習,從而滿足控制要求。
1 導彈控制系統智能化關鍵技術
智能導彈控制系統需要自動適應多變的飛行環境,根據接收到的探測信息和自身飛行參數,自動做出智能化決策[5]。因此,為更全面地實現導彈控制系統智能化,需要具備以下相關控制技術。
1.1 故障診斷與容錯技術
當導彈武器出現運行故障時,導彈控制系統首先通過接收的故障信息進行評估診斷,然后切換適當的容錯控制律維持導彈正常工作。這一過程屬于人工智能分支之一的導彈故障大數據學習,它利用先驗知識或深度神經網絡,學習大量故障信息與容錯控制技術,然后進行飛行能力評估,并采取相關容錯控制進行故障修復,實現導彈自主決策作戰,提高導彈的自適應能力。
1.2 自適應控制技術
導彈控制系統自適應技術需要對導彈飛行的全過程進行自適應控制。信息化戰況錯綜復雜,導彈的控制參數與飛行狀態會根據作戰環境和作戰任務發生變化,控制系統自主化調整到適應性的控制策略。通過對大量飛行數據進行精細化建模與學習,智能導彈控制系統可以提升控制算法性能,確保在不同飛行參數和飛行狀態下導彈能夠正常工作。
1.3 協同飛行控制技術
現代戰場具有立體化、全方位的特點,單位作戰導彈難以準確判斷戰場的形勢。為了提高導彈作戰能力,以蜂群的行為模式為例,多彈協同飛行控制模式往往能夠提高導彈的綜合攻擊能力和防御能力。多彈協同飛行控制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以最優控制法、自適應控制法、預測控制法、模糊控制算法為代表的現代控制理論方法和圖論法。應用協同控制技術的智能導彈控制系統可以根據不同的作戰任務和突發狀況,找到最優協同控制策略,進一步提升控制系統的綜合作戰能力。其中,導彈控制系統參數辨識與建模過程中,通常使用協同飛行控制技術中的預測控制法以降低預測模型與真實模型之間的差異。
1.4 多源信息融合技術
在未來戰場上,情報信息往往不是單一的,實時、準確、完整地處理多種情報信息,并及時挖掘它們之間的關系,是進行正確指揮決策的關鍵。多源信息融合技術的智能化表現為利用神經網絡或者智能專家系統等人工智能技術在導彈控制系統中進行多源信息融合、推理的過程。
1.5 智能自主決策技術
信息化戰場具有環境多變、抗干擾能力強、空間全方位等特點,傳統任務驅動型決策技術難以滿足復雜且多變的戰場態勢。因此,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決策技術,通過收集、整理、分析、融合情報數據,構建動態變化的三維廣域戰場態勢圖,根據邏輯推理及多目標優化技術對敵方威脅等級進行動態評估,實現實時決策規劃[1]。
1.6 導彈智能化控制基礎技術
導彈智能化控制基礎技術包括模糊邏輯理論和應用技術、深度神經網絡算法、遺傳算法控制技術、智能信息處理技術、傾斜轉彎控制技術、側滑轉彎控制技術等。導彈控制系統參數尋優過程通常使用深度神經網絡算法、模糊控制算法、遺傳算法等改進PID 控制器以解決控制精度不準確的問題。例如基于深度神經網絡的PID 控制器、基于模糊控制算法的PID 控制器、基于遺傳算法的控制器等。傾斜轉彎控制技術與側滑轉彎控制技術是導彈控制系統設計領域兩項重點的研究技術。
2 人工智能在導彈控制系統的應用
人工智能在導彈控制系統的主要應用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2.1 導彈控制系統參數尋優
面對被控對象的非線性特性以及環境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干擾性,控制器參數難以確定,通常導致控制器的數學模型不精準。因此,傳統比例-積分-微分(PID)控制器、線性二次型最優控制(LQR)控制器、比例-積分(PI)控制器無法保證導彈武器的控制性能。為了彌補傳統PID 控制器的不足,現有相關方法對控制器進行改進,例如基于深度神經網絡的PID 控制器、基于模糊控制算法的PID 控制器、基于遺傳算法的控制器等。
2.2 導彈控制系統故障診斷與容錯控制
故障診斷與容錯控制技術主要包括故障檢測、故障診斷和容錯控制。它的基本思想是通過冗余資源和容錯控制率保證當前運行狀態或通過損失部分性能達成既定目標。故障診斷顧名思義就是估計故障信息,然后應用容錯控制技術保持導彈當前的運行狀態。現有故障診斷方法主要包括3 種方法:基于信息的狀態估計方法、基于專家系統的方法、基于深度神經網絡的故障診斷方法。前兩種方法不但需要大量先驗知識,而且存在故障推理過程中的組合爆炸問題。深度神經網絡具有(自)學習和記憶的能力,為故障診斷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相比于反向傳播算法(BP 算法),快速誤差反向傳播算法(FBP 算法)解決了收斂速度慢和局部最小值的問題,能夠快速收斂,預測精準。同樣,徑向基函數網絡(RBF 網絡)具有簡單的結構和快速收斂的特點,對故障信息具有敏感的捕捉能力,是一種應用范圍廣的故障診斷方法。
2.3 導彈控制系統參數辨識與建模
參數辨識是將理論模型與試驗數據相結合的參數預測算法。參數預測算法也是協同飛行控制技術的一個分支。以質量矩導彈建模為例,為了使導彈控制系統具有穩定性、魯棒性和快速性,一般采用快狀態姿態角速度作為逆向控制器的輸入。然而,由于參數存在的不確定性和建模的誤差,賀有智等[6]構建多層神經網絡自適應控制器以減小系統的跟蹤誤差。此外,該方法基于李亞普諾夫(Lyapunov)穩定性理論,在參數確定無建模誤差和參數不確定有建模誤差的情況下,均證明系統的跟蹤誤差是收斂的。
2.4 導彈控制系統設計
導彈控制系統設計通常基于自適應控制技術、智能自主決策技術、傾斜轉彎(Bank-To-Turn, 簡稱BTT)控制技術與側滑轉彎(Skid-To-Turn, 簡稱STT)控制技術等。由于未來信息化、智能化戰爭對導彈武器的打擊精度和機動性具有更高的要求。傳統的STT 控制技術已經不能滿足戰爭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BTT 導彈控制技術可以提高導彈的機動性、穩定性和升阻比特性,因而研究的更加廣泛,并且迅速得到發展[7]。
BTT 導彈控制技術的控制方式要求導彈在限制偏航運動的情況下,需要快速轉到正確的機動方向。因此,BTT導彈控制系統是一個具有運動學耦合和慣性耦合的時變非線性多變量控制系統。時變非線性多變量控制系統一般采用反饋線性化方法以完成非線性被控對象的線性化以及通道的解耦控制。但是,這一方法通常對模型的誤差是敏感的。因此,在線補償飛行控制系統的動態逆誤差是一個熱點研究方向[8]。
3 智能導彈控制系統發展趨勢
為了提升導彈的自主控制能力與糾錯能力,智能導彈控制系統應時而生,它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導彈控制系統中,使導彈控制系統具有自主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目前,國內外還沒有研制出完全智能化的導彈控制系統,在未來相關技術的支持下,導彈控制系統部件智能化是前提,單位導彈控制系統智能化是基礎,多彈協同控制系統智能化是過程,任務自主的智能控制系統是結果。
3.1 導彈控制系統部件智能化和單彈控制智能化
目前的技術已經實現部件和單彈控制智能化。例如,挪威遠程打擊導彈(NSM),該導彈在運動時可以通過智能控制算法實現初步自主控制,從而提高目標打擊的精準度。當應用場景變為多彈同時打擊同一目標時,在多源信息融合技術與自適應控制技術的輔助下,協同NSM 導彈自動為每顆導彈設定不同的攻擊部位,但它并不具備完全協同控制的能力。
3.2 多彈協同控制系統智能化
多彈協同控制系統智能化以協同飛行控制技術與智能自主決策技術為基礎,實現多彈同時攻擊的高度配合。這種戰斗方式可以主動避障、自主控制協同彈間的飛行狀態,進一步提升協同對抗的能力。目前,理論上證實了多彈協同控制系統智能化是可行性的。任務自主的控制系統智能化最終目的是消除導彈控制系統中的人工操作,最終形成自主控制、精準打擊目標的智能化武器,使未來戰爭從“有人化”趨近于“無人化”。
4 結語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其在軍事戰爭中的突出表現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未來戰爭形勢朝向智能化發展,各國為了占領主動權,都在加緊研究智能導彈裝備。導彈控制系統作為導彈的“心臟”,其智能化水平決定導彈發射的成敗。
傳統導彈控制系統作為武器裝備的一部分,已經不能滿足未來戰場的需求。導彈控制系統的發展趨勢必將是智能化、自主化和協同化。智能導彈控制系統由最初的控制系統子系統智能化,逐步發展到單位導彈控制系統智能化、多彈協同控制系統智能化,最終實現任務自主的控制系統智能化。因此,將人工智能技術引入導彈控制系統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與實用價值,這必將推動導彈控制系統從信息化走向智能化,自主地完成從搜索目標到準確打擊的全過程,最終掌握未來戰場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