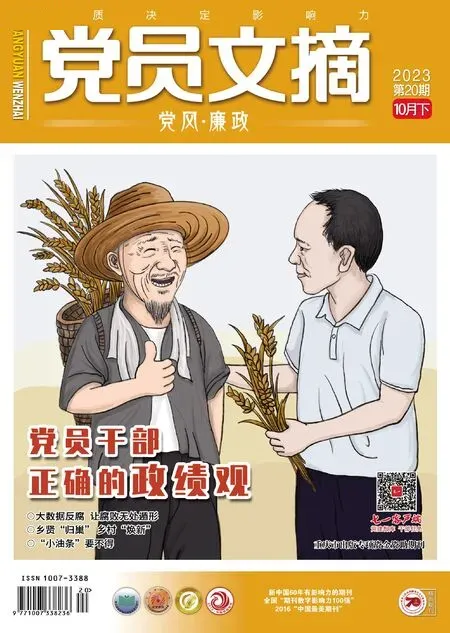反腐之下,如何開一次正常的醫(yī)療學術會議?
文/海陽

原本熱鬧的醫(yī)療學術會議,遇冷了。
這與近期的緊張氣氛密切相關。2023 年5月,國家衛(wèi)健委聯(lián)合13 個部門印發(fā)《2023 年糾正醫(yī)藥購銷領域和醫(y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要求重點整治醫(yī)藥領域突出腐敗問題。其中明確提出,重點監(jiān)管各級各類行業(yè)組織或學(協(xié))會以“捐贈”、學術會議等名義變相輸送非法利益的行為。
不能對學術會議“一刀切”禁絕,這是醫(yī)學界及國家衛(wèi)健委等部門的共識。8 月15 日,國家衛(wèi)健委在媒體問答中表態(tài),要大力支持、積極鼓勵規(guī)范開展的學術會議和正常醫(yī)學活動。
延期會議正自查有無流程違規(guī)
在LED 大屏環(huán)繞的舞臺上,演講者在聚光燈下宣讀著最新的醫(yī)學研究成果。酒店會議廳座無虛席,聽眾則是年輕醫(yī)生、藥企人員……這幅景象如何與醫(yī)療腐敗聯(lián)系在一起,是年逾七旬的心內科醫(yī)生黃榮梅所不能理解的。
真實學術會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黃榮梅從醫(yī)生涯始于20 世紀80 年代,在資源匱乏的環(huán)境中,是藥企舉辦的學術會議讓她跟上了外國研究者的步伐。黃榮梅表示,即使是在信息便捷的現(xiàn)在,三四線城市的醫(yī)生依然與大城市的醫(yī)生存在知識差距。如今她參加的許多學術會議是向同一醫(yī)聯(lián)體內的二級醫(yī)院醫(yī)生傳授規(guī)范的醫(yī)學知識,提高基層診療能力。
國家衛(wèi)健委在8 月15 日的媒體問答中稱,需要整治的是那些無中生有、編造虛假學術會議的名頭,進行違法違規(guī)利益輸送,或者違規(guī)將學術會議贊助費私分的不法行為。
北京大健康法商團隊負責人鄧勇表示,判斷醫(yī)藥企業(yè)贊助學術會議是否構成商業(yè)賄賂需從四點出發(fā):
贊助是否實際上影響了參會者的專業(yè)判斷。
贊助的目的在于介紹、推銷本企業(yè)的產品,還是交流用藥理念、藥品的研究發(fā)展和新藥的治療功效。
會議當中有沒有諸如不正當?shù)目铐椡鶃怼才怕糜雾椖康刃袨椤?/p>
會議本身是否真實,或其他往來是否有失公允。
協(xié)會辦會“江湖”
據(jù)某藥企管理人員劉虎介紹,學術會議的主辦方主要有三種,分別是藥企、協(xié)會與醫(yī)院。其中協(xié)會是最主要的一方。
在民政部官網(wǎng)的全國社會組織信用信息公示平臺上,通過搜索“醫(yī)藥”一詞,可查到1355家狀態(tài)正常的協(xié)會。理論上,這些社會組織都能主辦學術活動。
北京某三甲醫(yī)院骨科的主任醫(yī)師彭光明(化名)介紹,對一些醫(yī)生來說,參與協(xié)會的好處之一在于增加頭銜。“每年要進行全國醫(yī)院的評審排名,如果醫(yī)院里擔任協(xié)會主委和副主委的醫(yī)生數(shù)量多是可以加分的。”
成立完學會,接下來就要開會。“學術會議確實促進了知識的傳播,但也有很多主委為了謀私利,這次到你的城市辦會,下次你再請我。這次我給你5000 元,下次你給我8000 元。”彭光明表示,“這就是個江湖。”
而黃榮梅回憶,自己參加過藥企學術部門召開的小范圍討論會,用以收集醫(yī)生們的反饋意見。藥企向醫(yī)生了解藥物的安全風險或者在臨床操作中遇到的問題,接著再根據(jù)反饋改進產品。
至于醫(yī)院組織辦會,根據(jù)規(guī)定藥企不能直接付錢給醫(yī)院。在這種情況下,醫(yī)院之間往往會組成學術聯(lián)盟來作為辦會主體,再通過基金會等第三方收取贊助費。
藥企怎么贊助會議?
在彭光明的記憶里,從2010 年前后開始,協(xié)會主辦的醫(yī)療會議開始占據(jù)大頭。藥企不再直接辦會,只能以贊助商或協(xié)辦方的身份參與。
藥企贊助協(xié)會開展學術會議,更確切地說是藥企參與學術會議的招商。從傳單、展臺到衛(wèi)星會,學術會議上的各種商業(yè)曝光機會都能得到公開定價。
2013 年,葛蘭素史克(GSK)在華商業(yè)賄賂案被曝光,GSK 人員就是以舉辦會議的名義,從公司套取費用,再以講課費的形式支付給醫(yī)生專家,達到為產品開拓銷路的目的。最終,GSK被罰款約30 億元。
彭光明表示,虛構學術會議向醫(yī)生行賄的做法至今依然存在,但一些上市藥企會面臨更嚴格的監(jiān)管。曾參與丹麥一家知名跨國藥企審計工作的一位審計師表示,該公司每年在華贊助開展的學術會議達數(shù)十場,不少是在五星級酒店舉行。審計師會向酒店逐一核實,是否真的開會了?花了多少錢?
即便是公開招商得到的贊助費用,作為非營利性質的學術組織如果毫無節(jié)制,依然會有不當牟利之嫌。在學術會議中,用廣告展位、醫(yī)生通訊錄和注冊信息等作為回報,收取醫(yī)藥企業(yè)贊助費,是過去比較常見的“操作”。
“感情投資”界定難
彭光明稱,虛假學術會議每次支付給醫(yī)生的費用為一兩千元,這與一位正高級專家收取的正常講課費相當。
《中央和國家機關培訓費管理辦法》規(guī)定,副高級技術職稱專業(yè)人員每學時最高不超過500 元,正高級技術職稱專業(yè)人員每學時最高不超過1000 元,院士、全國知名專家每學時一般不超過1500 元。講課費按實際發(fā)生的學時計算,每半天最多按4 學時計算。該規(guī)定被許多協(xié)會和藥企作為參考標準。
黃榮梅則表示,擁有正高職稱的她一般每場能拿1000 元。“為了這點錢,專家要花上一周時間做PPT、備課,聽眾收獲的是知識。”想到網(wǎng)絡上對學術會議的非議,她感到很委屈。
除了講課費,醫(yī)生在會議中產生的差旅、食宿費用該由誰支付,這仍是行業(yè)內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2023 年2 月,深圳證券交易所發(fā)布《關于深市醫(yī)藥公司商業(yè)賄賂相關問題監(jiān)管工作情況的報告》提到,部分醫(yī)藥公司假借學術會議的名義,為參會醫(yī)生安排旅游、休閑活動,報銷各類費用,向醫(yī)生輸送不當利益。
比起真金白銀的暗通款曲,看不見的“感情投資”更難界定,也更難查處。“人家都贊助我去開會了,那我回來是不是多開開他們家生產的胰島素?這是人之常情,醫(yī)生一定會在做某些決斷的時候有傾向。”彭光明說。
醫(yī)生掙學分:線下跑會
一個鮮為人知的制度是,國內醫(yī)生需要每年完成不低于25 個學分的繼續(xù)教育,在醫(yī)學研究的道路上終身耕耘。獲得學分與職稱考評掛鉤,每個地區(qū)規(guī)定不同。
II 類學分的獲取途徑包括自學、發(fā)表論文、科研立項等,I 類學分獲得則主要通過參會。中華醫(yī)學會、中華護理學會、中華口腔醫(yī)學會等單位召開的學術會議因為能產出I 類學分,所以地位更高。
彭光明表示,一個會議多的有三四個學分,低一點的有兩個學分。雖然醫(yī)生也能通過網(wǎng)絡學習獲得學分,但一些上歲數(shù)的醫(yī)生不擅長用電腦,而且國家對遠程學習獲得的學分有上限規(guī)定,線下跑會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掙學分方式。這也給全國各地的學術會議提供了一個人數(shù)龐大的醫(yī)生聽眾群。
劉虎表示,常理而言,醫(yī)生參會應當用手頭科研項目的資金,或由所在醫(yī)院資助,有時會議方也會對醫(yī)生的注冊費進行減免。但在實踐中,醫(yī)生也可能受藥企資助參會,其中是否涉及賄賂,很難界定。
“與其他類型的學分獲取方式相比,參加學術會議本身并不需要醫(yī)生投入太多的精力,因此會有諸多醫(yī)生選擇大量參加學術會議以獲取學分。這種客觀存在的需求為協(xié)會主辦方提供了參會流量,而這種流量本身又會吸引藥企投入正當或不正當?shù)匿N售成本。”鄧勇指出,“我們可以說學分制度導致藥企多了一條投入銷售成本的渠道,但具體是否合規(guī),還需要在具體的個案當中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