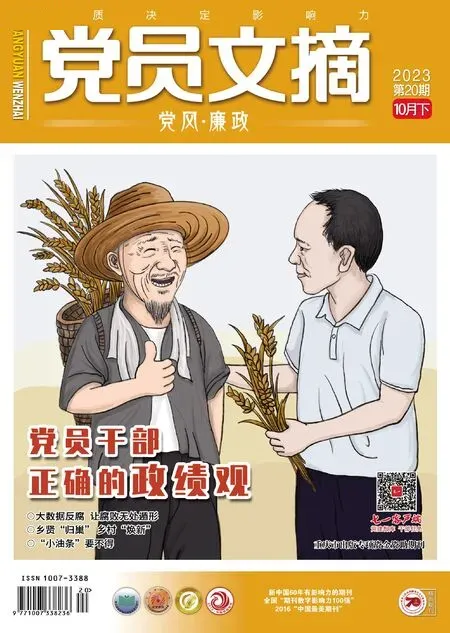鄉賢“歸巢” 鄉村“煥新”
文/呂金平 鮑蔓華 靳燕
前不久,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九部門聯合印發《“我的家鄉我建設”活動實施方案》,提出“鼓勵退休干部、退休教師、退休醫生、退休技術人員、退役軍人等回鄉定居,當好產業發展指導員、村級事務監督員、社情民意信息員、村莊建設智囊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誰來建設村莊、怎么建設村莊”,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的一道必答題。相對于單單依靠留守農民,為農村注入“新鮮血液”已勢在必行。其中,發揮好鄉賢作用,彌補鄉村人才的空心化,能夠為鄉村振興注入新活力。
化解矛盾,促進鄉村和諧
“有些家庭矛盾糾紛呈現隱蔽、突發等特點,咱們要多注意排查和收集這方面的線索。”
“村里現在仍有一些村民有迷信思想,存在盲目虛榮攀比心理,今后可以多舉辦一些宣講活動。”
初秋的晌午,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區德澤鄉左水沖村一戶農家院內,幾位鄉賢正一邊乘涼,一邊討論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設如何抓。
這是一支早在2011 年就成立的鄉賢隊伍,由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等組成。他們通過各種形式收集村情民意,掌握矛盾隱患,調解鄰里糾紛。
73 歲的王玉穩退休前是一名鄉村小學教師,也是一名老黨員。退休后,他帶頭參與家鄉建設,熱衷調解矛盾糾紛促和諧。
“在農村,矛盾糾紛的化解離不開公序良俗的制約。鄉賢們威望高、信譽好,人熟、地熟、情況熟,進得了門、說得上話,用親情、鄉情和真情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糾紛。”左水沖村黨總支書記王光奎介紹,近年來,為進一步推動移風易俗,建設文明村寨,左水沖村把鄉賢作為基層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表示,鄉村人才振興的核心是鄉村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回歸。
一方面,這些人可以把技術、信息、知識帶下鄉,彌補鄉村人才的空心化,以其對政策的理解,推動社會資本進入鄉村,再與鄉村資源結合,形成新推力。
另一方面,鄉賢返鄉,有利于鄉村價值重回社會視野,改變歧視鄉村、認為鄉村衰落的觀念。
建設陣地,推動鄉村富裕
近幾年,位于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洪塘街道的安山村,因為一群從事設計、藝術的人員入駐而變得熱鬧起來。
樸地建筑工作室等20 余個設計、藝術類工作室在這里生根發芽,創造了逾千萬元的年產值。而誰能想到,幾年前,這里還是一片無人問津的閑置廠房。
改變,就從村里來了“新鄉賢”開始。
2018 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張小晨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本土建筑師、藝術家看中了安山村,開始對這里的舊廠房進行改造、裝修和運營。
經過兩年多的摸索,這里變身“鄉野辦公社區”,每天在這里辦公的“新村民”多達百余人。
“城里人在給安山村帶來流量、關注度和消費的同時,我們也要利用好這些優勢。”張小晨說,在項目運營過程中,他們把農村資源和城市做對接,為村莊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產業聯動,真正實現了富民強村。
同是80 后,歸國留學生陳婧7 年前同樣以“新鄉賢”的身份,主動結對寧波市江北區慈城鎮王家壩村,承包了430 畝農田,建成布蘭登堡藝術莊園。
如今,莊園作為江北區文旅產業基地、中小學研學基地,每年為王家壩村村民增收63萬元,解決了近百名村民的就業問題。
創辦書屋,助力鄉村教育
每到周末,位于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沙河鎮棘城中街村的“樹理書屋”里都會熱鬧非凡。
不過,這里的熱鬧并不是人聲鼎沸的喧囂,而是源源不斷走進這里的孩子、青年和老人——他們有的安靜地坐在桌前看書,有的在書架前查找自己需要的書,還有的一邊翻看一邊在本子上記錄著。
看著這樣的場景,書屋主人王樹理眼中充滿了欣慰與滿足。
中街村是王樹理的老家,他和幾個兄弟姐妹從小生在這里、長在這里,這里的一草一木都記錄著滿滿的鄉愁。書屋坐落的地方,過去是幾間土坯房,也是王樹理一家幾輩人生活的地方。
“在村里建一座書屋,是我長久以來的想法。”王樹理的父親母親都不識字,但對學習文化卻有著特別強烈的愿望。特別是老母親,一輩子對書本、紙張非常珍視,在生活特別困難的時候,都沒有放棄讓兄妹四人上學讀書。
一家人因讀書而改變命運的經歷,讓王樹理很早就認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在外多年的工作經歷也讓王樹理意識到,要想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教育環境,光靠一個人、做幾件事還遠遠不夠,必須要在農村孩子的心里從小種下“要讀書”的種子。而母親在生命彌留之際留下的“希望子孫后代一定要認真讀書”的遺言,更是讓王樹理堅定了在家鄉辦書屋的想法。
2021 年,王樹理開始籌劃書屋的建造工作。他拆掉原來的老宅,重建了一座古香古色的二層小樓。書屋目前有各類藏書3 萬余冊,供村民和周邊各界人士免費閱讀。
“書屋計劃開展聽書講評、文體活動、醫療義診、農業講座,讓更多鄉親感受知識的魅力,讓鄉村文化振興真正落到實處。”說起書屋未來的規劃,王樹理滔滔不絕。
王樹理說,現在國家鼓勵有條件、有能力的人回鄉參與建設,各地政府部門要積極行動起來,強化政策引導,營造共同規劃家鄉、建設家鄉、服務家鄉的氛圍,這樣才能讓想干事的人穩得住、有期待、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