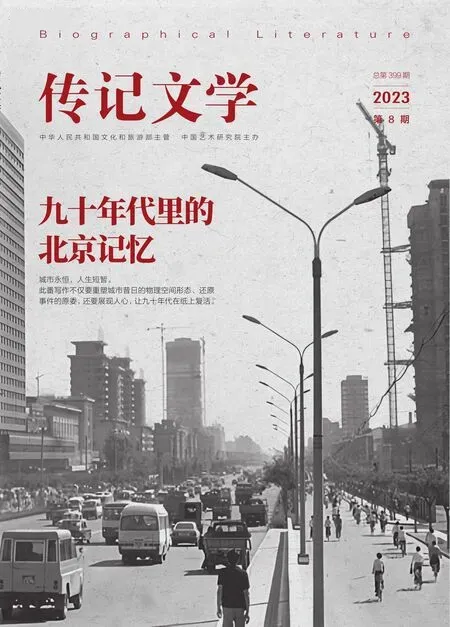詩與小天地
師力斌

從我個人的經歷看,詩意是生長出來的,與地理有關,與故鄉有關。
我想贊美的地方,都是哺育過我的。現在的愛詩,都源于這些地方,源于這些地方的山川草木、花卉果實。我越來越熱愛鄉村,近于偏執,對高樓大廈、汽車霓虹完全無感。如果簡單劃分我的詩歌,熱愛都出自山川草木、花卉果實,煩惱都源于高樓大廈、汽車霓虹。這或許是我先鄉村后城市的后遺癥。時常外出散步歸來,遙看小區多窗的群樓中住了多年的住宅,仿佛異地,陌生而可疑:小小的水泥格子就是自己的家嗎?城市住久了,心越不在城市,越往故鄉跑,往自然風景區跑,往公園跑,往京郊的山水間神游。路邊的一棵草、一株樹觸發的美的安慰,遠勝于劇院、美食和聚會。每當神游,詩便成了寶馬良駒,帶我前往精神上的昆侖瑤池。2023 年,我去川西高原,見到貢嘎雪山的剎那,我便臣服了。它不斷在上升、上升,仿佛在引領,氣場遠大于高樓大廈,遠大于一座城市。那種無以名狀的莊嚴神圣,不容置疑。人家靠的是億萬年的大修煉,一座城才多少年?細思好笑,鄉野出身、童年記憶、親近草木的歷史,決定了我的愛詩,主宰了我的精神世界。對人生來說,童年太重要了,多草木、多田園閑適、多山水清曠,培育了我內心的草木、閑適、清曠與詩。
從小到大,盡管生活百般艱難,但在住地上總是與美景為伍,真是獨特的“天賦”。2 歲至6 歲,我住在位于山西上黨盆地的小山村姬家嶺,南北兩莊,中間一溝,全村二十戶人家分住南北,獨我家在溝里。記憶中的姬家嶺像桃花源。一般的黃土高坡都是光禿禿的,這里四布的黃土崖上卻生出眾多柏樹,凌空盤曲,遠看像筆墨點染的國畫。北莊廟院里一棵兩圍多粗的老柏,高聳入云,小時候和伙伴們比賽仰望它,望得脖子疼。柏籽能吃,有奇香。柏的香味、松的香味、祖母燒火做飯的柴火味、院中海棠的花味,是我幼時記憶深刻的故鄉味道。后來,讀杜甫《古柏行》尤有感覺:“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云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正合我的兒時記憶,我們的廟院小學本就在高臺上,四望山巒起伏,可不就是“孔明廟前有老柏”“崔嵬枝干郊原古”,加之四時之景變幻,與杜詩如出一轍。我小學一年級在這里上課。
姬家嶺的樹哺育了我人生最初的詩意。生產隊的梨園秋收后開放,大部分梨子摘去分給各家各戶后,就成了孩子的天下。我們整天攀在樹上,尋覓剩梨。若能摘到一個,便驚呼同伴前來共享。秋天陽光明媚,梨葉幻化出各種顏色,從黃到橘到紅,啟蒙了我對“五彩繽紛”一詞的認識。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有一章寫果園采摘,情景與姬家嶺相似。我家屋前有一棵海棠,粗可合抱,花開時節,滿院飄香,蜜蜂飛舞,一團團粉白的花瓣把小院撐滿了。近秋果熟,我常在樹上待著,現摘現吃,像在蟠桃園里的美猴王。父親請了木匠師傅打家具,我和一幫小朋友在院子里瘋玩,陽光照耀下,木匠們身影晃動,刨花香味彌散滿院。中午,祖母做好工飯,一般有肉,木匠們端碗蹲著,談天說地,給我留下蒸蒸日上、日子紅火的記憶。90 年代,那棵樹被砍了。后來,我在北京郭沫若故居看到兩樹西府海棠,樹影婆娑,風姿綽約,睹樹思鄉,倍覺傷懷。我們總是留不住樹。姬家嶺院子西邊有一棵桃樹,也是我的伙伴。每年秋收,玉米棒運回,堆在院子里晾曬,大人剝玉米皮,小孩子就把玉米皮挽起來,西連桃樹,東接海棠,扯成一條幾十米長的繩子,做打電話游戲。這巨大的工程,十分令我自豪。還有香椿、紅棗、花椒、煙臺梨等樹,多是父親從城里農場帶回種下的。屋后還有一棵君遷子,土語叫“軟棗”,果實狀如羊糞蛋,在手里捏搓,軟綿可心,吃起來沙甜,是我們村的唯一。
還有放羊。羊圈在村外一里多的崖洞里,牧羊人早飯以后開洞門,羊群如學生放學般涌出,黑山羊、白綿羊,“咩咩”叫著,在黃土坡撒歡。小屁孩甘當跟屁蟲,我拿一個小羊鏟,鏟一塊土坷垃扔向跑到莊稼地的羊,意不在護莊稼,在于看扔得準不準,嘴里學著他們的吆喝,“達咯嘶,達咯嘶”。最快樂的是騎羊,沒坐穩便摔下來,躺在地上一身騷味,哈哈大笑,樂此不疲。那時當騎士游四方的理想,就是跟著牧羊人漫山遍野瘋跑。
田野是兒童永遠的樂園。秋收時節,夜里農忙,各家在地里點了火堆燒玉米吃,香甜的味道四下彌漫,比現在城里的烤玉米饞人得多。在夜幕鼓動下,我和小朋友們在各家的玉米堆前追打嬉戲,不亦樂乎。真是無憂無慮的日子。我對田野的渾厚感情就是在兒童時代產生的,與時俱長。實際上,那時的母親正不得志,郁郁寡歡,我卻根本領會不到。
小橋流水的最初經驗也在姬家嶺。房后二十米有一個小河溝,上有小橋通往南莊。秋雨過后,水溝涌溢,浸過石頭,激出潺潺水聲。可以洗菜,還可以拿了蓖麻桿做水槍,就地取水射擊,比現在玩手機打游戲過癮多了。小溪上溯,直至自留地。每年秋收,都能在地邊玩水,這個樂趣一直持續到1987年我到長治上高中。
6 歲至17 歲,我到父親工作的石哲鎮上學,距姬家嶺三四里。暑假和國慶節常回姬家嶺玩。石哲也是個很美的地方,名字獨特,地處小盆地,濁漳河上游,西為發鳩山,此山相傳是神話精衛填海的誕生地,是精衛鳥的故鄉。東臨申村水庫,建于1958 年。老人們說,當時王八多得像秋收之后地里的玉米茬子,想吃的人,到河邊拿腳一踹,它便翻了身,用臉盆裝起來就走。水庫寬闊,水光接天。兩岸綠樹縈繞,遠處青山脈脈,空氣里散發著河草的香味。河面水鳥飛鳴,漁人隱映,像極了江南。河上往來木船,載各色行人,紅黃藍綠的衣服、自行車、包袱、孩子,說說笑笑,水聲蕩漾。岸邊鋪墊著松軟的玉米稈,方便船客踩踏避水。這里是我人生最初體驗到風光無限的地方。我家“文革”結束后到石哲,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開始。我那時對大歷史沒有任何覺察,該上課上課,該玩耍玩耍,沉浸在石哲的美景中。80 年代上高中以后患上神經衰弱,每年利用暑假回到石哲的水庫邊釣魚休養,效果奇好,對故鄉的精神依賴從此更甚。后來,我帶父親來北京,逛了頤和園等地,問他怎樣,他說哪兒也不如石哲好。這可能正是國人常見的故鄉“偏見”,現在進城打工的一些年輕人好像恰恰相反。
我家在石哲租了多次房,在村里轉了一圈,最后定居在村子最西頭,院子大,周圍全部是田野。父親把院子當田園侍弄。沒有院墻,就用玉米稈編籬笆。80 年代,蓋了院墻,種了百十來棵楊樹,形成了一片小樹林。早晚在樹林里跑步,空氣新鮮,十分愜意。父親在院子里開辟了一個大菜園,再用一道籬笆圍起來,以防雞們偷吃。父親不愛交際,菜地便是他的社交圈。搭架、捉蟲、剪枝、固秧、修渠,自得其樂。菜園是父親的最愛,他潛心經營,蔬菜口味純正,植下了我對于綠色食品和農家樂的深刻記憶。夏天成熟季節,我家成了對面中學食堂的蔬菜供應地,品質好,比集市便宜。打水澆菜是又一個樂趣。院子里挖了一口深井,每次可以打二十來桶水,我星期天和放暑假幫父親搖轆轤打水,累得氣喘吁吁,樂此不疲。澆完,夕陽西下,金色的光從西院墻上灑到院子里,我就搬個方桌,放在院子中間,做暑假作業。如果是雨后,空氣清新,泥土潮濕,廊檐下的青磚略帶綠苔,倍覺恬靜。母親則一趟趟進出菜園,把快要熟了的蔬菜摘到一個塑料籃子里。她在秧苗間穿行,神情怡然,那種田園的滿足令我終生難忘。
另一項農家樂是養雞,找蛋。二十來只雞田野里散養,吃得羽毛豐滿、體態臃腫。每天產蛋一斤多。母親在每顆雞蛋上標上序號,以區別新舊,舊蛋先吃或先賣。母親每天都要把母雞抱在懷里摸蛋,說,黃雞有蛋,白雞有蛋,大黃雞沒有,肯定又下在什么角落里了。我就四處尋找大黃雞下的野蛋,某一天會豁然發現,在某個角落的草垛子里邊,或在一蓬荒草里,好多蛋。春天孵小雞令我和弟弟著迷,孵十七八天,把蛋放在一個水盆里,晃動的雞蛋可以出雞,一動不動的,則可能沒有希望。我們擠在母親的旁邊,東抓一下,西弄一次,充當養雞小專家。到二十一天小絨毛球們出殼,剛出來便可直立在磚地上,嘰嘰叫著,或躲在母雞肚子底下,第二天便歡叫著跑到院子里找蟲子。當時沒有感覺,似乎生活就應該這樣,現在住到大城市回頭看,這樣的生活實在奢侈。后來我住在太原、北京,常常做白日夢:一個大院子,菜園、雞鴨、樹林、水井,一家人圍坐院中,歲月靜好。這才是我心目中現代化幸福生活的圖景。進了城,失了地,沒了院,才知道土地對于人生多么重要,才明白自己種的菜多么香甜,才明白人的幸福想象,其實就是童年想象。未來的孩子年老時,記起的是不是只有手機?
石哲和姬家嶺給我留下印象的遠不止這些。記得最多的是13 歲以前的事,14 歲上高中以后記得少了。在長治、在太原,近年來在北京的生活,都恍惚朦朧,姬家嶺和石哲的生活卻像一部老電影,清晰的影像經常浮現。我知道這叫作懷舊,是衰老的征兆,但我無法排除,它們牢固構成我的鄉村記憶。
我的高中是在長治市太行中學,另名晉東南師專附中,同樣也美。太行中學名字好聽,氣魄宏大,聲韻感強,讓我想起太行山,那里是我離鄉進城的第一站。1984 年秋開學,到八一廣場下車,往東經煤炭電影院,再往北捉馬村方向,已近郊區,亦城亦鄉的景象,正合我的審美。路兩旁有高大的楊樹,讓我覺得人家城市里的楊樹也比農村氣派。柏油馬路在陽光下閃亮平整,車輛來往,喇叭鳴叫,一派繁忙。那一段路成為我記憶中最早的城市印象。太行中學比老家對門的石哲中學地盤大、樓高、樹多,靠東墻附近也有一片楊樹林,親切得讓我想起家鄉院子里的那一片。
我最早接觸當代文學是在太行中學。冬天雪后,平房宿舍生煤爐,挺溫暖,適合待著看小說。我借閱了好幾本小說集,大概是1981、1982年左右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獲獎作品集,對鐵凝的《哦,香雪》,何士光的《鄉場上》《種包谷的老人》,都有印象。那位老人在玉米地里干活的情景,感覺非常親切。我才知道,玉米還有包谷的別名。這是當時讓我陶醉的文學作品。那時青春萌動,還有另外的讀物。上英語課時偷看一種叫《多棱鏡》的小報,令人臉紅心跳。對女同學的感受也啟動了。同桌是城里女生,聲音清純,普通話極純正。我總是被她清晰標準柔和的說話聲吸引。人家的話講得多動聽!桌上還有三八線,相互很少說話,但心里早就越線了。每天早操時,播放蘇紅的歌曲《小小的我》和鄧麗君的《千言萬語》,勾起一種特別的憂傷:“不知道為了什么,憂愁它圍繞著我,我每天都在祈禱,快趕走愛的寂寞,那天起你對我說,永遠地愛著我。”我關注的不是最后一句,而是前四句,青春萌動的典型癥狀。更可笑的是,我把“那天起”理解為“那天氣”,不深究,也沒有和別人交流過,一直錯到后來。畢業時,班里一位漂亮女生,用她的大眼睛望著我說:“師力斌,你知道嗎,我還是你的半個老鄉。”她給我的留言簿留言,曾跟著下放的父母在石哲讀書,提到“上學路上的小橋、晨霧、雞鳴,以及石哲中學她家門前的核桃樹”。這是我高中時代難忘的一次奇遇,體驗到莫名的情愫,美、害羞、朦朧……她美麗的大眼睛是我最早的啟蒙。
中學時代的愛好,是一生重要的愛好。中學時代如饑似渴,不被此項占領,就被彼事迷惑,總需要什么來填充強烈的求知欲。要么旅游種地,要么畫畫寫字,要么游泳打拳,中學教育最好的辦法就是大人陪著,把孩子引導到一項入迷的事業中來。直到現在,我的地理知識仍然很牢固,那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底子。很多人犯愁的外國地名,比如山脈阿拉巴契亞、城市達累斯薩拉姆、國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等,我都可以隨口說出,不打磕巴。
文學黃金的80 年代,我在山西大學政治學系讀書。山西大學是國內為數不多的綜合性百年老校,歷史悠久,實力雄厚,但之前多年一直沒有進入重點大學行列,在山西還不如太原理工大學,讓人非常納悶,近幾年好像有所扭轉。山西大學的校園仍然美麗。在那里,我第一次聞到丁香,沁人心脾。我發奮讀書,各個門類的書,如手抄張賢亮的《習慣死亡》,其語言令我著迷。我熱衷學生社團活動,參加學通社,結識了一大群記者校友。我還參加了學生書法社團,聽過姚奠中、楊其群諸先生的書法講授。姚先生曾經是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班的弟子,與魯迅同門;楊先生專攻唐代詩人李賀。但那時的我仍是亂讀書,亂作為,毫無章法,一事無成。大學畢業21 歲,我進入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工作,屬于核工業系統,地點還在太原。
我這半生,兩句話可以概括,即做人還算成功,做男人很失敗。前者是說,近三十年,基本按自己的內心生活,喜歡文學,從事文學,人生大幸;后者是說,三十不立,拖家帶口,無房無車無工作,實在失敗。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工作以后的十年,才知道自己是典型的鄉村型菜鳥。以文學為業,才是內心所向,且不斷遇到文學界的貴人相助,這也促使我現在盡可能地幫助別人。1998年,改行的想法達到高潮。在單位工會和核工業神劍文學藝術學會的資助下,我自印了第一個詩歌散文小冊子《心靈散步》,視為珍寶。28歲,還算年輕。同事段瑞忠是一位詩人,常在報紙上發表詩歌,向我推薦余光中、北島、聶魯達等詩人,深深吸引了我。我迅速迷上了新詩,寫詩在段瑞忠編的院刊《輻射防護》副刊上發表,還有一點稿費。1993年以后,我的詩作在《太原日報》連續發表,受到編輯黃海波和編輯部主任陳建祖先生的鼓勵。1994 年,我參加詩刊社與《太原日報》舉辦的首屆全國新田園詩歌大賽,獲二等獎,受到李小雨等詩人老師的抬愛。在《詩刊》發表詩作后,得到了周所同老師的關注,文學積極性被調動了起來,對文學的想法也日漸膨脹,萌生了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念頭。2001 年,我第四次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成功。當拿到印有博雅塔的錄取通知書,真想親吻姬家嶺和漳河水。去世兩年的母親老人家若是在世該有多高興啊!母親從小教我寫毛筆字,督促我念書,寄望于我。此時,距大學畢業整整十年。我已經31 歲,但依舊信心百倍,夢想著此后新的生活,痛痛快快創作,弄出一點成績來。
北大七年,使我脫胎換骨,終身受益。一方面,張頤武先生等許多名師傳道授業,《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諸位學友共商學術,未名湖畔的師友情誼終生難忘,詳情記于《我在北大的修煉》一文;另一方面,大齡已婚男的求學生活相當痛苦。在食堂打飯,廚師喊我老師。在三角地修自行車,有女生喊我師傅。我騎自行車帶幼兒園的女兒出沒燕園的情景,進入許多同學的記憶。高處不勝寒,高手如云,學無止境。北大求學的第一感受是不再盲目自信。高人太多,文學太大;第二感受是文學作為謀生手段,實在不宜。文學夢想是之前的黃金時代留下來的,而自己必須在市場背景下文學走低的現實中掙扎。到畢業時,我方看清了文學夢的真面目,才體會到要坐十年冷板凳,才曉得文學是一個絕對寂寞的事業,才知道“百無一用是書生”,才知道北大不培養作家是一個多么正確而無情的概念。越來越明白自己是一個領悟力遲鈍的人,總要事情過后,才能認識其中奧妙。
畢業不等于結束,僅僅是個開始。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甚至是針尖對麥芒的兩回事。方法上沖突,思維上沖突,時間上沖突,情感上沖突,某些方面更南轅北轍。要靠學術研究吃飯,必須在大學謀教職;而靠創作吃飯,則必須有作品,必須有時間創作。幾個選項,我兩不靠。學的是文學理論,從事的是文學編輯,心中喜愛的仍然是文學創作。三張皮怎么能粘到一起呢?
2008 年到《北京文學》編輯部工作后,我才看清了此前的人生道路。那是一條彎路,十年彎路。假如早十年到北大讀書該是何等樣子呢?哪怕早三年、五年?人生無法假設,路只能走過才知道。回顧以往38 年,學識龐雜,無一精專,一無所成,而人生已過天命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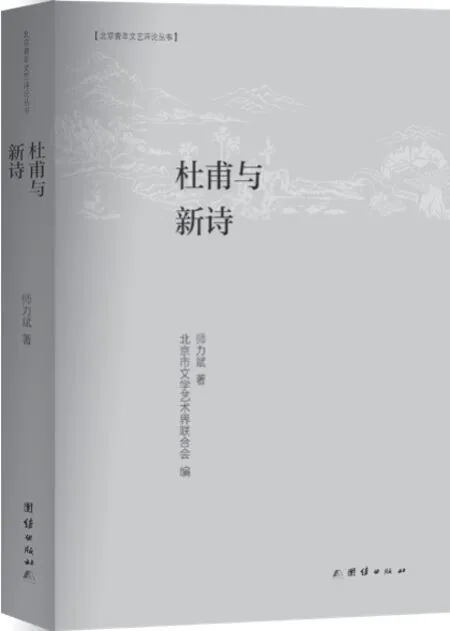
師力斌:《杜甫與新詩》
曲折乃人生本義。北大使我明白了學術之大、思想之富、自我之小,《北京文學》使我明白文學之美、之深、之古老。在《北京文學》的15 年是我在一個地方待得最長的15 年。故鄉待了14 年,長治3 年、太原14 年、北大7 年。《北京文學》的15 年是我全身心服務文學事業的15 年,也是逐漸領悟人生妙理的15年。15年來,我遇見了多種風格的作家、各種寫法的作品、五花八門的人生。有的作者從自然來稿相識,到他們成名成家,備感人生充實;有的我傾慕的作者已經仙逝,又覺人生如夢。跟作家打交道就是跟千百個自己的人生打交道,其間曲折進退,百感交集。幸運的是,在此又遇見了體己的領導和善良的同事。最重要的領悟是:文學是生命的結晶,值得投入,值得熱愛。文學并非權宜之計、生財之道、揚名立萬之物,它實在太可愛、太深奧、太有魅力,無法抵抗。
15 年來,我最意外的收獲是遇見了杜甫,寫了一本《杜甫與新詩》,將這位唐詩先賢與現代新詩勾連起來,踏上文學寫作的新路。一開始,我僅僅想寫一篇文章,表達對新詩和古詩關系的一點體會,表明新詩可以而且必須學習杜甫的想法,后來一發不可收拾,遂成一書。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這本書較為完整地闡述了我幾十年來關于漢語詩歌的看法,過癮。這本書得到了許多師友的指點、關愛和回應,他們提出修改建議,撰寫評論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相關章節。該書還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的重點扶持和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的獎勵扶持。以上種種,都使我備受鼓勵,鞭策我繼續探討杜甫與新詩。
回想來路,詩歌是命運對我的饋贈,來自故鄉的饋贈。激動、興奮、充實,是我投身詩歌常有的情緒,是從喝酒、看戲、刷屏、逛公園等娛樂中沒有得到過的。在《北京文學》做編輯,與詩人安琪合編《北漂詩篇》,獨自寫作《杜甫與新詩》,種種詩歌的勞作都是如此。三十年過去了,我對詩歌的興趣越來越濃,領悟越來越深,我在世俗世界得不到的,在詩歌這里都得到了。詩的小天地,雖然不大,足夠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