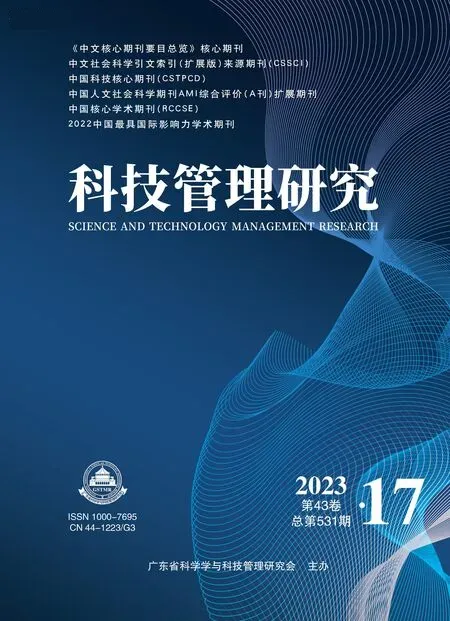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環境治理效率時空分異及其影響因素
何 姣,李露露,焦 銳,劉星池
(1.湖南理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南岳陽 414006;2.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湖南長沙 410082)
2023 年,國務院以國函〔2023〕9 號文件批復同意《新時代洞庭湖生態經濟區規劃》,致力于推動洞庭湖生態經濟區向更高層次發展。洞庭湖生態經濟區(以下簡稱“湖區”)作為中國三大主要生態經濟區之一,地跨湘鄂兩省四市一區,共33 個縣(市、區),規劃面積6.05 萬km2。近年來,為加快改善湖區生態環境質量,政府主管部門陸續出臺了《湖南省洞庭湖水環境綜合治理規劃實施方案(2018—2025 年)》《洞庭湖生態環境專項整治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等一系列與湖區環境治理相關的政策文件。中央和省級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也多次針對洞庭湖生態環境保護統籌安排專項督察“回頭看”,以確保專項治理政策得到嚴格落實。根據湖區所屬縣(市、區)年度政府財政決算數據顯示,2017—2021 年湖區累計投入生態環境治理資金約400 億元。總體上看,湖區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成效明顯,但仍面臨湖泊萎縮、生態退化、“九龍治湖”等諸多難題,亟須科學測度該地區環境治理效率并揭示影響效率的關鍵因素,以實現湖區環境協同治理和推動湖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1 文獻綜述
為切實提高環境治理效率,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學術界對環境治理效率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和技術支持,主要集中在環境治理效率的測度和影響因素分析兩個方面。關于環境治理效率測度,目前學者們多選擇熵權-TOPSIS 法、隨機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數據包絡分析(data d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等進行評價分析。其中,何偉等[1]、鄧正華等[2]分別基于長江、洞庭湖水資源視角,運用熵權-TOPSIS 法對其承載力進行綜合評價,研究發現長江水資源承載力呈現穩步提升態勢,洞庭湖則與之相反;黃萬華等[3]同樣運用該方法對長江水資源管理績效水平進行了靜態評價及動態分析。徐維祥等[4]基于SFA 考察了全國和東中西部地區環境規制效率的時空差異性,相較而言,DEA 模型已成為目前環境治理效率或績效評價的主流方法[5]。從研究角度來看,學者們選擇將研究對象重點放在省域或流域環境效率等上,如景曉棟等[6]、張吉崗等[7]、馬駿等[8]和Pan 等[9]采用傳統DEA 模型分別探析區域生態環境效率、省域節能減排效率和長江經濟帶生態補償效率的時空分異特征。另外,考慮到不同時間截面的綜合技術效率可能存在差異,向小東等[10]、胡振華等[11]、劉蒙罷等[12]、陳琦等[13]和周平[14]將超效率DEA或SBM 模型與Malmquist 指數相結合揭示環境或低碳效率的靜態空間異質性和動態時間演變趨勢。
關于環境治理效率影響因素分析,學者們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環境要素等對環境治理效率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中,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常甜甜等[15]、楊騫等[16]、王兵等[17]、張新林等[18]和萬斯斯等[19]認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GDP)對環境治理效率產生明顯促進效應,而李青松等[20]和范如國等[21]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用水綠色效率和環境治理效率時空分異的影響作用呈減弱趨勢。產業結構方面,韓晶[22]、葛世帥等[23]和咼亞玲等[24]發現優化產業結構對環境效率提升具有促進作用,而王珊等[25]和王建華等[26]的研究認為產業結構對環境效率提升沒有貢獻甚至存在反向作用。環境要素方面,鑒于有效減少與環境效率密切相關的污染物可提升效率水平,張婉玲等[27]、戢夢雪等[28]、陳詩一等[29]和張東敏等[30]將廢水、廢氣和固態廢物作為主要指標對生態環境質量進行了深入探討。此外,還有學者考察了技術進步、工業化水平等因素對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如汪克亮等[31]通過Luenberger 生產率指數分解發現技術進步對環境效率提升有很大的驅動作用,吳旭曉[32]則認為環境效率的下降是由技術進步無效率導致的結果;藺雪芹等[33]、崔葉辰等[34]發現工業化水平的提升會導致效率普遍偏低。
通過對現有文獻梳理發現,以往研究多集中在省域層面工農業環境效率或績效、長江經濟帶或湖區水資源利用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等方面,鮮有文獻對湖區縣域層面的環境治理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開展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選取湖區范圍內的岳陽、常德和益陽3 個地級市下轄24 個縣(市、區)為研究對象,運用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Malmquist 指數模型測度2017—2021 年湖區環境治理效率以探究其時空分異特征,并借助Tobit 回歸模型揭示影響其環境治理效率的因素,以期為提升湖區環境治理水平提供參考依據。
2 研究方法
2.1 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 模型
數據包絡模型是早在1978 年提出的針對同類型多投入、多產出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進行有效性評價的非參數方法[35]。而2001年Tone[36]基于傳統DEA 提出的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 模型,已被Wang 等[37]、李俊霞等[38]、錢麗等[39]、Wang 等[40]廣泛應用于生態環境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創新效率和能源效率等研究領域,該模型不僅克服了傳統DEA 測度效率值不能跨期比較的缺陷,也充分考慮了非期望產出。基于此,本文采用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 模型測度湖區環境治理效率,該模型見公式(1)至(2):
2.2 Malmquist 指數模型
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 模型雖然考慮了非期望產出所帶來的影響,但無法揭示環境治理效率動態變化情況。基于Fare 等[41]提出的Malmquist 指數模型,本文旨在運用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變化指數評估湖區環境治理全要素生產率,以直觀揭示環境治理技術進步時超效率前沿面的變化趨勢。該模型見公式(3):
2.3 Tobit 回歸模型
由于湖區環境治理效率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屬于受限因變量,若采用傳統的最小二乘法將導致系數估計偏誤。因此,本文選擇Tobit 模型可以用于解決受限因變量建模問題,具體見公式(5):
3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說明
3.1 投入和產出變量
根據超效率SBM 的投入產出框架,本文參考董會忠等[42]、盧麗文等[43]的研究成果并考慮數據可獲得性,構建了湖區環境治理效率的評價指標體系。其中,選取環境治理投入和能源投入兩個指標作為投入變量,環境治理投入采用縣(市、區)政府財政年度報告中披露的節能環保支出進行衡量,能源投入則采用包括三大產業用電和居民生活用電的全社會用電量。產出變量中的期望產出包括空氣質量達標率、污水處理率、森林覆蓋率3 個指標;非期望產出選取各縣(市、區)水質綜合指數作為代理變量,其數值越小說明水環境質量狀況越好,反之則越差。
3.2 解釋變量
湖區環境治理效率還受到經濟發展水平、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和政策制度等諸多因素影響,但由于客觀條件限制和模型本身局限難以將所有因素考慮進來。因此,參考劉偉等[44]、程鈺等[45]、馮雨豪等[46]的研究,選取各縣(市、區)第二產業占比、規模以上工業資產、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糧食播種面積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比值和有效灌溉面積六項指標作為影響環境治理效率的解釋變量。表1 總結了湖區環境治理效率的投入、產出和解釋變量,并對具體指標及其數據來源進行了說明。

表1 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環境治理效率評價指標
4 環境治理效率時空分異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4.1 環境治理效率靜態分析
基于本文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和采集的變量數據,運用MaxDEA 軟件測算2017—2021 年湖區3市下轄24 縣(市、區)環境治理效率值,并借助ArcGIS 軟件直觀呈現環境治理效率的空間分布情況,如圖1 所示。從圖1 可以看出,湖區環境治理效率整體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動趨勢,下降幅度達9%,僅2019—2020 年出現正增長。

圖1 2017—2021 年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環境治理綜合效率分布
從地級市層面來看,湖區環境治理效率按照從高到低排序分別是岳陽市、益陽市和常德市,其效率均值分別為0.66、0.63 和0.62。岳陽市高于其他兩個地區的原因為,近年來岳陽市政府陸續出臺實施了《岳陽市洞庭湖生態環境專項整治三年行動實施方案(2018—2020)》《岳陽市東洞庭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條例》和《岳陽市城市規劃區山體水體保護條例》等一系列與環境治理相關的政策文件,為開展專項整治行動提供了政策保障。另外,目前洞庭湖生態環境監測主要集中在岳陽市境內的東洞庭湖區域,其下設的6 個監測站著力對湖區環境治理各個環節進行質量控制。正是由于政策和監控的雙重保障,使得岳陽市整體環境治理能力穩步提升。
從縣域層面來看,湖區環境治理效率均值普遍偏低,僅極個別地區效率值大于1,且主城區效率值明顯優于其他地區。其中,武陵區、安化縣和岳陽樓區環境治理效率均值以1.01、0.98 和0.96 位居前列。究其原因為武陵區和岳陽樓區分別為常德市和岳陽市的主城區,其在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揮著主體功能作用,在環保資金投入、環保政策執行以及輿論監督等方面更有優勢;安化縣作為國家級重點生態功能區,在推動地區環境治理效率提升方面具有較好的前期基礎和實踐經驗。而環境治理效率最低的沅江市,雖然在2017—2021 年累計節能環保投入達14 億元,但其污水處理率和空氣質量達標率仍落后于其他地區,這表明環境治理效率的提升不完全依賴于投入資金,長期綜合治理過程也至關重要。
4.2 環境治理效率動態分析
為進一步揭示湖區24 個縣(市、區)環境治理效率的動態變化趨勢,本文引入Malmquist 指數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對其進行測算分析,如表2 和圖2 所示。

表2 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環境治理Malmquist 指數均值及其分解
從時間維度來看,2017—2021 年湖區全要素生產率均值為0.976,年均降低2.4%,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動趨勢。而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年均增長率為-2.5%和0.1%,可見湖區環境治理技術水平的改進作用相對有限,其管理水平、資源配置效率亟需提高。按時間階段劃分,湖區全要素生產率僅在2019—2020 年間有所增長,主要依賴于環境治理科技水平的提高,其技術效率指數不升反降這可能與各縣(市、區)生態環境管理的政策和方法緊密相關。而其他3 個時間階段存在明顯的短板效應,尤其是2017—2018 年和2018—2019 年全要素生產率降幅分別高達11.6%、13.1%。雖然湖區環境治理投入要素的配置結構較為合理,但技術創新難以促進湖區環境治理的發展。相較而言,2020—2021 年全要素生產率呈小幅下降態勢,其技術進步的提升無法彌補技術效率的下降。因此,今后湖區環境治理不僅要加強科技水平和技術創新,也要注重技術要素的投入及其資源配置。
從空間維度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常德市>益陽市>岳陽市”的空間格局。其中,岳陽市技術效率下降幅度高達7.1%,可見技術進步所產生的正面效應不足以抵消技術效率的負面效應。益陽市則由于技術進步出現2.1%的衰退,導致環境治理效率降低,故需增強環境治理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以提升其技術創新水平。相較而言,常德市屬于雙驅動型,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受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的共同影響。具體到縣域層面,華容縣、岳陽縣、津市市、澧縣、臨澧縣、桃源縣、石門縣、赫山區和沅江市9 個縣(市、區)全要素生產率呈增長態勢,漲幅最大的是津市市(27.6%),其次是沅江市(12.3%)和臨澧縣(9%)。而除漢壽縣降幅高達20%外,其他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呈現略微下降趨勢,下降幅度均控制在10%左右。降幅較大的漢壽縣、云溪區和湘陰縣技術效率均小于1,可見技術效率的降低是影響其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阻力。
4.3 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運用Tobit 回歸模型分析前文6 個解釋變量對湖區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如表3 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1)第二產業占比、糧食播種面積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比值與環境治理效率呈負相關性,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第二產業占比、農業種植結構對環境治理效率會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規模以上工業資產回歸系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每增長1 億元可提高12.26%的環境治理效率,不僅反映規模以上工業加大了對生態保護資金、技術、人力等方面的投入,也進一步說明湖區應積極推動工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3)有效灌溉面積與環境治理效率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雖然擴大灌溉面積能夠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但環境治理負面作用遠遠大于對經濟增長的正面作用。究其原因可能為,長期以來當地居民依靠湖區氣候濕潤、水資源充足等條件進行傳統人工灌溉的方式導致損水量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將加劇水污染、水土流失等多重負效應。(4)人均可支配收入回歸系數為負且滿足1%顯著,其原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密集型生產和消費實現,而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環境的污染和生產消費的其他后果往往被排除在經濟決策之外,從而間接導致湖區環境治理效率下降。(5)人均GDP 對環境治理效率呈1%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當地區經濟水平持續發展并到達一定高度時,會引起地方政府對其環境治理的關注,促進當地環境法規制定與實施和環保技術的使用。

表3 面板隨機效應Tobit 模型估計結果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基于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Malmquist 指數模型對2017—2021 年洞庭湖生態經濟區環境治理效率進行測度以探究其時空分異特征,在此基礎上利用Tobit 回歸模型實證分析湖區環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因素。通過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3 點結論:
(1)湖區環境治理效率整體水平偏低,且在空間上存在明顯的不平衡性。在地級市層面,湖區環境治理綜合效率呈現“岳陽市>益陽市>常德市”的空間分布格局;在縣域層面,僅武陵區等個別地區表現出強DEA 有效,且地級市主城區效率值明顯優于其他地區。
(2)湖區環境治理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變化趨勢,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交錯影響是導致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地級市層面的常德市,縣域層面的華容縣、岳陽縣、津市市等9 個縣(市、區)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增長趨勢。
(3)人均GDP 和規模以上工業資產對湖區環境治理效率存在正向顯著影響,而第二產業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業種植結構和有效灌溉面積則存在抑制作用,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有效灌溉面積的負向影響更為顯著。
5.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從以下3 個方面提出提升湖區環境治理效率的政策建議。
(1)構建區域協同機制,優化配置環境治理資源。針對目前湖區環境治理整體效率偏低、地區差異明顯的問題,湖區三市應在現有區域合作框架內,建立集環境保護、治理和監管于一體的區域環境治理協同機制。在具體操作上:首先,應結合湖區現實情況,構建科學的環境治理效率評估機制,以引導各地區環境治理資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其次,深化湖區各級層面的協同合作,充分發揮武陵區、安化縣等環境治理綜合效率相對較高地區的示范引領作用,鼓勵這些地區在環境治理政策制定與實施、關鍵技術手段和平臺數據資源等方面實現區域共享,從而縮小湖區環境治理的空間差異。第三,各地級市政府應在綜合考慮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資源要素稟賦、產業結構特征等因素的基礎上,做好各縣(市、區)環境治理資源規劃,避免資源要素對主城區過分傾斜,從而實現縣域間環境治理資金、人才、技術等資源的最優化配置。
(2)加大技術創新力度,提升環境治理全要素生產率。針對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變化對提升湖區環境治理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不高的問題,需要優化配置技術創新所需資金、人才等資源要素,促進湖區環境治理技術上的引進、轉化與開發。具體而言,岳陽樓區、云溪區、汨羅市等10 個受技術進步制約的地區應側重于加大環境治理資金的投入力度和專業管理、技術人才的引進力度,通過稅收減免、購房補貼、綠色信貸等多重優惠政策吸引高新環保技術企業和人才;而君山區、鼎城區、武陵區等8 個受技術效率制約的地區則應在現有環境治理資源約束下,確保環境治理資金專款專用,并通過改善環境治理資源投入的方向和廣度以提升環保資源投入的規模效應。
(3)優化產業結構布局,推進生態環境高質量發展。以綠色發展推動農業現代化和加快第二產業轉型升級是提升湖區環境治理效率的治本之策。因此,應結合湖區三市農業農村現代化“十四五”規劃提出的農業產業特色發展布局,借助現代工業設備和數字技術手段打造綠色高效和綠色現代農業高地,并持續推進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投入品減量使用。同時,針對湖區三市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占比偏高問題,加快第二產業向服務業的轉型升級,淘汰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產能,提高產業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開發推廣低碳清潔能源及節能低碳技術,有效構建綠色低碳的現代產業體系,以推動湖區生態環境高質量發展。
注釋:
1)考慮2017—2018 年湖南省生態環境廳《縣(市、區)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情況排名》數據缺失問題,本文基于2019—2021 年原始數據采用幾何平均值方法對缺失值進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