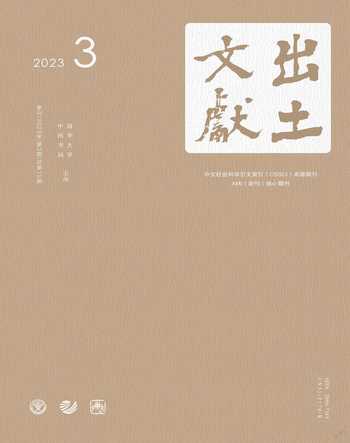咸陽閆家寨出土秦車器銘文釋義
魯超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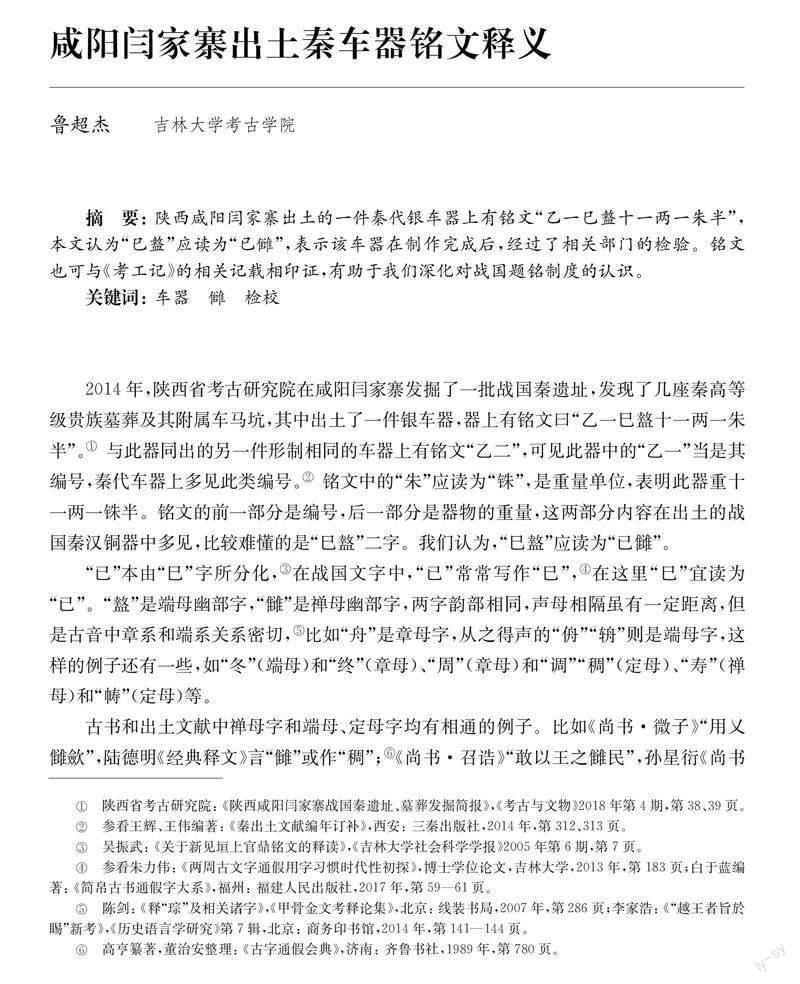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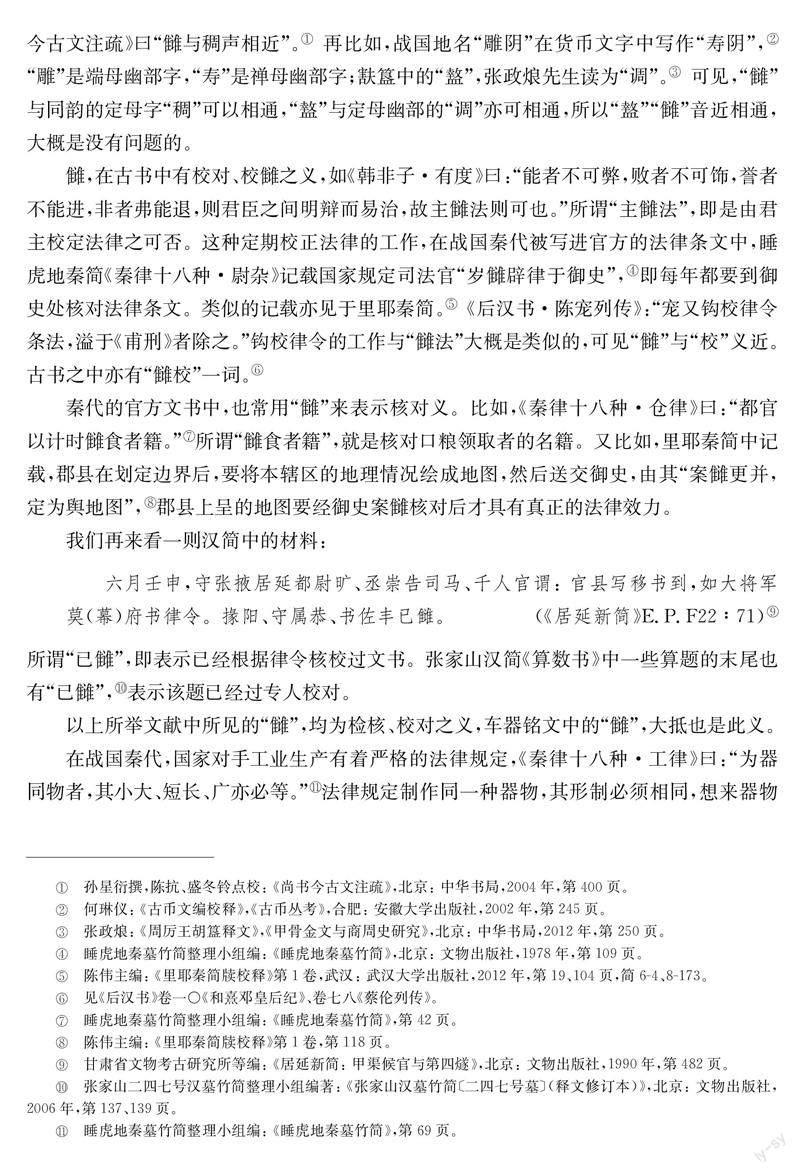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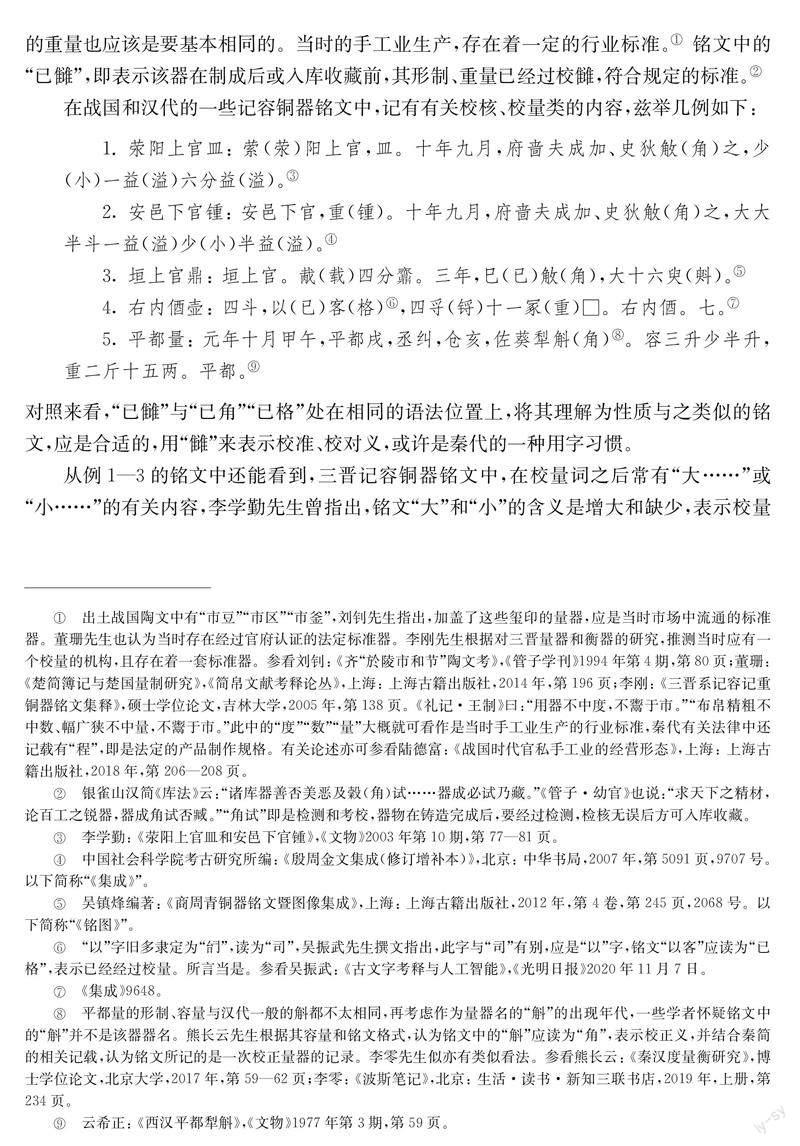
摘 要:陜西咸陽閆家寨出土的一件秦代銀車器上有銘文“乙一巳盩十一兩一朱半”,本文認為“巳盩”應讀為“已讎”,表示該車器在制作完成后,經過了相關部門的檢驗。銘文也可與《考工記》的相關記載相印證,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戰國題銘制度的認識。
關鍵詞:車器 讎 檢校
2014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陽閆家寨發掘了一批戰國秦遺址,發現了幾座秦高等級貴族墓葬及其附屬車馬坑,其中出土了一件銀車器,器上有銘文曰“乙一巳盩十一兩一朱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陜西咸陽閆家寨戰國秦遺址、墓葬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8年第4期,第38、39頁。)與此器同出的另一件形制相同的車器上有銘文“乙二”,可見此器中的“乙一”當是其編號,秦代車器上多見此類編號。(參看王輝、王偉編著: 《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312、313頁。)銘文中的“朱”應讀為“銖”,是重量單位,表明此器重十一兩一銖半。銘文的前一部分是編號,后一部分是器物的重量,這兩部分內容在出土的戰國秦漢銅器中多見,比較難懂的是“巳盩”二字。我們認為,“巳盩”應讀為“已讎”。
“已”本由“巳”字所分化,(吳振武: 《關于新見垣上官鼎銘文的釋讀》,《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6期,第7頁。)在戰國文字中,“已”常常寫作“巳”,(參看朱力偉: 《兩周古文字通假用字習慣時代性初探》,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13年,第183頁;白于藍編著: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61頁。)在這里“巳”宜讀為“已”。“盩”是端母幽部字,“讎”是禪母幽部字,兩字韻部相同,聲母相隔雖有一定距離,但是古音中章系和端系關系密切,(陳劍: 《釋“琮”及相關諸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 線裝書局,2007年,第286頁;李家浩: 《“越王者旨於睗”新考》,《歷史語言學研究》第7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41—144頁。)比如“舟”是章母字,從之得聲的“侜”“辀”則是端母字,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如“冬”(端母)和“終”(章母)、“周”(章母)和“調”“稠”(定母)、“壽”(禪母)和“幬”(定母)等。
古書和出土文獻中禪母字和端母、定母字均有相通的例子。比如《尚書·微子》“用乂讎歛”,陸德明《經典釋文》言“讎”或作“稠”;(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濟南: 齊魯書社,1989年,第780頁。)《尚書·召誥》“敢以王之讎民”,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曰“讎與稠聲相近”。(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 《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第400頁。)再比如,戰國地名“雕陰”在貨幣文字中寫作“壽陰”,(何琳儀: 《古幣文編校釋》,《古幣叢考》,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45頁。)“雕”是端母幽部字,“壽”是禪母幽部字; ?內簋中的“盩”,張政烺先生讀為“調”。(張政烺: 《周厲王胡簋釋文》,《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12年,第250頁。)可見,“讎”與同韻的定母字“稠”可以相通,“盩”與定母幽部的“調”亦可相通,所以“盩”“讎”音近相通,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讎,在古書中有校對、校讎之義,如《韓非子·有度》曰:“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所謂“主讎法”,即是由君主校定法律之可否。這種定期校正法律的工作,在戰國秦代被寫進官方的法律條文中,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尉雜》記載國家規定司法官“歲讎辟律于御史”,(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09頁。)即每年都要到御史處核對法律條文。類似的記載亦見于里耶秦簡。(陳偉主編: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104頁,簡64、8173。)《后漢書·陳寵列傳》:“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于《甫刑》者除之。”鉤校律令的工作與“讎法”大概是類似的,可見“讎”與“校”義近。古書之中亦有“讎校”一詞。(見《后漢書》卷一〇《和熹鄧皇后紀》、卷七八《蔡倫列傳》。)
秦代的官方文書中,也常用“讎”來表示核對義。比如,《秦律十八種·倉律》曰:“都官以計時讎食者籍。”(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42頁。)所謂“讎食者籍”,就是核對口糧領取者的名籍。又比如,里耶秦簡中記載,郡縣在劃定邊界后,要將本轄區的地理情況繪成地圖,然后送交御史,由其“案讎更并,定為輿地圖”,(陳偉主編: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第118頁。)郡縣上呈的地圖要經御史案讎核對后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
我們再來看一則漢簡中的材料: 六月壬申,守張掖居延都尉曠、丞崇告司馬、千人官謂: 官縣寫移書到,如大將軍莫(幕)府書律令。掾陽、守屬恭、書佐豐已讎。
(《居延新簡》E.P.F22∶7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 《居延新簡: 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82頁。)
所謂“已讎”,即表示已經根據律令核校過文書。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一些算題的末尾也有“已讎”,(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7、139頁。)表示該題已經過專人校對。
以上所舉文獻中所見的“讎”,均為檢核、校對之義,車器銘文中的“讎”,大抵也是此義。
在戰國秦代,國家對手工業生產有著嚴格的法律規定,《秦律十八種·工律》曰:“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長、廣亦必等。”(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69頁。)法律規定制作同一種器物,其形制必須相同,想來器物的重量也應該是要基本相同的。當時的手工業生產,存在著一定的行業標準。(出土戰國陶文中有“市豆”“市區”“市釜”,劉釗先生指出,加蓋了這些璽印的量器,應是當時市場中流通的標準器。董珊先生也認為當時存在經過官府認證的法定標準器。李剛先生根據對三晉量器和衡器的研究,推測當時應有一個校量的機構,且存在著一套標準器。參看劉釗: 《齊“於陵市和節”陶文考》,《管子學刊》1994年第4期,第80頁;董珊: 《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6頁;李剛: 《三晉系記容記重銅器銘文集釋》,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5年,第138頁。《禮記·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此中的“度”“數”“量”大概就可看作是當時手工業生產的行業標準,秦代有關法律中還記載有“程”,即是法定的產品制作規格。有關論述亦可參看陸德富: 《戰國時代官私手工業的經營形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06—208頁。)銘文中的“已讎”,即表示該器在制成后或入庫收藏前,其形制、重量已經過校讎,符合規定的標準。(銀雀山漢簡《庫法》云:“諸庫器善否美惡及穀(角)試……器成必試乃藏。”《管子·幼官》也說:“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角試”即是檢測和考校,器物在鑄造完成后,要經過檢測,檢核無誤后方可入庫收藏。)
在戰國和漢代的一些記容銅器銘文中,記有有關校核、校量類的內容,茲舉幾例如下: 1. 滎陽上官皿: 縈(滎)陽上官,皿。十年九月,府嗇夫成加、史狄GF8A9(角)之,少(小)一益(溢)六分益(溢)。(李學勤: 《滎陽上官皿和安邑下官鍾》,《文物》2003年第10期,第77—81頁。)
2. 安邑下官鍾: 安邑下官,重(鍾)。十年九月,府嗇夫成加、史狄GF8A9(角)之,大大半斗一益(溢)少(小)半益(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5091頁,9707號。以下簡稱“《集成》”。)
3. 垣上官鼎: 垣上官。胾(載)四分GF8AA。三年,巳(已)GF8A9(角),大十六臾(斞)。(吳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卷,第245頁,2068號。以下簡稱“《銘圖》”。)
4. 右內GF8AB壺: 四斗,以(已)客(格)(“以”字舊多隸定為“GF9A9”,讀為“司”,吳振武先生撰文指出,此字與“司”有別,應是“以”字,銘文“以客”應讀為“已格”,表示已經經過校量。所言當是。參看吳振武: 《古文字考釋與人工智能》,《光明日報》2020年11月7日。),四寽(鋝)十一冢(重)□。右內GF8AB。七。(《集成》9648。)
5. 平都量: 元年十月甲午,平都戌,丞糾,倉亥,佐葵犁斛(角)(平都量的形制、容量與漢代一般的斛都不太相同,再考慮作為量器名的“斛”的出現年代,一些學者懷疑銘文中的“斛”并不是該器器名。熊長云先生根據其容量和銘文格式,認為銘文中的“斛”應讀為“角”,表示校正義,并結合秦簡的相關記載,認為銘文所記的是一次校正量器的記錄。李零先生似亦有類似看法。參看熊長云: 《秦漢度量衡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17年,第59—62頁;李零: 《波斯筆記》,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上冊,第234頁。)。容三升少半升,重二斤十五兩。平都。(云希正: 《西漢平都犁斛》,《文物》1977年第3期,第59頁。)
對照來看,“已讎”與“已角”“已格”處在相同的語法位置上,將其理解為性質與之類似的銘文,應是合適的,用“讎”來表示校準、校對義,或許是秦代的一種用字習慣。
從例1—3的銘文中還能看到,三晉記容銅器銘文中,在校量詞之后常有“大……”或“小……”的有關內容,李學勤先生曾指出,銘文“大”和“小”的含義是增大和缺少,表示校量時發現的實測容量與應有容量之間的差異。(李學勤: 《滎陽上官皿和安邑下官鍾》,《文物》2003年第10期,第80頁。)可見,當時的容器都有一個標準值,(李學勤: 《滎陽上官皿和安邑下官鍾》,《文物》2003年第10期,第80頁。)校量的過程其實也是將實測容量與預設標準核對的過程。秦代記容銅器銘文中,在容量詞或重量詞前后有時會有一個“正”字,(如三十四年工師文罍、三十六年私官鼎、少工喜銀釦,分見《銘圖》13824、《集成》2658、《銘圖》19641。)在銘文中表示準確義,(吳鎮烽: 《工師文罍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 《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5—98頁。)大概是表示該器的容量或重量正好符合預設的標準。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車器銘文“讎”所表示的核對義與校量過程所體現出來的潛在含義是相吻合的,都是將實際數值與標準數值進行核對比較。
《考工記》中記載,古代車的車輪在制作完成后,要接受六道工序的檢測,其中包括“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鄭玄注:“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唐代學者賈公彥進一步解釋說:“兩輪有畸輕畸重,則馬引之輕者而重者難;又以輪貫其軸,其公重心不在軸之正中,則車行必不正: 此皆不可不侔之義。”(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 《周禮正義》,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第3176—3178頁。)車的兩輪必須要保持相同的重量,否則車的重心就會偏離,就行不正。
可見,為了保證車輛的正常行駛,車輪在制作完成后,要經過稱量,確保兩輪保持相同的重量,車兩側的其他車器,應該也需要保持大致相同的重量,制成后也需要經過類似的檢測工序。本文所討論的車器,大概也在檢測范圍之內,銘文“已讎”或許就包含了這一層意思。
學者指出,戰國時期隨著秦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和對外戰爭的擴大,國內的手工業生產逐漸形成嚴密的生產體系,有著嚴格的制作工序和統一的生產標準,車輛的零部件常要求使用標準化的通用件以確保其良好的性能,并且在制作工序上有著前后繼承關系,上一道工序中制作的不合格者不能交給下一道工序,從而追求產品在器形、質量和性能上達到統一。(王學理: 《秦代軍工生產標準化的初步考察》,《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5期,第57—67頁。)所以,車器在制成后需要經過檢測,以確保其符合相應的標準,這是可以理解的。
綜上而言,這件車器銘文應讀作“乙一。巳(已)盩(讎),十一兩一朱(銖)半”。
值得一提的是,閆家寨這件車器的出現,對我們認識和研究戰國時期的題銘制度以及手工業生產或許有著特殊的意義。以往校量類銘文多出現在戰國記容銅器中,車器銘文的出現,提示我們在一些特殊的銅器生產完成后,可能也需要對其進行校準,檢查是否符合標準。當然,這件銀車器所體現的可能僅僅是秦國的制度,不過若將其與戰國記容銅器相聯系,它們所反映出來的校量程序,大概是值得注意的。同時,已有戰國秦系題銘中似乎還是首次看到有關檢校制度的內容,這也正是這件車器銘文的價值所在。
(責任編輯: 徐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