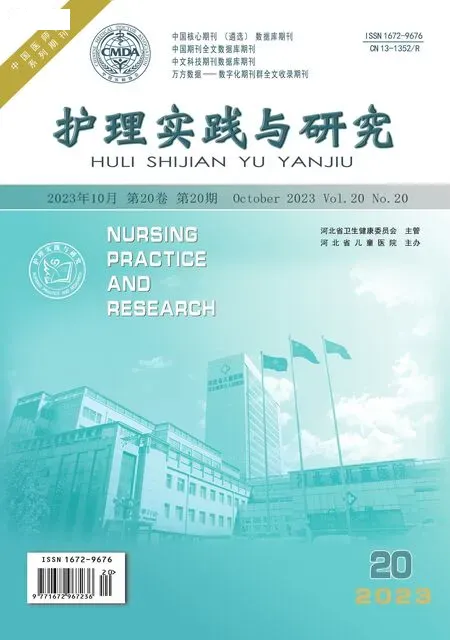認知行為干預對頭頸癌放療患者的影響
梁曉一 楊滿紅 鄭玉玲
頭頸癌(head and neck cancer,HNC)指解剖范圍在顱底至鎖骨之間的各類腫瘤[1],是全球第六大高發腫瘤[2]。頭頸癌發生部位與吞咽進食功能密切相關,在腫瘤治療過程中會引起患者吞咽困難、疼痛等不良反應,引發患者進食量減少、厭食等不良攝食行為[3],持續不健康的攝食行為,會導致患者營養不良。調查統計顯示,接受放射治療或同步放化療的HNC 患者營養不良發生率高達80%~88%[4]。現臨床中多采取口服營養補充、腸外營養等營養干預手段[5]為HNC 患者補充營養,對異常攝食行為的干預較少見。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是運用行為激活、認知重建等方法,針對患者情緒和行為實施的治療措施[6],是進食障礙指南首選的行為干預方式[7]。動機性訪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MI)是促進行為改變的談話技術,通過增強患者的意愿和信心促進其產生自發的行為改變,適用于行為改變意向矛盾的情景[8]。相關研究[9-10]將認知行為療法聯合動機性訪談應用于HNC 放射治療患者,改變了患者攝食行為,獲得較好的療效。我科室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適應國內患者情況的調整,針對我國頭頸癌患者放射治療期間進食障礙的問題,制定了涵蓋動機性訪談的認知行為干預護理措施,探討對HNC 放射治療患者營養和情緒的影響。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0 年12 月—2021 年12 月在我院行放射治療的HNC 患者。納入條件:年齡18~60 歲;病理確診為頭頸部惡性腫瘤;放射治療最低劑量為60 Gy;患者認知正常。排除條件:患有精神類疾病或服用精神類藥物;有言語及聽力障礙,智力與情感障礙,認知功能障礙;存在腦部器質性疾病;有心、肝、腎衰竭;剔除條件:治療過程中出現嚴重并發癥或病情加重而放棄治療者;因個人原因自行退出者。本研究最終共納入76 例患者,按照組間資料均衡可比的原則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38例。其中對照組年齡24~59 歲,觀察組年齡22~60歲;對照組放射治療總劑量為60~76 Gy,平均劑量69.39±2.41 Gy,觀察組放射治療總劑量為60~72 Gy,平均劑量68.84±3.82 Gy,均為調強放射治療,每天1 次,5 次/周;兩組間上述指標及其他基線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他資料比較見表1。本研究項目通過所在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倫理批號:醫研倫審2019 第004 號)。患者自愿參加研究且書面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護理方法
1.2.1 對照組 采取放射治療科常規護理,包括病情觀察、用藥護理、飲食護理、生活護理、健康教育、功能鍛煉指導、康復指導、心理護理等。
1.2.2 觀察組 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增加認知行為干預護理措施。干預方法具體如下:共進行5 次面對面訪談,每次30~60 min。前3 次訪談實施認知行為干預,于放射治療前20 次內完成。患者放射治療20 次后開始出現較明顯的放射治療毒副作用如口腔黏膜炎,行同期化療患者可伴有惡心、嘔吐、食欲缺乏等影響進食的不良反應;放射治療25 次后患者因嚴重放化療不良反應如疼痛等出現明顯進食行為障礙。放射治療20 次后實施2 次動機性訪談,2 次訪談間隔1 周。每次訪談提前與患者預約時間,以患者方便為宜。訪談地點選取患者熟悉的病房或談話室。每次訪談后詳細記錄訪談內容。具體干預方案見表2。

表2 頭頸部腫瘤放射治療患者認知行為干預具體實施方案
1.3 評價指標
分別于干預前(首次放射治療前)以及5 次干預后(全部放射治療后)收集以下指標。
(1)血液學指標:采用血清白蛋白(Serum albumin,ALB)、血清總蛋白(serum total protein,TP)水平。血清白蛋白是肝臟合成的球蛋白,是臨床經典的營養狀況指標。血清總蛋白參與多種蛋白質生理免疫功能,也是常用的營養指標。
(2)焦慮情況:采用廣泛性焦慮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11]進行評估,該量表有7 個條目,對兩周內出現焦慮的情緒和癥狀的頻率進行評分,采用0~3 分的4 級評分法,總分≥5 分為輕度焦慮;≥10 分為中度焦慮;≥15分為重度焦慮。
(3)抑郁情況,采用抑郁癥篩查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naire-9,PHQ-9)[12]評估抑郁情緒,該量表有9 個條目,分別對出現抑郁癥狀、抑郁心境及自殺自殘意念等的頻率進行評分,0~3 分的4級評分法,總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0~4 分為無抑郁;5~9 分為輕度抑郁;10~14 分為中度抑郁;15~19 分為中重度抑郁;20~27 分為重度抑郁。
1.4 數據分析方法
2 名研究員將數據及時錄入Excel 文檔,由第3名研究人員進行核查。采用SPSS 24.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方差齊的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百分率描述,組間率的比較進行χ2檢驗;等級資料比較采用秩和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質量控制
資料收集由經過培訓的課題組成員專人負責。量表評估時使用一致性的語言向患者解釋清楚,避免患者漏填錯填。患者填寫完畢后由研究者當場核對,發現漏填或填寫不清時囑患者及時補充。實施干預的研究者均接受統一專業的培訓并通過考核。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血液學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干預前血清白蛋白和血清總蛋白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觀察組患者血清白蛋白和總蛋白高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放射治療前后兩組患者血液學指標比較(g/L)
2.2 兩組患者焦慮、抑郁水平比較
干預后觀察組患者焦慮、抑郁程度輕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放射治療后兩組患者焦慮抑郁水平比較(分)
3 討論
3.1 認知行為干預有助于改善HNC 放射治療患者營養狀況
由于腫瘤發生部位與進食嚴密相關,頭頸癌患者營養不良狀況是所有癌癥患者中最嚴重的[13]。既往研究[14]發現,95%的頭頸癌患者在放療結束時營養狀況惡化。本研究中,兩組患者的營養狀況在放射治療干預結束時低于干預前,體現了下降的趨勢,這與以往研究[15-16]相符,主要由于放射線對口腔內黏膜和腺體的損害,導致患者出現黏膜水腫、潰瘍、疼痛以及唾液黏稠等癥狀,進而影響患者的攝食行為。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后觀察組患者的血清白蛋白、血清總蛋白高于對照組,表明認知行為干預有助于改善HNC 放射治療患者的營養狀況,這與國外學者[9]研究結果一致。①Ho 等[17]研究也顯示,個性化的飲食結構對放化療期間HNC患者的體質量變化有積極影響。本研究通過記錄飲食日記,患者了解到自身飲食結構的缺陷,針對性調節飲食結構,有利于營養元素均衡攝入[18]。②認知行為干預還可幫助患者修正錯誤與不切實際的信念、假設,使其采取更實際的想法和行為。通過對HNC 放射治療患者治療期間飲食觀念和攝食行為的干預,使患者接受“飲食即治療”的觀念以及健康飲食的概念,使患者積極參與腫瘤治療和營養干預,了解自身營養狀況變化,并學會根據自身狀態調整攝食行為如調整食物種類、口味、烹飪方式、質地等以保證營養成分的吸收。③動機性訪談是挖掘和增強患者行為改變動機的面談技術。隨著放射治療的進行,毒副作用愈加明顯,患者的攝食行為會因疼痛、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產生變化,此時患者的攝食行為與其生存欲望產生明顯沖突。本研究中聚焦于患者不良攝食行為與生存欲望的矛盾心理,引導患者對不良攝食行為的思考,通過動機性訪談使患者察覺該沖突,并進一步溝通了解患者對腫瘤治療的預期,分析患者不良攝食行為的原因,針對口腔黏膜損傷、唾液粘稠等不良反應,與患者共同制訂改變飲食結構、膳食質地和進食時間的目標和計劃,在認知行為干預發掘其良性思維方式與行為改變的基礎上,激發患者行為改變的動機,引導其對抗自身不良攝食行為,向積極正向行為改變[19],從而實現患者攝食行為的改變。
3.2 認知行為干預可降低HNC 放射治療患者不良情緒水平
癌癥患者在確診腫瘤及腫瘤治療過程中會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郁情緒。頭頸癌患者由于腫瘤自身或手術治療等原因,顏面部會有外觀畸形、瘢痕以及生理功能異常等負面變化,其消極的情緒狀態是所有癌癥人群中報告最高的[20-22]。本研究中未干預前兩組患者均有一定程度的焦慮和抑郁等負性情緒,這與既往研究[20,23]相似。HNC 患者放射治療期間和治療后受到吞咽功能變化、疼痛等的影響,整個疾病軌跡中都有明顯的抑郁和焦慮癥狀,一項研究[24]顯示HNC 患者在放射治療完成后抑郁水平最高。本研究中放射治療后兩組患者的焦慮抑郁評分存在上升的趨勢,與Ghazali 等[25]研究相符。Richardson 等[21]對21 項包括認知行為療法、心理教育、正念、團體治療和遠程醫療在內的心理干預進行系統評價后發現,由護士主導的CBT 干預可以改善患者的焦慮和抑郁情況。本研究中,干預后觀察組患者焦慮、抑郁輕于對照組,表明認知行為干預可降低HNC 放射治療患者不良情緒水平。究其原因為:①認知行為干預可修正患者對癌癥的錯誤認知以及災難化的思想,重建正確認知,緩解或消除患者對癌癥和治療的負性情緒。以情緒“ABC”理論為基礎,引導患者在面對應激事件時,積極正面地看待與評價,糾正不良心理狀態。②漸進式肌肉松弛法、呼吸訓練和冥想放松法等針對病情的放松訓練可以幫助患者對抗放化療毒副作用帶來的疼痛、惡心、嘔吐等不適癥狀,積極應對治療副作用[26-28]。③動機性訪談是以患者為中心,引導其探索矛盾心態的心理干預方法[29-32]。認知行為干預和動機性訪談相結合,當患者動機獲取成功激發后可持續應用認知行為干預,當患者出現阻抗行為和矛盾心理時及時采用動機性訪談,兩種模式相互促進,幫助患者調整心態,增加治療信心。
綜上所述,認知行為干預在頭頸部腫瘤放射治療患者中具有應用可行性,能有效改善HNC 放射治療患者營養狀況,降低HNC 放射治療患者的焦慮、抑郁水平。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如未長期隨訪,單中心研究,今后將聯合其他醫院開展大規模、多中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