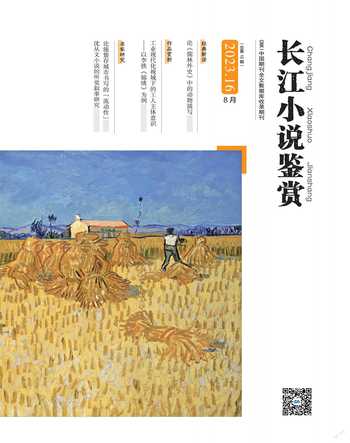從家庭系統理論視域研究《無聲告白》中 莉迪亞的悲劇成因
[摘? 要] 《無聲告白》是美國華裔作家伍綺詩的代表作。故事講述了在美國20世紀50至70年代的社會背景下,亞裔和白人結合的跨種族婚姻中的家庭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家庭悲劇。本文借助心理學領域的家庭系統理論,利用自我分化、三角關系、情緒阻斷等理論,從社會和家庭這兩個角度解析《無聲告白》中大女兒莉迪亞走向死亡結局的悲劇成因。
[關鍵詞] 《無聲告白》? 家庭系統理論? 自我分化? 悲劇成因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6-0033-04
《無聲告白》的出版在美國引起一波熱議,作品的主題書寫既反映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跨種族家庭尷尬的社會處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矛盾,也折射出普通家庭中父母期望與子女獨立成長之間的矛盾沖突。在美國20世紀30至50年代種族歧視、反異族通婚盛行和女性主義運動落入低潮的時代背景下,擁有華裔身份的詹姆斯不得不面臨亞裔在美國社會的隔離處境,瑪麗琳則面臨著性別歧視語境里白人女性的個人追求與女性回歸家庭的社會主流之間的對立,跨種族家庭的結合也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社會壓力。系統思想是家庭心理學研究和實踐的基本立場和出發點,家庭心理學將個體視為整個家庭的一部分,個體的任何問題都能追溯到家庭關系的問題,同時,家庭作為社會的子系統,家庭問題自然也關聯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因此,本文基于鮑文的家庭系統理論,聯系當時的社會環境,解析詹姆斯跨種族家庭內部成員自我分化不完全、夫妻子系統的矛盾沖突、三角關系等問題是如何一步一步導致莉迪亞的死亡悲劇。
一、特殊時代背景下華裔與白人不同的價值追求
小說《無聲告白》的故事背景是20世紀50至70年代的美國社會,但詹姆斯和瑪麗琳的問題則必須追溯到他們出身成長的年代,也就是30至50年代,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是反異族通婚以及陷入低潮的女性運動。從1882年到1943年,美國排華政策持續了六十一年,嚴苛的排華法案最終導致華人為了安全不得不長期居住在唐人街,他們很難融入美國社會;在就業上也受到各種限制,最終集中在餐館、洗衣、雜貨等行業;華工也不準攜妻子進入美國,導致男女比例失衡,滋生嫖妓、賭博等惡習[1]。作為30年代出生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后裔,詹姆斯·李在一種排斥和孤立的社會氛圍中長大成人,為了躲開排華政策,他們拼命融入周圍的環境,整日生存在一種擔驚受怕的狀態里。1938年,8歲的詹姆斯隨父母到美國東部艾奧瓦州,進入勞埃德學院讀書,并在此度過他的青少年階段。盡管在此度過了整個童年,但詹姆斯從來不認為勞埃德學院是他的家。作為勞埃德學院唯一出身工薪階層的亞裔學生,詹姆斯無法融入上流階層的白人學生群體,雖然他為此做了各種努力:放棄使用漢語、謝絕父母接送、了解美國主流文化。這種長期壓抑孤立的生活環境,使詹姆斯對獲得白人的接納認可、融入主流社會群體具有強烈的執念。他因為種族身份不得不成為白人社會中醒目的存在,從而飽嘗排斥冷遇,這是他內心痛苦的根源,潛藏在表象之下的是渴望合群的心靈。
和詹姆斯相反,作為白人女性的瑪麗琳在社會中面臨的是性別歧視、公私領域和某些就業崗位按照性別刻板劃分的問題。二戰結束之后,女性運動迎來前所未有的低潮,女性回歸家庭相夫教子再次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在這樣一種主流思想的控制下,社會中公私領域的性別歸屬重新劃分成女性屬于家庭、廚房之類的私領域,而男性則占據醫院、學校、律所之類的公領域;在就業方面,女性被劃分到無足輕重或者輔助類的工作崗位,例如,醫院中的醫生職位由男性主導,護士職位則屬于女性。在瑪麗琳的成長經歷中,性別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無所不在。例如,高中時候,學校不允許她用手工課代替自己母親的家政課;上大學時,只有她選擇了化學實驗課程,這期間,她遭遇老師的質疑勸阻、男同學的輕視挑逗;結婚多年后鼓起勇氣打電話求職,卻被告知她應該專注照顧丈夫和孩子。瑪麗琳的聰慧、勇氣和野心使她在女性被集體壓抑的環境中脫穎而出,她渴望實現個人的自我價值,而不是被束縛在家庭中僅僅做一個“幸福”的家庭主婦。這也是她在生活的偶然安排下意識到自己正重復母親的命運時做出離家出走、重新學醫、拒絕下廚做飯、專注于督促莉迪亞學習等一系列決定的內在動因。
總之,詹姆斯作為一個華裔與當時的美國社會格格不入,瑪麗琳作為一個具有強烈事業心的女性同樣在那個性別歧視嚴重的年代舉步維艱。不同的是,詹姆斯其實是渴望融入白人群體的,長期地被隔絕在社會主流群體之外帶給他更多的是挫敗感、孤獨感和自我懷疑;瑪麗琳則希望做與眾不同的人,打破社會的偏見和制約,追求個人價值。兩者在一種錯位的期待中結合,詹姆斯認為瑪麗琳普通且漂亮,完美地融入人群,正是他期待的自我的樣子;瑪麗琳則看到詹姆斯與眾不同的一面,獨特且富有異域魅力,同一般的白人男性不一樣,她試圖通過與詹姆斯的結合反抗平庸。
二、低水平自我分化的家庭系統
詹姆斯一家的家庭成員有:詹姆斯(父)、瑪麗琳(母)、內斯(大兒子)、莉迪亞(二女兒)、漢娜(小女兒)。這個家庭系統又可根據代際關系劃分為夫妻子系統、兄妹子系統;根據期待和滿足期待的關系可劃分為詹姆斯-莉迪亞-瑪麗琳子系統、局外人內斯-漢娜子系統;作為經歷過母親離家出走創傷性事件的當事人,內斯和莉迪亞之間也單獨形成一個子系統。詹姆斯一家的家庭結構經歷過一次變動,在瑪麗琳離家出走之前,他們的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瑪麗琳盡職盡責地照顧孩子和詹姆斯的日常生活,詹姆斯則努力升職加薪,父母子系統與兄妹子系統合作運行維持家庭穩定。瑪麗琳重新回歸家庭后,家庭結構則發生轉變:莉迪亞介入夫妻子系統中,形成三角關系,成為維系家庭安定的核心;內斯和漢娜則形成邊緣性子系統,成為家庭中被忽視的成員;同時內斯和莉迪亞之間還形成共同分擔家庭創傷的子系統。改變后的家庭結構選擇回避創傷事件,家庭結構失衡,孩子被迫成為替罪羊,從而導致家庭成員間的關系過度融合或過度疏離,不能進行充分的自我分化。
鮑文認為家庭內部存在尋求歸屬和尋求個人化兩股力量,家庭成員之間為獲得距離感和整體感同時進行著推拉作用。自我分化具有三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個體自身情緒和思維的分離;第二,個體與家庭成員在情緒上的分離;第三,自我成熟程度[2]。參照這三個指標,在夫妻子系統中,詹姆斯由于亞裔的出身經歷導致個人價值感低、渴求認同,過度追求融入集體,反映在家庭中就是致力于營造一個類白人中產階級家庭結構,忽略妻子的個人價值追求,希望妻子做主流文化宣傳中幸福的家庭主婦;排斥與自己性格經歷類似的兒子內斯,忽視遺傳自己種族特征的小女兒漢娜;過度關注大女兒莉迪亞的社交,喜愛莉迪亞面容里遺傳的白人種族特征。瑪麗琳則剛好相反。20世紀60年代,美國女性運動第二次復蘇,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女性打破性別偏見擔任重要的社會職位。瑪麗琳在50年代還面臨著女性不能擔任醫生的窘境,到60、70年代,女醫生已經成為醫院稀松平常的一部分。丈夫的不理解,一直在價值觀念上形成對抗的母親的去世,以及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重復母親命運的恐懼,促使瑪麗琳決心擺脫家庭的束縛,追求個人理想,但第三次懷孕粉碎了瑪麗琳的逐夢之旅。回歸家庭的瑪麗琳在大女兒莉迪亞的身上發現實現自我的另一種方式——讓同自己十分相像的女兒莉迪亞努力成長為女醫生,代替自己追求夢想。從此,瑪麗琳和莉迪亞之間形成非常緊密的情感依賴關系,莉迪亞不得不背負不屬于自己的人生重任,朝母親期待的目標奮進。詹姆斯和瑪麗琳的這種情況都屬于不能正確處理社會造成的個人心理創傷,將焦慮傳遞給子女,使子女成為個人情緒的承載者,但這種過度關注只會導致子女自我分化過低,無法獨立思考和行動,并產生逃離家庭的負面想法。
在兄妹子系統中,莉迪亞、內斯和漢娜由于父母的偏愛或者忽視處于時而分裂時而合作的狀態。莉迪亞是與家庭融合最為緊密的孩子。莉迪亞年幼時遭遇母親離家出走、被母親拋棄的創傷性事件,這導致莉迪亞非常害怕母親拋棄她,出于對母親的愛和挽留,莉迪亞從此對瑪麗琳言聽計從,滿足她的一切期待。莉迪亞自發成了緩沖家庭矛盾、維護家庭穩定的鐵錨,她一方面滿足父親詹姆斯融入集體的期待,裝作社交達人,緩沖父親不被主流群體接納的挫敗感;一方面全盤接受母親瑪麗琳的學習安排:做算術、看科學讀物、上大學生物課、考出優秀的成績,代替母親實現理想,補償母親被迫放棄自己人生的遺憾。家庭投射過程是指分化不良的父母將低分化水平傳遞到最容易受影響的孩子身上[2]。詹姆斯和瑪麗琳同時將自己人生受挫的痛苦轉移到莉迪亞身上,希望通過她彌補自身的缺憾。害怕被拋棄的情感經歷使莉迪亞愿意做任何事情取悅父母,在這種長期的期待和滿足期待的單向性關系中,莉迪亞漸漸失去自我,無法正常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趨向和思想觀念,在虛假的理想女兒形象背后是莉迪亞疲憊壓抑的真實自我,她平庸普通,不會社交,不討人喜愛也不聰明,這個真實的莉迪亞在父母期待的眼神中越藏越深,只有淹沒在湖水中那一刻她才感覺到釋放和輕松,因為她不必再掩藏和偽裝自己。
與此相反,內斯和漢娜則面臨父母的忽略。漢娜總是作為局外人活動在家庭的邊緣,甚至會成為被忘記的存在。因此漢娜極度渴望父母的愛和關注,她的內心世界極為敏感細膩,總能敏銳地觀察到家庭成員的情緒問題。作為一個小孩子,漢娜天然地學會做家庭中的隱形人,不會表達自己的情感需求,默默接受父母的忽略。內斯內心的掙扎是無法得到父親的認同和母親的關注。作為一個亞裔小孩,他的成長經歷跟自己的父親如出一轍,這也導致父親詹姆斯將自己的挫敗情緒投射到內斯身上,父子之間的關系斷裂,出現溝通問題。同時,母親瑪麗琳則過度關注自己作為女性被家庭拖累,失去實現自我的機會,因此將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同為女性的莉迪亞身上,希望她代替自己圓夢。內斯轉而投入知識世界,封閉自我,一心渴求考上大學、脫離原生家庭。內斯的這種行為也就是鮑文家庭系統理論中的情緒阻斷,即從與原生家庭未解決的情緒聯系中逃離。這種方法雖然避免了家庭情感聯系中焦慮的一面,但同時也回避了家庭矛盾,剩余的兄弟姐妹則不得不承擔更多的焦慮情緒。莉迪亞和內斯正是這樣的關系,他們在父母失衡的情感表達中結成同盟,內斯幫助莉迪亞分擔壓力和焦慮情緒。因為內斯即將上大學,他們的長期同盟關系岌岌可危,莉迪亞在這種關系解體的危機感下焦慮指數直線上升,甚至做出藏匿錄取通知書、撕毀邀請函的舉動。
自我分化是鮑文家庭系統理論的核心概念,是指個體思維和情緒功能的分離,兩者差異越大,個體就越能不被卷入所處家庭的情緒反應之中,從而使個體不易產生功能失調[2]。在詹姆斯一家中,詹姆斯、瑪麗琳在成長過程中遭遇過情感挫折,并不自覺將焦慮傳遞給下一代。莉迪亞、內斯和漢娜在失衡的家庭結構中各自歸屬于中心或邊緣的位置,同時面臨著父母極度關注或極度忽略的情感問題:莉迪亞在與父母情感過度融合的處境下導致個人自我分化過低,習慣于迎合期待,壓抑真實的自我表達,活在窒息的家庭空間里;內斯逃避自己的情緒問題,通過讀書上大學脫離原生家庭;漢娜則習慣于做家庭中的隱形人,壓抑自己的情感需求。
三、情感三角關系
鮑文認為,在家庭中,當一個兩人的子系統遇到壓力時,會將第三人拉入系統以降低情感強度和焦慮并獲得穩定。三角關系是一個最小的、穩定的關系系統,是家庭情緒或關系系統的基石[2]。詹姆斯和瑪麗琳一直沒有就離家出走事件做一個溝通交流,雙方都不約而同回避掉這個問題。詹姆斯是由于內心的膽怯自卑,在他和瑪麗琳結合的年代,跨種族婚姻在一些州還是被法律禁止的事情,華裔在美國社會的處境可想而知。詹姆斯害怕瑪麗琳后悔和他結婚,后悔陷入被白人群體孤立的狀態才拋棄他和他的孩子們。瑪麗琳則在社會和家庭的雙重規訓下處于失語的狀態,現有的話語無法正確地表達她的內心欲求,她的丈夫孩子不是阻礙,他們是愛的所在,但她的人生價值也不能滿足于做一個家庭主婦,她有更大的野心抱負。于是,夫妻倆不約而同將矛盾的焦點轉移到莉迪亞身上,父母的雙重期待——做一個受歡迎的華裔小孩和一個不被家庭和丈夫所束縛的優秀女性——投射到莉迪亞身上,幼小的莉迪亞犧牲自己、被動地承擔維系家庭和諧的責任。由于對母親過度依戀,莉迪亞一直沒有機會做主自己的人生,在自由的選擇和獨立中長大成人,已經是高中生的莉迪亞身上還依舊散發著寶寶護理霜的香味兒。尤其在內斯即將上大學的情況下,莉迪亞的焦慮反應更為顯著,她撒謊,應付學習,和男孩約會,學習抽煙,甚至想提前體驗性關系,這些反常行為都是為了減輕心理壓力,博取內斯的注意,因為莉迪亞害怕一個人承擔父母所有的期待和焦慮,卻沒有人在身邊支撐。莉迪亞學習駕車的出發點就在于此:“她也不會孤零零地困在父母身邊;她可以在自己選定的時間逃離。只是想到這些,她的腿就激動得打戰,仿佛迫不及待想要逃跑。”[3]
三角關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兩人關系的緊張,分散了家庭焦慮,但實際上家庭矛盾并沒有得到解決,只是延遲了。在這種畸形的三角關系下,莉迪亞成為唯一受寵的孩子,內斯和漢娜成為被忽視的孩子,無論是過度關注還是情感疏遠,三個孩子實則都在這種家庭關系模式中受到父母的情感傷害。
莉迪亞死后,詹姆斯一家分崩離析。在瑪麗琳和詹姆斯追逐真相的過程中,家庭內部關于種族歧視的敏感問題漸漸浮出水面,兩人在一次次爭吵對立中試探對方的真實想法,白人和亞裔的不同社會處境使亞裔作為弱勢群體無法得到應有的權利保護并被主流群體排擠冷落:“詹姆斯曾經天真地認為——與瑪麗琳的母親和其他人的想法不同——瑪麗琳對不同人種一視同仁。現在,瑪麗琳嘴里說出來的話——如果她是個白人女孩——證實了詹姆斯一直以來的恐懼:內心深處,她還是會給所有事物貼上標簽。白種人和非白種人,正是這些標簽讓世界面目全非。”[3]由于再也沒有莉迪亞作為緩沖劑,詹姆斯在失去女兒和誤解妻子的情況下和自己的亞裔學生路易莎出軌以麻木自己受挫的情感體驗。夫妻-孩子三角關系在莉迪亞死后演變成夫妻-情人三角關系。在詹姆斯和瑪麗琳的情感沖突里雙方總是采取拉入第三者的方式緩沖矛盾,兩個人不是逃避溝通就是在互相誤解中矛盾更深。在瑪麗琳識破丈夫的出軌之后,兩個人終于在平靜和釋然中一起交流他們做過的那些錯誤的事情:比如說對莉迪亞的過度期望,對內斯的失望不滿,對漢娜的忽略,他們直面家庭中的那些傷痕,互相慰藉。
四、結語
作者伍綺詩在小說《無聲告白》里運用了一種獨特的敘事手法:在兩種不同的時間流速下,一面描述莉迪亞死后給詹姆斯一家人帶來的種種震動,一面爬梳往事,通過過去的事件追溯莉迪亞死亡的原因。歷史給個人刻下的傷痕不會消失,它隱入家庭,將這種悲傷擴散到每一個人的身上。詹姆斯和瑪麗琳都是這種歷史傷痕的攜帶者,前者在種族主義的語境中渴望融合,后者在性別歧視的背景下追求獨特,兩者都遭遇挫敗,都在對自己人生無解的情況下將所有的期待和希望強加到莉迪亞身上,而莉迪亞最終則在這種背負無盡期待的處境中不堪重負。
參考文獻
[1] 萬曉宏.美國對華移民政策研究(1848-2001年)[D].暨南大學,2002.
[2] 張秀琴.家庭心理學思想的理論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2008.
[3] 伍綺詩.無聲告白[M].孫璐,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5.
[4] 張卓.美國華裔文學中的社會性別身份建構[D].蘇州大學,2006.
[5] 李潤潤,張慧榮.《無聲告白》中莉迪亞悲劇原因探析[J].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6,39(7).
[6] 吳冬麗.拷問“模范少數族裔”:家庭系統理論視角下的《無聲告白》[J].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8(4).
[7] 黃虛峰.美國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下的異族通婚[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5).
[8] 顧悅.超越精神分析:家庭系統心理學與文學批評[J].南京社會科學,2014(10).
[9] 范令一.試評述鮑文家庭系統理論[J].才智,2016(14).
(特約編輯 張? 帆)
作者簡介:劉明儀,西南民族大學,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