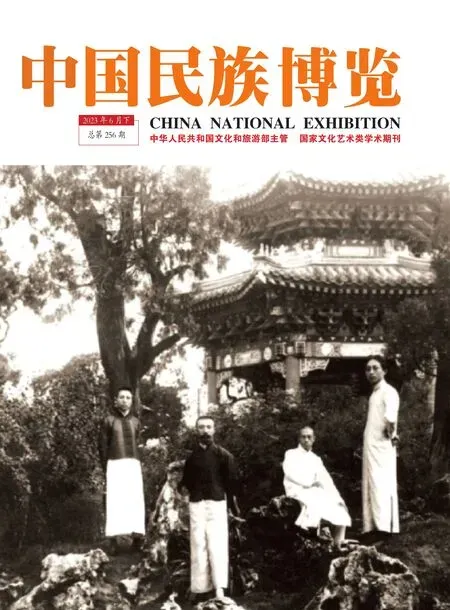藝術審美視域下國家級非遺“得榮學羌”的舞蹈動作語匯
——基于網絡民族志的田野調查
何洋托美次仁 楊麗萍
(1.成都大學中國—東盟藝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0081;2.成都市龍泉驛區新果泥藝術培訓學校,四川 成都 610100)
引言
“得榮學羌”是藏民族一種自娛性的民間歌舞表演形式,發源于得榮縣的瓦卡鎮(原子庚鄉),最初流傳地僅限于瓦卡鎮境內,目前保持活態傳承的有瓦卡、子實、八子斯熱、阿稱、吳擁共、子庚六個村落。[1]2008年6 月14 日,“得榮學羌”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序號:Ⅲ—66。[2]
本文從藝術審美的視域對非遺傳統舞蹈項目“得榮學羌”的舞蹈動作語匯進行觀察。藝術審美是人類審美活動的一種高級、特殊的形態,是以藝術作品作為對象,去感受與領悟客觀事物本身所蘊含、表達的美學境界。通過網絡民族志的方法,筆者與傳承人建立虛擬社區,使用微信進行語音的深度訪談、發放在線問卷和收集圖片、視頻,借助抖音等自媒體進行舞蹈動作觀察和解讀,了解其歷史起源、特色動作和寓意內涵。針對保護非遺舞蹈急需調研記錄的動作語匯,文中著重調研了“得榮學羌”外在展示出的“下肢動作”“上身及手部動作”和動作內在蘊含的“寓意”。
一、“得榮學羌”歷史起源與傳承現狀的田野調查
“得榮學羌”是地處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得榮縣廣為流傳的一種藏族自娛性的民間歌舞表演形式。關于“得榮學羌”的歷史起源大致有以下三種說法:唐代文成公主進藏時途經瓦卡,得榮大土司子庚阿吾為迎接公主駕到,特意召集當地民間藝人,創編能讓文成公主看懂又有地方特色的歌舞,最終產生了融漢族、藏族、納西族、白族等民族歌舞風格為一體的“學羌”舞;部分學者們認為,明代晚期納西族曾管理中甸、巴塘、理塘一帶,得榮因舊屬巴塘管轄,所以跳“學羌”舞時的服飾、唱調、舞姿等與這些地區特別相近;最具依憑的觀點是“學羌”由藏族傳說人物江根阿坡創作,他綜合了康巴三江沿岸的鍋莊與踢踏的舞步,又融入了滇西北少數民族的一些舞蹈元素。結合江根阿坡創作的歷史傳說,從歷史上看,得榮瓦卡(茶馬古道金沙江碼頭)曾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座重鎮,各民族的馬幫和商人曾集聚在此。或許,人們常常在這里載歌載舞,久而久之在碰撞和交流中慢慢融合出了一個新的舞蹈:“學羌”。[3]
歷史傳承中,得榮學羌主要是以口傳心授的形式流傳。雖沒有歌本與文字記錄,但因表演形式活潑且互動性強,舞蹈語匯豐富且易學易懂,民俗文化內涵豐富且多姿多彩,深受當地民眾喜愛,并廣為流傳至今。同時,由于得榮地處四川省西南隅的川滇交界的高海拔地區,交通閉塞、對外交流較少等地理、歷史傳統因素,也是促成其保留完整和傳承至今的外部客觀因素。正如傳承人在微信語音中口述道:“以前沒有手機、沒有電腦,外出交通也不方便,跳這個舞蹈就是大家覺得最好耍的事情,所以大家當時都喜歡跳,都愿意學”。但是,隨著當代交通的便利、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網絡信息化普及,年輕人多外出打工,“得榮學羌”原有的傳統傳承方式受到了挑戰與破壞,特別是隨著當下手機、自媒體的大眾普及,年輕一代得榮人的審美需求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國際信息的交流發生了轉變,傳統古老的非遺舞蹈的保護與傳承正在面臨消失的危機。所幸,當地有關部門加大對非遺項目的保護力度,探索非遺在當代保護和傳承的新途徑。“我17 歲就跟隨我的老師也就是現在的國家級傳承人格瑪次仁學習跳舞,他多次帶領我們的演出隊奔赴康定、得榮縣參加演出并獲獎。我現在也免費給學生孩子們教跳舞。我們縣還成立了一支以“學羌隊”為主,規模60 人的文化藝術協會,會員年齡在20—50 歲之間”,傳承人單珍洛布對當地的傳承現狀介紹道。
但是,保護和傳承非遺傳統舞蹈項目,調查和記錄其舞蹈的外在動作、內在文化內涵,是保護和傳承的關鍵所在,也是促進其教學和傳承的基礎。鑒于該非遺項目動作語匯記錄的缺少,本文從藝術審美的視角解析了該舞蹈外部呈現的下體、上身和手部的特色動作,賞析了舞蹈動作所蘊含的內在寓意,從而揭示“得榮學羌”的藝術美學價值與民俗文化功能,為當前的非遺保護與傳承提供藝術審美視角的理解。
二、“得榮學羌”舞蹈動作語匯的田野調查
欲解析舞蹈蘊含的藝術美,先需了解該舞蹈外在的動作構成及特色所在。[4]提起“得榮學羌”,傳承人在微信語音中對該舞蹈的動作做了以下的詳細敘述。
“‘得榮學羌’以得榮鍋莊舞步為基本舞步,舞步融匯了得榮的‘九步鍋莊’‘弦子’‘踢踏舞’,形成獨特的‘學羌舞’動作,舞蹈動作剛勁有力、古樸大方,動作特點在于腳下踏、跺的和諧組合。具體的跳法分為下肢的舞蹈步伐、上身的動作和手上的動作”。
(一)下肢的舞蹈步伐
“跨步悠腿,是左腳向前跨步時右腳自然地向前抬起約25 度悠腿,右腳悠腿后落于原位時左腳隨著重心向后移動,自然抬起左腳前悠腿約25 度(女性左腳點地)。身體處于放松狀態,節奏較緩慢且平穩。
原地換腳踏步,是右腳、左腳依次踏步十下,隨后右腳旁踏兩下。重拍在右腳,膝蓋放松,保持顫膝。
前踢步,即為右腳做原地踏步時左腳直膝快速向前踢步,依次快速交替。主力腿膝部松弛帶有顫膝,腳下踢踏有力,節奏輕快保持勻速。
踏步吸腿跳動作,是左腳踏步時右腳小幅度吸腿,隨后左腳小步蹭跳一次,第二次換右腳先踏步左腳吸腿,隨后右腳小步蹭跳一次,依次交替,踏步有力,吸撩時膝部力度柔和,節奏短促有力。
俯身踏步行徑,即為右腳向前踏步時左腳自然屈膝后勾腿,左腳落腳后右腳快速前抬腿邁步,該動作用于圍圓行徑,右腳向前踏步時身體前傾,行徑時雙膝松弛且有韌性。
側身行徑跺踏步,是右腳向前踏步時左腳緊跟踏步,形成靠腿步伐后左腳兩次踏腳的同時右腳兩次跺腳,三步一停,跺踏腳結合,雙膝頓顫,跺踏剛勁有力,踏點清晰,節奏均勻”。
(二)上身及手部特色動作
“曲臂甩袖。雙手位于胸前小臂交替向上甩袖,右手曲臂向上甩袖時左手向前斜下位放下,依次交替,上身處于沉肩放松狀態,甩袖有力,節奏平穩。
齊眉晃手。雙手下垂,動作時屈腕、屈肘,以腕帶動,兩手于胸前交替晃手,右手順時針劃圓,左手逆時針劃圓。[5]
晃蓋手。一手晃,另一手曲臂立腕,用手心抹,經過上弧線由旁及里。
俯身甩袖。動作時,上身向右旁俯身,左手背手,右手向左斜下方甩袖,重拍向內。
橫向甩袖。動作時右手由大臂帶動小臂,由右旁橫劃手到左肩胸前,再用力向右旁甩袖,左手動作與右手動作相同,從左至右,再向左甩袖,依次左右交替進行”。
三、“得榮學羌”舞蹈動作語匯的寓意審美
“得榮學羌”作為一種民俗性舞蹈,傳承方式與民眾的民俗活動是緊密相連的。在得榮方言中,“學”有勾兌、結交、配對的意思,“羌”是“跳”的意思,因此“得榮學羌”舞蹈的起源最早意為:男女交往中跳的“情舞”。[6]該舞蹈無論其唱詞、韻調、舞步都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其中蘊涵著得榮人民代代相傳的優秀傳統文化、價值取向,具有獨特的美學意境,也是人類學、歷史學、民俗學、舞蹈學等方面研究的重要資料。從藝術審美的視角來看,該舞蹈的外部動作是構成該項非遺藝術審美呈現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屬性。“動作美”是根據舞蹈動作的呈現來展示的,而舞蹈動作呈現的“表現性”功能,是具有描繪人的情感、展現人的思想、刻畫人的性格等作用。[7]通過傳承人的口述發現,“得榮學羌”舞蹈的動作中具有的“同手同腳”“跺踏結合”的外部特色形態,以及“因情而動”的內在動機構建,這三點的構成因素是動作背后“得榮學羌”的內涵寓意所在。
(一)“同手同腳”的和諧美
“得榮學羌”舞蹈中手腳相結合的動作都以“同手同腳”的肢體形態進行展示的。每當右腳吸撩腿時,右手做齊眉晃手,右腳向下跺踏時,右手向下做蓋手。手部動作需配合腳下步伐的起伏,做上下擺動,四肢線條流暢且舒展,呈現出大方、灑脫的動作美感,體現出了得榮人民對舞蹈動作外在審美的展示。“我們得榮人認為,跳舞的時候上肢與相對應的下肢同時做同方向的運動,有著‘相連’的意思,寓意吉祥、和睦”。傳承人的介紹,讓我們更清晰的了解到了,通過肢體“相連”的外在肢體展示,其核心是詮釋出對“吉祥、和睦”的寓意。這種重統一、重和諧的思維方式的本體論認為,在矛盾的同一性和個性中,同一性更為根本,而對立與差異乃是包含在統一與和諧之中的,兩(對立)乃一(統一)的內容,一乃兩之本。[8]統一的和諧之美是中華美學的特性,“得榮學羌”舞蹈中“同手同腳”的和諧、外化美和內在美的統一,正是中華美學的一種印證。
(二)“跺踏結合”的流暢美
“得榮學羌”舞步融合了藏族踢踏舞中的碎踏、顫踏、顫撩腿等步法,表演者進行“跺”“踏”“撩”動作時,施加不同程度的強弱對比力度,使“跺”與“踏”動靜結合。“下步要有力,踏腳要清脆,腳下的跺踏動作要給人行云流水的流暢感”,傳承人介紹道,“當舞者俯身而變化了節奏的強弱感后,這一動作則又顯得柔韌、灑脫,為舞蹈增添了一絲流暢美,給人舒適、難忘的審美體驗”。舞蹈的流暢是一種美,更是舞蹈藝術美的呈現基礎。[9]舞蹈的表演首先就要“流利、通暢”,讓觀眾在一氣呵成中感受舞蹈藝術帶來的暢快之感,方才有美的體驗。“得榮學羌”舞步在跺踏時,膝蓋動律連綿不絕,極富柔韌性和彈性,顫動和屈伸有時小而快、有時沉而慢,身體重心配合跺踏,被動且松弛的運動,身體形態總體呈現出松弛感,體現了藏族舞蹈特有的流暢美。
(三)“因情而動”的內涵美
舞蹈起源說中有性愛起源說一種,該起源說專門解釋到舞蹈是因男女為表達情感和求偶的需要,而進行的肢體展示與肢體接觸。[10]同樣,在傳承人的介紹中也說到了男女之間的情感交流是“得榮學羌”舞蹈最原始、最具代表性的主題。“‘得榮學羌’同手同腳的動作代表著男女情感生活的聯系,舞姿時而激情、時而柔美,描繪著男女間美好情愫,展現著人們對愛情的渴望與憧憬。表演時,隊形有時是男女各一排面對面,有時是拉手圍圈,一人領唱后,男女間自行填詞一問一答,反復對唱,以此方式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互表心中愛意”,傳承人解釋道。在得榮,“學羌”意為“一起跳”的意思,不僅節日里可以欣賞到優美的藏族歌舞表演,在平時的廣場上、草原上、人群聚集的地方也可以看到群眾自發的跳舞、唱歌的場面,且不受場地、人數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加入到舞蹈的隊伍中盡情唱跳。因為高原的地熱資源豐富,白天時男女大都各自分散泡溫泉,搞野炊活動,同伴之間討論唱詞、探討音律、切磋舞步、敘述友情。傍晚開始就在溫泉邊點燃篝火,青年男女載歌載舞,唱詞隨興而起,曲調時抑時揚,歌舞表演情真意切,男女之間抒發著彼此愛慕之情,此起彼長,高潮迭起,充分展示出“得榮學羌”舞蹈“因情而動”的特色之美。
四、結語
從藝術審美的視域觀察,“得榮學羌”的舞蹈動作語匯有著“和諧美”“流暢美”“內涵美”等特色的體現,分別通過“同手同腳”“跺踏結合”的外在動作和“因情而動”的內在動機得以展示。舞蹈動作是內心情感的外化和延展,而內心情感則是舞蹈動作創作和表演的起因與動力。正如傳承人解釋道:“男女之間為了表達愛情而聚在一起跳舞,跳舞要跳的好看才能吸引對方,這就是當時得榮本地的男女青年為什么喜歡跳‘得榮學羌’的原因”。美本身只是無限的感性形象,[11]但是對美的追求則是人類永恒的精神向往。舞蹈藝術通過身體動作的表達形式,讓人們可以抒發出其他藝術形式所難以表達的人的最深層次的內心情感,印證了“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得榮學羌”正是在男女表達愛意的語言交流的基礎上,進行了現場即興對唱的敘述,又在其詠唱的基礎上借用舞蹈肢體語匯充分的傳遞思想情感,并伴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豐富了該舞蹈的動作、賦予了每個動作的寓意、傳承了舞蹈的歷史文化內涵,最終形成了當地獨具特色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舞蹈項目。
“得榮學羌”非遺傳統舞蹈無論其動作、隊形、唱詞、曲調、服飾都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并蘊涵著當地世代相傳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和審美意趣,具有其獨特的美學研究價值。本文通過藝術審美的視角,觀察并賞析了該舞蹈的外部動作與內在寓意,并運用網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與傳承人建立了虛擬社區,對該舞蹈的動作與內涵進行了田野調查。但是,真正的保護和傳承非遺,還需要全面的調研和記錄該非遺的包括前期準備、心理活動、演跳過程、曲調唱詞、服飾道具等完整的藝術行為及心理活動過程。未來的計劃中,將對該非遺的演跳隊形、曲調唱詞及服飾道具等進行田野調查,以期完善和豐富國家級非遺“得榮學羌”的調查記錄體系和理論研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