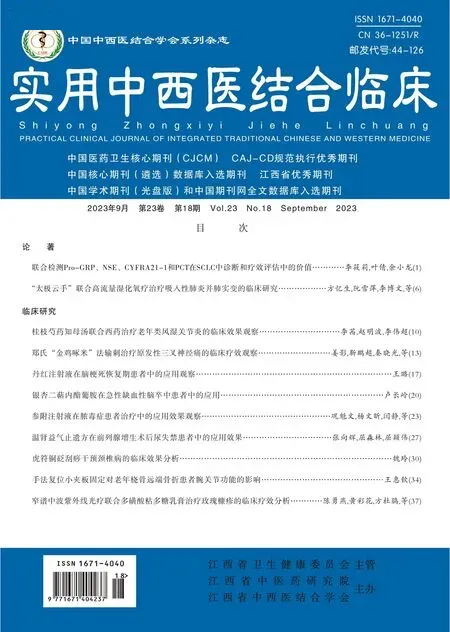桂枝芍藥知母湯聯合西藥治療老年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效果觀察
李茜 趙明波 李偉超
(廣東省臺山市中醫院內六科 臺山 529200)
類風濕關節炎(RA)是一種炎癥性、慢性、系統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老年人免疫能力下降,是該病的高發群體[1]。該病表現為關節疼痛,并逐步發展為功能障礙、關節畸形,病情呈慢性進行性持續加重,是老年致殘的重要原因[2]。西醫治療該病主要采用抗風濕藥物、激素類藥物、非甾體類抗炎鎮痛藥物等治療,甲氨蝶呤是治療RA 的常用藥物,可有效減輕患者關節癥狀,但無法抑制RA 進展,且存在不良反應等問題[3]。近年來,中醫藥在該病治療中的療效得到肯定,與西藥可形成互補。中醫學將RA 歸屬于“痹癥、歷節風”等范疇,認為該病是由寒邪、濕邪、風邪所致,臨床實踐發現該病以寒熱錯雜證較為常見[4]。《金匱要略·中風歷節篇》中記載的桂枝芍藥知母湯是寒熱錯雜證的常用方劑。本研究探討在西藥治療老年RA 患者基礎上聯合應用桂枝芍藥知母湯的臨床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2020 年1 月至2022 年12 月醫院收治的老年RA 患者98 例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49 例。對照組男25 例,女24例;年齡61~80 歲,平均(70.25±3.97)歲;體質量指數18.6~29.7 kg/m2,平均(23.42±1.25)kg/m2;關節功能障礙分級:Ⅰ級14 例,Ⅱ級29 例,Ⅲ級6 例;病程1~6 年,平均(3.23±0.50)年。觀察組男27 例,女22 例;年齡61~79 歲,平均(69.97±4.01)歲;體質量指數18.5~29.3 kg/m2,平均(23.37±1.26)kg/m2;關節功能障礙分級:Ⅰ級13 例,Ⅱ級30 例,Ⅲ級6 例;病程1~6 年,平均(3.18±0.47)年。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西醫診斷標準參照《2015 年美國風濕病學會類風濕關節炎的治療指南》制定[5]:關節壓痛≥6 個;關節腫脹≥6 個;血沉>28 mm/h;晨僵持續時間>45 min。中醫診斷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6]:辨證為寒熱錯雜,證見關節腫痛,局部灼熱,肢冷畏風寒;關節冷痛,筋脈拘急,煩躁,口干苦(主癥);關節紅腫熱痛,局部畏寒,得暖則舒;肌肉關節冷痛拘急,潮熱、盜汗,麻木不仁。關節疼痛,自覺局部發熱,觸之不熱,或自覺局部怕冷,但觸之發熱;皮膚紅斑,四肢不溫;發熱,口干,肢體困重,喜熱飲或不欲飲(次癥)。舌紅苔白,脈弦數或弦緊(舌脈象)。
1.3 入組標準 納入標準: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年齡>60 歲;臨床資料完整;符合上述中西醫診斷標準。排除標準:合并關節先天畸形、殘疾及關節其他病變者;合并嚴重骨質疏松者;對本研究所使用藥物過敏者;有認知障礙、無法溝通者;嚴重精神障礙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結核病等;長期服用糖皮質激素者;合并心、肝、腎等嚴重功能不全者。
1.4 治療方法 對照組口服甲氨蝶呤片(國藥準字H22022674)治療,10 mg/次,1 次/周。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桂枝芍藥知母湯治療,組方:知母、麻黃、防風、桂枝各12 g,炮附子10 g,白術、生姜各15 g,白芍9 g,甘草6 g。炮附子先煎30 min,之后加水1 200 ml 煮沸后再用文火煎煮30~40 min,取湯液300 ml,分早晚2 次溫服,1 劑/d。兩組均連續治療12 周。
1.5 觀察指標 (1)臨床療效。參照《類風濕性關節炎中醫臨床診療》[7]評估,類風濕因子(RF)、血沉(ESR)等實驗室指標接近正常值,癥狀及體征積分減少≥70%為顯效;RF、ESR 等實驗室指標均有所改善,癥狀及體征積分減少>35%且<70%為有效;未達上述標準為無效。(2)癥狀體征。于治療前、治療12 周后對患者關節疼痛指數、關節腫脹數、關節壓痛數及晨僵時間進行評估,其中關節疼痛指數按照正常、輕度、中度、重度分別計0 分、1 分、2 分、3 分。(3)實驗室指標。抽取患者治療前、治療12 周后空腹靜脈血,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RF、ESR、C 反應蛋白(CRP)水平。(4)生活質量。治療前、治療12 周后采用斯坦福大學關節病健康評價量表(HAQ)評估,包含洗漱、進食、行走、站立、抓握、伸手取物、穿衣和修飾、活動等8 項日常活動,每項按照無困難、稍有困難、很困難、無法完成分別計0 分、1 分、2 分、3 分。(5)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如肝功能損害、白細胞下降、惡心嘔吐等。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臨床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例(%)]
2.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體征情況比較 治療后觀察組關節疼痛指數評分、關節腫脹數、關節壓痛數低于對照組,晨僵時間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體征情況比較()

表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體征情況比較()
?
2.3 兩組治療前后實驗室指標比較 兩組治療前實驗室指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RF、ESR、CRP 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實驗室指標比較()

表3 兩組治療前后實驗室指標比較()
?
2.4 兩組治療前后HAQ 評分比較 治療后觀察組HAQ 各項評分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治療前后HAQ 評分比較(分,)

表4 兩組治療前后HAQ 評分比較(分,)
?
2.5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 對照組出現惡心嘔吐2 例,肝功能損害1 例,不良反應發生率為6.12%(3/49);觀察組出現惡心嘔吐3 例,肝功能損害、白細胞下降各1 例,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0.20%(5/49)。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36,P=0.461)。
3 討論
中醫學認為RA 的病因是因老年人氣血虧虛,正氣虛弱,臟腑功能失調,復感風寒濕邪,致使肌肉筋骨關節產生痹癥,瘀血內生,血行不暢,形成寒熱錯雜之證[8]。寒熱錯雜證與其他證型不同,病理變化過程中寒凝、熱毒的病理反應明顯矛盾,畏寒肢冷與關節局部灼熱存在反差[9~10]。風寒濕邪侵襲可導致血循環處于收縮狀態,引起微循環障礙,加重炎癥反應。基于寒熱錯雜這一紛亂錯雜的反應,平衡寒熱是關鍵。
桂枝芍藥知母湯中知母性寒,具有潤燥生津、清熱解毒之效;麻黃性辛、溫,具有利水解表之效;防風性微溫,具有祛濕止痛、解表祛風之效;桂枝性辛、溫,具有溫通心陽、發汗解表之效;炮附子性熱,具有散寒止痛、補火助陽之效;白術性溫,具有利水消腫、健脾燥濕之效;生姜性微溫,具有解表散寒之效;白芍性微寒,具有調經止痛養血之效;甘草調和諸藥。桂枝芍藥知母湯中溫陽散寒、平調寒熱、清熱解毒合用,寒熱并調,溫熱之藥可驅邪外出,寒涼之藥可養血制熱,剛柔并濟,邪出而不傷正,可祛除頑固的經絡血脈之痹[11~12]。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對照組比,觀察組臨床總有效率較高,治療后晨僵時間較短,關節疼痛指數評分、關節腫脹數、關節壓痛數、HAQ 各項評分較低,說明老年RA 患者應用桂枝芍藥知母湯聯合西藥治療效果較佳,可改善患者臨床癥狀,提升其生活質量。吳鳳嘉[13]研究顯示,寒熱錯雜型RA 患者應用桂枝芍藥知母湯聯合西藥治療效果顯著,可明顯改善患者體征及實驗室指標。惠婷等[14]研究顯示,RA 患者應用加味桂枝芍藥知母湯加西藥治療可保護關節功能,降低關節腫痛程度。相關藥理學研究顯示,桂枝可擴張皮膚下汗腺及周圍微毛細血管,改善關節周圍微循環;白芍具有明顯的抗炎作用,對急慢性及免疫性炎癥反應均具有較好的抑制作用;炮附子可直接作用于中樞阿片受體而發揮鎮痛作用,并能夠改善微循環,減輕炎癥反應;知母能夠減輕關節腔內慢性炎癥反應[15~17]。RF 是目前臨床診斷RA 的主要指標之一,可反映RA 病情及骨侵蝕程度;ESR 也是診斷RA 的重要指標之一,可反映關節疼痛程度;CRP 是當前臨床上常用的炎癥標志物,當機體處于應激狀態時其水平顯著升高,RA 患者存在關節炎性病變,故CRP 水平呈高水平表達[18~20]。觀察組治療后RF、ESR、CRP 水平較低,提示老年RA 患者應用桂枝芍藥知母湯聯合西藥治療可有效改善RF、ESR、CRP 水平。與西藥甲氨蝶呤的治療效果形成互補,能更好地改善臨床癥狀,且從安全性角度分析,聯合用藥并不會增加不良反應,安全性好,利于患者預后。
綜上所述,在西藥甲氨蝶呤治療老年RA 的基礎上聯合桂枝芍藥知母湯可提升療效,改善患者臨床癥狀及實驗室指標,提升患者生活質量,且安全性好,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