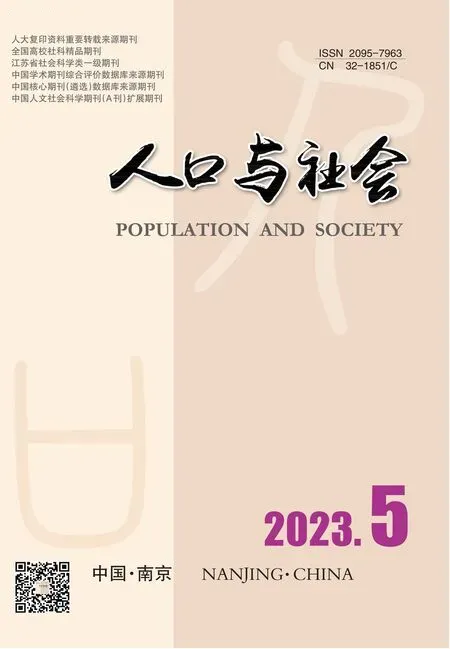城市老年人網絡沉迷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周建芳,公 茗
1.南京郵電大學 人口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42;2.江蘇高質量發展綜合評估研究基地,江蘇 南京 210042;3.南京郵電大學 社會與人口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一、問題的提出
2021年11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印發《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要求促進全民共建共享數字化發展成果,彌合數字鴻溝。社會更加重視“數字鴻溝”問題,社區與老年大學開設了老年人群數字教育等一系列課程并提供相關服務,全社會采取多種手段通過數字技術提高老年人群的生活質量,讓更多老年人觸網,以“數字化”促進健康“老齡化”,讓老年人共享數字社會的發展成果。根據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年12月,互聯網普及率達75.6%,60歲及以上網民占比由2021年6月的12.2%提升至14.3%[1],老年網民成為互聯網時代不可忽視的用戶群體,相關政策的實施效果漸顯。然而,隨著老年群體觸網的比例加大,老年人的網絡粘性也在不斷增加。《2020老年人互聯網生活報告》指出,超過10萬老年人日均在線超10小時,60歲及以上老年用戶日均上網時長超1小時,平均一天之內登錄5次APP,登錄頻率高于其他年齡段用戶,部分老年人每天除了基本生活之外的時間都消耗在移動互聯網上[2]。那么,網絡粘性不斷增加的老年群體是否會出現網絡沉迷現象?又有哪些因素影響著老年群體網絡沉迷的發生呢?
二、文獻回顧
既有關于網絡沉迷的研究主要包括定義與測量、現狀及影響因素和應對舉措三方面。
從網絡沉迷概念的界定來看,匹茲堡大學Kimberly Young博士發展完善了伊萬·戈登伯格提出的網絡沉迷概念。對于網絡沉迷的測量,國內外大多數研究量表依據Young的診斷標準改編而來,這些量表和問卷作為區分網絡沉迷和非沉迷的重要工具,對網絡沉迷的評定和診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國臺灣學者陳淑惠根據國外已有的工具,修訂和編制了適合中國人群的測查量表——中文網絡沉迷量表(CIAS);崔麗娟等參照Young和戈登伯格的標準,編制了包括12個項目的測查量表[3];白羽、樊富珉等以大學生為樣本,對陳淑惠的量表進行修訂,建構了包括19個題目的4級自評量表[4]。
在網絡沉迷的現狀及影響因素方面,既有研究大多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截至2018年9月,全球過度依賴網絡的青少年人數占比6%,而我國則接近10%,高出4個百分點[5]。陳天麗等人研究發現大學生網絡成癮率為18.03%[6]。影響因素可以分為個體、家庭、社會等方面。其中個體特征分為生理、心理和行為選擇等方面。在心理因素方面,滕雄程等人通過研究發現個體焦慮與網絡沉迷顯著正相關[7]。還有學者認為,網絡沉迷主要源自青少年主動的個體行為選擇,他們往往被網絡限制了眼界,認知機制受到影響,從而主動選擇沉迷于其中[8]。從家庭特征來看,青少年網絡沉迷的主要原因離不開家庭。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網絡沉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不良的家庭環境是青少年網絡沉迷的主要影響因素[9]。從人際交往和社會支持方面來看,有學者認為缺乏社會支持是導致青少年網絡沉迷的主要外部原因[10]。另外,網絡自身所具有的更新快、互動強、個性化的特點以及時間無限制、空間無邊界、道德幾乎無約束的環境對年輕人具有極強的誘惑力[11]。
網絡沉迷的應對舉措也主要針對青少年人群。從應對主體看,建議從青少年自身和家庭介入進行預防。從青少年自身入手,可以采取思想調控、行為干預、心理介入、沉迷轉化等多種方法介入防治[12],有研究證明了采用認知干預防治青少年網絡沉迷的有效性[13]。另有學者認為,重塑家庭規則和改善溝通方式是解決青少年網絡沉迷問題的主要辦法之一,應促進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交流[14]。還有部分學者認為,青少年網絡沉迷問題的治理需要政府、社會、學校、家庭、青少年個體等多方共同努力[15]。從應對時效來看,網絡沉迷的治理不可能一勞永逸,需要持續不斷地修正和反饋[16]。從應對手段看,在技術層面上,建議針對不同類別、不同級別的網絡信息,設定不同等級的訪問權限,尤其要盡量避免青少年接觸網絡色情、暴力等信息[17],在分級制度中應當讓青少年增強對負面內容的免疫力[18]。同時,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應加大執法力度,擴大懲處范圍[19]。
學界關于老年群體網絡沉迷的研究較少,僅個別研究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老年人沉迷網絡的發生機制和干預措施[20]。孫瑜晨對北京地區329名老年人進行調研發現,老年網絡沉迷者的比例不容輕視[21]。杜鵬認為老年人自身的特點以及家庭、企業和社會支持不足共同造成了老年網絡沉迷這一現象[22]。還有少數研究關注到老年人過度使用網絡的不利影響[23]。可以看出,既有對老年群體網絡沉迷的研究尚未形成體系,且缺少專題的實證研究,使得社會對老年群體可能存在的網絡沉迷及其影響因素缺乏了解。因此,本研究將洛陽市的城市觸網老人作為研究對象,對老年人網絡沉迷程度進行測量,并分析個體、家庭、社會因素對老年人網絡沉迷的影響,以期為促進老年人科學用網、提高數字素養提供參考。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作者團隊在2023年開展的“城市老年群體網絡使用現狀”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在河南省洛陽市內定居的、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使用網絡的老年群體。調查以作者所在社區的觸網老年人為種子,采用滾雪球抽樣方法產生樣本,被調查老年人覆蓋全市。2023年1月在河南省洛陽市進行了預調查,正式調查于同年3月底完成,最終回收有效問卷共計302份。問卷調查主要采取自填、送發問卷、調查員上門訪問被調查對象后代填的方式。問卷內容是研究者參考既有研究自我設計的,包括被調查老人個人信息、家庭基本信息、網絡使用情況、網絡沉迷情況、網絡使用的影響5個方面。
(二)變量設置
1.因變量
由于目前國內尚沒有專門針對老年群體網絡沉迷的量表可參考,研究團隊結合老年人群體的特點,借鑒Kimberly Young博士于1998年提出的網絡沉迷測查量表,對臺灣陳淑惠教授本土化的中文網絡沉迷量表(CIAS)進行改良,并在預調查的基礎上設計本研究的老年人網絡沉迷測查量表。網絡沉迷量表共有26個條目,包括戒斷癥狀(如若被迫離開網絡,個體就會坐立不安、情緒低落)、耐受癥狀(如隨著使用者網絡使用經驗的增加,必須通過增加網絡使用時間才能在網絡中獲得與原來相當程度的滿足感)、強迫癥狀(如個體有無法自拔的上網沖動)、時間管理問題(如個體因為在網絡中沉迷時間太長而耽誤吃飯、睡眠等)和人際與健康問題(如個體因為在網絡中沉迷時間太長而與身邊人疏遠或造成身體不適)5個維度。量表采用李克特自評式4點量表記分方法(極符合4分、符合3分、不符合2分、極不符合1分)。各維度的總分為所含條目之和,取值范圍分別為5~20分、4~16分、5~20分、5~20分、7~28分。量表總得分則是5個維度得分之和,取值范圍為26~104分,得分越高,表示網絡沉迷程度越深[24]。各條目的傾向性比率為“極符合”和“符合”兩項的占比累加。由于因變量分布為非正態分布,因此本研究在具體分析老年人網絡沉迷的影響因素時,參照并沿用以往研究的劃分標準,采用66分作為分界點,將網絡沉迷發生風險定義為一個二分類變量,得分大于66分為網絡沉迷,小于等于66分為正常,即可認為受訪者目前沒有沉迷網絡[25]。分析顯示,本次樣本中,網絡沉迷測量的26個指標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數為0.972,說明內部一致性較好,有較高的測量信度。
2.自變量
關于青少年的網絡沉迷問題,網絡具有的負面特性、家庭溝通缺乏、學校有關網絡教育的不足以及青少年個體認知與心理需求的缺失,是人們最常歸因的幾個方面[26]。個體因素中除了個人基本特征,心理健康情況與對網絡的認知與態度也是重要的變量;家庭因素包括家庭對學生上網的教育與引導、家庭溝通與交流等;社會因素涉及政府對網絡環境管制的政策措施、校園活動參與、校園環境等[27]。而在研究老年人網絡沉迷問題時,雖然主體不同,但同樣離不開當下社會環境、家庭以及老年人個體作用的影響,有學者倡導分析老年人網絡沉迷的影響因素應從“個體—家庭—社會”出發并結合老年群體的特點[22]。綜上,參考以往研究框架及變量選取,針對老年群體及其所處社會階段的特點,研究從個體、家庭、社會3個層面考慮老年人網絡沉迷的影響因素。在個體特征層面,將受教育程度、所患慢病數量、心理健康、網絡利弊認知、在業情況、收入情況作為自變量。其中,以抑郁情況來考察心理健康,借鑒中國家庭追蹤調查選用的抑郁量表(CES-D)中的5個指標來計算心理健康得分,按頻率將相應的4級選項調整后重新編碼賦值,這5個指標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數為0.856,說明內部一致性較好,可進行加總求和。總分在0~15分之間,得分6分及以下為正常,6~9分為輕度抑郁,9分以上為重度抑郁,要尋求專業心理輔導[28]。在家庭特征層面,將代際溝通頻率、家庭約束等指標納入自變量。在社會特征層面,將社會交往頻率、社會活動參與項數等作為自變量。
四、研究結果
(一)被調查老人基本情況
被調查老年人中男性有149人,占比49.34%;女性有153人,占比50.66%。60~69歲的老年人占比最大(78.81%),其次是70~79歲的老年人(17.88%),80歲及以上老年人僅占3.31%。個體特征方面,有42.39%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為高中/職高/中專及以上,90.07%的被調查老年人有配偶。沒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占1.99%,超過2/3的老年人患1種慢性病,26.49%的老年人至少患有2種慢性病。心理健康狀況良好的老年人占80.13%,19.87%的老年人有抑郁癥狀,其中7.62%的老年人需要尋求專業心理輔導。另外,半數以上老年人認為上網利大于弊。有31.13%的老年人在業,其中,處于全職工作狀態和部分時段兼職的在業老年人比例相等。每月個人收入在1000~3000元之間的老年人占42.05%,個人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老年人占33.11%。家庭特征方面,有2個子女和有3個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占比較大,分別為46.36%和43.71%,有9.27%的老年人獨居。代際溝通頻率每周至少1次的被調查者占88.08%。來自家庭的約束根據頻率由低到高分別是從不、偶爾、有時、經常。社會特征方面,社會交往頻率每周至少1次的被調查者占81.46%。參與過1項線下活動的老年人占34.77%,參與過4項及以上的老年人占11.59%。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被調查老年人基本情況
(二)老年人網絡沉迷現狀
被調查者網絡沉迷總得分為70.74±14.54分。得分高于66分,出現網絡沉迷的有175人(57.95%),戒斷癥狀、耐受癥狀、強迫癥狀、時間管理問題、人際與健康問題5個維度的條目均分分別為3.07±0.63分、2.67±0.60分、2.75±0.59分、2.85±0.57分和2.67±0.60分,說明被調查老人戒斷癥狀維度上的沉迷狀況最為嚴重。表2各項具體表現中,出現癥狀的傾向性比率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因上網而眼花/腰酸/背痛,或有其它身體不適”(50.66%)、“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會兒,但常常一待就待很久”(49.01%)、“上網的時間越來越長”(48.68%)。而得分較低的,也即傾向性最弱的兩項為“曾不只一次因為上網而睡不到4小時”“習慣減少睡眠時間,以便能有更多時間上網”,都屬于時間管理問題。

表2 被調查老人網絡沉迷各條目選擇比例及傾向性比率 %
(三)不同特征老年人的網絡沉迷比較
研究運用卡方檢驗將不同個體、家庭和社會特征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狀況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特征老年人的網絡沉迷差異分布
個人特征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的網絡沉迷狀況有所不同,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的比重相對較高(χ2=4.681,P=0.031)。患有2種及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在網絡沉迷組中所占比重小(χ2=10.656,P=0.001),有重度抑郁癥狀的老人網絡沉迷比重低(χ2=12.860,P=0.002)。相比認為網絡利大于弊和利弊相當的老年人,認為網絡弊大于利和不知道的老人網絡沉迷占比高(χ2=14.431,P=0.002)。個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老年人在網絡沉迷組的比重高,在對照組的比重較低(χ2=8.476,P=0.014)。
家庭特征中,代際溝通頻率、家庭約束與老年人網絡沉迷顯著相關。隨著代際溝通頻率增加,老年人網絡沉迷的占比減小。在家庭約束中,經常受到家庭約束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的比例最低,從未受到家庭約束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的比例最高(χ2=48.873,P=0.000)。
社會特征中,不同社會活動參與情況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狀況不同,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隨著老年人社會活動參與項數的增多,網絡沉迷的比例逐漸下降(χ2=15.249,P=0.002)。其他因素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四)老年人網絡沉迷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以老年人是否網絡沉迷為因變量,以前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顯著性差異的變量受教育程度、所患慢病數量、心理健康、網絡利弊認知、收入情況、代際溝通頻率、家庭約束、社會活動參與項數為自變量,變量具體賦值情況見表4。自變量的容忍度數值均大于0,VIF值均小于2,說明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關系。表5給出了Logistic回歸的結果,所患慢病數量、心理健康、網絡利弊認知、代際溝通頻率、家庭約束、社會活動參與是影響老年人網絡沉迷的顯著相關因素。

表4 老年人網絡沉迷的Logistic回歸模型變量賦值

表5 老年人網絡沉迷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在個體因素層面:患有2種及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發生風險是患有1種慢性病或沒患病老年人的0.384倍;有重度心理抑郁傾向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發生風險是無抑郁傾向老年人的0.228倍;對于網絡利弊認知不清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發生風險是認為網絡利大于弊老年人的12.554倍。
在家庭因素層面:每2~3天有1次代際溝通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發生風險是每天進行代際溝通的老年人的2.639倍,表明較低的代際溝通頻率可能是老年人發生網絡沉迷的危險因素。從沒有受到家庭約束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發生風險是經常受到家庭約束的老年人的6.784倍,表明家庭約束少可能是老年人發生網絡沉迷的危險因素。
在社會因素層面:參與2項社會活動的老年人網絡沉迷發生風險是參與1項社會活動的老年人的0.415倍,表明豐富的社會活動參與可能是老年人網絡沉迷的保護因素。老年個體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與老年人網絡沉迷的關聯并不顯著。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觸網老年人的網絡沉迷現象應當引起社會關注。在本文調查對象中,半數以上的觸網老年人具有網絡沉迷情況,老年人網絡沉迷的主要表現由高到低依次是耐受癥狀、人際與健康問題、戒斷癥狀、強迫癥狀、時間管理問題。據統計,世界青少年網絡沉迷的發生率為 6.0%[5];中國青年網絡協會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城市地區14.1%的青少年網民受到網絡沉迷的困擾;孫瑜晨通過對比研究發現老年群體網絡沉迷得分顯著高于大學生[21]。由此可見,相比青少年群體,老年人網絡沉迷的程度更深,可能與青少年用網往往受到學校和家長多方面的制約,而老年人大多已經是完全退休狀態,閑暇時間明顯較多有關。但是,網絡沉迷現象的普遍存在,提示老年人自身、家庭和社會都需要進一步關注和跟蹤網絡沉迷的可能影響,以實現早期的預警和預防干預。
個體、家庭、社會層面因素均與老年人網絡沉迷息息相關,老年人健康用網的家庭層面和社會層面支持力度不足。個體方面,網絡利弊認知對其網絡沉迷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面老年人和青少年的情況相似,老年群體如果對于網絡的利弊認知不夠客觀,預防和緩解網絡沉迷的意識也會相應不足。從家庭來看,超過1/3的老年人從未受到網絡使用的家庭約束,家庭中代際溝通較少,家庭成員給予老年人網絡使用的正確引導較少。在社會特征層面,社會活動參與是影響老年人網絡沉迷的重要因素,這與青少年群體網絡沉迷在社會層面上的主要影響因素一致,鄧英欣發現社會支持與青少年網絡沉迷呈顯著負相關[29]。相當一部分老年人退出了社會生產領域,擁有充足的閑暇時間,由于線下社會活動參與度較低,許多老年人選擇上網來消磨時間,這導致部分老年人逐漸沉迷于網絡。另外,互聯網中的虛擬社區和社交群體沒有時間和空間障礙,促使一些老年人在網絡上尋求慰藉,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通過上網獲得滿足,但是部分老年人可能將現實的心理需求過多轉移到線上,導致其陷入網絡沉迷。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僅僅考慮老年人的物質保障是不夠的,對于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需要予以充分支持,線下活動的匱乏和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使得老年人缺少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機會,缺乏社交途徑,也可能會致使其沉迷于各種網絡應用之中[30]。
(二)建議
由于對老年人網絡沉迷的關注處于起步階段,尚沒有成熟和較為權威的量表可以借鑒與利用,本研究借鑒青少年網絡沉迷相關研究對此進行了嘗試,對老年人網絡沉迷的測量如何更為科學和有針對性還需要學界的進一步研究。同時,由于可行性的限制,本研究采用了局部地區非隨機調查的樣本,研究結果尚不能推論到所有城市老人。但本研究樣本的基本構成(年齡、性別、收入等)與實際觸網老年群體較為一致,研究結果仍然具有較好的參考意義,可以反映當前老年群體存在的網絡沉迷問題及其嚴重性。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建議:
1.加強網絡認知教育,提升老年群體自我管理能力
加強網絡素養教育是促進老年群體健康用網的長久之計。建議將網絡沉迷認知納入當前教育部門主管的各級老年教育和民政部門主管的社區數字適老化促進行動之中,創建并推廣符合老年群體生理心理特征的網絡素養教育課程。首先,在觀念層面,倡導老年人自我管理,積極調整上網的情緒和心理狀態,清醒地接觸網絡。認清網絡的根本屬性,自覺抵制不良誘惑,更加理智地看待網絡,提升網絡認知。其次,在健康知識層面,促進老年人關注過度用網對自身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可能影響,注意用網后的健康調適;在行為層面,發揮老年人心智發展相對成熟、社會閱歷相對豐富的群體優勢,提高其抵抗誘惑的能力,增強用網時間的自我控制,更加主動地采取健康上網行為。
2.加強家庭情感支持和約束作用,助導老年人適度用網
家庭是預防和應對老年人網絡沉迷的重要主體。建議宣傳部門利用多種途徑加大社會宣傳,促進家庭對老年網絡沉迷現象的關注,更多參與到老年人網絡沉迷的預防之中。第一,發揮家庭正向情感作用,加強代際溝通,創新代際之間的互動模式。個體進入老年階段,社交網絡及社會角色發生變化,此時需要親友的陪伴與關懷來緩解孤獨感。家人要密切關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不僅要重視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更要關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為老年人提供更充足的情感支持,并且充分認識老年人在上網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健康與安全風險。第二,增強家庭約束力,以應對老年人不健康的上網行為。對待具有網絡沉迷狀況的老年人,需要發揮家庭正向壓力作用。面對老年人不健康的上網方式,家庭成員要適當給予壓力,約束他們的不良行為,比如通過規定上網時間、上網時長等幫助他們適度用網。第三,子輩增加對老年人的“數字包容”,幫助老年人提升網絡信息辨別能力和網絡素養,促進老年人有平等的機會和適當的技能在數字技術的進步過程中受益。通過感性層面更充足的情感支持和理性層面更嚴謹的家庭約束引導老年人適度用網。
3.政策引導多方社會參與,共同促進老年人健康用網
在家庭結構小型化的背景下,社會組織逐漸成為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重要供給主體。鑒于此,行政部門可組合使用經濟性補貼、非經濟性褒獎等激勵工具,引導基層老齡協會、老年大學等社會組織開展預防網絡沉迷的活動。媒體、企業、網絡平臺等應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媒體在向老年群體傳播、普及網絡科學知識時,確保網絡科學知識入耳、入腦、入心;企業和網絡平臺通過技術手段增加防沉迷、深夜休息語音提醒等產品功能,多角度促進老年用戶健康上網。對于誘導鏈接、詐騙信息等啟動預警和阻斷機制,借鑒“青少年模式”[31],相關企業和網絡平臺還可以推出“老年模式”,進入該模式后,老年用戶在線時長、內容設置等受到限制,從而有效引導老年用戶合理作息享受數字生活。另外,要充分發揮基層社區的參與功能。基層社區應當積極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線下社交活動,大力加強街道養老服務中心、社區老年活動室、社區衛生站、老年數字支持中心、戶外鍛煉區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開發更多適合老年人參與的文娛活動,激發老年群體線下社交活動參與的積極性,引導老年人社會活動參與由“表層”走向“深層”,促進老年人健康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