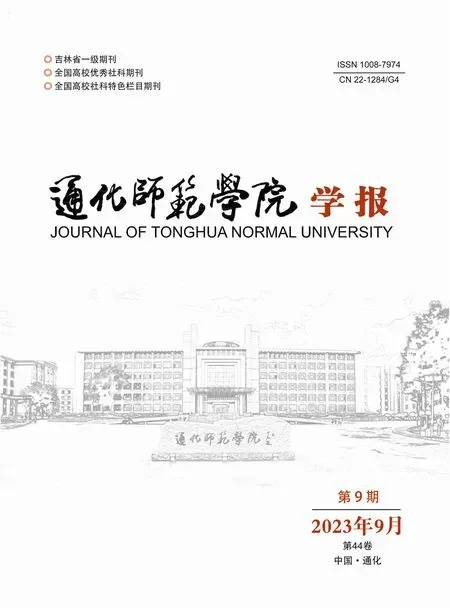從名稱變遷探討國際中文教育的內涵與外延
張嚴秋,汪 璇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的對外漢語教學到如今的國際中文教育,對外漢語教育事業經歷了70年的發展歷程。新中國的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展歷經了對外漢語教學、漢語國際教育和新時期的國際中文教育三個階段[1],盡管這三個階段都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進行教學,但每個階段的教學目標和方式卻有各自的特點。學科建設和事業發展都需要首先了解其核心性質,對外漢語教學作為一門學科進入學術界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然而這一學科的性質和特點至今沒有被人們所普遍理解。本文旨在從對外漢語教學到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名稱變遷入手,討論不同階段漢語教學事業的核心特點和主要任務。
一、對外漢語教學階段
1950 年6 月,周恩來總理召開會議,決定從捷克斯洛伐克等5 個國家交換5 名留學生,還決定在清華開設專門的漢語課程,專門招收東歐地區的交換生,這是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個起點。20 世紀60—70 年代,我國對外漢語教學理論初步形成,對外漢語教學經驗得到系統總結,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課堂教學方法,但這一時期的對外漢語教學基本停留在實踐經驗總結層面。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會于1983 年成立,并確定學科名稱,對外漢語教學專指對外籍人士進行漢語授課。[2]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這一時期學科建設的三項任務,分別是完善教學體系、加強學科理論研究和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把 “對外漢語教學” 明確為一門學科具有標志性意義,標志著對外漢語教學從經驗型階段向科學型轉變,所以此后的對外漢語教學更強調以科學理論指導實踐,加強理論研究,這也是我國對外漢語教學事業的一個里程碑。20 世紀80 年代開始,對外漢語教學理論建設進入了一段繁榮期,以呂必松教授為首的一批學者開始了對外漢語教學的宏觀研究和理論建設。這一時期學者們達成了共識,對外漢語教學有別于傳統的漢語作為本族語的教學,因此在實踐過程中需要吸納其他第二語言教學的經驗。這一時期,也提出了對外漢語教學學科建設的任務:處理好教學與科研、理論研究與理論應用、單項研究與綜合研究等幾對關系。學者們指出,對外漢語教學不能照搬照抄其他語言教學的方法,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個立身之本就是 “漢語” 。因此,對外漢語科學教學理論需要以深入研究漢語理論為基礎[3]。
與對外漢語教學同時使用的名稱還有 “國際漢語教學” ,雖然名稱有一些變化,但其內涵和外延基本相同,這一細微改變標志著學者們的視角已經從 “對外” 逐漸轉向了 “國際” ,這是一種站位上的調整。
二、漢語國際教育時期
2007 年教育部頒布高等學校專業碩士目錄時開始正式使用 “漢語國際教育” 這一學科名稱(當時使用的是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 )。2012年,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將以往所列的學科名稱對外漢語教學替換為漢語國際教育。[4-5]自此, “漢語國際教育” 作為正式使用的、規范的學科名稱被廣泛接受。漢語國際教育的核心本質仍然是中文教育,它是對非中文母語者的中文教學,包括國際上的中文教學和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所以它的本質仍然是中文教學,核心的立足點是中文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與之前的對外漢語教學相比,漢語國際教育在教學對象、教學領域、學習環境等方面發生了更新,概念的外延變得更加豐富寬廣。漢語國際教育的教學場域已經從 “國內” 擴展到了更廣闊的 “海外” 。與此同時,漢語學習者的語言環境也隨之從目的語環境擴展到了目的語環境與非目的語環境兼有,學習場域得到了極大擴展。其次,漢語國際教育的教學對象已經不局限于 “來華留學生” ,而拓展到僑居海外的中國人、華人華僑及想學習漢語的外國人。
學科名稱由 “對外漢語教學” 改為 “漢語國際教育” ,體現了研究者對學科內涵的深入理解,標志著漢語教學的重心由國內向國際轉移,漢語學習者的核心人群由海外留學人員向海外各年齡層次學生轉變。同時,由于這一時期的漢語學習者更加廣泛,不同的學習者有不同的漢語學習目標,對漢語學習的認識也不同。漢語國際教育應當充分考慮不同教學對象之間的群體和個體差異。例如,以郭熙教授為代表開展的對華裔兒童的漢語教學研究,就是國際漢語教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漢語國際教育這一名稱的出現標志著漢語教育事業進入了調動各種社會力量進行學科建設的全新發展階段。
三、國際中文教育時期
國際中文教育大會于2019年12月在長沙召開。孫春蘭副總理所作的主題報告,時任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副部長田學軍等領導所作的報告,一改過去對漢語國際教育的表述,首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學科名稱——國際中文教育(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這一術語一經提出就引發了學界關于國際中文教育內涵和外延的廣泛討論。
國際中文教育將以前概念中的 “漢語” 替換為 “中文” , “漢語” 更傾向于指口語,而 “中文” 更傾向于指書面語。國際中文教育泛指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教學,體現了新時期學科創建以漢語書面語言教學與研究為重點。從教師角度講,國際中文教育的教師可以是華人、華僑、外國人;從教學對象角度看,教學對象可以是母語不是漢語的外國人,也可以是母語不是漢語的海外華人及其后代。因此相比于之前的兩個概念名稱,國際中文教育的外延在教學內容、教學者、教學對象上均有擴展。在新的環境中,國際中文教育在教師隊伍構成、教材和教學法等工具層面會發生變化,這些變化來源于國際中文教育事業規模的擴大,在發展路徑上逐漸轉向內涵式發展。
國際中文教育既指事業,又指學科。就其學科屬性而言,國際中文教育明顯具有跨學科性質,涵蓋了語言學、教育學、心理學等眾多學科的知識;就事業屬性而言,國際中文教育的使命是面向全球開展中文教學、服務中外文化交流互鑒[1]。國際中文教育的重要發展路徑是國際中文教育所包含的三個方面:中國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海外的漢語教學和海外的漢語教育。但從理論研究的角度來看,它們又分屬不同的學科,因此在各自的理論研究中存在著差異。作為事業的國際中文教育同作為學科的國際中文教育相輔相成,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國際中文教育作為學科的理論研究可以指導這一事業的長足發展,同時作為事業的國際中文教育可以為理論研究提供豐富的研究材料。
從最初的 “教學” 發展到 “教育” ,可以看出,學界對國際中文教育的研究和關注已經從 “小教育” 走向 “大教育” ,不僅關注對學習者中文能力的培養提高,也著力提高學習者的文化素養,培養一批能夠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理解中國的國際友人。因此國際中文教育的研究視野已經從國際中文的 “三教” 問題擴展至更為廣闊的領域,如:國際中文教育的政策研究、國際中文的傳播機構研究、國際中文的傳播力研究及國際中文教育的時代背景和環境研究等。然而研究領域的擴大沒有削弱對國際中文 “三教” 問題的研究,相反為國際中文 “三教” 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環境和背景信息,使我們更加深化了對當前國際中文 “三教” 問題的認識,從而為問題的解決提供更多的角度和抓手。同時,從 “教學” 到 “教育” ,也標志著國際中文教育正式突破了 “學科” 認知的藩籬。國際中文教育不是簡單的知識傳授,同時也涉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現實國情等內容,旨在培養一批熱愛中國文化、了解中國實際國情的國際友人,國際中文教育不僅僅是學科,更是一項有意義且需要持續發展的重要事業。發展國際中文教育這一問題牽涉的范圍和復雜性確實遠遠超過將國際中文作為一門學科的認識。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與研究需要放在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背景下,需要充分認識國際中文教育在促進中外人文交流、人文相親、文明交流互鑒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過孔子學院的相關資料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借助語言教學開展的漢語傳播工作,自國際漢語教育這一學科問世以來,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尤其是到了2019年,這種進步更是可圈可點。孔子學院總部以 “孔子新漢學計劃” 為依托,吸引了37個國家的86名博士研究生參加,積極支持將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詩經》等譯成外文,與多家國際出版社達成了出版意向。孔子學院總部向23個國家的孔子學院派出了13支中國高校代表隊進行巡演,共吸引觀眾20余萬人次。在全球110多個國家360所孔子學院舉行的 “孔子學院日” 活動,吸引了100多萬人次參加。[6]新時期的國際中文教育基于語言教育,同時不限于語言教育,走上了 “語言+文化” 的復合型國際中文傳播新路徑。
當然,國際中文教育的基礎仍然是其作為一門學科的角色和屬性,有效的 “教” 和 “學” 依然是影響語言傳播和推廣的最重要因素。國際中文教育這一說法更好地總結了當前漢語國際教育的發展現狀,同時更科學地反映了當前漢語國際教育的一些新特點及未來發展的新動向和趨勢。雖然目前學術界對國際中文教育內涵和外延的認識還沒有達成完全統一的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國際中文教育較以往的對外漢語教學和漢語國際教育的外延更為豐富和廣泛,是對前兩者的繼承和發展,學科名稱的變化反映了學術界對國際中文教育認知的深化。
國際中文教育這個學科名稱最早是在2019年被提出的,經歷了三年的發展,走向了另外一種繁榮的形式, “互聯網+國際中文教育” 被普遍認為是面對面課堂的重要補充,在線漢語教學、數字漢語教材的研發也成為國際中文教育的研究外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急速發展起來的線上國際中文教育探索已經為之后的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國際中文教育理論建設提供了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路向。加之目前的數字技術革命風起云涌,以ChatGPT為首的人工智能大有沖擊傳統語言教學之勢,因此,之后的國際中文教育與數字技術深度結合是大勢所趨,作為國際中文教育的研究者應當主動適應新環境,強化這方面的理論建設。
四、結語
名稱的演變不僅反映了國際中文教育對象的發展變化,還反映了我們作為國際中文教育的主體站位發生了變化。早期的對外漢語教學是針對在中國的外國留學生開展的,教學對象受到了很大約束;而新時期的國際中文教育面向的對象則是包括來華留學生在內的全球華人學習者、各地域的大量學習者,以及擁有豐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中文教育從立足于 “國內的” 對外國留學生的教學,發展成為全世界的中文學習者服務。我們作為國際中文教育的主體,已經從服務者角色轉變成為國際化的積極參與者和建設者。這不僅是發展國際中文教育和傳播中華語言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會和時代發展的大勢所趨。歷經幾十年的發展建設,國際中文教育已經從規模發展逐漸轉向內涵發展,從粗放型轉向精細化,從追求數量轉向追求質量。對于學科名稱變遷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明晰不同階段漢語教學工作的內涵外延和首要任務,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國際中文教育實踐的認識,有助于我們把握國際中文教育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和任務。
早期的對外漢語教學經歷了從 “經驗型” 到 “學科型” 的轉變,新時代的國際中文教育又經歷了從 “學科型” 到 “事業型” 的跨越,這并不是學科發展的倒退,反而是學科建設 “螺旋式” 的發展進步。早期的對外漢語教學脫胎于教學實踐,因此當時非常需要作為一個學科構建理論框架、介紹國外語言教學流派、研制教學大綱,這是由學科發展的階段所決定的。而新時期的國際中文教育從 “學科型” 轉型成了 “事業型” ,這并不意味著國際中文教育放棄了傳統的理論建設,而是在原有基礎上將更多的內容,如中文國際傳播、文明交流互鑒、語言政策與規劃等納入了國際中文教育的研究體系之中,這也是學科發展的階段所決定的。因此,從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建設,再到國際中文教育的 “學科型” 轉向 “事業型” 都是學科發展的必經途徑,漢語教學工作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中有最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認識到,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隨著實踐的發展和新技術的出現,概念的內涵外延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學界和其他國際中文教育的參與者都需要不斷地更新認識,把握最新發展動向,力求更客觀地反映和指導實踐,推動國際中文教育高水平發展,促進中文的傳播。發展中文教育、增強國際中文的語言競爭力,對提升我國的國際話語權、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