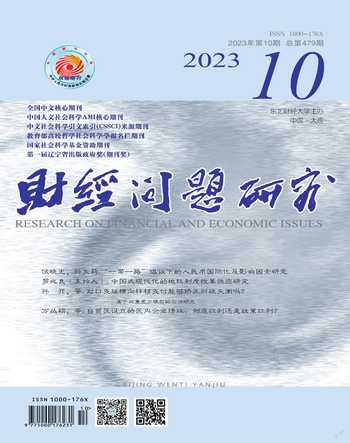地權(quán)穩(wěn)定會強化農(nóng)戶的生育激勵嗎?
洪煒杰 羅必良



摘 要:地權(quán)制度如何影響生育決策?雷州半島同時存在的承包地和祖宗地制度為觀察不同地權(quán)制度安排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激勵差異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準自然試驗。本文基于農(nóng)戶問卷數(shù)據(jù),采用OLS和2SLS方法研究發(fā)現(xiàn):祖宗地村莊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較低,并隨著村莊祖宗地占比的增加,農(nóng)戶家庭新增人口數(shù)量會減少;農(nóng)地調(diào)整發(fā)生次數(shù)的增加則會提高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激勵。機制檢驗表明,地權(quán)制度對人口增長的影響與產(chǎn)權(quán)穩(wěn)定性緊密關(guān)聯(lián)。在農(nóng)地調(diào)整下,較多的家庭人口意味著可以獲得更多的土地,從而生育行為成為農(nóng)戶獲得更多土地的重要策略。
關(guān)鍵詞:地權(quán)制度;承包地制度;祖宗地制度;農(nóng)戶生育行為
中圖分類號: F3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3)10-0016-15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青年項目“非農(nóng)轉(zhuǎn)移、代際轉(zhuǎn)換與農(nóng)地撂荒發(fā)生機理研究”(72203064);廣東省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青年項目“農(nóng)地撂荒的發(fā)生機理及其政策啟示:基于農(nóng)戶承包地規(guī)模的考察”(GD22YGL20);廣東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創(chuàng)新工程特別委托項目“農(nóng)民共同富裕的生態(tài)邏輯及其實現(xiàn)路徑”(GD22TWCXGC08);廣東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特別委托重點項目“清遠高質(zhì)量發(fā)展研究”(GD23WTC02-08)
一、問題的提出
經(jīng)濟學(xué)對人口及其生育問題的關(guān)注可以追溯到Malthus[1],他認為,由于人類的情欲是沒法控制的,人口總會傾向于過度增長,直到自然資源消耗殆盡。因此,抑制人口的過快增長,成為眾多國家人口政策的基調(diào)。然而,最近二百多年的經(jīng)驗事實卻表明,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口增長速度會出現(xiàn)大幅度下降[2]。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顯示,由于生育率下降,2017年世界范圍內(nèi)14歲及以下人口占總?cè)丝诘谋戎仄骄呀抵?5. 94%,而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cè)丝诘谋戎仄骄焉?. 70%,這意味著全球已經(jīng)步入老齡化社會。其中,無論是經(jīng)濟發(fā)達的歐美國家,還是經(jīng)濟快速增長的東亞地區(qū),這些國家或地區(qū)14歲及以下人口占總?cè)丝诘谋戎囟嫉陀?0%。
對于上述現(xiàn)象,主流經(jīng)濟學(xué)家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給出了解釋。在宏觀方面,Modigliani和Brumberg [3]基于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生育率下降和預(yù)期壽命延長能夠影響人口增長和儲蓄水平,進而提高物質(zhì)資本積累。生育率下降能夠減輕少兒撫養(yǎng)負擔(dān),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并促進經(jīng)濟增長,而預(yù)期壽命延長則減少了父母對孩子的預(yù)防性需求[4]。在微觀方面,Becker和Lewis[5]從人口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相互替代的角度出發(fā)認為,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會更加重視人口的質(zhì)量而傾向于減少人口的數(shù)量。Tamara [6]進一步研究了生育率對公共人力資本和私人人力資本的影響發(fā)現(xiàn),生育率的上升并沒有影響公共人力資本投資,卻降低了私人人力資本投資。
上述研究忽視了社會體制和文化的影響。Caldwell [7]認為,人口生育率和人們的生育決策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社會體制和文化沖擊的影響。Kocher[8]注意到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是,在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土地分配格局的變化,因為土地的分布決定社會財富的最初分布,是影響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土地是農(nóng)耕社會最重要的資產(chǎn),不僅決定著社會經(jīng)濟格局和社會結(jié)構(gòu),而且對人們的生育決策也產(chǎn)生關(guān)鍵性的影響[9]。然而,地權(quán)制度如何影響生育激勵存在不同的理論假說:一方面,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多由自家勞動力進行耕作,持有土地的增加會提高農(nóng)戶使用自家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提高農(nóng)戶的生育激勵[10];另一方面,在財富約束下,對土地投資和對后代投資存在相互替代關(guān)系,這意味著土地增加可能會降低農(nóng)戶的生育激勵[2]。相關(guān)的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jié)論。Merrick[11]利用巴西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土地可得性與生育激勵正相關(guān)。不同的是,Stoeckel和Chowdhury[12]基于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的數(shù)據(jù)卻發(fā)現(xiàn),土地規(guī)模與生育率負相關(guān),婦女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與土地規(guī)模正相關(guān)。
土地分配格局與生育行為之間的關(guān)系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特別是因地權(quán)制度,包括土地產(chǎn)權(quán)和土地可繼承性的變化而變化。Easterlin[13]發(fā)現(xiàn),美國新拓荒區(qū)的生育率要高于舊區(qū)域,原因在于土地拓荒后歸私人所有,且具有可繼承性,所以拓荒者有動力拓展土地并生育更多的后代,以便對土地財富進行代際傳承。而在墨西哥1992年的土地改革之前,社區(qū)土地往往屬于由25個家庭組成的社團所有。每個家庭都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quán),如果有農(nóng)戶連續(xù)兩年不進行耕作,這個農(nóng)戶家庭所擁有的土地就會被社區(qū)收回。Soberon?Ferrer和Whittington[14]認為,這一地權(quán)制度安排能夠激勵農(nóng)戶生育更多的孩子。原因在于,一方面,人口越多的家庭意味著在社區(qū)具有更多的話語權(quán);另一方面,當父母外出務(wù)工時,土地可以由孩子繼續(xù)耕作而不會被社區(qū)集體收回。
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同樣的土地分配方式對生育激勵在不同時期也存在不同的影響。如印度,Kleinman[15]研究表明,土地越集中,人口的生育激勵越低,因而如果將土地平均分配將會提高人們的生育激勵;而Singh [16]基于Punjab和Haryana兩個地區(qū)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相對于無地農(nóng)民,有地農(nóng)民生育孩子的數(shù)量更少。Desai和Alva[17]利用印度國家家庭健康調(diào)查(NFHS,1992—1993年)數(shù)據(jù)在控制家庭類型和家庭資產(chǎn)后發(fā)現(xiàn),與無地農(nóng)戶和擁有大量土地的農(nóng)戶相比,擁有小規(guī)模土地的農(nóng)戶生育率更低,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害怕生育過多的小孩會進一步加劇土地細碎化。基于此,他們認為,農(nóng)地調(diào)整或重新再分配可以作為一種抑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政策手段。
中國的事實或許提供了與上述并不一致的邏輯線索。眾所周知,中國的均田制由來已久,表面看來似乎與人地關(guān)系或生存壓力有關(guān),而實際上起關(guān)鍵作用的是租稅制度。由租稅制度所誘發(fā)的逃役策略,從秦朝開始就逐步形成了不斷固化的諸子均分的制度遺產(chǎn)[18]。李楠和甄茂生[19]利用清代至民國初期浙南鄉(xiāng)村的族譜及分家契約文書,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分家制度與農(nóng)民生育行為的關(guān)系進行考察的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分家制度作用下,父輩出生次序與其生育水平存在顯著的負相關(guān)關(guān)系,出生次序每滯后1個單位,其生育子女數(shù)量平均減少0. 3人。其原因在于,分家制度導(dǎo)致分家前后財產(chǎn)產(chǎn)權(quán)屬性發(fā)生了變化,這對處于不同婚育周期的兒子產(chǎn)生了不同的生育激勵。出生次序靠前的兒子,容易產(chǎn)生“搭便車”行為,可以用分家前大家庭的財富養(yǎng)育自己的兒女;而出生次序靠后特別是分家時還未到婚育年齡的兒子,由于養(yǎng)育孩子的所有成本都要自己承擔(dān),其家庭生育水平會受到抑制。可見,即使在土地私有制背景下,盡管存在排他性的產(chǎn)權(quán)安排,但家庭組織的裂變(分家)依然會帶來不同的生育激勵,即在分家前結(jié)婚的兒子更具有生育動機,而在分家后結(jié)婚的兒子則表現(xiàn)為生育抑制。
根據(jù)上述歷史證據(jù),筆者提出一個“周期性產(chǎn)權(quán)調(diào)整”的生育激勵解釋框架。
與西方私有地權(quán)制度相比,中國現(xiàn)行的農(nóng)村地權(quán)制度具有獨特性。最為重要的是,農(nóng)村土地所有權(quán)屬于村莊農(nóng)民集體所有,農(nóng)民個體(或家庭)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quán)。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背景下,農(nóng)村集體土地需要依據(jù)農(nóng)民的社區(qū)成員身份進行均分,從而以家庭為單位落實農(nóng)戶土地承包的成員權(quán)。由此,中國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具有兩個特點:一是穩(wěn)定性。在承包期內(nèi),農(nóng)戶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由每個農(nóng)戶所有,對其他農(nóng)戶具有排他性。二是公平性。村莊集體土地均權(quán)原則決定了當農(nóng)戶家庭因人口增減導(dǎo)致的地權(quán)不公平達到一定程度時,村莊集體就有可能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顯然,對于村民而言,農(nóng)地調(diào)整的周期性是可預(yù)期的。盡管在每次農(nóng)地調(diào)整之后,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是穩(wěn)定的,但是農(nóng)戶對于農(nóng)地調(diào)整的再一次發(fā)生是存在穩(wěn)定預(yù)期的。
中國農(nóng)村集體土地的均分及其調(diào)整與中國歷史上的分家制度在邏輯上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在分家制度下,分家之前進行生育的兒子可以通過“搭便車”的方式利用大家庭的財富養(yǎng)育自己的后代,同樣,由于農(nóng)地調(diào)整是可預(yù)期的,所以,在土地兩次調(diào)整之間,農(nóng)戶可以通過采用多生育孩子的策略在下一次農(nóng)地再分配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土地。不同的是,在分家制度中,由于不同排序的兒子所處的婚育階段不同,且每次家庭組織裂變(分家)后的財產(chǎn)存量有減少的趨勢,所以,出生次序較后的兒子“搭便車”的可能性會較低;而在農(nóng)地調(diào)整中,地權(quán)均分是在村莊的全部土地存量中進行的分割,因而每一個農(nóng)戶都有動機和機會通過多生孩子的方式在下次農(nóng)地調(diào)整中獲得更多的土地。顯然,如果農(nóng)地調(diào)整不再發(fā)生,那么農(nóng)戶希望通過生育來獲取更多土地的動機就會受到抑制。因此,中國農(nóng)村土地“周期性的產(chǎn)權(quán)調(diào)整”對農(nóng)戶會產(chǎn)生生育激勵。
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實施可能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由圖1可知,國家統(tǒng)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diào)查資料》顯示,隨著農(nóng)地制度改革的推進,如土地承包關(guān)系維持15年不變、30年不變,以及抑制甚至禁止農(nóng)地調(diào)整相關(guān)政策的出臺,不僅農(nóng)地調(diào)整發(fā)生的頻率逐漸下降[20],而且新增的人口數(shù)量也逐漸減少。
從已有文獻來看,實證考察農(nóng)地制度如何影響人口增長應(yīng)該存在一些困難。首先,改革開放以后,大量農(nóng)村勞動力的跨市甚至跨省流動,使得利用宏觀數(shù)據(jù)(如縣或縣級市)刻畫區(qū)域人口數(shù)量可能并不準確。其次,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在短期內(nèi)推廣至全國各地(—年),但生育行為卻并非是即時的決策與響應(yīng),這將導(dǎo)致區(qū)域的對比研究并不可行。最后,進行跨區(qū)域的對比研究也容易因為其他難以觀測的變量,如文化、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往往會導(dǎo)致研究結(jié)論的可信度不高。
幸運的是,位于廣東省雷州半島核心區(qū)域的雷州市(縣級市)存在相鄰村莊地權(quán)制度不一樣的現(xiàn)象。這種獨特的現(xiàn)象為進一步的經(jīng)驗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準自然試驗數(shù)據(jù)。在雷州市,有一些村莊在最初解散人民公社實施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時,土地分配是根據(jù)20世紀50年代實施集體化之前的土地私有格局進行“復(fù)原”的,即農(nóng)戶憑借保存下來的地契將原來私有制時期各自擁有的土地收回進行家庭承包經(jīng)營(下文統(tǒng)稱為“祖宗地”),并在后期很少進行調(diào)整或者再分配。而在相鄰的一些村莊,則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框架下平均分配土地,并在后期不同程度地進行過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由于這兩類村莊均處于同一區(qū)域,其地理特征類似、文化底蘊和風(fēng)俗習(xí)慣相同,宏觀政策環(huán)境一致,這些均為研究不同的地權(quán)制度如何影響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提供了可以對比研究的重要事實判據(jù)。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厘清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機理,進而利用準自然試驗數(shù)據(jù)揭示地權(quán)穩(wěn)定性所隱含的激勵效應(yīng)。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與實施祖宗地的村莊相比,以農(nóng)地調(diào)整為特征的均包制對于農(nóng)戶家庭的人口生育決策具有正向的激勵作用。
二、制度背景與邏輯線索
(一)中國地權(quán)制度:一個簡述
1949—1952年,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土地改革運動,廣大農(nóng)村普遍實施了以農(nóng)戶家庭為單位的土地私有制與家庭經(jīng)營。1951年和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發(fā)布了《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互助合作的決議》,目的就是要促進農(nóng)民聯(lián)合起來,逐步實現(xiàn)農(nóng)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最初由農(nóng)民自發(fā)組建的生產(chǎn)互助小組,主要是農(nóng)戶自主聯(lián)合,在農(nóng)忙時相互幫忙進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1955年,中央全會通過了《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進一步加快。到1956年底,有96. 3%的農(nóng)民參加了初級社,87. 8%的農(nóng)民參加了高級社。高級社成為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的基本生產(chǎn)經(jīng)營單位,與此同時,土地產(chǎn)權(quán)從私有制轉(zhuǎn)化為集體所有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包括牲畜和農(nóng)具也歸集體所有。1958年,中共中央發(fā)布了《關(guān)于在農(nóng)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短短3個月的時間內(nèi)(1958年8—11月)就形成了24 000個人民公社,包含全國99%的農(nóng)民[21],并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確立了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chǔ)”為核心的正式制度[22]。
然而,人民公社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勞動力監(jiān)督和管理困難,大量無效勞動的存在導(dǎo)致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效率低下[23]。由于長期干旱天氣的影響,糧食收成欠佳,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于1978年率先將集體土地承包給村民。這一舉動大大提高了糧食產(chǎn)量而使得土地承包的做法在全國范圍內(nèi)迅速得到模仿[24]。1982年的《全國農(nóng)村工作會議紀要》正式認可農(nóng)村實行的各種責(zé)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責(zé)任制。自此,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jīng)營成為中國農(nóng)村的基本經(jīng)營制度。
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制度框架下,盡管土地所有權(quán)依舊是集體所有,但農(nóng)戶卻以保證對國家的稅收和承擔(dān)經(jīng)營責(zé)任換得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以及稅費上繳之余的剩余索取權(quán)[25]。農(nóng)民生產(chǎn)熱情因此得到普遍提高,農(nóng)業(yè)產(chǎn)出在20世紀80年代也有了顯著的增長[26]。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往往表達為社區(qū)集體的每個成員都天然地平均享有對土地使用的權(quán)利。為了保證產(chǎn)權(quán)分配(界定)的公平性,從初始的按人(勞)均分配土地使用權(quán),到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口變化而重劃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追求產(chǎn)權(quán)界定公平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成為普遍的周期性現(xiàn)象,從而成為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中國農(nóng)村最顯著的產(chǎn)權(quán)特征[27]。農(nóng)地調(diào)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大調(diào)整,即在農(nóng)地調(diào)整時將全村的土地打亂,再根據(jù)各戶人口的多少重新分配農(nóng)戶承包地。一種是小調(diào)整,只在家庭人口有變化的農(nóng)戶之間進行。簡單來說,當農(nóng)戶家庭有新增人口時,則在下一次農(nóng)地調(diào)整時能夠從集體中多獲得一份土地,相反地,如果老人去世,則在下一次農(nóng)地調(diào)整時會被集體收回部分土地。無論是大調(diào)整還是小調(diào)整,家庭人口增加的農(nóng)戶都可能獲得更多的土地。
(二)祖宗地制度:雷州半島的特殊性
雷州半島位處中國廣東省的西南部,與海南島隔岸相望,距離廣州市約450千米,距離北京市約2 300千米,遠離政治行政中心。處于雷州半島核心區(qū)域的雷州市(原名海康縣),于1949年12月5日解放,是最晚一批被解放的地方之一。雷州市靠近海洋,具有典型的海洋文化,民風(fēng)彪悍。與廣東省其他地方一樣,雷州市人多地少,人地關(guān)系緊張,農(nóng)民對于土地十分珍惜。
事實上,雷州市是最早探索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地區(qū)之一。早在1977年底,當時的北和公社(現(xiàn)為北和鎮(zhèn))的譚葛大隊在南村第五生產(chǎn)隊試行聯(lián)產(chǎn)到戶。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雷州市在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時,各個生產(chǎn)隊也是按照土地均分原則,根據(jù)家庭人口的多少將集體土地分配給農(nóng)戶。
由于雷州半島解放較晚,也沒有進行深刻的土地改革運動和與之相關(guān)的廣泛的政治斗爭(尤其是對地主富農(nóng)的政治斗爭),加之“尚武好斗、獨立不羈”的民風(fēng)和家族勢力[28],眾多農(nóng)戶還較為完整地保存了集體化之前的地契,并且能夠清晰辨認自家土地的位置。所以,在實施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時,部分農(nóng)戶,尤其是村莊中的大姓宗族,就以地契為由,從公社集體土地中領(lǐng)回祖宗地進行“家庭承包”。盡管這一做法有悖于中央實施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基本政策,但基層政府和村莊集體組織并未予以制止,而是得到村莊其他農(nóng)戶的認可,并紛紛效仿認回集體化之前的土地。由于被認領(lǐng)的祖宗地在此之后也不再參與集體的重新調(diào)整,所以,在這些村莊形成了與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權(quán)制度,即祖宗地制度。這類現(xiàn)象一直有擴散蔓延的趨勢。無論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在2000年前后,即使在已經(jīng)實施土地均分的周邊村莊,也出現(xiàn)了農(nóng)戶通過領(lǐng)回自家祖宗地進行“家庭承包”經(jīng)營的情形。所以,雷州半島形成了與其他地方迥異的農(nóng)地制度,即除了以土地均分原則實施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之外,還存在以祖宗地為依據(jù)實施的“家庭承包”。盡管祖宗地制度在雷州半島的徐聞縣和雷州市等眾多村莊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卻以雷州市的覃斗鎮(zhèn)和烏石鎮(zhèn)最為突出。
必須指出的是,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本質(zhì)是土地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分離,是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前提下進行的家庭承包經(jīng)營。其合法性在于:其一,由于土地集體所有是農(nóng)民集體所有,任何一種作為家庭承包的土地分配方式,如果得到村民的一致同意并被村集體認可其承包關(guān)系,農(nóng)戶由此獲得的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均具有合法性和道義性。其二,由于家庭承包中的土地分配方式并不具有決定性的法理意義,所以,與普遍實施的維護集體土地所有權(quán)的“均田承包”分配方式不同,雷州半島的部分村莊則以“家庭承包”經(jīng)營的名義實施了祖宗地回歸。顯然,由此存在的重大區(qū)別在于:均田承包地是憑借社區(qū)集體成員權(quán)所獲得的,從而使得家庭承包的土地經(jīng)營內(nèi)含著公平性,并存在可進一步調(diào)整(或再分配)的基因;祖宗地則是憑借早期私有制留下的地契所獲得的,因而此類“家庭承包”的土地則具有可繼承性,隱含著產(chǎn)權(quán)固化的基因。如果說前者使農(nóng)戶獲得的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具有“準所有權(quán)”性質(zhì),那么后者使農(nóng)戶獲得的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則幾乎接近“準私有權(quán)”性質(zhì),從而兩類農(nóng)地制度在產(chǎn)權(quán)強度和穩(wěn)定性方面具有重大差異。由于均田承包內(nèi)含著周期性的產(chǎn)權(quán)調(diào)整,因而會強化農(nóng)戶的生育激勵,而祖宗地因產(chǎn)權(quán)固化則不存在類似的機制。
(三)理論模型: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


由此可見,對于一個代表性或者平均意義上的農(nóng)戶,盡管他在不同制度下最終能夠獲得的土地可能是相等的,但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農(nóng)戶的生育激勵要高于祖宗地制度下農(nóng)戶的生育激勵。從模型還可以得知,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即使農(nóng)戶能夠獲得的土地略少于祖宗地制度下的土地,其生育激勵依舊可能更高。由此可以推斷,即使在可獲得土地數(shù)量相同的情況下,地權(quán)制度的改變依然能夠影響農(nóng)戶的生育激勵。
三、研究設(shè)計
(一)數(shù)據(jù)來源
為了研究不同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本課題組于2018年春在廣東省雷州市進行入戶問卷調(diào)研。選取祖宗地制度最為突出的覃斗鎮(zhèn)和烏石鎮(zhèn)作為研究的試驗組(簡稱為“祖宗地村莊”),選取與其相鄰但以土地均分進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英利鎮(zhèn)和北和鎮(zhèn)作為控制組(簡稱為“承包地村莊”)。試驗組和控制組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環(huán)境類似,這有利于降低不可觀測變量的影響,進而提高研究結(jié)論的可信度。進一步在兩組中各隨機抽取30個村(行政村),每個村根據(jù)村民花名冊現(xiàn)場隨機抽取20個農(nóng)戶,各有600個農(nóng)戶,一共構(gòu)成了1 200個農(nóng)戶樣本。
圖2描繪的是60個村中祖宗地地塊在所有地塊中占比的核密度圖。由圖2可知,在承包地村莊,祖宗地地塊占比大約為10%,只有少數(shù)村莊祖宗地占比超過20%。而在祖宗地村莊,所有村莊祖宗地地塊占比都超過20%,并且大部分村莊祖宗地占比都超過40%。可見,祖宗地村莊和承包地村莊在地權(quán)制度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
在合作化尤其是人民公社時期,所有村莊都實行了集體所有集體統(tǒng)一經(jīng)營的地權(quán)制度,不存在周期性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只有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實行之后才會有農(nóng)地調(diào)整。通過統(tǒng)計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如表1所示):其一,承包地村莊與祖宗地村莊相比,家庭成員出生在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之前(1978年)的多0. 037人,但兩者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其二,2017年,承包地村莊的戶均人口數(shù)是4. 017人,祖宗地村莊的戶均人口數(shù)是3. 435人,兩者相差0. 582人,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由此再次說明,承包地村莊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對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具有正向的激勵效應(yīng)。


(二)模型構(gòu)建和變量定義
⒈模型構(gòu)建
其中,i為農(nóng)戶,j為村莊。被解釋變量Birthsafter為家庭中在1979—2018年出生的人口數(shù);解釋變量Landinstitution為地權(quán)制度;X為控制變量,主要是控制可能同時影響地權(quán)制度和農(nóng)戶家庭人口增長的變量;ε為隨機擾動項。
⒉變量定義
被解釋變量:新生人口(Birthsafter1978),用農(nóng)戶家庭中在1979—2018年出生的人口數(shù)衡量。
解釋變量:地權(quán)制度(Landinstitution)。考慮到制度具有持續(xù)性和延續(xù)性,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刻畫地權(quán)制度:(1)將樣本農(nóng)戶分為兩類,一類是處于祖宗地地區(qū),另一類是處于承包地地區(qū),前者賦值為1,后者賦值為0。(2)由于同一村莊可能會同時存在不同類型的地權(quán)制度,本文進一步采用祖宗地地塊占全部地塊的比重作為村莊地權(quán)制度的代理變量。(3)單純以某一年是否發(fā)生農(nóng)地調(diào)整可能無法刻畫農(nóng)地制度的全貌,鑒于農(nóng)地調(diào)整是兩類制度最為明顯的區(qū)別,所以在穩(wěn)健性檢驗中將采用自1978年以來農(nóng)地調(diào)整的次數(shù)作為地權(quán)制度的另一個代理變量。
機制變量:為了檢驗相關(guān)機制,本文選取農(nóng)戶農(nóng)地總面積、農(nóng)業(yè)投資和住在農(nóng)戶家中的勞動力占比作為本文的機制變量。
控制變量:已有研究表明,在廣大農(nóng)村,不僅僅擁有政治資源的行為主體能夠影響農(nóng)地制度,村莊中的家族勢力也可能會影響地權(quán)制度的實施[27]。所以,本文控制農(nóng)戶的政治勢力和家族勢力。另外,控制農(nóng)戶的人均耕地面積、1978年前出生的人口數(shù)和戶主特征。各變量的定義如表2所示。
表3是變量的組間差異統(tǒng)計結(jié)果。由表3可知,兩類村莊的大部分變量都沒有顯著差異,從而使得對比研究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差異較大的是人均耕地面積,承包地村莊人均耕地面積比祖宗地村莊多1. 513畝,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祖宗地村莊人地關(guān)系更為緊張,人地關(guān)系可能是影響地權(quán)制度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計量模型將對此予以控制。
農(nóng)地制度與人地關(guān)系緊密相關(guān)。農(nóng)地制度可能是一個內(nèi)生變量,即農(nóng)地制度影響人口增長,而人口增長反過來會影響農(nóng)地制度變遷。本文試圖通過工具變量法降低可能存在的內(nèi)生性問題。筆者使用的工具變量是1956年(即集體化之前)村莊擁有的祖宗地農(nóng)戶占比。正如前文所述,1956年以后,中國農(nóng)村地權(quán)制度變革經(jīng)歷了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土地的所有權(quán)也從私有產(chǎn)權(quán)變成集體產(chǎn)權(quán)。如果祖宗地以1956年的土地所有格局為依據(jù),那么在祖宗地村莊中,擁有祖宗地的農(nóng)戶越多,那些當時沒有土地的其他農(nóng)戶就很難在1980年家庭承包以及隨后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中進行平分。圖3描繪了集體化之前各村擁有土地的農(nóng)戶占比和后來各村祖宗地塊數(shù)占比之間的關(guān)系。由圖3可知,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表明1956年擁有私有土地的農(nóng)戶占比的大小對后來農(nóng)地制度的分化或差異化選擇具有顯著影響。
四、經(jīng)驗分析
(一)地權(quán)制度與生育行為:鎮(zhèn)級層面的刻畫
如前所述,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地權(quán)制度存在著系統(tǒng)性差異。由于樣本農(nóng)戶都是本地原住戶,在本地進行居住的決策是多年之前祖輩的選擇,所以居住在何種類型的鎮(zhèn)村對于現(xiàn)有農(nóng)戶而言是外生的。兩種類型地區(qū)的地權(quán)制度存在顯著的差異,因而可用農(nóng)戶所在鎮(zhèn)村類型對地權(quán)制度進行刻畫(試驗組賦值為1,控制組賦值為0)。表4匯報了鎮(zhèn)級層面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其中,列(1)和列(2)的被解釋變量為1978年以后的新生人口數(shù),列(3)和列(4)的被解釋變量則是1978年以后的新生人口數(shù)+1的自然對數(shù)。列(1)和列(3)只加入了地權(quán)制度變量,列(2)和列(4)則加入了其他控制變量。考慮到村莊內(nèi)部農(nóng)戶生育行為可能存在相關(guān)性,所有模型系數(shù)的標準誤都在村莊層面進行了聚類。由表可知,作為試驗組祖宗地鎮(zhèn)級戶籍農(nóng)戶,其生育行為要低于居住在承包地區(qū)域的農(nóng)戶。從列(2)和列(4)可知,居住在典型祖宗地區(qū)域的農(nóng)戶家庭在1978年以后的新生人口要比承包地區(qū)域少0. 997人,或者說少出生25. 8%的新生人口。
考慮到各個村莊往往同時存在祖宗地和承包地,也就是說,即使在同一種類型的鎮(zhèn)村內(nèi)部,地權(quán)制度也存在差異,因而下文以各村祖宗地占比對地權(quán)制度進行刻畫。
(二)地權(quán)制度與農(nóng)戶生育行為:村級層面的刻畫
表5匯報了村級層面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在所有模型中,祖宗地占比的系數(shù)都為負,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隨著祖宗地地塊占比的增加,人口增長的幅度減小。列(2)和列(4)顯示,如果村莊完全實行祖宗地制度,則每個農(nóng)戶家庭在1978年以后的新生人口數(shù)會比完全實行承包地制度的村莊平均少1. 508人,或減少39. 9%。這表明地權(quán)制度差異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存在顯著影響:村莊祖宗地地塊的占比越多,農(nóng)戶家庭的生育行為越低,新生人口越少。相反,村莊承包地地塊的占比越多,農(nóng)戶生育行為越高,新生人口越多。

(三)工具變量法的估計結(jié)果
應(yīng)該強調(diào),表5中的模型可能存在兩類內(nèi)生性問題:其一,盡管樣本農(nóng)戶所處的地理位置相同,他們的文化偏好和政治環(huán)境應(yīng)該是相同的,但是依舊可能存在一些不能夠測度的變量會影響模型的估計結(jié)果,即可能存在遺漏重要變量而引起的內(nèi)生性問題。其二,農(nóng)地調(diào)整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適應(yīng)人地關(guān)系的變化,因而農(nóng)地調(diào)整與生育行為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guān)系,從而導(dǎo)致估計結(jié)果有偏。
為了弱化這兩類問題,本文進一步通過工具變量法進行重新估計,回歸結(jié)果如表6所示。如前所述,本文采用的工具變量是村莊1956年擁有土地農(nóng)戶的占比(祖宗地占比)。表6中的列(1)匯報了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第一階段的估計結(jié)果,工具變量的系數(shù)為0. 78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村莊在集體化之前擁有土地的農(nóng)戶占比越高,后期實行祖宗地制度的可能性(或程度)越大。第一階段的F值為125. 228,經(jīng)驗上該工具變量是弱工具變量的可能性比較小。列(2)和列(3)報告了第二階段的估計結(jié)果,其中,列(2)的被解釋變量是1978年以后的新生人口,而列(3)則是在此基礎(chǔ)上+1的自然對數(shù)。由列(2)和列(3)可知,祖宗地制度對生育行為具有負向影響,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并且與表5相比,第二階段系數(shù)的相對大小在控制內(nèi)生性問題之后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由此可見,在考慮內(nèi)生性問題之后,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依舊是穩(wěn)健的,即相對于實施祖宗地制度,實施承包地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具有更加明顯的激勵效應(yīng)。
(四)穩(wěn)健性檢驗和討論①
⒈替換工具變量1
如前文所述,在人民公社解散時,地契是農(nóng)戶認回自己祖宗地的重要依據(jù),因而村莊擁有地契農(nóng)戶的比例可能會決定村莊農(nóng)地制度的走向,但是地契更多的是一種財產(chǎn)的憑證,對于生育行為的影響較低。本部分嘗試利用村莊擁有地契的農(nóng)戶占比作為地權(quán)制度的工具變量進行估計。結(jié)果顯示,第一階段的工具變量系數(shù)為0. 89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村莊擁有地契的村民占比越高,則村莊選擇祖宗地制度的程度越高。第一階段F值為42. 742,這說明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的可能性較低。第二階段的估計結(jié)果與前文結(jié)果相似,即村莊中祖宗地的占比越高,農(nóng)戶家庭人口增長越慢。
⒉替換工具變量2
不能忽視的是,由于時間比較久遠,部分農(nóng)戶可能并不清楚其家庭在1956年(集體化之前)是否擁有土地或者擁有的地契已經(jīng)丟失,從而導(dǎo)致前述工具變量的測度不準確。本文嘗試用另一個工具變量進行估計,即除了本村外同鎮(zhèn)其他村的平均農(nóng)地調(diào)整次數(shù)。在中國農(nóng)地制度安排中,往往會受到鎮(zhèn)政府行為的影響,由此在同一個鎮(zhèn)的不同村,其農(nóng)地制度具有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但是,同鎮(zhèn)其他村的地權(quán)制度很難影響到本鎮(zhèn)農(nóng)戶的生育決策。因此,本文采用這個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就農(nóng)地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估計結(jié)果顯示,第一階段的工具變量系數(shù)為-0. 33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同鎮(zhèn)其他村莊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次數(shù)越多,本村祖宗地地塊的占比越低。第一階段F值為91. 773,這說明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的可能性較低。第二階段的估計結(jié)果與前文結(jié)果相似,即村莊中祖宗地的占比越高,農(nóng)戶家庭人口增長越慢。這證明了前文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
⒊替換解釋變量
如前所述,農(nóng)地制度能夠影響農(nóng)戶家庭的生育行為主要源于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多生育意味著能夠從集體中獲得更多的土地。因此,本文進一步采用農(nóng)地調(diào)整次數(shù)作為地權(quán)制度的代理變量,采用OLS進行估計。考慮到農(nóng)地調(diào)整與人口增長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guān)系,本文采用2SLS進行估計,工具變量則是1956年擁有土地的農(nóng)戶占比。結(jié)果顯示,隨著各村農(nóng)地調(diào)整次數(shù)的增加,1978年后農(nóng)戶家庭出生的人數(shù)也隨之增加,并且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內(nèi)生性問題之后,結(jié)論依舊是穩(wěn)健的。
⒋婚喪嫁娶:被解釋變量的測度問題
對于被解釋變量的測度可能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部分農(nóng)戶可能會經(jīng)歷分家或者部分人口死亡,從而導(dǎo)致被解釋變量的測度不準確,即1978年之前出生的部分人口因為分家或者死亡導(dǎo)致在調(diào)研時不能被觀測到。如果地權(quán)制度對分家和死亡的影響沒有系統(tǒng)性的差別,則該問題并不會影響本文的主要結(jié)論,否則可能會導(dǎo)致本文對被解釋變量的測度存在偏差。
為了降低婚喪嫁娶的影響,本文分別把被解釋變量定義為1990—2018年出生的人口數(shù)、2000—2018年出生的人口數(shù)和2010—2018年出生的人口數(shù)。相對于1978年以后的新生人口數(shù),這三個時段出生的人口涉及分家和死亡的可能性相對較低。估計結(jié)果顯示,所有模型的系數(shù)都為負,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地權(quán)制度對于各個時段的出生率都具有顯著影響。這表明本文的回歸結(jié)果具有穩(wěn)健性。
五、機制檢驗
(一)地權(quán)制度、土地分配與生育行為
其中,F(xiàn)amilylandarea為農(nóng)戶家庭的農(nóng)地總面積,其他變量與式(13)一致。此處重點關(guān)注交互項的系數(shù)δ3,如果δ3顯著為負,則說明隨著村莊中祖宗地占比越多,在相同家庭人口規(guī)模的情況下,農(nóng)戶家庭總共擁有的土地面積越少。相反,在祖宗地占比越少的村莊(更多地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則家庭擁有的土地會越多。這說明通過生育更多的孩子在農(nóng)地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土地,可能是地權(quán)制度對于生育行為的一個可能的影響機制。
地權(quán)制度、土地分配與生育行為的檢驗結(jié)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列(1)是采用OLS進行估計的結(jié)果,列(2)則是采用2SLS進行估計的結(jié)果。結(jié)果顯示,列(1)和列(2)的交互項系數(shù)分別為-0. 428和-0. 511,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與承包地村莊中相同人口的家庭相比,隨著祖宗地占比的提高,家庭中所擁有的土地總量會減少。由此可見,第一個作用機制得到經(jīng)驗數(shù)據(jù)的支持。
(二)對農(nóng)地投資替代假說的檢驗
除了上述作用機制外,可能還存在的作用機制是:由于農(nóng)地投資與生育行為之間可能存在可替代性,因而在家庭資源存在約束的情況下,隨著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變得穩(wěn)定,農(nóng)戶會將更多的資源分配到農(nóng)地投資和生產(chǎn)經(jīng)營中,而減少用于養(yǎng)育孩子的資源,由此降低人口增長速度。為了檢驗該機理是否存在,本文構(gòu)建如下模型:
其中,Investment為家庭對農(nóng)地的投資總額,其他變量與前文一致。如果式(15)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則第二個作用機制得到數(shù)據(jù)的支持,即祖宗地地塊占比越多,農(nóng)地投資越多,進而降低人口數(shù)量。表7中的列(3)采用2SLS進行估計,結(jié)果顯示,地權(quán)制度的系數(shù)并不顯著,這說明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業(yè)投資并沒有顯著的影響。所以,產(chǎn)權(quán)穩(wěn)定性的提高,并不會誘導(dǎo)農(nóng)戶將更多的資源用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這個作用機制并沒有得到經(jīng)驗數(shù)據(jù)的支持。
(三)地權(quán)制度與勞動力遷移決策
祖宗地制度之所以會抑制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可能存在另一種作用機制:即隨著地權(quán)穩(wěn)定性的提高,農(nóng)戶因為不需要再擔(dān)心土地在調(diào)整中被村莊集體收回,而選擇勞動力的異地遷移(打工)。而異地遷移的生活成本往往較高,為避免養(yǎng)育后代的機會成本太高從而理性選擇降低生育行為。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么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弱化則可能是因為地權(quán)穩(wěn)定促進勞動力遷移引發(fā)的結(jié)果。為了排除這種可能性,表8進一步估計了地權(quán)制度對居住在家庭中的勞動力占比的影響,其中,列(1)用OLS估計,列(2)用2SLS估計。兩種方法的估計結(jié)果都顯示,祖宗地制度對勞動力遷移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未有證據(jù)表明地權(quán)制度會通過影響勞動力遷移而作用于生育行為。
六、結(jié)論與討論
土地問題是農(nóng)村社會的核心問題,農(nóng)地制度對農(nóng)民行為具有重要的激勵效應(yīng)。其中,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不僅因?qū)嵤┑纳鐣尘安煌煌遗c地權(quán)制度實施的具體情境或者細節(jié)密切相關(guān)。本文結(jié)合中國農(nóng)村地權(quán)制度的歷史遺產(chǎn)和雷州半島的現(xiàn)實格局,基于準自然試驗的農(nóng)戶問卷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通過構(gòu)建“周期性產(chǎn)權(quán)調(diào)整”的分析框架,分析地權(quán)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激勵效應(yīng)。研究結(jié)果表明:在農(nóng)村土地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地權(quán)制度背景下,由于農(nóng)村集體成員平等地擁有土地的使用權(quán),所以,當人地關(guān)系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農(nóng)地調(diào)整就會發(fā)生。由于農(nóng)地調(diào)整的周期性是可預(yù)期的,所以,農(nóng)戶能夠自我激勵生育更多的孩子以期在下一輪農(nóng)地調(diào)整中獲得更多的土地。本文基于廣東省雷州半島祖宗地村莊的準自然試驗數(shù)據(jù)進行經(jīng)驗研究發(fā)現(xiàn):祖宗地村莊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激勵較低,且隨著祖宗地地塊占比的增加,農(nóng)戶家庭的新生人口數(shù)量也隨之減少。相反,農(nóng)地調(diào)整發(fā)生頻率的增加則會顯著提高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機制檢驗則表明,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的背景下,越多的家庭人口則意味著可以獲得越多的土地,從而生育行為成為農(nóng)戶獲得更多土地的重要策略。此外,本文沒有發(fā)現(xiàn)支持地權(quán)穩(wěn)定性的改善會通過農(nóng)地投資或勞動力遷移而間接影響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經(jīng)驗證據(jù)。
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有助于增進對多篇文獻的理解。首先,已有文獻強調(diào)了農(nóng)地投資與后代養(yǎng)育之間的替代關(guān)系,認為地權(quán)穩(wěn)定性的提高能夠增加農(nóng)戶對農(nóng)地的投資,從而降低家庭養(yǎng)育更多孩子的需求,本文的經(jīng)驗證據(jù)并不支持這一推斷。另外,經(jīng)驗分析結(jié)論也不支持地權(quán)制度的改善會通過勞動力遷移而間接影響農(nóng)戶的生育決策。其次,已有文獻強調(diào)了農(nóng)戶持有土地的多寡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影響。本文研究發(fā)現(xiàn),相對于土地的多寡,地權(quán)制度的實施細節(jié)更為重要。即使擁有的土地相對較少,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的農(nóng)戶依然會因為周期性的農(nóng)地調(diào)整而產(chǎn)生更為強烈的生育激勵。最后,學(xué)術(shù)界強調(diào)了土地可繼承性的作用機制,認為土地可繼承性能夠激勵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本文研究表明,土地產(chǎn)權(quán)是否存在可繼承性并不是影響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決定變量。顯然,無論是從過去兩輪農(nóng)村土地承包期延長的事實,到穩(wěn)定農(nóng)戶承包關(guān)系的政策導(dǎo)向,還是到農(nóng)地確權(quán)“生不增死不減”的產(chǎn)權(quán)固化,這些均表明承包地制度和祖宗地制度下的土地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可繼承性。但不同的是,農(nóng)戶在祖宗地制度下繼承的是土地的所有權(quán),而承包地制度下繼承的則是土地的使用權(quán)。從這個角度講,祖宗地制度下土地的可繼承性無疑更具強度。然而,計量結(jié)果表明,祖宗地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激勵卻顯著低于承包地制度。因此,可繼承性并不是決定生育行為的充分條件。
此外,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中國農(nóng)戶的生育行為與長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緊密關(guān)聯(lián)。由此,不同地區(qū)農(nóng)戶家庭生育行為差異可能與其地方政府政策執(zhí)行力度的強弱不同有關(guān)。這就是說,地權(quán)制度的村莊差異或許并非是農(nóng)戶生育差異的根源。本文應(yīng)該不存在這種可能性。首先,本文選擇的試驗組和控制組是地域和文化特征幾乎具有同質(zhì)性的區(qū)域,且同屬于雷州市的縣域范圍,計劃生育政策及其執(zhí)行強度不可能在1978年以來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內(nèi)仍存在系統(tǒng)性差異。其次,試驗組的祖宗地制度是局部性的,而控制組的承包地制度則與全國其他地區(qū)并沒有本質(zhì)差異,如果本文的計量結(jié)果是因為遺漏了計劃生育政策執(zhí)行力度的變量而引發(fā)的,那么唯一的可能性是實施承包地制度的地區(qū)所執(zhí)行的政策力度應(yīng)該更為強烈。這將意味著,本文計量結(jié)果揭示的兩類制度所導(dǎo)致的農(nóng)戶家庭生育差異,不僅是低估了,而且更是低估了祖宗地制度對農(nóng)戶生育的抑制效應(yīng)。
本文的政策含義是:農(nóng)地制度與農(nóng)村人口政策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鑒于地權(quán)制度對于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激勵更多地來自于“周期性產(chǎn)權(quán)調(diào)整”所蘊含的分地預(yù)期,那么,一旦這種預(yù)期不復(fù)存在,地權(quán)制度對于農(nóng)戶生育行為的激勵效應(yīng)就會大幅度降低。由此,本文不僅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nóng)村人口增長速度回升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放緩提供了可能的解釋,另外,考慮到全國范圍內(nèi)以“四至”界定和“生不增死不減”為主線進行產(chǎn)權(quán)固化的農(nóng)地確權(quán)工作已經(jīng)基本完成,因此,本文也為農(nóng)地確權(quán)及其制度完善,以及未來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對農(nóng)村家庭生育行為的影響提供了可能的證據(jù),從而為農(nóng)地政策與人口政策的相機抉擇提供決策參考,為政府部門制定合理的生育激勵政策提供理論依據(jù)。
參考文獻:
[1] 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M]. London: J. Johnson,1798.
[2] LUCAS R E.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C]. KURIHARA K K.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
[4] KIMBALL M S.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J]. Econometrica,1990,58(1):53-73.
[5] BECKER G S, LEWIS H 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2):279-288.
[6] TAMARA F. Child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public vs private educatio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0,23(1):73-97.
[7] CALDWELL J C. Social upheaval and fertility decline[J].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2004,29(4):382-406.
[8] KOCHER J E. Rural develop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fertility decline[M]. New York: The Population Council,1973.
[9] MENCARINI L. A note on landholding and fertility in rural South Africa[J].Genus,2000,56(3-4):109-119.
[10] SCHUTJER W A, STOKES C S, POINDEXTER J R. Farm size, land ownership, and fertility in rural Egypt[J]. Land economics,1983,59(4):393-403.
[11] MERRICK T W.Fertility and land availability in rural Brazil[J]. Demography,1978,15(3):321-336.
[12] STOECKEL J, CHOWDHURY M A. Fertility, infant morta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in rural Bangladesh[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13] EASTERLIN R A.Population change and farm settlement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6,36(1):45-75.
[14] SOBERON?FERRER H, WHITTINGTON L A. The fertility incentive of land tenure in Mexico[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3, (5):1249-1253.
[15] KLEINMAN D S. Fertility variation and resources in rural Indi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73,21(4):679-696.
[16] SINGH K P. Correlates of fertility behavior: a study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Punjab and Haryana[M]. New Delhi:Concept Publishing,1986.
[17] DESAI S, ALVA S. Land redistribution a population stabilization strategy?[J].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1998,33(10):533-536.
[18] 趙岡.永佃制的經(jīng)濟功能[J].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06(3):52-55.
[19] 李楠,甄茂生.分家析產(chǎn)、財富沖擊與生育行為:基于清代至民國初期浙南鄉(xiāng)村的實證分析[J].經(jīng)濟研究,2015(2):145-159.
[20] 冀縣卿,黃季焜.改革三十年農(nóng)地使用權(quán)演變:國家政策與實際執(zhí)行的對比分析[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13(5):27-32.
[21] 黃英偉,張晉華.人民公社時期生產(chǎn)隊差異與農(nóng)戶收入:基于分層線性模型分析[J].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6(3):151-160.
[22] 辛逸.試論大公社所有制的變遷與特征[J].史學(xué)月刊,2002(3):76-80.
[23] LIN Y.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 peasants institutional choice[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7,9(2):410-415.
[24] BAI Y, KUNG K S. The shaping of an institutional choice: weather shocks, the great leap famine, and agricultural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4,54(10):1-26.
[25] 羅必良.農(nóng)地產(chǎn)權(quán)模糊化:一個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釋[J].學(xué)術(shù)研究,2011(12):48-56.
[26] LIN Y.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1):34-51.
[27] BRANDT L, HUANG J, LI G. Land rights in rural China: facts, fictions and issues[J]. The China journal,2002,47(1):67-97.
[28] 劉嵐.雷州半島民風(fēng)悍勇成因探析[J].廣東海洋大學(xué)學(xué)報,2010(2):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