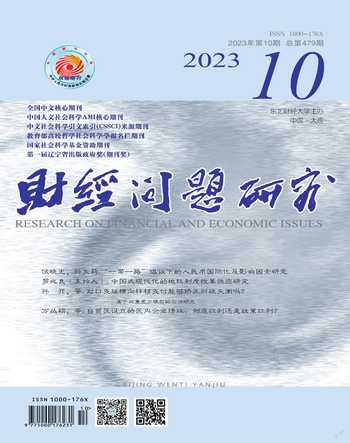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能夠矯正財政失衡嗎?
孫開 牛曉艷 張磊



摘 要: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調節同級政府間財政關系的政策工具,在矯正財政失衡方面有突出優勢。本文基于2003—2019年西部地區地級城市數據,在對縱向財政失衡和橫向財政失衡進行測度的基礎上,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矯正財政失衡的有效性。研究發現: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顯著降低了縱向財政失衡;經濟欠發達地區在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后人均財力水平有所提高,橫向財政失衡程度有所緩解。在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這一結論依然成立。異質性分析表明,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相比,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政策效應更強。本文不僅為研究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功能增加了新證據,也為推動構建中國式橫向轉移支付制度提供了經驗證據。
關鍵詞: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財政失衡;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3)10-0080-1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的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研究”(16ZDA066)
一、問題的提出
確保政府間財政分配平衡是我國公共財政制度建設的基本目標之一,然而,在財政分權體制下,財政失衡現象存在于各級政府之間。過度的財政失衡會扭曲資源配置,造成轄區居民福利受損。矯正財政失衡是激勵地方政府有效履職、促進財政橫向公平的必要路徑,而轉移支付是緩解財政失衡的重要手段。在我國,除了中央對地方的縱向轉移支付之外,還存在應用廣泛、形式多樣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1]。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克服區域非均衡發展難題和消除突發性資源供需失衡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是縱向轉移支付的有益補充。然而,由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資金規模以及實施規范性方面均比不上縱向轉移支付,多數學者對縱向轉移支付的改革和完善給予較多的關注,而聚焦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研究卻滯后于實踐的發展。事實上,合理運用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這一政策工具,不僅有助于彌補受援地政府履行支出責任的財力缺口,削弱央地間權責劃分不匹配導致的縱向財政失衡,還可以扶持落后地區經濟發展,抑制政府間財政收入能力的兩極分化,從而推動構建國家財政均衡體系[3]。基于此,本文著重探究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能否矯正財政失衡,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援助之手”還是“激勵陷阱”,這不僅關系到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新一輪財政體制改革中如何有效架起地方政府間財力均衡的橋梁,也可以為構建激勵兼容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論依據。
學術界關于轉移支付與財政失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縱向轉移支付與財政失衡的關系。①早期的財政分權理論認為,中央政府采用轉移支付手段可以彌補地方財政收支缺口,強化對地方的宏觀調控[4-5]。后續研究從實際出發,就轉移支付能否降低縱向財政失衡、縮小橫向財力差異開展分析,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Dabla[6]分析了我國政府間財政關系的演變歷程,認為轉移支付對省際政府間財政失衡的矯正作用有限。儲德銀和遲淑嫻[7]通過實證檢驗發現,我國轉移支付總體上助推了縱向財政失衡,但從轉移支付內部結構上講影響不同。劉溶滄和焦國華[8]考察了我國轉移支付的財政均衡效應,發現轉移支付在降低中央與地方之間縱向財政失衡方面具有積極影響,而對于實現橫向財政平衡則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財政失衡源于轄區內財政能力的差異[9-10],我國地區間人均自有財力差異較大,轉移支付使得財政資金分配時向財力較弱的地區傾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橫向財政失衡,具有財力均等化效應[11-12]。
關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功能的研究基本限于促進邊疆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的效果評估,而有關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財政失衡影響的成果則不多,已有文獻主要從理論層面進行了闡述,形成了以下兩種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可以降低財政失衡。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由中央政府指導地方政府之間進行財政資金的平級調撥,屬于既定財政體制下的特殊政策安排,具有橫向財政均衡效應[13-15]。王恩奉[16]則指出,我國縱向轉移支付僅在調節中央與地方縱向財政關系上發揮作用,建立橫向轉移支付制度是縮小地區間財力差距的現實要求。王磊和黃云生[17]進一步強調,中央財力畢竟有限且要滿足眾多領域的支出需求,難以完全兼顧各地的發展需要,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對欠發達地區建設的重要補充,有利于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另一部分學者則持相反的觀點,認為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將縱向財政關系扭曲為橫向財政關系,將原本屬于中央的支出責任轉移給地方,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職能配置錯位的一種表現[18]。王瑋[19]基于德國財政平衡體制的比較分析,從我國對口支援政策本身與運行結果出發,發現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存在科學性不足、規范性欠缺和多頭管理等弊端,在矯正橫向財政失衡時效果不佳,因而認為我國尚不具備基于對口支援建立橫向轉移支付制度的現實條件。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對于縱向轉移支付影響財政失衡的問題,學者們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證層面都給予了充分的研究。而從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功能出發,探討其對財政失衡影響的成果較為缺乏,已有研究也僅從理論層面進行了定性討論,缺乏實證分析。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豐富和拓展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相關研究,通過梳理我國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演進邏輯,揭示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不同時期與財政體制的契合性,并總結各階段的特征事實。第二,從理論層面系統地詮釋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財政失衡的影響機理,從而為后續研究提供一個研究框架。第三,不同于現有文獻大多從縱向或橫向單一維度入手探究財政失衡問題,本文將縱向財政失衡和橫向財政失衡納入同一個框架,通過準自然實驗法實證檢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矯正財政失衡的有效性。
二、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制度背景
新中國成立至今,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已有近七十年的發展歷程。以關鍵節點為劃分依據,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經歷了萌芽、初步確立、蓬勃發展和改進完善四個階段,不同時期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通過不同的舉措服務于當時的政策目標。
萌芽階段(1949—1978年)。新中國成立初期,基于國內外環境,中央提出在全國適當布局工業生產,動員上海、天津等東部省份支援新疆、內蒙古、陜西等內陸省份的工業建設,形成了對口支援的雛形。此時正值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財政管理體制,地方財政收入統一上繳中央,而財政支出必須經由中央審核后逐級撥付。沿海支援內地盡管表現為省份與省份之間的橫向支援,實質上依托的財政資金由中央統籌,地方不具備直接負擔財政支出的能力,以支援地干部、工人、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人才跨區域流動是橫向支援的主要內容。這一時期,對口支援還不具備橫向轉移支付性質,但已表現出橫向轉移支付形式,與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非公共性財政運行格局限制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實施領域,使得其在職能發揮上缺乏財政的公共性,并未形成明確的、穩定的國家政策。
初步確立階段(1979—1992年)。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比較分權的財政包干制被應用到財政體制改革中,財政分權讓利的結果便是地方政府可支配財力遠遠大于中央政府,削弱了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而受自然環境和經濟發展滯后等因素制約,我國相當一部分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發育程度低、貧困面大,推動邊疆民族地區發展的任務十分迫切。在此背景下,中央將一部分扶持邊疆民族地區發展的任務發包給經濟發達省份。1979年,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在全國邊防工作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要組織內地發達省份對口支援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對口支援被確立為一項國家政策。不論是項目建設所需財政資金的直接橫向轉移支付,還是教育、醫療等專業技術人才跨區域交流與培養所需支出的間接橫向轉移支付[20],實質上都是財政資金由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橫向配置。此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參與主體范圍不斷擴大,支援地從東部沿海省份演變為沿海與內地省份共同參與,財政資金投入從基礎設施建設拓展到醫療衛生、文教科技等方面。
蓬勃發展階段(1993—2012年)。1994年,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地方政府間具有相對獨立的財政關系,同一層級地方政府間在財力水平、支出規模以及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拓展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適用空間,為促進橫向公平,中央啟用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頻率逐漸加大。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參與主體范圍進一步擴大,東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區的省份都承擔不同類型的對口支援任務。這一時期,不僅有省際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還延伸出省域內地方政府之間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例如,江蘇、浙江、廣東和福建等東部沿海省份探索建立省內橫向財政平衡機制。此外,中央逐步明確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資金投入規模與增長辦法,使財政扶持力度穩步提升。①
改進完善階段(2013年至今)。步入新發展階段,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需求相匹配的現代財政制度深化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應用場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解決這一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完善。支援地政府財政援助力度持續加大,為貧困地區發展注入了大量財政資金。《中國扶貧開發年鑒》數據顯示,—年,參與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東部省份為西部地區投入財政資金8 050 800萬元。在此期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東西部扶貧協作考核辦法(試行)》,以目標和結果為導向,中央對結對雙方協作成效開展考核,初步構建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執行—評價—反饋機制。鑒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本地區具有的適應性和協調性優勢,湖北、四川、河南、湖南和安徽等省份陸續加入省內對口支援行列,基于本轄區內地方政府間財力水平與發展需求建立起不同的橫向財政平衡機制,如表1所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根據財政聯邦主義的觀點,通過財政分權由中央政府和分散化的地方政府分工提供差異化公共產品具有明顯優勢[21]。但在一國的財力分配格局中,出于收入分配、經濟穩定和資源配置等宏觀因素考慮,中央政府往往集中了大部分財政收入,地方政府面臨相對匱乏的自有財力和廣泛的支出需求并存的格局,而中央政府擁有較充裕的自有財力和相對較少的支出需求,引發了不同級政府間縱向財政失衡。與此同時,中央要求各地方政府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但各地方政府所轄區域在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差別在財政上便體現為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充實而部分地方政府財政拮據,產生同一級政府間橫向財政失衡[22]。因此,在客觀上促使中央政府基于自身權威從更高層次予以調節,通過縱向轉移支付或橫向轉移支付補償財政能力相對不足的地方,使得貧困落后地區擁有比過去相對充裕的財力,從而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推動地方政府間財力均等化,實現居民福祉的橫向公平。因此,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會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作用于財政失衡。
⒈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縱向財政失衡的影響
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會從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個方面對縱向財政失衡產生影響。已有研究表明,縱向財政失衡的變化主要源于財政收入的調整[23]。在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實施的過程中,支援地政府的財政資金援助不僅會直接增加受援地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具有財政激勵功能[24],會從更深層次帶動受援地經濟增長[25],進而增強當地政府財政收入能力。經濟欠發達地區受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等因素的制約,長期以來不僅交通、通信和農林水利等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且支撐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本著“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援助思想,支援地政府不單是幫助受援地政府興建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等“看得見”的項目,也引導技術、知識、管理和發展理念等“看不見”的生產要素跨區域配置,發揮了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和溢出效應,逐步提升經濟欠發達地區自我發展能力,避免受援地區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26]。隨著實踐的逐步深入,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除了依賴支援地政府的無償援助,還通過市場化運作促進資金、人才和技術等要素有序轉移,吸引更多的項目、投資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落地。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由早期的物資支援和財政資金轉移支付逐步轉型到兼顧“硬件軟件”的對口幫扶,從而實現受援地由接受外來輸血式救濟到自我造血式發展的轉變[27]。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和創新將推動受援地經濟增長[25],增強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汲取能力。
與此同時,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會規范受援地政府財政支出行為。“項目制”是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落實的基本載體,遵循“項目根據資金定,資金跟隨項目走”的原則,其直接目的是硬化預算約束,從而規避財政資金配置的隨機行為[28]。按照中央政府制定對口支援政策的目標和要求,支援地政府限制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資金用途。財政援助資金需投入到改善受援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提高當地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扶持農業農村發展等項目,重點向基層、民生傾斜。不得用于與民生無關的項目,如行政支出、彌補預算支出缺口和償還債務、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①因此,與縱向轉移支付引致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擴張的理論邏輯不同,即便額外的財政援助資金也很難成為受援地自主安排的收入來源,受援地政府財政支出擴張的能力與意愿不足,因而能夠克服縱向轉移支付導致的預算軟約束問題。此外,以支出結果為導向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通過構建中央與結對雙方、支援地與受援地相結合的績效考核機制,將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資金投入與成效有機銜接,②保障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沿著制度設計的預期軌道運轉[29]。可見,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能夠打破縱向轉移支付的逆向激勵桎梏,成為受援地發展的“援助之手”,從而降低縱向財政失衡。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能夠降低縱向財政失衡。
⒉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橫向財政失衡的影響
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不僅能對縱向財政失衡產生影響,還能直接作用于橫向財政失衡,主要體現為調節同級政府間財政收入和促進結對雙方互利合作兩個方面。稅收是地方政府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而我國稅收體系的生產性特征使得稅收貢獻地與稅收歸屬地之間相互背離,稅收收入進一步向產業集聚地區轉移,不利于政府間橫向財力均衡。而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由上級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主導,經濟發達地區給予邊疆民族地區、欠發達地區、特殊困難地區的政治、經濟、文教科衛等支持。本質上是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再分配,具有非趨利性和指向性特征,有助于矯正原有稅收體系下的財力分布格局。“對口”是資源流動的方向,“支援”是財政資金以及以財政資金為載體的物質、技術、人才等要素匯集和轉移的過程,既體現了“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的縱向層級關系,也體現了結對雙方橫向伙伴關系[30]。與此相對應,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一方面,包含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執行義務;另一方面,包含支援地政府對受援地政府的支援義務,從而實現財政援助資金無償地由支援地向受援地轉移。此外,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具有明顯的指向性,例如,東部沿海省份對口西部偏遠地區的省級層面定向幫扶、省域內發達地區對口欠發達地區的市級、縣級層面定向幫扶,財政援助資金向貧困落后地區精準傾斜,調整了同級地方政府間財政收入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并非“劫富濟貧”,更不是“平均主義”。盡管中央要求支援地給予受援地財政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則的“拉郎配”行為[31],結對雙方不僅有單向援助關系,還存在優勢互補、互惠共贏的雙向經濟合作關系。在資源匹配方面,西部地區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而東部地區具有資金、技術和管理等比較優勢。中央鼓勵結對雙方開展不同形式的互利合作,以經濟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優勢盤活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等要素,將受援地的自我優勢轉化為促進當地經濟持續發展的有益支撐。例如,支援地政府通過設立“飛地產業園區”和招商引資等方式吸引當地企業入駐受援地,實現結對雙方互利共贏,進而促進區域協同均衡發展。作為打破空間壁壘,實現資源地理空間轉移、重新配置的創新實踐,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突破了行政區劃的束縛,提高了地方政府跨區域協同發展的積極性。在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實施過程中,支援地與受援地之間并不存在“為經濟增長而相互競爭的”的財政競爭關系。此外,支援地政府之間可能存在關乎幫扶效果的競爭關系,中央對支援地幫扶績效的考核與評價會促使支援地政府積極扶持受援地發展,以求幫扶效果走在全國前列,從而調節同級政府間的競爭與協作關系[33],矯正橫向財政失衡。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能夠矯正橫向財政失衡。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初始樣本為2003—2020年西部地區所有地級城市,以除新疆之外的其他西部地區地級城市作為新疆的對照組。原因在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期存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發展差距較大,不同地區的城市樣本并不具有良好的對照性。鑒于2010年開始實施的“對口援疆”是全國東部和中部19省份對新疆的支援,因而在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政策效果的評估中,本文將研究樣本限定在西部地區既可以緩解政策內生性,也可以保證樣本的相似性。
對于初始樣本,做如下處理:(1)由于2008年四川發生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發生玉樹地震,中央針對受災區頒布實施了期限不同的對口支援政策,該部分城市在考察期內前后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因此,剔除四川和青海所轄城市。(2)重慶是直轄市,行政管理體制特殊,不存在地級市,因此,不在研究范圍。(3)考慮到西藏以及個別地級城市數據缺失嚴重,本文的樣本中不包含西藏以及數據缺失嚴重的其他城市。(4)由于烏魯木齊是省會城市,克拉瑪依是石油能源城市,中央未將其列入對口援疆政策實施范圍,故剔除烏魯木齊、克拉瑪依等省會城市和能源城市,以增強樣本內各城市之間的可比性。(5)為規避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突發性沖擊,剔除2020年的數據,最終得到西部地區82個地級城市2003—2019年的1 394個面板數據。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有效的實驗組樣本包含:吐魯番、哈密、巴音郭楞、博爾塔拉、昌吉、克孜勒蘇、伊犁、和田、喀什、阿克蘇、阿勒泰和塔城。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及統計公報。
(二)變量選取與說明
⒈被解釋變量
2.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為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Htp)。將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城市賦值為1,其他城市賦值為0。由于本文樣本期是2003—2019年,當樣本年度為2010年之后時取1,否則取0。
⒊控制變量
為了盡可能地不遺漏可能影響財政失衡的其他因素,本文選取了如下控制變量:(1)縱向轉移支付(Vtp),本文借鑒呂冰洋等[36]與向鈺和趙靜梅[37]的做法,用自有財力指標即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比近似衡量。(2)稅收努力(Effort),用實際稅收收入與理論稅收收入的比計算。(3)經濟發展水平(Econ),用地區實際人均GDP的自然對數衡量,利用GDP平減指數對各城市的人均GDP進行相應平減,再計算出各城市的實際人均GDP,對其取自然對數。(4)人口密度(Den),用該城市總人口除該城市面積計算。(5)產業結構(Ind),用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GDP比重度量。(6)固定資產投資水平(Fix),用實際固定資產投資額的自然對數來測度。
(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縱向財政失衡的均值為0. 763,縱向財政失衡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 5倍,說明縱向財政失衡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橫向財政失衡的均值為1. 542,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 884和0. 913,極差為1. 971,說明橫向財政失衡數值分布比縱向財政失衡更為離散,數值波動范圍更大。其余變量取值均處于正常范圍,滿足計量檢驗的基本要求。
(四)模型設定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平行趨勢檢驗
其中,各變量的含義上文已述。
圖1a和圖1b報告了政策估計系數及其95%的置信區間。由圖1a和圖1b可知,在實施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之前的年份,政策變量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95%置信區間包含0),這表明實驗組和對照組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不存在顯著差異。在實施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之后的年份,政策變量的回歸系數均顯著(95%置信區間不包含0),這表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實施以后,實驗組和對照組的變化趨勢具有顯著差異。以縱向財政失衡為被解釋變量時,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由政策實施年份前的不顯著轉變為顯著為負;以橫向財政失衡為被解釋變量時,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由政策實施前的不顯著轉變為顯著為正。這說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會對縱向財政失衡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對橫向財政失衡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雙重差分模型通過平行趨勢檢驗。
(二)基準回歸分析
表3報告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縱向財政失衡和橫向財政失衡的影響。表3中列(1)和列(2)分別是以縱向財政失衡和橫向財政失衡作為被解釋變量時的基準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當被解釋變量為縱向財政失衡時,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為負,且在1%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顯著降低了縱向財政失衡,假設1得到驗證。當被解釋變量為橫向財政失衡時,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為正,同樣在1%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實施使得受援地人均財力水平相較于其他地區變高,有助于緩解橫向財政失衡,假設2得到驗證,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是“援助之手”而非“激勵陷阱”。從實際情況來看,在全國對口援疆實施的十年中,以五年規劃為一個階段,2011—2015年,援疆省份投入財政資金607. 26億元;2016—2020年,援疆省份投入財政資金763. 1億元,19個援疆省份投入的財政資金數量相較于前期有明顯提升。不同支援地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財政資金規模與當地財力水平正相關,東部發達省份如廣東、江蘇、北京、浙江等撥付的財政資金數額位居前列,中部以及東北地區的各省份也給予了受援地不同程度的財政資金支持。①
各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不同,顯著性各異。當縱向財政失衡作為被解釋變量時,稅收努力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稅收努力的程度決定了地方潛在稅收收入轉化為現實收入的可能性,這表明地方政府提高稅收努力是矯正縱向財政失衡的有效措施。縱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縱向轉移支付有助于降低縱向財政失衡。由于縱向轉移支付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力的再分配,地方政府將縱向轉移支付作為自有收入的一部分,因此,縱向轉移支付可以彌補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缺口,改善中央與地方之間失衡的財政收支關系。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人口密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人口密度與縱向財政失衡同方向變動,可能的原因是,較高的人口密度對公共服務配套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財政壓力變大,致使地方財政收支缺口擴大,縱向財政失衡程度加深。產業結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第三產業占比越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經濟較為活躍,地方財政收入能力較強,進而有助于降低縱向財政失衡。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固定資產投資水平越高,會刺激地方經濟增長,帶動財政收入的增加,從而緩解縱向財政失衡。當橫向財政失衡作為被解釋變量時,稅收努力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地方政府增強稅收努力會使得該地區相較于其他地區人均財力水平變高,橫向財政失衡程度向上偏離。縱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這說明縱向轉移支付的橫向財力均等化效應尚不明確。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帶動當地人均財力水平的提升,從而縮小橫向財力差距。人口密度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人口密度的增加使得地方政府相較于其他地區人均財力水平變低,橫向財政失衡程度向下偏離。產業結構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
(三)穩健性檢驗
⒈反事實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法的前提條件是實驗組和對照組具備可比性,即如果沒有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外部沖擊,受援地的財政失衡程度與未受援地的財政失衡程度不會隨時間變化產生顯著差異。反事實檢驗的基本思想是通過設定不存在的事實排除其他因素導致的沖擊效應。若實驗組未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一些其他政策或因素也會帶來當地財政失衡的變化,由于這些潛在不可識別的因素導致的財政失衡變化與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無關,從而使得結論不可信。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參照史丹和李少林[38]的做法,將2008年假設為政策開始實施的時間,進行同基準回歸一致的檢驗,表3中列(3)和列(4)是反事實檢驗的結果。可見,將政策實施時間提前至年時,無論被解釋變量是縱向財政失衡還是橫向財政失衡,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這說明識別的政策效應來源于真實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而非隨機產生。意味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實施能夠矯正財政失衡,前文的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⒉安慰劑檢驗
借鑒Cai等[39]的做法,通過隨機抽取部分城市作為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偽實驗組,并將剩余城市設定為未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對照組,隨后重新構建安慰劑檢驗中的政策交互項。由于偽實驗組是隨機生成的,因此,安慰劑檢驗中的政策交互項應當不會對被解釋變量產生顯著作用,即回歸系數應分布在0附近,且P值大于10%。換言之,如果沒有顯著的遺漏變量偏差,安慰劑檢驗中政策變量的回歸系數不會顯著偏離0;反之,如果估計系數在統計上顯著偏離0,則表明模型設定存在偏誤。為避免其他不可觀測事件對回歸結果的干擾,本文重復500次上述過程進行回歸分析。從檢驗結果來看,無論是以縱向財政失衡還是以橫向財政失衡作為被解釋變量,回歸系數的均值都接近于0,且絕大多數P值大于10%,回歸結果并沒有因為遺漏變量出現嚴重偏誤,這說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財政失衡的影響結果穩健。
⒊PSM?DID檢驗
為克服實驗組城市與對照組城市固有差異造成的內生干擾,本文采用PSM?DID方法進行再次檢驗,利用臨近匹配法進行估計,結果如表3列(5)和列(6)所示。當被解釋變量為縱向財政失衡時,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當被解釋變量為橫向財政失衡時,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再次證明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四)異質性分析
盡管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能夠矯正財政失衡,但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城市初始經濟條件存在差異,可能因為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而導致政策效應存在差別。例如,雖然同為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城市,但受資源稟賦以及歷史發展等因素的影響,新疆內部呈現出“北疆相對強而南疆相對弱”的發展格局。北疆是新疆發展較快的地區,經濟基礎薄弱的南疆則發展相對滯后,進而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財政失衡的矯正作用可能表現出區域異質性。因此,本文將全樣本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兩個子樣本,分別與西部其他城市合并,運用基準模型再次回歸。表4報告了分組后的估計結果,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以縱向財政失衡還是以橫向財政失衡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回歸系數符號方向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且系數均顯著。值得一提的是,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政策回歸系數絕對值高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相應值,這說明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表現出更強的政策效應。根據對口援疆結對關系,經濟基礎薄弱的阿克蘇、喀什、和田等由北京、上海、廣東等東部發達省份對口支援,而經濟狀況相對較好的塔城、阿勒泰等由遼寧、吉林、河南等東北和中部省份對口支援,雖然從支援力度和規模上講前者都大于后者,但異質性檢驗結果表明,并非支援力度越大,政策效應越強。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本身的經濟基礎和財力狀況優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使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實施具有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實施條件,因此,政策效應更為突出。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實施符合我國疆域遼闊、地區發展懸殊的現實國情,其不僅涉及財政資源的橫向分配,同時也是一個涵蓋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重要話題。研究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財政失衡的影響有助于深入了解財政資源分配、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等方面的關鍵問題,為政府制定更具包容性與可持續性的政策提供理論指導。鑒于此,本文梳理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演進邏輯,揭示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不同時期與財政體制的契合性,并總結各階段的特征事實。而且本文從理論層面系統地詮釋了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財政失衡的影響機理,基于2003—2019年西部地區地級城市數據,在對縱向財政失衡和橫向財政失衡進行測度的基礎上,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分析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矯正財政失衡的有效性。研究發現: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顯著降低了縱向財政失衡。并且,欠發達地區在接受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后人均財力水平提高,橫向財政失衡程度有所緩解,與橫向轉移支付理論意義上的財政均衡目標相契合。同時,受政策環境和實施條件的制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對財政失衡的矯正作用具有區域異質性,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相比,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政策效應更強。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重視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制度建設,通過科學設計與完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制度發揮其對財政失衡的矯正功效。有鑒于其矯正財政失衡的積極效果,應當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考慮逐步將其納入現行轉移支付體系,既是補充縱向轉移支付、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現實舉措。
第二,優化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資金分配與績效考核。在財政資金分配環節,應從“基數法”向“因素法”轉變,綜合考慮經濟狀況、財力水平、人口規模與結構等因素科學核定受援地的資金需求量以及支援地的轉移支付貢獻額,使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逐步由臨時性舉措轉變為規范化的長期性財政制度。同時,將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資金績效考核結果作為下一年度項目安排以及資金計劃的重要依據。設置包含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的綜合性評價指標體系,投入方面包括:財政援助資金數量及增長比例、財政援助資金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例、財政援助資金向貧困地區傾斜程度等;產出方面包括:貧困人口脫貧數、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改善程度、群眾滿意度等。從而避免財政援助資金的浪費,有效補充受援地政府履行公共服務支出責任的財力需求,降低縱向財政失衡。
第三,鼓勵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結對雙方根據實際情況創新幫扶機制。從異質性分析可以發現,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在經濟狀況不同的地區政策效果存在差異。這也在客觀上要求支援地政府在財政援助資金投入方面要因時因地而變,避免政策工具的同質化。要充分考慮支援地、受援地資源稟賦與需求,鼓勵受援地主動尋求與發達地區的合作,發揮欠發達地區政府的主觀能動性,實現援助對象精準化、援助方式多元化。只有不斷增強欠發達地區內生可持續發展能力,才能從根本上促進財政均衡,實現居民福祉的橫向公平。
第四,加快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相關配套措施的同步調整調適。例如,加強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中財政以及與之相關的數據統計及公示工作。完善的數據統計及公示是開展科學研究與改進決策的重要基石。我國大量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內容以零星分散的政策文件和簡短報告形式分布在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因此,可參照一般公共預算統計形式,立足實際,重點反映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總體投入情況、財政援助資金使用領域,數據發布應通過單位門戶網站、數據庫等平臺向社會公開。完善財政數據的統計與公示不僅有助于精準把握我國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發展與應用水平,也能為相關學術研究和政府決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 石紹賓,樊麗明.對口支援:一種中國式橫向轉移支付[J].財政研究,2020(1):3-12+44.
[2] 王禹澔.中國特色對口支援機制:成就、經驗與價值[J].管理世界,2022,38(6):71-85.
[3] 伍文中,張楊,劉曉萍.從對口支援到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基于國家財政均衡體系的思考[J].財經論叢,2014,177(1):36-41.
[4] PERSSON T, TABELLINI G.Federal fiscal constitutions: risk sharing and redistribution[J].Journal of publitical economy,1996,104(5):979-1009.
[5] MELLO L 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J]. World development,2000,28(2):365-380.
[6] DABLA N E. Issues in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in China[ R].IMF Working Paper,2005.
[7] 儲德銀,遲淑嫻.轉移支付降低了中國式財政縱向失衡嗎[J].財貿經濟,2018,39(9):23-38.
[8] 劉溶滄,焦國華.地區間財政能力差異與轉移支付制度創新[J].財貿經濟,2002(6):5-12.
[9] BOADWAY R, TREMBLAY J F.A Theory of fiscal imbalance[J].Public finance analysis,2006,62(1):1-27.
[10] BIRD R M, VAILLANCOURT F .Perspectives on fiscal federalism[M].Washington,DC:World Bank Institute,2006.
[11] 賈曉俊,岳希明.我國不同形式轉移支付財力均等化效應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5,289(1):44-54.
[12] 趙永輝,付文林.轉移支付、財力均等化與地區公共品供給[J].財政研究,2017,411(5):13-23.
[13] 趙桂芝,寇鐵軍.我國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均等化效應測度與評價——基于橫向財力失衡的多維視角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6):64-70.
[14] 谷成,蔣守建.我國橫向轉移支付依據、目標與路徑選擇[J].地方財政研究,2017,154(8):4-8+26.
[15] 賈康,程瑜,于長革.優化收入分配的認知框架、思路、原則與建議[J].財貿經濟,2018,39(2):5-20.
[16] 王恩奉.建立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研究[J].改革,2003(1):59-65.
[17] 王磊,黃云生.對口支援資源配置的效率評價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對口支援西藏為例[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15(2):161-176.
[18] 李楠楠.央地協同治理:應急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的法治進路[J].地方財政研究,2021(9):21-30.
[19] 王瑋.“對口支援”不宜制度化為橫向財政轉移支付[J].地方財政研究,2017,154(8):20-26.
[20] 楊明洪,劉建霞.橫向轉移支付視角下省市對口援藏制度探析[J].財經科學,2018,359(2):113-124.
[21] 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72.
[22] 孫開.縱向與橫向財政失衡理論述評[J].經濟學動態,1998(5):66-68.
[23] 魯建坤,李永友.超越財稅問題: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國財政體制垂直不平衡[J].社會學研究,2018,33(2):62-87+243-244.
[24] BOEX J,MARTINEZ?VAZQUEZ J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
[25] 劉金山,徐明.對口支援政策有效嗎?——來自19省市對口援疆自然實驗的證據[J].世界經濟文匯,2017,239(4):43-61.
[26] 丁忠毅,李夢婕.邁向共同富裕的跨域協作治理:東西部協作的政治經濟學闡釋[J].經濟問題探索,2023,486(1):60-72.
[27] 趙明剛.中國特色對口支援模式研究[J].社會主義研究,2011,196(2):56-61.
[28] 謝煒.對口支援:“項目制”運作的梯度適配邏輯[J].中國行政管理,2022,442(4):95-104.
[29] 汪波.中國特色對口支援的激勵機制研究[J].學海,2022,194(2):140-146.
[30] 王宏偉,周光輝.對口支援:破解大國非均衡性難題的創新實踐[J].南京社會科學,2023,423(1):70-80.
[31] 梁琴.由點到網:共同富裕視域下東西部協作的結對關系變遷[J].公共行政評論,2022,15(2):133-153+199.
[32] 杜國明,黎春,何仁偉.中國精準扶貧的區域治理思想解析[J].資源科學,2020,42(4):649-660.
[33] 王小林,謝妮蕓.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從貧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J].探索與爭鳴,2022,389(3):148-159+180.
[34] EYRAUD L, LUSINYAN L.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advanced economi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3,60(2):571-587.
[35] 儲德銀,邵嬌,遲淑嫻.財政體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稅收努力嗎?[J].經濟研究,2019,54(10):41-56.
[36] 呂冰洋,李巖,李佳欣.財政資源集中與預算偏離[J].財經問題研究,2021(1):74-84.
[37] 向鈺,趙靜梅.基于數字經濟的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研究[J].中國軟科學,2023,387(3):203-212.
[38] 史丹,李少林.排污權交易制度與能源利用效率——對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測度與實證[J].中國工業經濟,2020,390(9):5-23.
[39] CAI X, LU Y, WU M ,et al.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rive away in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6,123(1):73-85.
Can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Correct Fiscal Imbalanc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SUN Kai1, NIU Xiao-yan1, ZHANG Lei2
(1.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s a policy too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regulates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t the same level, and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correcting fiscal imbalance. Research on transfer payment and fiscal imbalance in the academia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vertical transfer payment and fiscal imbalance. However, there are few achievements i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by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only conducted qualitative discussion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t reveals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ummarizes facts and features of each stage. Secondly,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t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and summari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Given that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explores fiscal imbalance from a single vertical or horizontal dimension, this paper will incorporate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iscal imbalance into the study. Using data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2003 to 2019, this paper measures fiscal imbalance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iveness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n correcting fiscal imbalance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s beneficial for reducing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fter receiving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the per capita financial resourc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has increased, and horizontal fiscal imbalance has been alleviated. After conduct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on fiscal imbal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regions with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s, the policy effect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is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developed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functional research of 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style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paired-aiding; horizontal transfer payment; fiscal imbalanc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責任編輯:巴紅靜)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0.005
[引用格式]孫開,牛曉艷,張磊.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能夠矯正財政失衡嗎?——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23(10):80-93.
① 廣義的轉移支付既包括縱向轉移支付也包括橫向轉移支付,財政學界研究的轉移支付通常是指中央對地方的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支付,本文表述為縱向轉移支付是為與橫向轉移支付作出區分。
① 2010年,中央確定對口援疆中各支援地政府財政資金投入規模與增長辦法為:參照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扣除部分有專門用途的收入項目)的0.3%—0.6%測算,上年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率高于8%,當年對口支援資金量按8%遞增;低于8%,按照實際增長率遞增;負增長時,除發生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按上年對口支援資金量安排。
① 參與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的地方政府制定了管理辦法,如《上海援滇專項資金管理辦法》(云財農〔2022〕282號),《粵黔東西部協作資金管理辦法》(黔鄉振發〔2021〕2號)等,對資金使用范圍、項目管理、資金撥付和資金監管作出了詳細規定。
② 例如,2017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的《東西部扶貧協作考核辦法(試行)》(國開發〔2017〕6號)中指出,要對支援地財政資金投入增長情況以及受援地財政資金整合、管理和使用效益進行考核。
①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2010年以后,我國經歷了幾次重要的財稅改革,這對縱向財政失衡或橫向財政失衡產生了直接影響。例如,2010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新疆原油天然氣資源稅改革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以新疆為試點地區,對原油和天然氣實行從價計征。同年12月,中央將試點范圍擴大到西部12省份,全面實施原油、天然氣的從價計征改革。油氣資源稅改革可以增加西部資源豐富地區的財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調節區域間的收入差距。2012年,我國分區域、分階段、分行業推行“營改增”,東部地區率先在部分行業試點;2013年開始向全國推廣,西部地區各省份同步實行“營改增”;2016年,為進一步理順“營改增”后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關系,所有行業的增值稅收入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五五分成”。筆者注意到,雖然這些改革會影響財政失衡,但本文的研究樣本已限定在西部地區,考察期內實驗組與對照組同時間執行相關政策,滿足雙重差分模型政策環境一致性的要求。
① 根據各援疆省份政府公開數據整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