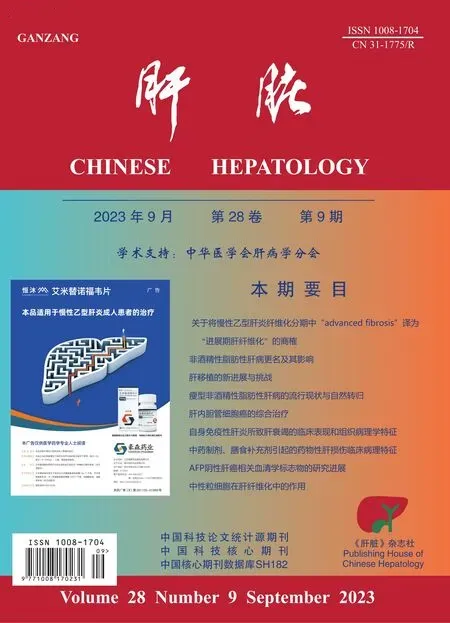術前炎癥標志物評估肝細胞癌手術預后價值的研究進展
彭國慶 王小梅 王瑞 余歡 王思涵
目前,原發(fā)性肝癌是我國第四位常見惡性腫瘤及第二位主要致死病因,其中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典型的炎癥相關惡性腫瘤,占原發(fā)性肝癌的75%~85%[1]。隨著外科技術的進步,肝切除術是目前HCC患者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其預后得以極大改善[2]。但其總體生存率仍不理想,肝癌切除術后5年腫瘤復發(fā)轉移率高達40%~70%[1]。
以往臨床上對HCC患者預后的評估主要根據其生理狀態(tài)(如年齡、性別等)、病理特征(包括病理亞型、腫瘤大小及數量、微血管侵犯、遠處轉移等)及腫瘤微環(huán)境(有無合并病毒感染或肝硬化等)。隨著人類對腫瘤的深入研究,多項研究表明炎癥在腫瘤進展中的重要作用,生物學指標如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纖維蛋白原不僅代表炎癥反應,也可預測腫瘤預后[3-5]。由于腫瘤的復雜性和異質性,在評估炎癥整體情況,運用單項指標價值有限。因此,有學者提出了系列復合指標以更好地預測HCC患者預后,其中包括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淋巴細胞(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PLR)、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FIB)、預后營養(yǎng)指數(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PNI)、控制營養(yǎng)狀態(tài)評分(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COUNT)、天冬氨酸轉氨酶/血小板計數(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 platelet count ratio index,APRI)及天冬氨酸轉氨酶/中性粒細胞(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 neutrophil ratio,ANRI)等。現(xiàn)就此類炎癥標志物對于HCC患者預后影響進行綜述。
一、NLR
NLR為中性粒細胞計數與淋巴細胞計數之比,是臨床常見非特異性炎癥指標,NLR升高提示中性粒細胞升高或淋巴細胞下降。中性粒細胞在腫瘤進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中性粒細胞分泌IL-6作用于癌細胞,并促使其遷移和侵襲腹膜[6, 7];而淋巴細胞發(fā)揮抗腫瘤免疫功能,通過啟動細胞毒性反應,以及抑制癌細胞的增殖、侵襲和遷移,使具有免疫增強作用的CD4+淋巴細胞減少,免疫抑制作用的CD8+淋巴細胞增加。
NLR可預測各種腫瘤患者預后,已證實可作為肝癌患者術后預后指標[8]。但NLR與癌癥關聯(lián)的機制尚不完全清楚,且對其臨界值的判定仍存在爭議。一項關于73例行根治性肝部分切除術患者總體生存情況研究顯示[9],當NLR臨界值為3.46時,與腫瘤分化程度相比,NLR對患者總體生存情況預測效果更好;另有研究表明[10],在首次HCC治療中,以NLR=5為臨界值,NLR值越高,患者中位生存率越低;Johnson等[11]研究發(fā)現(xiàn),NLR以2.5為臨界值,術前高NLR組的疾病特異性生存期和無復發(fā)生存期均降低。綜上所述,NLR臨界值可能因HCC患者接受不同治療而產生差異,因此探尋患者亞組之間的差異及其與癌癥預后關聯(lián)的確切機制是今后研究的重點。
二、PLR
PLR為血小板計數與外周淋巴細胞計數之比,血小板在參與機體炎癥代謝的同時,通過釋放多種細胞因子及血管干擾物質來促進腫瘤生長轉移,是腫瘤進展的關鍵調節(jié)因子。研究表明[12],CX3CL1在缺氧微環(huán)境中誘導血小板直接遷移,促進HCC細胞凋亡,減少原發(fā)性腫瘤生長和自發(fā)性肝轉移,從而改善HCC患者的預后。
有研究表明PLR值越高,患者總生存期、無病生存期越短,且PLR是影響患者預后的獨立因素[13]。Yang等[14]也證實PLR是腫瘤復發(fā)和患者總生存期的獨立因素,進一步指出以PLR=150為臨界值,PLR<150的患者5年生存率為71.8%,PLR>150則為57.2%。PLR臨界值存在差異,大部分集中于100~200。關于PLR預測能力目前存在爭議,國內外多項研究顯示,PLR不是影響HCC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Kabir等[15]研究顯示,PLR未能預測總生存期和無復發(fā)生存期;Zhao等[16]也發(fā)現(xiàn)PLR未能預測無復發(fā)生存期。綜上,PLR預測能力存在爭議,其預測價值有限,仍需進行大量研究探索其預測價值。
三、FIB
FIB是由肝細胞合成的可溶性糖蛋白,在凝血系統(tǒng)、炎性反應和腫瘤系統(tǒng)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高FIB水平可能與腫瘤組織成分中FIB沉積物數量增加有關,從而降低腫瘤細胞黏附性及阻礙細胞基質遷移,導致晚期腫瘤組織轉移,促進早期腫瘤新生血管和組織形成,增強黏附和侵襲作用,在癌癥進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17]。Zhu等[18]首先報道了FIB水平升高與腫瘤分期和HCC患者腫瘤血栓形成相關;Dai等[19]發(fā)現(xiàn)以FIB=4 g/L為臨界值,>4 g/L的患者總生存期更低;由于NLR在腫瘤預后發(fā)揮重要作用,故有學者將FIB和NLR聯(lián)合預測肝癌患者預后情況。有研究將FIB=3.35 g/L和NLR=2.47為臨界值[20],結果顯示F-NLR評分是HCC手術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且與腫瘤病理特征和BCLC分期有顯著相關性,證明了NLR結合FIB預測作用優(yōu)于單一指標。綜上所述,FIB可積極有效地預測HCC患者的肝功能儲備及預后。
四、PNI評分
PNI評分=血清白蛋白+5×外周血淋巴細胞總數,評分降低表示血清白蛋白低或淋巴細胞計數低。相關研究顯示[21],白蛋白不僅反映機體營養(yǎng)狀態(tài),還反映體內肝功能儲備、炎癥等代謝狀況,較低的白蛋白水平與炎性因子升高有關。這導致患者預后較差,同時也增加腫瘤相關病死率。
PNI評分最初由Onodera提出[22],用來評估胃腸手術患者的手術風險和營養(yǎng)儲備。后來多項研究表明,術前PNI評分可用于判斷HCC患者預后。相關研究表明[23],低PNI評分者預后較差,且與腫瘤、淋巴結、轉移分期相關。此外,PNI評分還可以反映患者營養(yǎng)狀態(tài),因此有學者將PNI評分和另一項營養(yǎng)狀態(tài)指標(體重指數,BMI)聯(lián)合應用來評價HCC患者結局[24],證實PNI和BMI是HCC患者結局的獨立預測因子,低PNI評分聯(lián)合BMI可準確預測較差結局,預測范圍比單獨使用更敏感。也有學者將NLR和PNI評分聯(lián)合使用[25],發(fā)現(xiàn)高NLR和低PNI評分患者的總生存期顯著低于低NLR和高PNI評分患者。綜上所述,基于兩個客觀、價廉的實驗室指標,PNI評分可有效預測HCC患者的預后。
五、COUNT評分
CONUT評分最早于2005年由Ulibarri等報道[26],并作為住院患者常規(guī)營養(yǎng)篩查工具。COUNT評分基于總膽固醇水平、淋巴細胞計數和白蛋白水平這3個參數。COUNT評分總分12分,評分越高,表明營養(yǎng)狀況越差,能更準確地反映術前的免疫營養(yǎng)狀況。作為一種新興炎癥標志物,COUNT評分可預測多種實體腫瘤(如胃癌、食管癌等)的預后[27, 28]。在其組成部分中,膽固醇不僅是儲備熱量的指標,還反映終末期肝功能狀態(tài),與癌癥預后不良有關。在生長過程中,腫瘤組織中膽固醇的消耗增加,血清膽固醇濃度降低,導致促炎細胞因子循環(huán)水平升高,促進癌細胞擴散,抑制凋亡。
有研究顯示[29],COUNT評分是HCC患者術后總生存期的獨立預測因素,且評分高的患者總體預后明顯差于評分低的患者;評分高的患者術后并發(fā)癥發(fā)生率高于低評分患者,且30天病死率顯著升高[30]。綜上所述,COUNT評分簡單快捷,能夠很好地預測HCC患者預后,是評估患者術前免疫學和營養(yǎng)狀況的較好選擇,特別是對于血脂異常的HCC患者。
六、APRI
APRI為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與血小板計數比值,是慢性肝病患者判斷肝硬化及肝纖維化的常用指標[31]。相關研究證實,APRI可作為HCC患者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32]。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是評價肝細胞損傷的金標準,當其發(fā)生異常減少或血小板計數異常增加時,APRI會顯著降低,這可能與大部分患者既往合并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等肝炎病史,造成機體正常肝臟組織再生與修復能力較差相關。當癌細胞大量侵襲肝臟時,正常肝細胞被大量破壞,導致溶解機制異常而產生大量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癌細胞為迅速適應機體環(huán)境不斷擴張血管,造成血小板數量急劇上升[33, 34]。
孫波等[35]發(fā)現(xiàn)APRI 是肝細胞癌患者術后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APRI>1.75 提示患者預后差及生存率降低。Maegawa等[36]調查顯示APRI與生存率顯著相關,當APRI>1.5時,患者30天和90天病死率增加。另有研究顯示[37],NLR和APRI是肝癌早期復發(fā)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只有APRI可預測肝癌晚期復發(fā),且APRI越高,晚期復發(fā)風險越大。綜上所述,APRI僅需測定兩項常規(guī)監(jiān)測指標,即可全面反映肝癌患者的肝硬化程度,且對預后有良好的預測價值,但APRI 與肝癌預后的機制尚不完全明確,且臨界值也尚不統(tǒng)一。
七、ANRI
ANRI為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與中性粒細胞計數比值,2016年中國學者首次提出[38],ANRI可用來預測HCC根治性切除術后的腫瘤復發(fā)和生存率。術前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與中性粒細胞對腫瘤患者的預測作用在上文已描述,在此不再進行贅述。
有研究顯示[38],術前ANRI是HCC患者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ANRI水平越高,患者結局越差;以7.8為臨界值,將患者分為高ANRI組和低ANRI兩組,發(fā)現(xiàn)ANRI可預測HCC患者的預后,且術前高水平的ANRI表明預后較差[39]。隨后,有學者探討了ANRI在肝切除術后對于肝內膽管癌的預后價值[40],發(fā)現(xiàn)ANRI不僅可在術前預測患者預后,還對肝內膽管癌各亞組預后具有顯著預測價值。因此,術前ANRI是HCC患者預后的無創(chuàng)且簡單有效的預測指標。由于針對該指標研究較少,且數據來源主要是中國乙型肝炎感染的肝癌患者,故仍需進行大量研究探討其預測價值。
綜上所述,與傳統(tǒng)腫瘤標志物相比,炎癥標志物獲取具有衛(wèi)生經濟學優(yōu)勢,僅通過患者入院時常規(guī)抽血檢查即可計算出多種炎癥指標,從而反映患者預后情況。但此類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多指標有待進一步組合,以提高臨床診斷的準確性;其次,目前各指標臨界值不盡相同,可能與研究對象的種族、樣本量、治療方式存在差異相關,且大部分研究通過繪制ROC曲線,由最高約登指數獲取最佳臨界值,未考慮時間因素影響;最后,當前多數研究局限在單中心或回顧性研究,治療期間指標動態(tài)變化與預后之間是否相關尚不清楚。因此,需探尋患者亞組之間的差異,尋找最合適的方法確定炎癥標志物的最佳臨界值,開展多中心大規(guī)模的前瞻性研究,以及在HCC患者預后中應用,以建立更加科學的評估系統(tǒng)。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