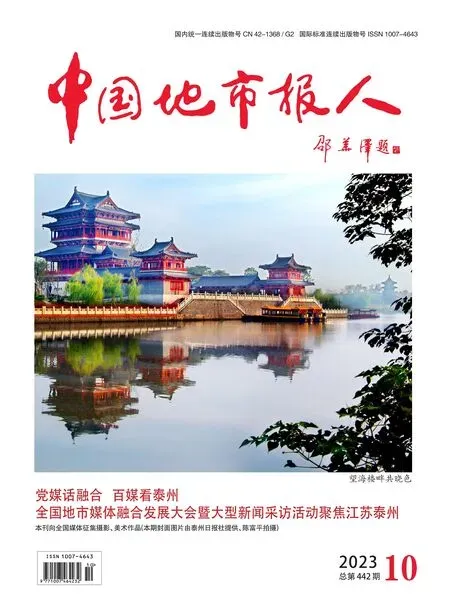講好南充故事 讓地方文化“活”起來
——《南充日報》副刊創新文化報道的探索
夏 新
什么是文化?“文”是記錄、表達和評述;“化”是分析、理解和包容。文化是智慧群族的社會現象與內在精神的表達、傳承和發展的總和,是群族所有物質表象與精神內在的整體。“文”和“化”是動詞,“文化”是名詞,也是動詞。尤其作為延續至今、未曾斷層的中華文化,始終處在不斷演進、不斷革新、不斷升華的過程中,文化存在的意義就不僅僅是讓我們感到驕傲,更是要我們不斷去“文”、去“化”,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創造出更加燦爛輝煌的新的文化,這就是繼承和發展。中華文化是由無數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等組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魅力。深度挖掘地方文化、立體展現文化風貌,是地方主流媒體義不容辭的責任。
四川南充地處川東北,嘉陵江中游,有著2200多年建城史。數千年來,我們的先民創造出繽紛絢爛的文化景觀,如三國文化、絲綢文化、紅色文化、嘉陵江文化等等。近年來,地方政府從發展經濟和旅游業的角度出發,總結、提煉、宣傳、推介地方文化,取得了較大成效。但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其實文化的內涵遠不止此,要豐富、深厚、博大得多,比如,一個村莊、一座古橋、一首詩詞、一門技藝,都有一段獨特的歷史,都蘊含著獨特的文化內涵。怎樣把這些歷史“挖”出來?用哪種方式把這些文化景觀呈現出來?怎樣才能讓這些歷史“活”起來?我們經過深入思考,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嘗試,也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受到政府部門、讀者、社會各界等高度贊揚,為傳承、豐富、發展地方文化走出了一條新路子。
一、以詩文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南充
早在新石器時代,南充境內就有先民居住,夏代為“有果氏”之國,殷商為巴人之國,春秋以來歷為都、州、郡、府、道之治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南充是省級行政機構川北行署所在地,胡耀邦同志曾任川北行署主任。
千百年來,嘉陵江哺育了優秀的南充兒女,積淀了燦爛的文化。從《太初歷》的創制者落下閎到賦圣司馬相如,從《三國志》作者陳壽到“蜀中碩儒”譙周,近現代更有朱德總司令、羅瑞卿大將、民主革命家張瀾先生等革命先賢,可謂人杰地靈,群星璀璨。美麗的嘉陵江也吸引了無數的文人騷客,留下了數以千計的詩文,如“閬中盛事可斷腸,閬州城南天下稀”(杜甫《閬水歌》)“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煙帶月碧于藍”(李商隱《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我初入蜀鬢未霜,南充樊亭看海棠”(陸游《海棠歌》)這些詩文及其背后的故事和人物,是南充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怎樣才能讓它們“活”起來,為大眾所熟知并喜愛?2017年初,《南充日報》編輯部決定在文化副刊推出“歷代名家詠南充”系列報道,報道的方式就是“以詩文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南充”,既尊重歷史文獻資料,又注重實地考察取證,還請有關專家學者解讀、核實、訂正,這樣,就避免了單純對詩文的解讀、文字的簡單“搬家”,通過“揭秘”詩文與人物的關系,一下子就讓“故紙堆”里的歷史文化活起來了。
當年2月,各路記者深入山鄉田野和歷史現場,訪古跡、登山崖、尋后人、查資料,通過各種方式搜集詩文和歷史名人不為人知的故事,對于有爭議的事,進行實地考察,采訪專家學者,還原故事的本來面目。通過大量的采訪,發回了一篇篇生動的報道,如《湯顯祖:相如美辭賦 氣俠殊繽紛》《曾鞏:智勇雙全“萬人敵” 張飛廟里寫傳奇》《溫庭筠:中原逐鹿不由人 從此譙周是老臣》等等。數月時間,在《南充日報》刊發稿件50多篇。這些報道有人物介紹、作品選登、作品賞析、延伸閱讀等,內容豐富、形式生動,可信、可讀,讓人耳目一新、大開眼界,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
當年12月,經過再次編輯加工,這些報道結集成書,由文匯出版社出版,書名為《歷代名人詠南充》。該書出版后,被許多單位和個人收藏。
二、走進地名里的歷史文化
地名,是村莊的文化印記,是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是農業大國,數千年的農耕文明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也塑造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魂。可以說,每一座山,每一條河,每一個小村莊,都是“有故事”的。而這些故事往往和它們的名字有關。
2019年,南充村級建制調整改革啟動。歷時一年,調整改革完成,全市原有的5000多個村(社區),減少到2000多個。有的村(社區)將永遠“消失”,只是留存在人們的記憶里。怎樣才能留住記憶?《南充日報》編輯部著手策劃“我們的村莊——地名故事”系列報道,決定以“地名”為切入口,尤其是村莊的地名,來進行報道,不僅留住記憶,留住歷史,更是深入挖掘村莊的文化內涵,從地理、歷史、名人、文學、民俗等多個角度,探尋地名背后深厚的人文底蘊、文化氣質和人生百態。
經過分析思考,編輯部篩選出100多個有人文故事、歷史文脈的村莊,力求以故事的形式,生動再現與地名有關的歷史傳說、民間故事、趣聞軼事、地名來歷,再現南充特定的時代風貌與歷史文化。
2020年5月,各路記者深入各地鄉村采訪。2020年7月4日,“我們的村莊——地名故事”推出第一篇報道《魯班村:寫在橋上的故事》。報道一經發表,便受到讀者廣泛關注。不少讀者打進本報熱線電話,有的還主動提供采訪線索、幫記者尋找知情人。
隨后,一篇篇報道陸續“出籠”,如《古樓營村 馬氏宗祠的古韻新風》,講述的是儀隴縣柴井鄉古樓營村的故事,據傳該村因張獻忠曾在此屯兵而得名,該村曾經有一面大鼓,每當村里有大事發生,便擊鼓通知全村人集合。該村九成以上都是馬氏族人,如今每年春節、清明節,馬氏后人都會從四面八方趕回家鄉祭祖。《夫子洞村 泥土里“長”出馬王皮影戲》,講述的是南部縣八爾鎮夫子洞村的故事,該村因觀音山摩崖石窟“夫子洞”而得名,誕生了被列入聯合國“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馬王皮影戲而得名。
這些地名中,有的流傳了數千年都沒有變化,成為當地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有的地名則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著這樣那樣的演變,將這些演變串聯在一起,便成了一部生動的村史教科書。每一個地名背后,都有著豐富的傳統、歷史、文化,有鄉風、鄉音、鄉情,凝聚著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人文基因,觸動人們的鄉愁。

《南充日報》開設的文化專欄“我們的村莊——南充地名故事”第63期報道的版面(2022年7月20日七版)。
在近兩年時間里,記者先后采訪了60多個村(社區)地名故事,并在報紙固定位置發表,收到很好的社會效果。該系列報道被評為2021 年度四川省副刊好新聞一等獎。2022年,南充市民政局主動聯系報社,把發表的報道整理成書,出版發行,書名即為《我們的村莊——南充地名故事》。
三、讓“非遺”活起來傳下去
在“文化”這個大家庭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重要成員。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它不僅對于研究人類文明的演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展現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具有獨特作用,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全人類的珍貴財富,在世界文化寶庫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保護和利用好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凝結和綿延,對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義。
怎樣保護和利用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留和延續主要依靠世代相傳,一旦停止了傳承活動,也就意味著消失、死亡”。[1]
目前,南充共有國家級“非遺”項目傳承人4人,省級“非遺”項目傳承人11人,市級“非遺”項目傳承人66人,縣級“非遺”項目傳承人296人。這些人個個“身懷絕技”,平時卻鮮為人知,他們一邊默默堅守在優秀傳統文化的第一線,一邊卻承受著資金、人才、營銷等各種困難。為了更好地弘揚和傳承優秀文化傳統,吸引更多的人關心、關注、支持“非遺”傳承,2018年5月,《南充日報》開辟專欄“走近非遺傳承人”。
根據有關方面的列表,記者走訪一個個“非遺”傳承人,通過面對面采訪,現場觀摩,收集到大量生動的一手資料,把這些“絕技”的來龍去脈、精妙之處,傳承人的喜與愁等等,形成文字,陸續在報紙顯著位置刊發。如《川北大木偶戲第五代傳承人李樂:37年如一日 戲說精彩“木偶人生”》《“嘉陵江石畫”傳承人盧靜:石上作畫 描摹鄉情》《手工打結絲毯編織技藝省級非遺傳承人楊淑芬:方寸之間“織”錦繡 古老技藝薪火傳》等等。
從2018年到現在,該欄目已刊發上百篇報道,不僅讓這些“藏在深閨人未識”的“非遺”項目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走到了前臺,為人們所了解、熟知,而且把這些“非遺”項目的窘境推向了社會,得到更多人的關注和支持,很快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非遺熱”,一些以前面臨失傳危機的項目,得以延續傳承,一些年輕人踴躍加入非遺項目學習、傳承隊伍,如2022年6月17日報道的:扎染入選第二批嘉陵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95后”姑娘孫蓉成為非遺傳承生力軍。至今,“走近非遺傳承人”尚在繼續報道中。
四、文化報道的幾點啟示
《南充日報》近年來的文化報道,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對當地的文化建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不失為成功的嘗試。回顧和總結這些嘗試,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重新審視“文化”,高度重視“文化”。作為黨報,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以經濟報道為重中之重,有意無意之間把“文化”置于次要位置,甚至覺得是“豆芽科”。這實際上是對“文化”的誤解,至少是認識不全面、不深入。我們應該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去認識文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懂得我們的發展“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文化自信,我們的發展才能不迷茫、不走偏。文化是人類在漫長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只有在汲取前人營養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發展。地方文化是一個地方獨特的文化標簽,具有鮮明的文化印記,挖掘、整理、報道好地方文化,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是經濟社會發展之必須,是“文化自信”的具體體現,是地方黨報應盡之責。
(二)策劃先行,任何一次成功的報道都離不開策劃。策劃不是無中生有,不是生編硬造,而是對整個報道的宏觀把握,戰略部署,包括主題設置、內容預設、報道方式、版面安排、報道規模、人員配備等等,都要有一個通盤考慮。過去,我們也曾進行過不少文化報道,但由于策劃缺位,缺乏系統性,大多都淹沒在海量的新聞中,未能產生應有的社會反響。在此番報道中,不僅固定版面位置,還固定記者,固定采訪、寫作框架,既便于閱讀,又形成規模效應,不僅吸引了大量讀者,還培養了編輯、記者,可謂一舉多得。同時,把報紙報道與成書結合起來,形成了更廣泛的邊際效應,使這些文化報道持久發揮作用。
(三)突出故事性,文化報道最大的優勢就是其可讀性。可讀性從何而來?就是要有故事性。故事性從何而來?就是要有人物、有現場、有對話等。無論是“歷代名人詠南充”,還是“我們的村莊——南充地名故事”,抑或是“走近非遺傳承人”,我們始終堅持一條,那就是突出故事性,記者一定要到現場,要與人物直接接觸,要通過活生生的情節、現場、對話,更直觀、更立體、更全面地呈現文化的全貌,使之更具可讀性。在當今互聯網背景下,人們“快餐式”閱讀日益嚴重,報紙只有堅持內容為王,做好質量,做足可讀性,才能吸引更多的讀者。
(四)突出時代感,讓文化活起來找到其現實存在的意義。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文化不僅有點“邊緣化”,有時還與“老古董”畫等號。但事實上,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它不僅是過去人類文明的映照,也是當下人們生活的重要參照。要讓文化活起來,就必須突出時代感,必須找到其現實存在的意義。在“歷代名人詠南充”里,很多作品都有現實生活的影子;而“走近非遺傳承人”,把非遺傳承人的真實現狀、喜樂愁盼淋漓盡致展現出來,躍然紙上;在“我們的村莊——南充地名故事”中,更是濃墨重彩描述這些村莊里的人們努力奮斗、投身鄉村振興、創造幸福生活的故事,讓人讀來倍感親切,有極強的代入感。
當然,地方文化的內涵非常博大,我們所涉及、報道的領域、內容等,還遠遠不夠,報道的方式方法也還有待完善。我們將繼續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