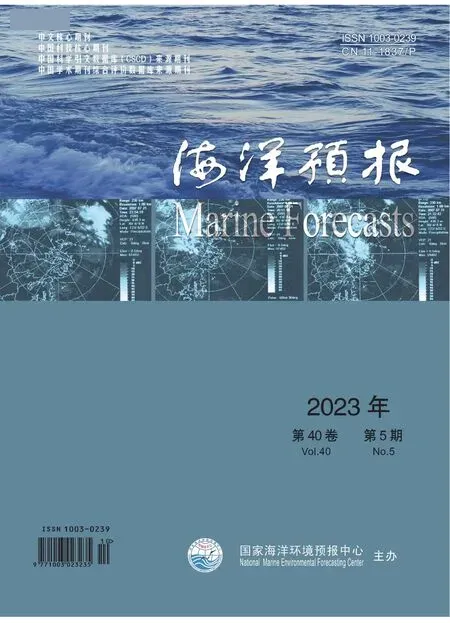基于最優訓練期的風力預報小時級訂正釋用方法
劉菡,於敏佳
(舟山市氣象局,浙江舟山 316000)
0 引言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傳統的氣象預報產品已較難滿足政府部門、市場企業和社會公眾與日俱增的精細化、數智化要求,因此急需研發時空精密、預報精準、數字智慧的預報產品。風力預報事關臨港產業、漁業捕撈、航線運輸的安全與發展,因此精細化的風力預報小時級訂正釋用技術研究至關重要。
目前風力預報的訂正釋用方面已有較多成果。錢燕珍等[1]將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回歸方法應用于近海和登陸熱帶氣旋的強度預報;胡海川等[2]利用概率密度匹配方法對我國近海10 m 風預報進行修正;楊曉君等[3]將BP(Back Propagation)人工神經網絡引入到渤海海風的預報訂正中;趙文婧等[4]應用相似誤差訂正方法訂正了短期風速預報;楊程等[5]基于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開展了區域風速預報訂正技術研究;劉鴻升等[6]設計了最大值-閥值綜合集成法并實現偏北大風的數值預報釋用;李江萍等[7]初步探討了基于統計降尺度方法的數值預報產品釋用技術。以上方法都取得了一定的訂正釋用效果,可應用于實際業務中。
但是,風力預報精細化方面的成果相對較少。美國從2003 年開始最早發展了國家數字預報數據庫[8],可提供逐1h更新、2.5 km/5 km 分辨率的無縫隙網格天氣預報。德國基于強大的數值模式能力,利用多個模式解釋應用和統計后處理預報的優化集成預報方法,提供逐5 min 更新、2.5 km 分辨率的分鐘級—延伸期30 d 的訂正網格預報[9]。陳豫英等[10]采用多元線性和逐步回歸的MOS 統計方法進行風的精細化釋用;楊程等[11]將站點監測資料和數值模式產品應用統計回歸和數據融合技術,對近地面風速產品進行精細化修正;榮艷敏等[12]采用逐步回歸的模式輸出統計方法(Model Output Statistic Method,MOS)方法,針對山東12 個海區指標站的風速進行模式產品的解釋應用;董美瑩等[13]探討了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驅動場水平風場譜逼近技術對浙江臺風精細化預報性能的影響。上述方法均表明可以用數理統計方法對固定間隔時次的預報進行訂正釋用。於敏佳等[14]利用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的關系和逐時加權滾動訂正的方法對風力預報進行了逐小時的精細化訂正釋用,但此方法需逐時滾動更新。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探究適用于日常業務的定時一次性輸出的風力預報小時級訂正釋用技術。
1 資料和方法
1.1 資料說明
風力預報資料采用浙江省氣象局的Fruit細網格產品。該產品是針對中國氣象局下發的ECMWF產品全要素的整合和縮容產品,模式起報時間是20 時(北京時,下同),資料覆蓋區域為0°~60°N,60°~150°E,時間分辨率為3 h,預報時效為0~240 h,空間分辨率為0.125°×0.125°。選取時間段為2020年1月1日—2021年1月1日每日20時的起報場預報數據。
實況最大風速和極大風速資料來自浙江省自動氣象站嵊泗國家基準站、定海國家基本站、普陀國家一般站、岱山國家一般站和舟山浮標站。站點位置見圖1。這些站點代表性強,數據完整,經人工剔除了異常值并消除了缺測記錄,數據較為真實可靠。數據選取時間段為2012 年1 月1 日—2021 年1月1 日,其中2012—2020 年的數據資料用于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關系分析,2020—2021 年數據資料參與最優訓練期計算,并作為獨立樣本進行檢驗。

圖1 指標站站點位置圖Fig.1 Location of index stations
1.2 訂正釋用方法
分三步對浙江省氣象局的Fruit 細網格產品進行訂正釋用。第一步將Fruit細網格產品逐3 h 風力預報線性插值至逐小時;第二步對照實況最大風速選定最優模型,計算得出各預報時效(0~72 h)的最優訓練期,并對各預報時效的風力預報進行訂正;第三步套用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的關系,最終得出基于最優訓練期的訂正釋用后的逐小時極大風速預報。
1.3 效果檢驗方法
對于訓練方法的檢驗,除了分析風力預報誤差的訂正效果外,在實際業務中的可應用性也尤為重要。計算得出穩定的各預報時效對應的最優訓練期是業務可應用的關鍵。在誤差訂正效果方面,利用最優訓練期逐小時計算各預報時效(0~72 h)的訂正釋用效果。結果用修正率(Cri)表示:
式中:MAE0i為各預報時效(0~72 h)采用日常實際業務慣用的人工經驗所得的極大風(如最大風速為5~6 級對應極大風速為7 級)與實況極大風的平均絕對誤差;MAE1i為各預報時效(0~72 h)經本文方法訂正釋用后的極大風平均絕對誤差。
2 最大風速訂正
2.1 最大風速訂正方法
2.1.1 線性回歸
該方法分整年、半年、季度、單月4種方案(以下簡稱4 種方案),利用前一日20 時—當日05 時10 個時次的預報實況偏差,取當日06 時前的2~10 個時次,共9種訓練期,建立預報時效與預報實況偏差的一元線性回歸方程。方程為:
式中:En為第n個預報時效的預報實況偏差;Tn為第n個預報時次;a為回歸系數;b為常數項;a、b通過最小二乘法求解。
2.1.2 加權誤差
按照4種方案,利用前一日20時—當日05時10個時次的預報實況偏差,取當日06 時前的2~10 個時次,共9 種訓練期,計算前一日20 時—后一日20時所有預報時效(0~72 h)的加權誤差:
式中:E為加權誤差;En為當日06時前n個預報時次的預報實況偏差;an為對應時次預報偏差的權重,且an為大于0且和為1的等差數列;d為公差。
假設:越靠近06時(預報時次)的預報實況偏差(前一日20時—當日05時)越具參考性,則d<0。
根據設定,求a1和d的取值范圍并取值:
因為a1+a2+...an= 1,且an為大于0 的等差數列,所以
因為an=a1+(n- 1)d>0,= 1,將代入式(4),則
2.1.3 平均誤差
按照4種方案,利用前一日20時—當日05時10個時次的預報實況偏差,取當日06 時前的2~10 個時次,共9 種訓練期,計算前一日20 時—后一日20時所有預報時效(0~72 h)的平均誤差。計算公式為:
式中:E為平均誤差;En為當日06時前n個時次的預報實況偏差。
2.2 方法對比
2.2.1 訂正效果
按照4種方案設計線性回歸、加權誤差、平均誤差3種訓練方法,取當日06時前的2~10個時次,共9 種訓練期,計算各站點各預報時效(0~72 h)的最優訓練期及對應的最小平均絕對誤差。結果表明(見圖2),3 種方法對風力預報誤差都有改進,其中線性回歸法表現出較為平穩的小波動性,加權誤差法和平均誤差法在0~15 h 之間波動幅度較大,這表明兩種方法對于0~15 h 預報時效具有明顯的訂正效果(在10 h處最大風速絕對誤差達到0.2 m/s的精度),11 h 后訂正誤差快速增加,直到15 h 處回歸小波動性緩慢增加的態勢。因此,0~15 h加權誤差法和平均誤差法的風力預報誤差改進優于線性回歸法,具備更好的臨近預報訂正效果。

圖2 各訓練方法0~72 h預報時效訂正前后站點風力誤差對比和最優訓練期分布Fig.2 Comparison of wind force errors and distribution of optimal training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correction of 0~72 h forecast time of each training method

圖2 (續)Fig.2 (Continued)
對比分析5 個站點的訂正效果。地形方面,定海地形遮蔽最為嚴重,模式預報原誤差也最大,岱山、普陀次之,嵊泗遮蔽少,舟山浮標四面開闊,代表性最好。風力預報誤差方面,與嵊泗、舟山浮標相比,岱山、普陀常年風力小,原預報誤差相對較小;定海原風力預報誤差存在24 h 的周期變化性,其中大致在12~24 h、36~48 h、60~72 h 存在明顯的日變化特征,且每日12 時達到最小,具備一定的規律性,加權誤差法和平均誤差法并不適用,在原誤差最小的時次訂正誤差反而較大,而線性回歸法則抹去了原誤差的日變化性,訂正效果相對較優。
綜上分析可知,0~15 h 加權誤差法和平均誤差法的風力誤差訂正效果明顯優于線性回歸法,15 h 后3 種方法訂正效果相差較小;但對于受地形遮蔽較大且原誤差存在日變化的站點,線性回歸法優于加權誤差法和平均誤差法。
2.2.2 業務應用
圖2 還展示了3 種方法的最優訓練期。線性回歸法最優訓練期以2 h 和10 h 為主,但各站點存在差異,且同一站點各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也變化較大。加權誤差法和平均誤差法在各個站點的表征一致,最優訓練期都以10 h 居多,在0~10 h 預報時效內最優訓練期從10 h快速遞減到2 h,而在10~20 h預報時效內最優訓練期又出現快速遞增。
圖3 為4 種方案在9 種訓練期(2~9 h)下計算的各預報時效(0~72 h)的平均絕對誤差。結果表明,線性回歸法誤差發散,最優訓練期不穩定,沒有可用于日常業務預報的最優訓練期。加權誤差法和平均誤差法的結果大致相同,誤差不發散,最優訓練期穩定,可將10 h 作為0~5 h 和20 h 后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但5~20 h 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并不明確。

圖3 各站點0~72 h預報時效平均絕對誤差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mean absolute error of 0 to 72 h forecasts at each station
分別計算了在4 種方案下利用3 種方法得到的5 個站點(每個方法共20 個樣本總量)各預報時效(0~72 h)的最優訓練期的概率分布。從圖4 可以看出,線性回歸法的最優訓練期分布散亂,以2 h 和10 h為主,除7~11 h預報時效對應的最優訓練期概率達50%以上外,其余預報時效均較低,無法給定各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加權誤差法對0~5 h、23~72 h 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分布有明晰表現,6~10 h、16~22 h 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概率也都大于50%,但仍有5個預報時效(11~15 h)的最優訓練期分布相對較廣,其中11~12 h 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以2 h 為主,13 h 預報時效以4 h 為主,14~15 h預報時效以10 h為主;平均誤差法則對0~10 h、16~72 h 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分布有明晰表現,11~12 h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以2 h為主,13 h預報時效以4 h為主,14~15 h預報時效以10 h為主。

圖4 各方法預報時效最優訓練期概率分布Fig.4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optimal training period of each prediction time
總體而言,線性回歸、加權誤差、平均誤差3 種方法在業務應用層面效果遞進。線性回歸法各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散亂且無法確定,業務應用效果差;加權誤差法對0~5 h、23~72 h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表現明晰,平均誤差法則將明晰范圍進一步擴大到0~10 h 和16~72 h 預報時效,但兩者在11~15 h預報時效都未給出絕對大概率值,根據概率分布可知,2 h、4 h、10 h 分別為11~12 h、13 h、14~15 h 預報時效的最大概率最優訓練期。
3 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關系
對于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的關系,目前已有較多研究[15-24]。對各站點以一元線性方程進行擬合,并計算相關系數和絕對誤差,結果見表1。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較好地符合y=ax+b的一元線性關系,在沒有地形影響的開闊海面上,舟山浮標的相關系數更是高達0.99。

表1 站點擬合方程和效果檢驗Tab.1 Site fitting equation and effect test
3.1 地形影響
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的關系與地形密切相關。地形作用主要包括山體阻擋、爬坡、狹管效應、繞流等,都會對風力的陣性產生影響。各縣區測站16風向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擬合方程各不相同(見圖5a—c),所擬合的一元線性方程中的常數項仍相對較小,最大的也僅有0.84,在推算極大風速時,也僅有不到1 m/s的影響,可見在以最大風速推算極大風速時,起主導作用的是一元線性方程y=ax+b中的一次項系數a(即風力陣性系數)。嵊泗、岱山、定海、普陀4 個縣區本站分16 風向的系數a分別為1.18~1.58、1.40~1.93、1.60~2.15、1.43~1.91,當最大風速達到13.9 m/s(風力為7 級)時,4 個縣區本站在16 風向上的極大風速最大差可達5.56 m/s、7.37 m/s、7.65 m/s、6.67 m/s;而對舟山浮標分16風向進行分析發現(見圖5d),該海上浮標站16風向的陣風系數基本穩定在1.11~1.15,各風向上的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關系基本一致。由此可見,地形的作用致使各個風向上風力陣性差異明顯,風向不同,陣性系數a也不同,a差異越大,則風力的陣性差異也越大。

圖5 嵊泗、岱山、定海、舟山浮標16風向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關系對比圖Fig.5 Correlation between maximum and extreme wind speeds at Shengsi,Daishan,Dinghai and Zhoushan buoys
3.2 下墊面影響
相較于陸地和沿海粗糙的硬地下墊面,海上下墊面為光滑水面,在大尺度運動中,海上空氣質點的運動較遵從地轉風規則。對比2012 年1 月—2020 年1月嵊泗、岱山、普陀、定海4個縣區本站和舟山浮標站16風向的實況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之差,發現4 個縣區本站相差較小(差值分別為2.51 m/s、2.37 m/s、2.37 m/s、2.51 m/s),而舟山浮標站的平均差僅為0.91 m/s。在各個風向上,舟山浮標的風力陣性都明顯小于硬地站點(見圖6),因此下墊面也是直接影響風力陣性系數a的因子之一。

圖6 嵊泗、岱山、定海、普陀、舟山浮標16風向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之差對比Fig.6 Comparison of maximum and extreme wind speeds at Shengsi,Daishan,Dinghai,Putuo and Zhoushan buoys
3.3 天氣系統影響
當有臺風、冷空氣、低壓等系統影響時,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的差異往往較大,能達到8 m/s 甚至10 m/s 以上,這與同等氣壓梯度條件下的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之差有較大差別。對2012—2020 年在低壓、冷空氣、臺風3個系統影響下對應時次的最大風速和極大風速進行擬合發現(見圖7),嵊泗、岱山在各系統影響下的差異比較小,岱山站的陣性系數基本都在1.5 左右,嵊泗的陣性系數基本在1.2 左右;而定海和普陀的差異比較大,低壓和冷空氣在定海站的陣性較強,陣風系數高達1.85 和1.9,定海臺風的陣性系數僅為1.59。舟山浮標低壓、冷空氣和臺風的陣性系數分別為1.14、1.15、1.2,結果較為接近,舟山浮標不分影響系統的陣風系數也為1.14。因此可以看出,各天氣系統對于陸地和沿海風力的陣性有影響,而在開闊的漁場上,各天氣系統的風力陣性基本一致。

圖7 站點分系統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關系對比圖Fig.7 Comparison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ximum wind speed and extreme wind speed in station sub-system
4 訂正釋用效果檢驗
利用本文訂正釋用方法,計算各站點各預報時效(0~72 h)逐小時的極大風速平均絕對誤差修正率,并與日常業務慣用的人工經驗結果進行對比,結果見圖8。除個別站點的個別時次外,基于最優訓練期的訂正釋用方法總體修正效果較好,5 個指標站點的修正率分別達到14%、16%、34%、9%、31%。定海和舟山浮標的修正效果最好,72 h 的平均修正率超過30%,其中舟山浮標在各預報時效均有正修正效果,最高達到40%以上,定海除在個別小誤差時次修正效果為負外,總體為正,最高達到50%以上;嵊泗基本也為正修正效果;岱山、普陀負修正時次相對較多,但總體仍是正修正效果。

圖8 各站點日常業務慣用方法與訂正釋用方法對比修正率Fig.8 Comparison of correction rate between routine business methods and revised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t each site
5 結論
本文介紹了一種基于最優訓練期的風力預報小時級訂正釋用技術,該技術加密細網格風力預報產品至逐小時,選用平均誤差最優訓練期模型,利用站點最大風速和極大風速的關系進行訂正釋用。相比實際業務慣用的人工經驗,該方法具備一定的改進效果。結論如下:
①以平均誤差為模型的最優訓練期方法能有效改進ECWMF 模式的風力預報結果。加權誤差法、平均誤差法在0~15 h 預報時效的改進結果明顯優于線性回歸法,15 h 后3 種方法的改進效果相差較小。線性回歸法對于各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散亂不確定,業務應用效果差;加權誤差法對0~5 h、23~72 h 預報時效的最優訓練期表現明晰,平均誤差法則將明晰范圍進一步擴大到0~10 h 和16~72 h預報時效,但兩者在11~15 h 預報時效都未給出絕對大概率值,根據概率分布結果,2 h、4 h、10 h分別為11~12 h、13 h、14~15 h 預報時效的最大概率最優訓練期。
②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的關系總體上以一元線性回歸為主,但與地形、下墊面、天氣系統等有關。地形致使各風向的風力陣性差異明顯,嵊泗、岱山、定海、普陀4個縣區本站各風向陣性系數范圍分 別 為1.18~1.58、1.40~1.93、1.60~2.15、1.43~1.91,而海上浮標站16 風向陣性系數基本穩定在1.11~1.15;下墊面不同導致風力陣性也不同,4 個縣區本站最大風速與極大風速16 風向的平均差分別為2.51 m/s、2.37 m/s、2.37 m/s、2.51 m/s,而舟山浮標站的平均差卻僅為0.91 m/s;與陸地沿海站點不同,在開闊的海面上,各天氣系統的風力陣性基本一致。
③基于最優訓練期的風力預報訂正釋用方法能有效利用實況數據,將精細風力預報提高至小時級,改進了ECWMF 模式的訂正釋用效果。對比實際業務人工慣用經驗結果,除個別站點的個別時次外,本文使用的訂正釋用方法總體上修正效果較好,各站點的修正率為9%~34%,其中定海和舟山浮標的修正效果最好,72 h平均修正率超過30%。舟山浮標在0~72 h各預報時效上均有正修正效果,最高超過40%;定海除在個別小誤差時次修正效果為負外,總體修正效果為正,最高達到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