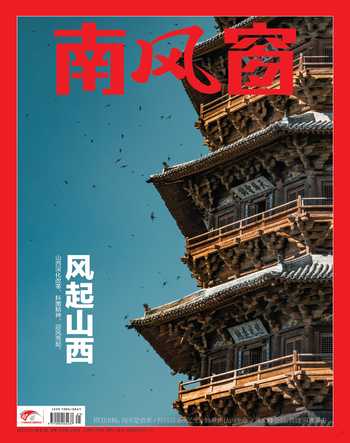全球經濟的敵人并非保護主義
“自由貿易時代似乎已經結束。保護主義籠罩下的世界經濟將向何處去?”這是目前我所耳聞的最常見的問題之一。但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之間的區別,并非特別有助于理解全球經濟,甚至還歪曲了近代歷史。
“自由貿易”令人聯想到政府后退一步,允許市場自行決定經濟格局。但是,任何市場經濟均需要規章制度,它們通常由政府頒布和執行。此外,當國家管轄權借助國際貿易和金融建立聯系時,還會產生其他問題:全球市場企業競爭應優先遵守哪些國家的規則和法律?是否應當通過國際條約及區域或全球機構來實現規則的重新制定?
從這個角度來看,顯而易見,從1990年代初一直持續到新冠疫情暴發才結束的超級全球化,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時期。過去30年所簽署的貿易協議,與其說重點在于取消對貿易和投資的跨境限制,還不如說關系到監管標準、健康和安全規則、知識產權、勞工、環境等此前屬于國內政策領域的問題。
上述規則也并不中立,它們往往優先保障國際銀行、制藥企業和與政治相關的跨國公司等大企業的利益。上述企業能更順利地進入全球市場,那些旨在推翻致使利潤減少的政府規章的特別國際仲裁程序,也主要使它們受益。
同樣,收緊知識產權規則—即容許醫藥和科技企業濫用其壟斷權力—這樣的私貨販賣,實際打著放松自由貿易的幌子。政府被迫放松資本流動,但勞動力卻依然受困于邊境封閉。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問題遭到忽視,部分原因是超級全球化議程將之排擠在外,但同時也因為上述兩個領域所創造的公共產品都將損害商業利益。
近年來,我們親眼看見了上述政策所引發的強烈反對,以及對更大范圍內經濟優先政策的重新考慮。遭到某些人譴責的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思想,實際是在重新“平衡”解決勞動力流離失所、地區落后、氣候轉型和公共衛生等重要國家問題。對療愈超級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和環境損害以及為未來建立某種更為健康的全球化形式而言,上述進程均不可或缺。
美國總統拜登推出的產業政策、綠色補貼和美國制造條款,就是這種重新定位最為顯著的例子。誠然,這些政策在歐洲、亞洲和發展中世界引發了憤怒,因為它們被視為與既定的自由貿易規則背道而馳。但它們往往也在同樣的國家,被尋求超級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替代方案者視為有效模式。
我們不用回溯太遠的歷史,就可以找到上述新政策可能形成的類似體制。在1980年代初曾盛極一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各國政府在工業、監管和金融政策領域,均保留了很大自主權;相較于全球一體化,當時許多國家更重視國內經濟。當時的貿易協定,范圍狹窄且力度薄弱,對發達經濟體、更不用說對發展中國家,幾乎鮮有限制。對短期資本流動的國內控制在當時是常態,而不是例外的東西。
盡管當時的全球經濟更加封閉,但事實證明,布雷頓森林時代對重大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更為有利。發達經濟體收獲了數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經濟的相對平等。那些采取了有效發展戰略的低收入國家—如東亞四小虎—實現了跨越式增長,盡管它們當時面臨比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高得多的壁壘。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傳統,理應讓那些認為允許各國保留更大余地以推行其自身政策必然不利于全球經濟的人重新考慮。相比所謂的背叛“自由貿易”,對地緣政治競爭管理不善,更容易令全球經濟陷入困境。決策者和評論人士必須對真正重要的風險保持關注。
丹尼·羅德里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國際經濟學會主席,著有《貿易直言:對健全世界經濟的思考》。本文已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