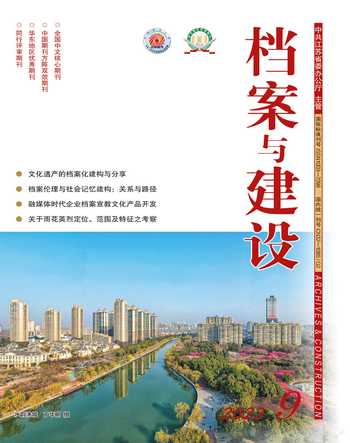對質疑檔案客觀性的理論思考
呂文婷 吳林澤
摘 要:受后現代主義影響,質疑檔案客觀性的聲音中尤以檔案記憶觀中對權力和檔案關系的研究為甚。文章首先簡述了質疑的濫觴與后患,然后基于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視角從理論角度對質疑檔案客觀性的聲音進行思考,認為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并非水火不容,主觀性更不是對客觀性的“玷污”,通過戳破質疑的“紙老虎”為檔案正名。
關鍵詞:檔案客觀性;后現代主義;合目的性;合規律性
分類號:G270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Questioning the Objectivity of Archiv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urposiveness and Regularity
Lyu Wenting, Wu Linze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the voices in academic circles questioning the objectivity of archives are obvious, especially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wer and archives in the view of archival memory.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origin and future problems of the questioning, and then considers the voices of questioning the objectivity of archiv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urposiveness and regularity. It is believed that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 archives and archival management are not incompatible, subjectivity is not a stain on objectivity, and the name of archives is justified by puncturing the "paper tiger" of doubt.
Keywords: Objectivity of Archives; Postmodernism; Purposiveness; Regularity
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后檔案學界對檔案與記憶關系的探討明顯增多,如丁華東認為檔案是控制社會記憶的“結構性媒介”[1],徐擁軍在檔案與社會記憶的雙向建構關系的基礎上思考了檔案職業的形象[2]等;也有學者探討權力在檔案建構社會記憶中的積極與消極作用[3-4]。但隨著檔案與記憶研究的深入,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也被質疑是否客觀、中立。弗朗西斯·布勞因指出“檔案是權力的共謀”,統治者通過控制檔案來決定誰可以被記住[5],其觀點隱含了權力通過對檔案的控制來建構國家的歷史記憶;而特里·庫克也指出主要的歷史詮釋行為發生在檔案工作者裝盒之際,“在于另外98%被銷毀的未裝進檔案盒的文件潛在的影響”[6];阿萊達·阿斯曼認為“對檔案的控制就是對記憶的控制”[7];米歇爾·福柯認為檔案是在權力的作用下片面地展現出來以達到控制社會記憶的目的[8]。其中關于權力對檔案、對社會記憶的影響廣泛地引起了對檔案原有的客觀性的質疑,檔案作為原始憑證的立身之本受到刀刃向內的后現代主義極大地沖擊。徐擁軍和熊文景基于唯物史觀針對后現代主義檔案觀的謬誤之一——消解檔案的客觀性[9]進行批判,但文章更多地著眼于檔案的客觀性在其被解釋時的不確定性,而本文則嘗試從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視角聚焦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中主觀性與客觀性二者關系,這或將有助于回應后現代主義對檔案客觀性的質疑。
1 質疑的濫觴與后患
在百花齊放的后現代檔案學學術圖景中,檔案記憶觀的成果格外豐碩,自1996年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以來檔案記憶逐漸成為國內檔案學界的研究熱點。在后現代主義影響下,學者們運用社會學理論研究檔案記憶時,對于檔案的客觀性難免產生質疑——檔案真的可以講述真實的歷史嗎?質疑檔案客觀性的聲音逐漸抬頭,給學界相關理論的進一步研究及實踐工作開展帶來了后患。
1.1 質疑的濫觴
無論中外,官方對檔案的管理行為自古有之。檔案一詞,在外文中起源于古希臘的“ ρχε ον”,其本意是“官署所在的地方”[10];中國“檔案”的詞源從語義與字源角度出發,經歷了“中”—“當”—“檔”的演變,“中”字蘊含著“法令”的意味[11],因而檔案的政治功能千百年來在中國也為王朝統治者所重視,藏于石室金匱。官方對檔案的管理行為一直被認為是政府的應有之義,不管是歐洲檔案學的鼻祖亞克伯·馮·拉明根認為登記室應是與辦公室和財務室并列的機構[12],還是中國漢朝的官方檔案保管機構如蘭臺、東觀,其中嚴密存放的是詔令、奏章、律令、地圖、官員人事檔案等官方檔案,都是以記錄國家活動為心,檔案是權力的檔案,服務于塑造國家檔案敘述體系。國家權力默默地建構著檔案,既包括檔案作為歷史證明的觀念,也包括檔案的資源實體[13],而對檔案客觀性的質疑濫觴于后現代主義,尤其是以否定性為主要特征的解構性后現代主義。
后現代主義于20世紀50年代出現,盛行于80年代,是后工業社會背景下對工業文明弊端的反思。后現代主義反對一元的話語權威,追求多元性、差異性與不確定性,反對基礎主義和本質主義[14],其對現代主義及其價值取向的激烈批判在諸多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解構了人類社會原有價值的相對確定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福柯、德里達等人為代表的解構性后現代主義與檔案學結合的產物——后現代檔案學理論在拓寬檔案學研究道路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理論與實踐上的變革。檔案記憶觀深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人們發現了檔案的記憶屬性,伴隨著理論中關于檔案與身份認同、檔案與社會記憶的探索不斷深入,檔案與權力的相關研究為質疑檔案的客觀性提供了土壤,對檔案一貫真實的、客觀的、中立的形象進行了解構。隨著后現代檔案學者將目光投向檔案管理活動,以往人們習以為常的檔案管理流程在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觀照下也不再是原本正當、合理的面目。
1.2 質疑的后患
對檔案客觀性的質疑給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造成了負面影響。從檔案價值的消解到檔案職業的危機再到對檔案事業的誤解,這些影響必須引起重視。
(1)檔案價值的消解
檔案實體中的主觀性被發現,檔案被指責其從形成到利用都遵循著統治階級的有目的的計劃。后現代檔案學者一反原有的經驗實證主義的檔案本體概念,不再認為檔案僅僅是一種客觀存在,而是在其概念中強調了主觀性成分。檔案與權力千絲萬縷的關系使得檔案不再只是記載歷史事實的故紙堆,而是在權力的互動下集體建構的產物,檔案最后成為了權力斗爭的外化結果。正如德里達提出的檔案化行為不僅僅是記錄事件,更是包括對事件的背景及過程的關注、記錄和闡釋。[15]王明珂也指出渭水流域出土的西周青銅檔案展示了當地貴族從里到外的層次認同結構。相較于把檔案文獻作為歷史事實的載體,探究檔案中隱晦傳遞的“這是誰的記憶”“它對制造者有何價值”以及“為何是它而不是別的檔案被保存下來”[16]要有趣得多。
詮釋學理論的引入使得原本固化的檔案文本不再只有一種解釋,后現代主義學者主張“不存在事實,只存在解釋”[17],后現代主義檔案學者更傾向于將檔案看作一種“超越時空的人類交流方式”[18]。檔案并非是被詮釋的客體,而是與其使用者平等對話的另一個主體。由于對話的檔案使用者不同,在這種詮釋模式下,檔案文本信息所傳達的歷史事實也具有不確定性,檔案使用者(尤其是歷史學家)得出的歷史解釋也并非一致,同時對每一個檔案文本的詮釋并非只有一次,也不是固定確定的,共時性的與歷時性的歷史解釋趨向多元化會造成社會民眾心中歷史記憶的多元,使得歷史事實在人們心中逐漸模糊,對檔案憑證價值的尊崇也不復往日。
(2)檔案職業的危機
在對檔案實體進行解構之后,與檔案管理關系最密切的檔案職業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討論。檔案職業公信力建立在檔案及檔案職業的客觀性上,檔案的客觀性來源于傳統認知中檔案因其原始記錄性而成為堅實的證據,詹金遜主張檔案工作者應保持超然的工作心態,避免個人的主觀因素介入到檔案管理工作,提倡被動地接收檔案,而非主動地收集。[19]這樣看來檔案工作者只需要按章辦事,做好檔案的保管者即可。但在后現代主義視角下,檔案工作者在按照權力允許的規章制度去收集、整理、鑒定、保管、銷毀和利用檔案時便已經失去了其試圖保持的客觀中立的地位,成為權力控制檔案的“幫兇”。檔案管理工作的每個流程都體現著權力之手的控制,都隱含著檔案工作者的主觀性。檔案工作者不是客觀的保管者,傳統的檔案職業公信力遭受質疑,檔案工作者的職業形象面臨危機。
(3)檔案事業的誤解
檔案事業,從廣義上來說就是檔案工作,包括各種對檔案和檔案工作進行管理的活動,通過管理和開發利用檔案信息資源為國家和社會各項事業服務。由上述對檔案及檔案職業的主觀性論述不難得出具有明顯后現代主義色彩的結論:檔案事業中也必定包含主觀性,不管是個人的還是組織的,檔案事業都難以脫離權力的影響,是建構符合權力需要的主流話語的工具之一。在后現代主義的審視下,從檔案業務管理、檔案行政管理、檔案法治、檔案教育、檔案科研到檔案宣傳、檔案服務、檔案國際合作與交流等一系列有人參與的工作都充滿著人的主觀目的性。檔案事業的政治性被過分強調,筆者認為這是對檔案事業的誤解。
2 對質疑的思考
2.1 合目的性視角
雖然后現代主義對權力及其影響檔案的客觀性進行了批判,但若結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推敲便可柳暗花明,為檔案正名。質疑檔案客觀性的立足點均在于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中的主觀性,但其主觀性與客觀性并非只是單純的矛與盾的關系。
部分學者在承認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具有主觀性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無法避免其中的主觀性,那檔案工作者便應該積極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推動檔案資源體系建設走向開放,構建多元的、囊括社會各階層的社會記憶,維護社會與歷史的公平正義。[20]這種觀點雖然肯定了檔案工作者正確發揮主觀性的正面作用,但仍將主觀性與客觀性相對立,是一種試圖彌補主觀性給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的客觀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做出的努力。那么是否可以直接正面肯定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中主觀性的作用呢?覃兆劌教授認為,“檔案是處于合目的控制的憑證信息”[21],該觀點將檔案看作人類合目的的產物,不再單純認為檔案只是人類社會活動的自然的客觀副產品,檔案是人有意識地形成和控制的,正視了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中人的主觀目的性。
在后現代主義影響下,關于權力對檔案影響的研究大多習慣性地將人的主觀目的看作洪水猛獸,認為人的主觀性破壞了檔案神圣的原始憑證價值。但是,社會歷史過程并非一般的客體運動過程,社會也不是獨立于人這一主體之外的實體,而是一個由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體構成的有機系統。劉福森指出,在對社會歷史進程的把握中不能忽視其主體性,應注意把握其合目的性與選擇性。[22]具體到檔案學領域上,我們應當認識到不管是檔案的書寫還是受控管理,其實踐活動的主體都是人,實踐主體的合目的性與選擇性應當得到正視,而并非詹金遜認為的那樣——檔案人員的個人判斷會玷污檔案的證據神圣性和妨礙保存檔案的目的[23]。檔案事業肩負著偉大的歷史使命,是黨和國家建設各項事業不可或缺的環節,是歷史得以延續的前提和基礎,不僅要做到對歷史負責、為現實服務、替未來著想[24],更要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社會歷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上的展開,而人的實踐活動又無不是有各自目的的。合目的性思維是貫穿人類認識與改造世界過程中的兩大思維之一,人恰恰是在按照自己的目的、計劃參與實踐活動中體現了自身的主觀能動性。這也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同于以往哲學家將現實中的人從歷史中剝離出來的做法,唯物史觀視野下的歷史是人的歷史,本質上是人類追求著自己目的的實踐的歷史。[25]因此,不管是權力影響下的檔案規章制度還是檔案工作者懷著自己的主觀意圖參與檔案管理工作,就其行為本質來說不外乎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合目的性。
此外,歷史活動的目的是預期的,而歷史活動的結果則是非預期的,雖然個人通過實踐去實現各自的目的,但在無數個人意志相互沖突、作用以后形成的結果往往不是任何一個人可預想到的,這也是恩格斯的“歷史合力論”的重要觀點之一。[26]個人目的之間的差異性在相互碰撞中被消弭后留下的是其共同性,這是超脫于個體的社會運動的總體要求與趨勢,是各方意志的最大公約數,也就是說檔案管理工作最后并非是被某一方單獨決定的,而是各方力量相互作用后被社會整體接受的結果。因此檔案的書寫以及受控管理中的主觀性不是由行為主體單方面決定,而是也會受到其周圍主體主觀性的影響。以檔案事業發展為例,在中國的決策體制下,中國共產黨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這一根本組織原則,將其貫穿于民主政治之中,要求“正確處理黨委同人大、政府、政協、司法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關系,實施黨委決策、人大立法、政府實施、政協建言的聯動機制,改進領導方式和方法,做到領導、統攬、統籌、協調而不包辦代替”[27],上述反映了中國的協商政治傳統。楊光斌提出,“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幾乎滿足了共識民主的所有要求和特征”[28],狹義上的共識民主是一種謀取共同認識的民主,例如在多元利益分化的社會中制定決策,既聽取各方的意見和建議,同時又與各方協商討論,在各方達成基本共識的基礎上作出決策。我國檔案事業的許多重大決策都體現了共識民主,例如1987年誕生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其歷時8年,改稿30余次,既體現了黨和政府的意志,也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共同意愿[29];又例如編制《“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堅持開門問策,深入10多個省(區、市)和部分中央國家機關、國企、高校開展調研,召開座談會、研討會20余場,在網上征求意見建議1000余條,反復研究論證后形成初稿[30]。不難看出,在中國決策體制下中國共產黨的共識型決策體現了民主化、科學化與法治化,逐步形成了一個中國共產黨主導、多方參與、科學論證、過程開放、依法運行的決策模式。[31]因此,黨對檔案事業發展作出的共識型決策體現了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即社會各方意志的共同性,而這共同性從深層根基上源于中華民族求生存謀發展的共同利益或訴求[32],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必由之路。
2.2 合規律性視角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社會歷史的發展永遠不是被人的主觀目的所決定,因為社會發展不只有合目的性,更有合規律性。馬克思主義中的人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是社會生活的前提,當然也是政治生活的前提,他們“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33],換言之,人發揮自己的主觀性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到其身處的客觀物質環境的限制。雖然在政治生活中人都是懷抱著預期的目的推動事物按自己的意圖發展,仿佛看起來其是由人們的主觀性決定的,但事實則截然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只是政治發展中的一個要素,政治中的人首先是社會存在物,是“現實的人”,他們實際是在社會發展規律的決定下參與的。“在不同的人群、階級乃至民族、國家之間往往彼此相異、相互沖突,加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傳統乃至制度安排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歷史規律的形成。但無論其作用性質如何,必然內滲著人的某種意志、期望和價值追求……目的作為主觀性要素必然嵌入到客觀的歷史規律中來……規律作為客觀性要素也必然嵌入在人的主觀目的之中。”[34]
回到檔案工作,雖然后現代主義對于政治權力介入檔案工作心懷不滿,但它并未看到國家管理權力的運作是根源于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了維持目前仍處于階級社會的各種利益的平衡,國家管理權力必須采取措施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以防止矛盾和沖突導致社會解體。國家管理權力不是統治階級強加于社會,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35],其參與檔案管理并非某一個體的主觀意志所為,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新挑戰,歷史虛無主義再次抬頭,通過不斷對歷史進行歪曲、虛構,試圖擾亂主流意識形態、消解國家認同與歷史認同,國家必須擔負起守護與開發歷史記憶資源庫、筑牢國家認同防線的責任,例如在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歷史文獻為依據出版了百萬字巨著《日本國竊土源流 釣魚列嶼主權辨》,用無可爭議的檔案捍衛國家領土主權。[36]檔案真實地記錄了歷史事實,是歷史建構的基本素材,是歷史解釋的邊界。歷史解釋的多元會造成社會民眾心中歷史記憶的多元,此時便需要國家維護歷史記憶的整合權、詮釋權與論斷權[37],對人們的歷史意識施加主導性影響,畢竟事物的發展如果失去主體的引導便容易陷入無序、混亂的狀態。[38]權力的行使人在制定決策時也受到客觀規律的決定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而人在現實的目的支配下做出的選擇并非完全自由的選擇,而是在前人既定的活動基礎上進行的,體現的是代際間客觀的、歷史的聯系。由此,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中人的合目的性是由社會的合規律性所決定,其實踐活動若想成功,不僅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更要遵循客觀規律性,即將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統一于檔案管理實踐之中,在客觀規律提供的選項中選擇最符合現實需要的路徑。
綜上,對于正確看待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的主觀性這一問題,我們一方面應該摒棄將其妖魔化的言論,正視主觀性不管是在檔案形成還是管理中的作用。人正是在某種動力的驅使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才獲得人之為人的真正本質,才成為具體的、歷史的、實踐的人。[39]另一方面應該明確,不是某個人的主觀性在影響檔案及檔案管理工作,而是社會中的各方意志互相博弈,個人的主觀性不應該過分夸大,因為個人是以階級的身份而存在,階級是個人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的“意義”,只有將個人與社會聯系起來考察才能真正地理解。[40]
3 結 語
本文從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視角對檔案、檔案職業以及檔案事業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進行論述,消解了傳統觀念中二者單純的矛與盾的關系,戳破了現實中質疑檔案客觀性的“紙老虎”,為檔案中的主觀性提供合理支撐,更好地發揮其記錄好、留存好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這一憑證作用,為檔案工作者正視職業的主觀性提供理論依據,更好地推動其積極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保管好、利用好黨和國家豐富的檔案資源,為檔案事業堅持其政治性進行現實闡釋,更好地發揮檔案事業服務中心大局、服務人民群眾的作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添磚加瓦,用馬克思主義為檔案、為檔案職業、為檔案事業正名。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西方檔案學理論本土化批判研究”(項目編號:22Y005)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與參考文獻
[1]丁華東.論檔案與社會記憶控制[J].檔案學通訊,2011(3):4-7.
[2]徐擁軍.檔案記憶觀:社會學與檔案學的雙向審視[J].求索,2017(7):159-166.
[3]劉迪.檔案建構社會記憶中的權力因素及其積極作用——從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說起[J].檔案學通訊,2016(2):90-94.
[4]張林華,蒙娜.權力因素在檔案建構社會記憶中的消極作用及其應對策略[J].檔案,2007(5):7-10.
[5]布勞因.檔案工作者、中介和社會記憶的創建[J].曉牧,李音,譯.中國檔案,2001(9):48-51.
[6]庫克.銘記未來——檔案在建構社會記憶中的作用[J].李音,譯.檔案學通訊,2002(2):74-78.
[7]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M].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398.
[8]徐辛酉.米歇爾·福柯檔案思想的淵源及其當代實踐[J].檔案管理,2018(4):20-23.
[9]徐擁軍,熊文景.后現代主義檔案觀批判——基于唯物史觀的視角[J].思想教育研究,2019(5):81-85.
[10]黃霄羽.外國檔案管理學 第2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5.
[11]覃兆劌.“中”—“當”—“檔”[J].檔案學研究,2000(3):17-21.
[12]黃霄羽.外國著名檔案學者縱覽[J].四川檔案,1996(4):7-9.
[13]陸陽.論權力對檔案的建構[J].浙江檔案,2009(12):26-28.
[14]葛晨虹.后現代主義思潮及對社會價值觀的影響[J].教學與研究,2013(5):96-103.
[15]何嘉蓀,馬小敏.后保管時代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之四——檔案化問題研究[J].檔案學研究,2016(3):4-11.
[16]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J].歷史研究,2001(5):136-147,191.
[17]加小雙.后現代檔案學理論的范式成長與范式批判[J].檔案學通訊,2021(3):34-39.
[18]FOOTE K E.To Remember and Forget: Archives, Memory, and Culture[J].The American Archivist,1990,53(3):378-392.
[19]譚必勇.“證據的神圣性”:希拉里·詹金遜古典檔案思想成因探析[J].檔案學通訊,2017(2):19-22.
[20]丁華東,余黎菁.論特里·庫克的檔案記憶思想[J].檔案管理,2014(6):6-9.
[21]覃兆劌.雙元價值觀與“檔案”的定義[J].北京檔案,2003(9):16-19.
[22]劉福森.社會歷史過程中的主體性、合目的性和規律性——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的觀念變革[J].哲學研究,1988(10):33-39,54.
[23]楊秀茹,桑毓域.詹金遜“證據神圣觀”理論價值再認識[J].檔案管理,2015(6):4-6.
[24]楊文. 發揮檔案在堅定文化自信中的作用[EB/OL].[2022-07-28].http://www.zgdazxw.com.cn/news/2022-07/28/content_335506.htm.
[25]葉澤雄.論恩格斯對“歷史”本質的科學闡釋[J].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1(1):25-32.
[26]葉澤雄.論馬克思人學視野中的“歷史規律”[J].哲學研究,2014(12):31-35.
[27]陳偉俊.把民主集中制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N].學習時報,2021-08-11(1).
[28]楊光斌.中國決策過程中的共識民主模式[J].社會科學研究,2017(2):39-49.
[29]鄭金月.回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誕生[N].中國檔案報,2019-11-12(1).
[30]藍圖繪就奮向前 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譜新篇——《“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解讀[J].中國檔案,2021(6):24-26.
[31]周光輝.當代中國決策體制的形成與變革[J].中國社會科學,2011(3):101-120,222.
[32]葉澤雄,趙鵬.再論恩格斯歷史合力論思想及其當代意義[J].江漢論壇,2019(9):13-19.
[3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
[34]葉澤雄,王杰.歷史發展合目的性的唯物史觀解釋[J].江漢論壇,2022(5):73-78.
[35]王滬寧.政治的邏輯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70-171.
[36]《日本國竊土源流 釣魚列嶼主權辨》出版[J].歷史檔案,2002(1):30.
[37]詹小美.選擇與建構:歷史記憶固基政治認同的邏輯共生[J].思想理論教育,2016(12):20-26.
[38]谷佳媚,程含笑.社會記憶的再生產向度:歷史虛無主義的消解[J].思想教育研究,2021(10):99-105.
[39]余永躍,陳曙光.馬克思“人的本質”思想解讀[EB/ OL].[2006-06-26]. https://www.gmw.cn/01gmrb/2006-06/26/ content_439634.htm.
[40]方玨.個人與階級——馬克思階級理論對“無階級的神話”的批判[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6):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