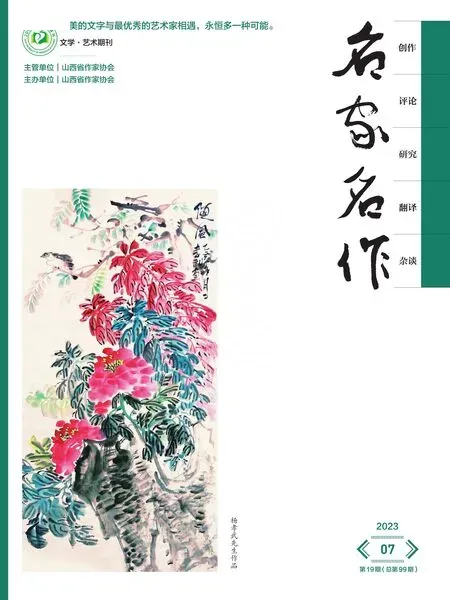AR 模式下詩(shī)歌翻譯的情感審美及再現(xiàn)研究
——以《紅豆曲》為例
秦龍蛟
情感是人類認(rèn)識(shí)和體驗(yàn)世界不可或缺的途徑,是存在于人腦的一種生物基因。審美的本質(zhì)就是情感體驗(yàn),情感不僅是一種審美需求,更是翻譯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的重要依據(jù)。同時(shí),情感作為詩(shī)歌的本質(zhì)屬性,在詩(shī)歌翻譯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將基于AR 模式對(duì)譯者審美能力的調(diào)查,對(duì)詩(shī)歌情感的特征、功能以及翻譯審美再現(xiàn)模式進(jìn)行探索研究。
一、基于AR 模式的譯者審美能力調(diào)查
(一)AR 簡(jiǎn)述
AR 是Action Research 的簡(jiǎn)稱, 由Kurt Lewin 于1946 年正式定名,主要指通過計(jì)劃、實(shí)施、觀察與反思的方式來解決現(xiàn)實(shí)問題,具有現(xiàn)實(shí)性、參與性和反思性等特征[1]169。具體而言,AR 強(qiáng)調(diào)主體以實(shí)際行動(dòng)參與集計(jì)劃、步驟與反思為一體的研究,以解決自身問題、改善現(xiàn)狀為目標(biāo),其過程表現(xiàn)為動(dòng)態(tài)性和非規(guī)約性,以What-Why-How 為其常規(guī)操作模式,即探查具體問題、分析問題成因、尋找解決方案。自20 世紀(jì)80 年代傳入中國(guó)以來,AR 主要被應(yīng)用于聽力、口語(yǔ)、閱讀、寫作等方面的教學(xué)研究,但受其應(yīng)用屬性影響,該模式為發(fā)現(xiàn)和研究翻譯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對(duì)于探索譯者培養(yǎng)機(jī)制、提升譯者審美及再現(xiàn)能力有著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和實(shí)踐參考價(jià)值。
(二)調(diào)查方式及譯者審美能力現(xiàn)狀
為了解當(dāng)下譯者的審美水平、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及其在翻譯審美上的主要訴求,筆者將其分成若干小組進(jìn)行詩(shī)歌翻譯練習(xí),要求以小組為單位探討翻譯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相關(guān)成因和具體解決方案,并以PPT 呈現(xiàn)的方式與其他小組分享本組的最終譯文和翻譯體會(huì)。除此之外,筆者通過私信或訪談的形式隨機(jī)了解個(gè)體的疑問與心得,將其與各個(gè)小組的匯報(bào)情況進(jìn)行整合,然后適時(shí)調(diào)整翻譯方法并在隨后的實(shí)踐中進(jìn)行驗(yàn)證,以此來了解相關(guān)方法的有效性、可行度以及譯者翻譯審美及再現(xiàn)能力的改善情況。
通過調(diào)查,筆者初步發(fā)現(xiàn)譯者的翻譯審美及再現(xiàn)能力存在理解失真、表達(dá)不暢、校對(duì)不力、審美意識(shí)淡薄等問題。針對(duì)上述問題的解決模式包括四點(diǎn):第一,基于朗誦的審美路徑,即通過誦讀的方式理解原文,整體把握原文大意,體會(huì)其節(jié)奏、韻律、情感等蘊(yùn)含意義;第二,基于探意、凝神、正言、潤(rùn)色的翻譯步驟,即在朗誦原文的基礎(chǔ)上識(shí)別原文主旨大意,把握其內(nèi)在精神,以目標(biāo)語(yǔ)言形式表達(dá)出來之后再進(jìn)行文辭上的修正與潤(rùn)色;第三,基于真、善、美的翻譯原則,即在總體翻譯原則上要力求原文義旨轉(zhuǎn)換之真實(shí)、譯文語(yǔ)言表達(dá)之完善以及翻譯效果之優(yōu)美;第四,基于形式與非形式系統(tǒng)的情感焦點(diǎn),即在語(yǔ)言形式之外,要尤其注重以情感為主的蘊(yùn)含意義。為此,本文將著力探討詩(shī)歌翻譯中情感審美及再現(xiàn)問題的解決模式。
二、詩(shī)歌翻譯中的情感研究
詩(shī)歌作為歷史久遠(yuǎn)、影響廣泛的一種文學(xué)體裁,是語(yǔ)言運(yùn)用原始樸素性和現(xiàn)代藝術(shù)性的完美結(jié)合。然而,在詩(shī)歌的所有特征中,情感是其最為明顯、最為強(qiáng)烈和最為穩(wěn)定的一個(gè)特征。本部分將就詩(shī)歌與情感的關(guān)系以及情感的翻譯問題進(jìn)行研究。
(一)詩(shī)歌與情感
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藝?yán)碚撝校憴C(jī)在《文賦》中明確指出“言寡情而鮮愛”,認(rèn)為缺乏強(qiáng)烈情感的詩(shī)歌無(wú)法獲得讀者喜愛;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指出,情感是詩(shī)歌的根本;司空?qǐng)D在《二十四詩(shī)品》中提出“情性所至,妙不自尋”,視情感為詩(shī)歌境界的決定因素。在現(xiàn)當(dāng)代詩(shī)歌文學(xué)理論中,朱光潛[2]6視詩(shī)歌為情感的最佳表達(dá)方式,而成仿吾和郁達(dá)夫等學(xué)者則認(rèn)為情感是詩(shī)歌的生命和實(shí)質(zhì)。
而在西方傳統(tǒng)文藝?yán)碚撝校琒ocrates 認(rèn)為好的詩(shī)歌要以真摯的情感投入作為基礎(chǔ);Aristotle 認(rèn)為,詩(shī)歌是基于情感體驗(yàn)的創(chuàng)作,可以激發(fā)并給人帶來審美愉悅;Horace 闡述了詩(shī)歌說教與娛樂的主旨功用,從側(cè)面證實(shí)了情感在詩(shī)歌中的價(jià)值[3]10-30。而在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流派中,以詩(shī)歌見長(zhǎng)的浪漫主義認(rèn)為情感表達(dá)是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初衷和目的,可以激發(fā)人的心弦并引起共鳴。
由此觀之,情感作為詩(shī)歌的本質(zhì)屬性未曾受到歷史時(shí)序、地域空間、文化異質(zhì)等客觀外在因素的影響,是中、西方詩(shī)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接受的主要內(nèi)容和驅(qū)動(dòng)因素。同時(shí),從翻譯審美再現(xiàn)及接受的角度而言,情感是中、西方詩(shī)歌譯/讀者期待視野的融合區(qū)域,是詩(shī)歌認(rèn)知理解與跨文化傳播的內(nèi)在動(dòng)力。
(二)情感翻譯研究綜述
許淵沖[4]84-100認(rèn)為,詩(shī)歌翻譯的最終目的在于使讀者樂之,實(shí)現(xiàn)情感上的愉悅,提出了等化、深化、淺化等審美再現(xiàn)策略,倡導(dǎo)文化寓意、語(yǔ)言文字、審美效果等多層面的優(yōu)化。劉宓慶[5]110-140指出,審美主體對(duì)客體內(nèi)在情感的感知、理解與把握存在明顯的間接性,需要主體借助審美想象與移情等手段來進(jìn)行捕捉和再現(xiàn)。Newmark[6]14-15主張從韻律、修辭、文化等多個(gè)角度對(duì)情感的理解和審美再現(xiàn)進(jìn)行把握。
但是,通過想象與移情捕獲詩(shī)歌內(nèi)蘊(yùn)情感離不開有效的意象營(yíng)造,而詩(shī)歌意象往往是特定文化審美取向在審美主體內(nèi)心世界的選擇性映射,詩(shī)歌翻譯若想取得近似于原文的審美效果須重視意象營(yíng)造的文化適應(yīng)性。同時(shí),詩(shī)歌抒情目的與效果的達(dá)成有賴于語(yǔ)言的合理塑造及傳遞,這就需要從韻律、修辭等語(yǔ)言層面對(duì)譯文進(jìn)行優(yōu)化。因此,詩(shī)歌翻譯的情感審美及再現(xiàn)可以通過意象營(yíng)造、文化適應(yīng)和語(yǔ)言優(yōu)化的綜合運(yùn)用予以展開。
三、詩(shī)歌翻譯中情感的審美再現(xiàn)模式
基于上文對(duì)詩(shī)歌情感及其翻譯的研究,本部分將以《紅豆曲》及其翻譯為例,對(duì)詩(shī)歌翻譯中的情感審美再現(xiàn)模式進(jìn)行具體分析。
(一)意象營(yíng)造
意象是一種基于物象、形而上的精神產(chǎn)品,可以促進(jìn)意義的表達(dá)和情感的傳遞。在《周易·系辭》中,孔子曾提出了“立象以盡意”的問題解決范式,并對(duì)立象途徑和功能作了進(jìn)一步的解釋和說明,表明意象營(yíng)造是審美敘事的重要路徑。
《紅豆曲》原文營(yíng)造出了動(dòng)覺、意覺、視覺、聽覺和觸覺等多維并置的意象集群,賦予了該詩(shī)獨(dú)特的具象美和虛象美。原文借助視覺所營(yíng)造的具體意象和借助意覺所營(yíng)造的虛擬意象,在楊憲益和霍克斯(Hawkes)等主流譯文中[7]167-169都有所呈現(xiàn),但受詩(shī)學(xué)、意識(shí)形態(tài)、主體能動(dòng)性、主體間性等因素的影響,其呈現(xiàn)方式不一而同。
通過對(duì)比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楊、霍的意象營(yíng)造方式主要表現(xiàn)為再現(xiàn)、重構(gòu)、新造、省略。在具象的審美再現(xiàn)中,楊憲益的譯文以再現(xiàn)為主,如將“春柳”譯為willows;而霍克斯的譯文則以新造為主,如“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的魔鏡意象。在虛象的審美再現(xiàn)中,楊憲益以重構(gòu)為主,如將“相思血淚”重構(gòu)為drops of blood 和tears of longing 這一視覺和意覺相結(jié)合的復(fù)合意象;而霍克斯則全部采用了重構(gòu)方式,如將“玉粒金莼”重構(gòu)為food and drink 等意覺意象。
總之,楊憲益的意象營(yíng)造方式以再現(xiàn)和重構(gòu)為主,而霍克斯則以重構(gòu)和新造為主。從兩個(gè)譯本在國(guó)內(nèi)外讀者群體及學(xué)界的不同反響可以得知,在以傳達(dá)信息為目的的翻譯前提下,再現(xiàn)是一種合理的意象營(yíng)造方式,而在考慮讀者的審美期待、審美接受與反應(yīng)以及詩(shī)學(xué)等因素的情況下,重構(gòu)和新造則更為可行。
(二)文化適應(yīng)
文化是特定思想、物質(zhì)和行為的多元集合,反映或代表了特定審美理念和審美取向。集體審美意識(shí)、習(xí)慣及實(shí)踐的傳承、變革和創(chuàng)新構(gòu)成了文化發(fā)展與演變的主要模式,審美始終都是文化的核心與靈魂所在。因此,為觀照目標(biāo)讀者的審美期待及其與作者的情感同向,文化適應(yīng)在翻譯實(shí)踐中更多的體現(xiàn)為審美適應(yīng),要求譯文與目標(biāo)受眾所屬的文化傳統(tǒng)、意識(shí)形態(tài)、詩(shī)學(xué)理念及社會(huì)規(guī)約等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相契合,使譯文在文化異質(zhì)性審視下以恰當(dāng)方式確保非通約性信息的有效傳播。
《紅豆曲》使用了中國(guó)詩(shī)學(xué)審美敘事所獨(dú)有的系列文化詞匯,且皆與愛情、相思、盼念有關(guān)。通過分析楊、霍兩個(gè)譯本可以得知,兩者都用到了簡(jiǎn)化性縮略,即原文本意義與目標(biāo)文本意義基本對(duì)等,但后者是對(duì)前者進(jìn)行淺化或省略的結(jié)果。不同的是,霍譯本采用了適應(yīng)性改寫,即在觀照目標(biāo)受眾審美期待、詩(shī)學(xué)規(guī)約和文化從屬的前提下,譯者對(duì)原文意義進(jìn)行了重構(gòu)性或創(chuàng)造性的改寫,致使目標(biāo)文本意義與原文意義明顯不同卻又更容易為目標(biāo)受眾所接受。
具體而言,楊氏對(duì)文化蘊(yùn)意的處理以簡(jiǎn)化性縮略為主,如在目標(biāo)文本中直接省略“紅豆”,并將“畫樓”淺化為painted pavilion。霍氏則主要采用了適應(yīng)性改寫,如將“紅豆”譯為little red love-beans,在保留其文化異質(zhì)性和非通約性的同時(shí),又使其意義和形象可以為目標(biāo)讀者所理解和接受。此外,如果說上述案例只是在措辭上的文化適應(yīng),那霍氏對(duì)于“菱花鏡”的處理則是在風(fēng)格、內(nèi)涵、聯(lián)想和移情等蘊(yùn)意上多方位的文化適應(yīng),“Mirror,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在目標(biāo)讀者對(duì)“菱花鏡”的認(rèn)知理解上添加了神秘性、方位性、功能性和審美性的留白。
總體而言,楊、霍兩位譯者在文化信息的呈現(xiàn)方式上各有特色,但就譯文的審美接受與傳播而言,霍氏的適應(yīng)性改寫更為值得參考和借鑒。
(三)語(yǔ)言優(yōu)化
語(yǔ)言是情感與意義的外在形式,而情感與意義則是語(yǔ)言的內(nèi)在構(gòu)成。在語(yǔ)言表達(dá)中往往會(huì)出現(xiàn)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情況,但這并不意味著對(duì)語(yǔ)言形式重要性的貶低。相反,美學(xué)注重形式的提煉,語(yǔ)言之美通常體現(xiàn)為確切和穩(wěn)定的客觀形式。翻譯美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主體從審美視角對(duì)客體的翻譯再現(xiàn)進(jìn)行語(yǔ)言優(yōu)化,在保證基本語(yǔ)法、句法和邏輯正確性的基礎(chǔ)上從修辭、韻律、節(jié)奏等層面力求譯文的進(jìn)一步完善。
曹雪芹在創(chuàng)作《紅豆曲》的過程中從整體上對(duì)該詩(shī)進(jìn)行了藝術(shù)把握。就修辭而言,原詩(shī)用到了對(duì)偶、排比、夸張和用典等多種修辭手法,強(qiáng)化了情感的靈動(dòng)性和觸動(dòng)性;在韻律層面,原詩(shī)以尾韻“ou”為基準(zhǔn),在保證詩(shī)歌音樂性的同時(shí)也彰顯了主題情思的綿長(zhǎng),而臨近收尾處適時(shí)的變韻“a”和“in”則在起承轉(zhuǎn)合中強(qiáng)化了情感的強(qiáng)度和韌性;在節(jié)奏層面,原詩(shī)以一行三頓的模式為主,在情感轉(zhuǎn)折的節(jié)點(diǎn)上又輔之以一行一頓或兩頓,形成了輕緩?fù)鶑?fù)的情感脈動(dòng)。
通過對(duì)比可以發(fā)現(xiàn),楊、霍兩個(gè)譯本在語(yǔ)言優(yōu)化上各有特色。首先,在修辭應(yīng)用上,兩位譯者都借此來保證譯文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的簡(jiǎn)練精當(dāng)和意義傳達(dá)的靈活律動(dòng),但楊譯本以明喻、倒裝和排比為主,而霍譯本則更加多元化,涉及懸垂、錯(cuò)格、排比、聯(lián)珠和松散句,后者的語(yǔ)言張力更強(qiáng),而且在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上與原文存在著一定的共鳴。其次,在韻律安排上,兩位譯者都借鑒了十四行詩(shī)的格式,押尾韻且以雙行體收尾,但楊譯本采用的是隔行押韻模式,整體韻腳為abcb/bded/ff,而霍譯本主要是兩行轉(zhuǎn)韻模式,整體韻腳為aabb/ccddd/e/ff,后者的音樂感性更為明顯。最后,在節(jié)奏的把握與設(shè)計(jì)上,兩位譯者都充分發(fā)揮了音步的優(yōu)勢(shì),但楊譯本采用了五音步為主、六音步和七音步為輔的模式,而霍譯本則采用了六音步為主、多音步為輔的模式,更容易將讀者帶入共情語(yǔ)境。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在語(yǔ)言優(yōu)化過程中,韻律的作用最具感性,而兩行轉(zhuǎn)韻的韻腳模式由于其集中性、突顯性和規(guī)律性等特征,在審美樂感上要比略顯流散和隨意的隔行押韻模式更為強(qiáng)烈。同時(shí),節(jié)奏是詩(shī)歌韻律之美的重要支撐,可以有效激發(fā)讀者的情感體驗(yàn)。此外,修辭手法的靈活應(yīng)用可以促進(jìn)語(yǔ)言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的提煉和優(yōu)化,提升讀者的詩(shī)性體驗(yàn)與暢想。
四、結(jié)語(yǔ)
本文基于AR 模式下譯者審美及再現(xiàn)能力的調(diào)查結(jié)果,對(duì)詩(shī)歌翻譯中的情感焦點(diǎn)問題進(jìn)行了探索性研究。在分析和研究了情感與詩(shī)歌的關(guān)系以及相關(guān)學(xué)者對(duì)于情感翻譯問題的論述之后,初步提出了意象營(yíng)造、文化適應(yīng)和語(yǔ)言優(yōu)化的情感審美及再現(xiàn)路徑,并以“紅豆曲”及其翻譯為例,對(duì)該模式的具體應(yīng)用進(jìn)行了描述分析。情感作為詩(shī)歌翻譯過程中的一個(gè)焦點(diǎn)問題,是對(duì)譯者審美及再現(xiàn)能力的重要考量模塊,此次研究及相關(guān)成果對(duì)今后譯者審美及再現(xiàn)能力的培養(yǎng)和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