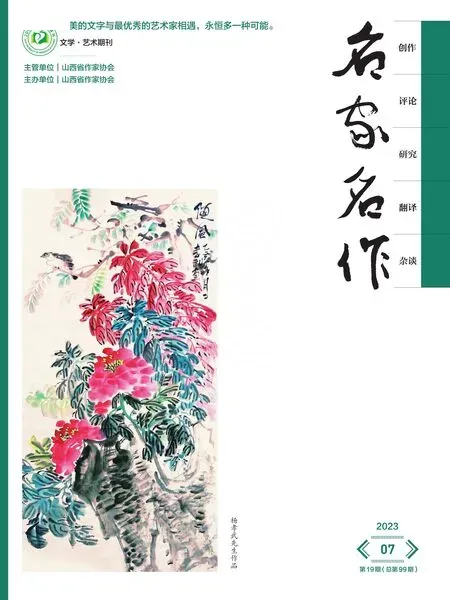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梁上君子》的跨語際實踐與戲劇中國化
畢賢慈
外國戲劇的改編是抗戰時期一種獨特的文學創作方式,是貫穿于我國現代話劇發展史始終并大有可觀的創作現象,改編劇作更是在中國舞臺上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上海1937—1945 年先后上演及發表的改編劇本多達40余部。改編熱潮不僅體現在數量上的大幅增加,還體現在范圍的進一步擴大,其中就涉及英國、法國、美國、匈牙利、蘇聯、意大利等眾多國家的劇作改編。[1]劇作家們“抓住中國的一切,完美無間地放進一個舶來的造型的形體”[2],在凸顯現實意蘊的同時,也推動著外國戲劇中國化的改編進程。也正是在此視域下,匈牙利作家費倫茨·莫爾納的《律師》(A Doktor Ur)進入了黃佐臨的文學視野,經由其中國化改編、出版并上演的《梁上君子》成為家喻戶曉的劇目,其盛況可謂空前。[3]本文以《梁上君子》這一具體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在其中國化改編具體而系統的探析中,試圖透視1937—1945 年上海外國戲劇中國化改編的整體概貌與文學史意義。
一、黃佐臨與《梁上君子》的改編及影響
中國現代話劇作為舶來品從無到有始終關涉“改編”,在1937—1945 年間,滯留在上海的進步作家將改編視為翻譯和創作之間的津梁,借由改編之名避人耳目以通過審查,表達自己的文學訴求與抗戰愿望,這也成為戲劇生存的一條可行之路。1944 年12 月世界書局出版發行的《梁上君子》便是黃佐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譯介選擇。
黃佐臨,原名黃作霖,廣東番禺人,1906 年出生于天津,是中國現當代史上頗負盛名的戲劇、導演藝術家。1925 年至1935 年間,先后赴英留學,并開始自覺地致力于探索中國話劇民族化的道路。抗日戰爭爆發后,黃佐臨義無反顧地返回祖國,先后在天津、重慶與上海三地開展戲劇事業,為中國現代戲劇在抗戰時期的再度興盛撒播希望的火種。黃佐臨熱衷于外國戲劇的中國化改編,《梁上君子》便是其中國化改編成功的最好例證。該劇自1944 年12 月世界書局發行初版,另有1947 年4 月再版和1948 年4 月三版[3],主要講述了大律師夏屏康與小偷包三狼狽為奸的故事。其中穿插了夏屏康之妻愛梅與屠副巡長的交易、愛梅之妹愛蘭與夏屏康秘書白夢蘭的交際,以及夏屏康與其同學、老師聚會的誤會等等,極具戲劇性與諷刺意味。
立足于創作層面本身,黃佐臨充分切實地保持和發揚了莫爾納原作幽默風趣的藝術風格,并在此基礎上植根于中國的社會情狀,精細地刻畫了每一個人物的心理與形象。劇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律師靠著一位“梁上君子”的罪行與“生意”斂取錢財,律師為罪犯獲得一次次“免死金牌”的同時,罪犯也將“重生”的價值回報給他。其表面在寫律師夏屏康與小偷包三、愛梅與屠副巡長見不得人的利益勾當,實則是在暗諷日本帝國主義與汪偽政府之間同惡相濟,對上海展開的政治奴役和文化殖民。包三冒名頂替夏屏康去國際飯店參加同學聚會,高談闊論的同時盜取了學生和老師價值連城的物品。其他寄生于夏屏康家中的愛蘭、馬露西與白夢蘭等都是抗戰時期上海都市中上層階級千姿百態的生活縮影。
《梁上君子》自1943 年首演以來,便轟動了整個上海,開了一年來話劇界前所未有的盛況。此劇在巴黎大戲院演出期間,其所在的霞飛路電車站被稱為“梁上君子”站,車到站之后,售票員竟然幽默地讓“梁上君子們統統下車”,甚而“戲迷坐了三輪車來看戲,三輪工人放下車,也進來坐在‘苦干座’看戲”。[4]《梁上君子》在各地劇場爭相上演,層出不窮,甚至在1946 年6 月苦干劇團宣告解散后,劇演的余音也仍在延續。
《梁上君子》不僅受到了大眾的關注與喜愛,更是激起了學界各方的回響,爭相論道其中意涵。大眾傳播媒介關于《梁上君子》的評價,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批評家一是從《梁上君子》的內容本身出發,表達個人見解與立場,包括劇本、上演情況、劇中人物、演員與場景等。其中,關于“梁上君子”包三這一人物形象的評價居多,多持贊揚態度,認為他是反映真實社會的一面鏡子。二是把落腳點置于《梁上君子》的形式上,即其作為鬧劇,向大眾呈現了作品的現實批判意義,同時肯定了黃佐臨外國戲劇中國化改編的成功性。
二、《梁上君子》的跨語際實踐及其在地性
抗戰時期的上海,民族危機已然成為大眾的普遍感受。在極端的政治環境下,戲劇不僅是人民消遣娛樂與發泄情緒的有效渠道,更成為劇作家戟刺社會的投槍。費倫茨·莫爾納的《律師》因其具有進步意義且避開了直接描寫啟蒙與革命、民族與國家等宏大主題,成為黃佐臨戲劇改編的不二之選,并在上海的戲劇界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梁上君子》的翻譯與改編作為一種跨文化行為,獲得歡迎與成功的背后,譯者在跨語際實踐進程中做了怎樣的努力?又是如何使其具有了適應中國劇場的特質呢?
在《梁上君子》的改編過程中,黃佐臨無意識地參與著“跨語際實踐”的生成,即在“忠實”原著的部分,作品文本本身與譯文存在著不同的語言之間的通約能力、不同詞語與意義之間的虛擬等值關系的展示。[5]黃佐臨跨越歷史、文化與語言之墻,在創造性闡釋中實現了一種語言模式向另一種語言模式的轉型與再造。其將題目《律師》改譯為《梁上君子》首先便做到了這一點。“梁上君子”作為竊賊的代稱,在漢語的文化語境中含有“俠盜”的深意,相較于“律師”,更能直接、深刻地觸碰受眾的內心。黃佐臨更是充分發揮翻譯接受方的主體作用,進行著語言層面民族化與中國化的“發明創造”:一方面是本土方言、俚語等口語的趣味表達。戲劇表演是一種社會化活動,其面對的是不同文化程度的觀眾群體,通俗易懂的個性化、口語化語言便成為改編的最佳方式。《梁上君子》運用大量語氣詞和感嘆詞,如“嚯”“啛”“嘍”“噯”“哎呀呀”“喏”“嗐”“嘖嘖”“唬”“唔”等,在表達人物情緒上更直接、更生動。“甭說”“久仰久仰,久違久違”“磨咕”“老油子”“拆白黨”“打哈哈兒”等方言、俚語的使用,更是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地域化與生活化,在妙趣橫生的俏皮與幽默中,推動戲劇的進一步傳播與接受。另一方面是典故修辭里滲透的中國蘊意。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劇作家將民間審美與傳統文化澆筑于外國戲劇中,使得改編劇煥發出新的現實力量。在《梁上君子》的中國化改編中,黃佐臨引用較多的成語、諺語、詩句與俗語,如“君子隱惡而揚善”“恨不相逢未嫁時”“打是痛,罵是愛”“攝成雙璧影,締結百年歡”“口若懸河”等,均體現出中國語言的意猶未盡與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語言之外,黃佐臨根植于民族傳統的中國氣質與形象,強調地方特性,在改編劇作與特定空間場域的連結中,為“梁上君子”賦予特殊的時代意義。《梁上君子》模糊了原作《律師》的歷史文化背景,對地點、場景、社會背景與人物身份等進行了本土化改編與重塑,更具民族特色與中國氣質。全劇不再以“律師”為中心進行演繹,而是圍繞“梁上君子”之意的“偷”字展開敘述[6]。其表面上寫梁上君子實名的偷盜,實則指向各階級不受法律約束的暗偷,黃佐臨將“梁上君子”作為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影射著彼時上海社會各階層的畸形與黑暗,以共同的家國記憶喚醒觀眾對混亂現實的覺察。
值得一提的是,《梁上君子》以鬧劇的身份進入中國劇場,黃佐臨對其中的西方式幽默進行在地化與本土化的改造,使其轉變為更適合中國劇場的譏諷。“空前鬧劇”“笑!笑!笑!”“狂笑102 次,大笑603 次,微笑161 次”等廣告詞盡顯劇作之趣,以至漢奸(包括日軍)也以為《梁上君子》是個娛樂戲,搶著買票來看戲[7],其鬧劇效果不言自明。笑聲與淚水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體兩面,“喜”同“悲”一樣成為豐富且復雜的存在,《梁上君子》之類鬧劇的“笑”便也成為“涕淚交零”的文學主流之外的另一種文學想象方式[8],成了傳統中國文化個性的再現。
三、外國戲劇改編與《梁上君子》的中國化
除《梁上君子》外,李健吾的《王德明》(改編自莎士比亞的《麥克白》)與《金小玉》(改編自薩爾度的《托斯卡》)、魏于潛的《甜姐兒》(改編自保羅的《買糖小女》)、顧忠彝的《三千金》(改編自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等,均是同時代其他劇作家致力于外國戲劇中國化改編的創作,對于中國戲劇民族化進程中的探索實績不容忽視。
《梁上君子》名不見經傳,卻衍生出很強的“中國化”潛力,表現有三:首先,在政治、文化高壓下,知識分子紛紛內遷,原創劇作極為貧乏。戲劇改編用隱晦曲折的方式表達著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意識與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其不僅滿足了“劇本荒”的社會要求,而且劇作家將深刻的民族現實蘊含其中,極具典型意義。其次,抗戰時期上海戲劇職業化、商業化,戲劇團體層出不窮,無論是劇作選擇還是舞臺效果都呈現出新的發展活力。最后,在“民族形式”討論的藝術空間下,《梁上君子》的改編于民族化與中國化方面更加注重“深入今日中國的民族現實”[9]。黃佐臨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中國化實踐,并在國際內容與民族形式的去蕪存菁中實現“樸素的,自然的,明確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帶泥土信息的”[10]戲劇追求。《王德明》《金小玉》《甜姐兒》等其他外國戲劇的改編概莫如是,其中國化在深刻的現實意蘊與民族性旨歸中得以進一步向縱深開掘。
在布滿創傷的歷史時空中,外國戲劇中國化改編的大放異彩,既有其進步的歷史意義,也存在時代的局限與困境。正如上文所言,抗戰時期上海戲劇文學相對沉寂與貧弱,中國化改編劇無疑是極為可貴的存在,其意義具體體現為文學荒地的開拓。《梁上君子》填滿笑腹紛紜全滬,在“偷”的貫穿之力中形象地刻畫出中國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面貌,在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感的感召下給予時代隱晦而嚴肅的吁求;《王德明》將故事背景放置于五代初期,并增加了《趙氏孤兒》的情節,在保持著《麥克白》激動人心力量的同時,也在內容到形式的呈現中盡顯中國特質;《三千金》在嫁接舊劇《王寶釧》內容的同時,更是將莎士比亞筆下的悲劇與倫理轉化為中國式大家庭的倫理悲劇,其中國化改編稱得上徹底二字。這些改編戲劇均在上海如火如荼地演出,并成為時代藝術的精華,在現實體察與藝術建構兩方面進行中國化與民族化的多元探索,歷久而彌新。
抗戰時期的上海現代戲劇已進入職業化、商業化演出的新階段,在嚴苛的政治干預與審查制度下,外國戲劇的中國化改編在飄搖的歲月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相對逼仄的生存空間,呈現出市場效益妥協下文學精神的失落。縱觀《梁上君子》《甜姐兒》等鬧劇,雖取得令人矚目的票房收益,并在幽默的微笑中兼容著嚴肅的社會批評,但無論在改編創作、舞臺呈現上,還是在廣告宣傳上,仍然無法擺脫“嬉笑玩鬧”的把戲與低趣。
抗戰時期上海外國戲劇的中國化改編,作為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戰爭泥沼下的一種精神寄托,也是民族文學的命脈延續。本文通過梳理與考察此時期外國戲劇中國化改編的真實情境。一方面是聚焦文藝本身,具體分析以《梁上君子》為代表的外國戲劇的改編,肯定其中國化過程中的跨語際實踐及其在地性。同時,其他劇作家也同黃佐臨一致走向了外國戲劇中國化的改編之路,其中滲透的文化內蘊不僅具有璀璨與落俗的兩極價值,而且對于重塑中國文化的自我形象有著跨文化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是撫今追昔,在全球化背景多元文明互鑒、中外戲劇交流日益活躍的背景下,進一步剖析外國戲劇中國化改編在我國戲劇發展史的獨特內涵,為當下及未來的戲劇創作提供可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