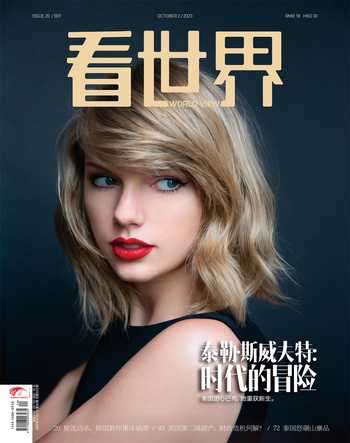《奧本海默》,你都說了什么?

艾弗尤
大眾科技產品專欄作家Brian X Chen最近發表文章說,多年來,他們家大多是依靠字幕來觀看影視作品的,原因是聽不清人物對話。而據調查,50%以上的美國人都因為聽不清對話而啟用字幕。一時間,跟帖如云:總算遇到了知音!原來,聽不清又羞于告人的,還有那么多人。
Chen文說,這一現象主要歸咎于流媒體對原作品音響合成的壓縮。現代電影院都有一整套復雜的音響系統,為這套系統而制作的音響合成,盡量凸顯并翻新背景音樂和其他音響。這樣的作品,通過流媒體軟件壓縮后,再在電視、電腦、平板和手機等平臺播出時,背景音響就難免喧賓奪主,淹沒了最為關鍵的人物對話。
跟帖者雖然附和,卻并不完全買賬,說流媒體壓縮只能是部分原因,主要責任必須由導演、演員、攝影和音響合成師等承擔;近年,影視制作者們一味追求各種花里胡哨的氛圍和效果,根本就不顧及這些效果能否抵達一般觀眾—聽不清只是一個方面,還有很多作品因為太暗,壓根兒就看不清。
音響合成師有高級設備,當然不顧其作品在一般電子產品上播出時的效果。而因為有現代錄音設備,現在的演員都不再經過嚴格的運氣和吐詞訓練,因而經常發音不清。有人指出,電視機上的經典電影就都能聽清對話。
還有人現身說法,指現在不少電影在有著超級音響設備的電影院中,一樣聽不清楚,主要原因是演員吐詞不清和背景音響太吵鬧。有人放出了手機截屏圖片,說正在熱映的《奧本海默》最高達到98分貝,甚至在隔壁影院都能不時聽到它的隆隆聲響。這些背景音喧賓奪主,不少人都條件反射式地尋找字幕。更有人干脆中途退場,說等流媒體出來以后,再打開字幕觀看。
奧片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并不是第一次受此指責。原來,據他最近接受《內幕》網站的采訪,這還正是他追求的效果。一般電影,都會讓演員在后期制作中,在錄音室里重新錄制對話,而諾蘭一直都拒絕這么做,為的是不想失卻更為真實的現場效果。
率先追求這種真實效果是文學。方言俚語堂皇入頁,讓小說中的人物形神畢現,充滿了世俗的人情味。繪畫和攝影等,隨后跟進。或問:從印象派開始,美術與現實愈益脫節,怎么反倒成了追求真實呢?
我在藝術欣賞上的啟蒙,得益于成都國畫家彭先誠先生在逛美國國家藝術畫廊時對我說的一句話:古典藝術都挺主觀。從這個角度看,古典美術追求盡善盡美,在視角、光線、線條和色彩等一應方面都難免美化乃至無視現實,確實挺主觀。
有人說,只要看看今天的希臘人,就知道古希臘那些美輪美奐的雕塑,不過是古代藝術家主觀臆造的罷了。而印象派模模糊糊,不正是現實的客觀寫照嗎?所謂主觀和客觀,就這么不可思議地反轉了。
當然,繪畫都是有錢人在聽信了專家的指點后收藏的,因而有了與現實完全脫節的經濟基礎,而電影則需要普羅大眾一張一張地購票,因而總不能客觀得讓人看不見、聽不清吧?
只是,《奧本海默》的全球票房已經逼近10億美元,諾蘭怕是聽不進他人聽不清臺詞的抱怨之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