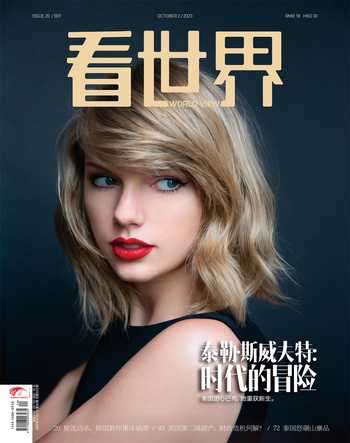盧旺達的牛奶

鄧晨
在東非大裂谷地區的盧旺達、布隆迪、烏干達、肯尼亞等國,許多牧民世代放牧一種擁有白色長角的黑牛。這些牛的成年體重大約在500公斤,在牛類的世界只能算中等身材,但它們的長角與眾不同,兩角間距往往可以長達200多公分,角粗達70—100公分,弧形美麗的牛角令人見過即難以忘記。
這種牛在盧旺達被稱為“伊延波牛”,在烏干達則被稱為“安科萊牛”。遺傳學研究者認為它們源于中東或非洲東北部,跟隨牧民南下來到東非大裂谷地區,這些牧民包括盧旺達及布隆迪的圖西族,烏干達的阿喬利族、肯尼亞的巴希瑪族等。相較于從事農業的其他部族,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與財富觀念都系于牛群,飲食也更依賴乳制品。
在盧旺達所發生的種族屠殺中,由于牛群是圖西族傳統財富的主要形式,因此有數十萬頭牛與它們的主人一起遭到屠殺。當盧國目前執政黨“盧旺達愛國陣線”的圖西族勢力在1994年擊敗胡圖族民兵后,再次從烏干達帶入了大量的安科萊牛,才使得盧國的牛只數量漸漸恢復。政府為了恢復受到重創的農牧業,還推動“每個貧戶一頭牛”的扶貧計劃。
“每個貧戶一頭牛”的效用是多重的,貧戶可以得到營養的牛奶,可以獲得肥料供應,還可以出售奶制品。同時牛本身就是財富及提升社會地位的載體,“愿你有許多牛”一直是盧國常見的問候語,傳統上牛可以用來締結婚姻及友誼等社會關系。在古代,圖西族與胡圖族的地位區分也并不是基于種族身體特征,而是基于擁有牛只的數量去判定。
如今,由于伊延波牛的產乳效率遠遜于現代乳業的專門牛種,因此盧國引入越來越多歐洲的荷爾斯泰因牛或澤西牛。雖然其對本地生態環境的契合程度不如伊延波牛,但生產效益顯著,未來飼養伊延波牛或許會變成文化象征意義。
由于官方致力推動養牛扶貧政策,牛奶與奶制品相關產業在盧旺達獲得支持,盧國城鎮街頭有不少專門提供牛奶的“奶吧店”。孩童從小也將牛奶作為重要的營養補充來源,可說是盧國的特殊景觀。然而令人多少有些質疑的是,喝牛奶畢竟是圖西族牧民的傳統習慣,他們普遍能夠消化乳糖,相較之下胡圖族具有乳糖不耐癥狀的比例則偏高。
當然,古代胡圖族與圖西族的身份是具有流動性的,而相互的通婚與交往也并不鮮見,原本從事農耕的胡圖族人如果擁有足夠多的牛就可以改變身份成為圖西族。過去胡圖族人之所以有更高的比例無法消化乳糖,可以說是因為獲得很多牛并采納牧民的生活方式,并非那么容易的事情。
1994年的種族屠殺過去已近30年,盧國政治斗爭的沖突在穩定秩序的表象下從未停止過。不管是胡圖族激進組織的活動,或是對于當年種族屠殺罪犯的追捕,都仍時常是媒體報道的焦點,同時政府嚴密的政治控制也引起了不少批評。
或許就像在許多東亞國家一樣,雖然存在乳糖不耐受問題,但奶制品消費確實已頗為普遍,盧國的養牛扶貧政策同樣也確實達成了一定的效益,養牛與牛奶產業的勃興,無疑是這些年來盧國發展的關鍵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