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未盡的戰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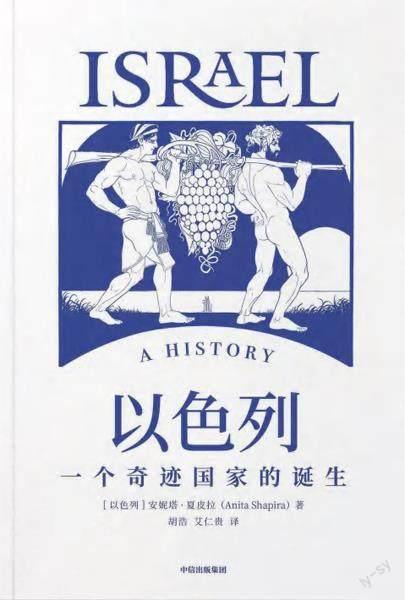
《以色列:一個奇跡國家的誕生》
[ 以] 安妮塔·夏皮拉 著
胡浩 / 艾仁貴 譯
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2022 年3 月
以色列的建立和存在伴隨著與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沖突。猶太人回到的并不是一個空無一人的荒地,盡管這里的人口相對稀少,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很難發現民族主義傾向。
但是自巴勒斯坦人與猶太民族主義相遇后,巴勒斯坦人對于自己與猶太人之間的差異性意識以及對巴勒斯坦地區的所有權的競爭意識都得以提升。事實上,這次遭遇是構成巴勒斯坦民族認同的重要因素。
拒絕承認的戰爭
巴勒斯坦人認為這個國家是他們自己的,并且不愿與他們認為是外部侵入者的人分享。猶太人也認為自己是這片土地的所有者,雖然他們準備允許阿拉伯人居住,但他們不會支持共享所有權。
最終顯而易見的是,在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實現和巴勒斯坦民族認同形成以及暴力沖突事件爆發的博弈中,猶太復國主義正在走向失敗。最后,猶太人只得妥協,同意在巴勒斯坦分別建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兩個國家。
然而,阿拉伯人不同意放棄對巴勒斯坦的專有權利,并拒絕分享。在阿拉伯國家卷入沖突的鼓舞下,阿拉伯人相信最終問題將通過武力解決。但是阿拉伯社會的崩潰,阿拉伯軍隊在獨立戰爭中的失敗以及“災難日”是阿拉伯人從未想象過的革命性發展。
而對于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這是猶太復國主義證明其有能力創造一個能夠承受生存戰爭的國家的時刻。對于猶太人來說,遷移或驅逐阿拉伯人是一個不可預知但是受歡迎的戰爭結果;他們沒有挑起戰爭,而戰爭給他們造成大量的傷亡。
巴以沖突并非始于1948 年的戰爭,但在阿拉伯人眼中,這場戰爭象征著猶太復國主義剝奪了他們的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角色顛倒,猶太人成為大多數,阿拉伯人成為少數,這是巴勒斯坦人創傷的根源,一直影響著巴勒斯坦人。直到1967 年,他們還希望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下一輪(較量)”能讓時間倒流。自那以后,特別是自1973 年戰爭以來,他們被迫接受以色列這一生活現實。
但與此同時,他們從未將其視為中東的一個合法實體。根據阿拉伯人的說法,猶太復國主義不是猶太人的民族運動。對于阿拉伯人來說,沒有猶太民族,只有猶太宗教;或者,用不那么苛刻的解釋,以色列人是一個民族,但世界猶太人不是。因此,猶太復國主義不是猶太人的解放運動,只是一種白人殖民主義的形式,即從當地居民那里竊取了一個國家。
現階段的結果是,巴勒斯坦人準備把以色列在中東的存在當作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并不認為它是正當的。因此,他們很難在和平協議上達成共識,以色列要求互惠和接受其基本要求:阿拉伯人放棄“回歸權”和沖突永恒性的神話,承認以色列是猶太民族國家。
不過,自從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以來,以色列在中東的非法性已經有所減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最初的溫和發展到阿拉伯聯盟的承認及和平化,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盡管雙方充斥著苦難和暴力,但以色列地并沒有經歷過在一些歐洲國家發生的種族滅絕或大屠殺,甚至一直到最近的20 世紀90 年代都沒有出現過。與其他民族間的沖突相比,巴以沖突仍然是有限度的,即便是考慮到定居點和以色列對民眾起義的鎮壓,或另一方面,即自殺式恐怖主義。由于以色列是沖突中較強的一方,可以說它在這場斗爭中對自己施加的道德限制是值得贊揚的。
以色列正在改變
自1967 年以來,對猶地亞、撒瑪利亞和加沙地帶的占領給以色列社會蒙上了陰影。大以色列支持者和支持“領土換和平”的人之間的兩極分化已經改變了以色列的政治。以前左翼和右翼的分歧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觀點,而現在以色列政治中,身份的指示者—鴿派或鷹派—體現的是關于以色列新近占領領土的不同立場。
這種沖突的主要內容已經規避了以色列社會本身的問題。對和平進程的失望削弱了以色列左派的力量。然而,最終的轉變不是向右,而是向中間。
在大多數以色列公眾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冷靜的和平意愿,但沒有了20 世紀90 年代早期那種彌賽亞的熱情。
今天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觀察以色列,看到的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國家缺少團結,各種組織和機構之間相互斗爭,組織凝聚力削弱。但從外部來看,這種觀點容易導致錯誤的分析。事實證明,當這個充滿不平等的社會面臨來自外界的危險時,它會召喚出堅定的意志,團結一致,找到共同點,鼓起勇氣面對攻擊者。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人們就會發出這樣的聲音:為什么只有在危機時刻才會出現這些志愿服務和愛國精神的優良品質呢?
在第三個千年的第一個10 年里,以色列出版了兩本書,可以作為以色列精神錯亂的向導。第一個是阿摩司·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幾年之后,大衛·格羅斯曼的《躲避消息的女人》緊隨其后。從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早期開始,希伯來文學就一直是一個地震儀,記錄著該運動的情緒和主導精神,以及它的良知和導向。20 世紀80 年代,以色列社會價值觀和共識的喪失導致的大蕭條與混亂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這些作品描述了對混亂的恐懼和失去早期文學所致力的公共空間的痛苦。在20世紀90 年代,這種真空成為表現虛無的新文學的主題。
現在,作為對和平進程失敗和第二次因提法達暴力活動爆發的回應,這兩部偉大的小說重新占據了文學的公共領域。阿摩司·奧茲講述了他的家庭故事,同時關涉了猶太復國主義的元篇故事。一個來自歐洲的移民家庭在以色列地的烈日下,在一種不利于只適應溫室條件的幼苗生長的環境中扎根。這種遭遇會帶來難忍和痛苦,但也會導致個人和社會的救贖與一個新世界的建立。這就是猶太復國主義故事的精髓所在。
對國家的熱愛,應對生存焦慮的隱性層面,保持人性的面相,是20 世紀開始以來希伯來文學中的典型主題。那些記錄著虛無的文學已經被致力于國家、社會和關于人類一切的文學所取代。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
責任編輯董可馨 dkx@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