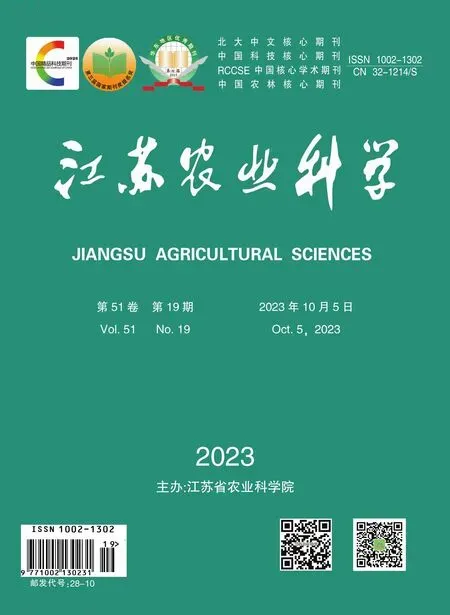2種用藥方案對不同栽培模式下山藥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
范琳娟, 劉子榮, 吳彩云, 徐雪亮, 康美花, 彭德良, 姚英娟, 姚 健
(1.江西省農業科學院農業應用微生物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200; 2.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北京 100193)
山藥別稱薯蕷、山薯、土薯、野薯等,在我國是一種常見的薯蕷科植物[1-2]。山藥在南北方地區均有種植,年產量僅次于馬鈴薯、甘薯和木薯[3]。作為藥食兩用的典型代表,山藥不僅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還具有很高的藥用價值,山藥能夠健脾益胃助消化,調節人體的免疫系統,防止血栓的形成,對心血管疾病有一定的預防作用[2]。近些年來,隨著種植面積的擴大及同一區域連續多年種植現象的出現,山藥連作障礙的問題也日趨嚴重,特別是山藥線蟲病越發嚴重[4]。作為一種土傳病害,山藥線蟲病較難根治,主要作用于山藥的根系和地下莖塊,對山藥種植業造成嚴重危害,嚴重時可導致山藥減產60%甚至80%以上[5]。目前,山藥線蟲病的防治主要依靠化學防治,包括土壤熏蒸、藥劑溝施、藥劑灌根等。土壤熏蒸常見藥劑有威百畝、棉隆等;溝施或灌根等方式施用的藥劑主要有噻唑膦、阿維菌素和辛硫磷等。化學防治山藥線蟲病效果好、見效快[6]。許念芳等研究發現,噻唑膦微囊懸浮劑可以起到長期防治山藥線蟲病的作用,對重茬地山藥具有較好的防治效果[4];董文芳等認為,威百畝水劑對防治山藥短體線蟲病的效果較好[7]。
土壤微生物作為土壤中物質轉化的動力,是決定著土壤化學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土壤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8],在營養物質的轉化、有機質分解、污染物的降解及土壤的修復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9]。土壤微生物群落在一定程度上調節著土壤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功能。土壤微生物的變化可作為評價土壤質量、維持土壤肥力和作物生產力的重要指標之一[8,10]。在山藥線蟲防治的過程中,殺線蟲劑的使用不僅對土壤線蟲群落有一定的消殺作用,也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造成一定的影響。王裔娜等研究表明,土壤熏蒸劑能明顯地影響土壤中真菌和細菌的生物量比例[11]。Fang等研究發現,二甲基二硫熏蒸雖然在門水平上對土壤細菌群落組成沒有明顯影響,但熏蒸后部分細菌的豐度卻發生了顯著變化[12]。Liu等研究發現,1,3-二氯丙烯可短暫抑制土壤中細菌種群結構,但細菌的豐度在后期可逐漸恢復[13]。目前,針對殺線蟲劑對山藥土壤微生物群落影響的高通量測序分析研究鮮有報道。本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礎上,根據江西省山藥線蟲的田間發生規律確定了2種殺線蟲施藥方案[8,14-15]。目前江西省山藥的種植模式主要有2種:傳統縱向栽培和淺生槽栽培,前者為縱向向下生長,后者為橫向生長。因此,本研究分別在這2種典型的栽培模式上對2種殺線蟲施藥方案進行了評價。為真實反映殺線蟲劑對山藥土壤細菌及真菌群落組成的影響,本研究基于Illumina HiSeq測序平臺,采用雙末端測序的方法,對用藥后的山藥土壤細菌16S rDNA V3~V4區和真菌 18S rDNA ITS_V1高變區進行PCR擴增,并對擴增產物進行高通量測序,分析2種用藥方案對山藥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及物種組成的影響,探索殺線蟲劑的使用與土壤微生物生態之間的關系,為利用土壤微生物生態指導殺線蟲劑在山藥種植業中的使用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供試作物為山藥,土壤樣品采自江西省泰和縣塘洲鎮朱家村(傳統栽培)和洲頭村(淺生槽栽培)山藥。供試藥劑:42%威百畝水劑,由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噻唑膦顆粒劑,由佛山盈輝作物科學有限公司提供;6%寡糖·噻唑膦水乳劑,由佛山盈輝作物科學有限公司提供。
1.2 田間試驗設計
試驗于2020年4—12月實施,共設計2種施藥方案,在傳統栽培區(江西省泰和縣塘洲鎮朱家村,114°57′E、26°27′N)和淺生槽栽培區(江西省泰和縣塘洲鎮洲頭村,114°57′E、26°27′N)分別實施,2個栽培區分別設置對照區,以不施用殺線劑為對照(CK)。小區面積 20 m2,每個處理重復3次。除防治線蟲用藥方案外,各試驗區所有的農事操作完全相同。方案1:威百畝,試驗田于4月3日施用42%威百畝水劑,按照750 kg/hm2的施用量兌水60 000 kg,蓋膜滴灌薰蒸處理。4月20日揭膜散氣。方案2:噻唑膦+寡糖·噻唑膦,試驗田于5月8日施用10%噻唑膦顆粒劑,按照22.5 kg/hm2的施用量拌適量沙撒施于栽薯畦面,并蓋土。7月5日用6%寡糖·噻唑膦水乳劑灌根,按照15 L/hm2的施用量兌水15 000 kg。
1.3 山藥土壤樣品的采集
山藥土壤樣品于12月(山藥成熟期)采集。采集20 cm深的土層,每個小區隨機選取3個點的土壤樣品,過2 mm篩,除去土壤樣品中的雜物后置于50 mL的無菌管中。液氮速凍運回實驗室,-80 ℃冰箱保存。樣品采集標記記錄見表1。

表1 2種用藥方案處理下山藥土壤樣品采集記錄對照
1.4 土壤樣品細菌16S rDNA擴增子V3~V4及真菌ITS_V1高變區微生物多樣性測定
將采集到的土壤樣品,每個樣本3個平行,送至上海派森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測定處理。具體操作步驟:提取土壤樣品總DNA,針對細菌16S rDNA擴增子序列V3~V4區使用引物338F(5′-ACTCCTACGGGAGGCGCAGCA-3′)和 806R(5′-GGACTACHVGGGTWTCTAAT-3′)進行擴增;真菌 ITS_V1 區使用引物ITS5(5′-GGAAGTAAAAGTCGTAACAAGG-3′)和 ITS1(5′-GCTGCGTTCTTCATCGATGC-3′)進行擴增。利用Illumina HiSeq測序平臺進行雙末端測序。通過對Reads拼接過濾、操作分類單元(OTU)聚類、物種注釋和豐度進行分析,利用R語言工具繪制各分類水平下的微生物多樣性群落結構圖,對各樣品在不同分類水平上的群落結構進行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2種用藥方案下山藥土壤微生物α多樣性指數差異性分析
α-多樣性指數分析可以反映樣本微生物群落的豐富度、均勻度和多樣性。Chao1指數表征樣本微生物的豐富度,Goods-coverage 指數表征樣本測序的覆蓋度,Pielou_e指數表征樣本微生物分布的均勻度,Shannon指數表征樣本微生物的多樣性。由圖1可知,樣本微生物的豐富度隨著測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并最終趨于平穩,意味著測序深度完全可以反映樣本微生物物種組成特征。由表2及表3可知,檢測樣本微生物Goods-coverage指數在95.47%~99.97%的范圍內,意味著測序結果足夠反映樣本所包含的微生物多樣性。


表2 不同處理山藥土壤細菌α-多樣性指數

表3 不同處理山藥土壤真菌α-多樣性指數
2種用藥方案對于不同栽培模式下的山藥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有著明顯的不同。如表2所示,經不同用藥方案處理以及1個山藥生長周期后,土壤微生物α-多樣性指數均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細菌的α-多樣性指數與對照組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種用藥方案處理的土壤細菌的Chao1指數、Pielou_e指數及Shannon指數明顯高于其對照組,說明2種用藥方案的處理有利于提高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山藥土壤細菌的豐富度、均勻度及多樣性,明顯地改變該模式下的土壤細菌的微生物群落結構。另外,在淺生槽栽培模式下,方案1處理對土壤細菌的豐富度、均勻度和多樣性影響不大,而方案2卻提高了該模式下的土壤細菌的豐富度、均勻度和多樣性。
由表3可知,經2種用藥方案處理后,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山藥土壤真菌的豐富度、均勻度以及多樣性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山藥土壤豐富度、均勻度以及多樣性卻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2 2種用藥方案下的山藥土壤微生物多樣性韋恩圖分析
由圖2-A可知,不同處理間的土壤共有細菌OTU數量為239,獨有的OTU數量分別為wbm12c 11 985、yh12c 10 557、ck12c 9 938、wbm12q 8 135、yh12q 9 810、ck12q 8 814。由圖2-B可以看出,不同分組間土壤共有真菌OTU數量為46,獨有的OTU數量分別為wbm12c 758、yh12c 515、ck12c 473、wbm12q 290、yh12q 269、ck12q 316。與對照組相比,除wbm12q外,試驗組的細菌OTU數量均高于其對照組。另外,2種用藥方案處理在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真菌OTU數量均高于其對照組,而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真菌OTU數量均低于其對照組。但總體上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細菌和真菌的OTU數量均高于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細菌和真菌的OTU數量。
2.3 2種用藥方案下的山藥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分析
2.3.1 細菌群落組成分析 物種注釋結果顯示,土壤細菌在門水平上主要分布在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綠彎菌門(Chloroflexi)和酸桿菌門(Acidobacteria),還有少量的厚壁菌門(Firmicutes)、WPS-2、藍藻細菌門(Cyanobacteria)、芽單胞菌門(Gemmatimonadetes)、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 和髕骨細菌門(Patescibacteria)。經2種用藥方案處理后,2種栽培模式下的土壤中的放線菌門和綠彎菌門的相對豐度變化不大。但在淺生槽栽培模式下,2種用藥方案處理的土壤中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有了明顯的提高,藍藻細菌門的相對豐度則明顯降低[12.33%降為3.27%(方案1)和1.05%(方案2)];在傳統栽培模式下,2種用藥方案處理的土壤中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均有明顯降低,另外方案1處理的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卻有明顯的提高(2.86%提高到9.88%)。在綱水平上,土壤細菌主要分布在放線菌綱(Actinobacteria)、γ-變形菌綱(Gammaproteobacteria)、α-變形菌綱(Alphaproteobacteria)、纖線桿菌綱(Ktedonobacteria)、酸桿菌綱(Acidobacteria)、產氧光細菌綱(Oxyphotobacteria)、 嗜熱油菌綱(Thermoleophilia)和芽孢桿菌綱(Bacilli)。2種用藥方案處理后,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山藥γ-變形菌綱的相對豐度明顯升高,而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山藥γ-變形菌綱的相對豐度則明顯降低。另外,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山藥產氧光細菌綱經2種用藥方案處理后,其相對豐度明顯降低,尤其是方案1處理后,其相對豐度從12.30%降為3.16%。在目水平上,土壤細菌主要分布在纖線桿菌目(Ktedonobacterales)、弗蘭克氏菌目(Frankiales)、根瘤菌目(Rhizobiales)、土壤紅桿菌目(Solirubrobacterales)、黃單胞菌目(Xanthomonadales)、微球菌目(Micrococcales)、酸桿菌目(Acidobacteriales)、β-變形菌(Betaproteobacteriales)、芽孢桿菌目(Bacillales)、念珠藻目(Nostocales)、加諾卡氏菌目(Pseudonocardiales)、鏈霉菌目(Streptomycetales)、棒桿菌目(Corynebacteriales)和芽單胞菌目(Gemmatimonadales)。 其中,在傳統栽培模式中,2種用藥方案處理均提高了土壤弗蘭克氏菌目和芽孢桿菌目的相對豐度,降低了根瘤菌目、黃單胞菌目、微球菌目、β-變形菌和鏈霉菌目的相對豐度。而在淺生槽栽培模式中,2種用藥方案處理則嚴重降低了念珠藻目的相對豐度。在屬水平上,2種用藥方案處理提高了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細菌熱酸菌屬(Acidothermus)、AD3、Subgroup_2和芽孢桿菌屬(Bacillus)的相對豐度,但對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細菌影響不大(圖3)。

2.3.2 真菌群落組成分析 根據物種注釋結果(圖4),在門水平上,土壤真菌主要分布在子囊菌門(Ascomycota)、擔子菌門(Basidiomycota)和被孢霉門(Mortierellomycota)。其中子囊菌門的相對豐度最高,在淺生槽栽培模式中占據93.3%(ck12q),但經方案2處理后,其相對豐度降為89.7%;而在傳統栽培模式中,其相對豐度略低(ck12c為87.7%),經方案1處理后,其相對豐度降為60.1%,而該處理下的擔子菌門的相對豐度卻由3.6%提高到11.4%。在綱水平上,土壤真菌主要分布在糞殼菌綱(Sordariomycetes)、盤菌綱(Pezizomycetes)、座囊菌綱(Dothideomycetes)和散囊菌綱(Eurotiomycetes)。其中,無論是淺生槽栽培模式還是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真菌,方案1處理都降低了糞殼菌綱的相對豐度,而方案2處理則提高了糞殼菌綱的相對豐度;另外,方案1處理大大提高了盤菌綱在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相對豐度,卻降低了盤菌綱在傳統栽培模式下的相對豐度。2種用藥方案處理都大大地降低了座囊菌綱在傳統栽培模式下的豐度。在目水平上,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土壤優勢真菌主要分布在糞殼菌目(Sordariales)、肉座菌目(Hypocreales)和盤菌目(Pezizales),其中方案1用藥方案處理嚴重降低了糞殼菌目在該培養模式下的相對豐度,卻提高了盤菌目的相對豐度;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土壤優勢真菌主要分布在肉座菌目(Hypocreales)、腔菌目(Pleosporales)和盤菌目(Pezizales),方案1處理嚴重降低了肉座菌目、腔菌目和盤菌目在該模式下的相對豐度,而方案2處理則提高了肉座菌目和盤菌目在該模式下的相對豐度,但嚴重降低了腔菌目的相對豐度。在屬水平上,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山藥土壤真菌主要集中在腐質霉屬(Humicola),約占46.7%,2種用藥方案處理均嚴重降低了腐質霉屬在該模式下的相對豐度,方案1和方案2的處理分別使其降低到了9.9%和39.1%,方案2處理提高了枝葡萄孢屬(Botryotrichum)在該模式下的相對豐度,由4.2%提高到了22.1%;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山藥土壤真菌主要分布在鐮孢屬(Fusarium)和彎孢屬(Curvularia),其中, 方案2處理提高了鐮孢屬在該模式下的相對豐度,但降低了彎孢屬的相對豐度,同樣,方案1處理也降低了彎孢屬在該模式下的豐度,但對鐮孢屬卻沒有影響。

2.3.3 山藥土壤微生物熱度圖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2種用藥方案對土壤微生物在屬水平上的差異,對細菌和真菌的優勢屬(前20)進行熱圖比較分析。如圖5所示,熱圖上方給出了不同處理下的土壤樣品在屬水平上的差異聚類分析,分為2部分——傳統栽培模式和淺生槽栽培模式。從左側各優勢屬在不同樣品中的組成聚類差異分析結果可知,與對照組相比,在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經方案1處理后,土壤細菌的測序結果差異主要體現在Actinospica、分枝桿菌屬(Mycobacterium)、WPS-2、Bryobacter、Acidothermus和Chujaibacter;而經方案2處理后的土壤細菌的測序差異主要體現在Actinospica;在傳統栽培模式下,與對照組相比,2種用藥方案處理的山藥土壤細菌的測序差異主要體現在Subgroup_2、AD3、Bacillus、Rhodanobacter、Chujaibacter、Burkholderia-Caballeronia-Paraburkholderia、鏈霉菌屬(Streptomyces)、Acidothermus、IMCC26256和Rhodanobacter;除此之外,方案2處理的山藥土壤細菌在HSB_OF53-F07和KF-JG30-C25也有較大差異。淺生槽栽培模式下,2種用藥方案處理的土壤真菌的差異性均體現在曲霉屬(Aspergillus)、Ovatospora、Microascus、Botryotrichum、Humicola和木霉屬(Trichoderma),而傳統栽培模式下,方案2處理的土壤真菌的差異性體現在青霉屬(Penicillium)、Cephaliophora、Plectosphaerella、Talaromyces、Fusarium、Mortierella、Curvularia、Pyrenochaetopsis、Myrmecridium和Saitozyma,而方案1處理土壤真菌主要在Curvularia、Pyrenochaetopsis、Trechispora、Hamigera、Phallus和Penicillium有較大差異,其余各屬在不同處理間的差異不明顯。
3 討論與結論
土壤施用化學藥劑后,對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結構組成及多樣性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李君研究了熏蒸劑威百畝對土壤微生物多樣性及群落結構的影響,發現施用威百畝后,土壤細菌群落結構受到影響,優勢菌群發生變化[16]。Li等研究發現,采用威百畝熏蒸后,土壤中細菌群落和優勢菌群發生了改變,但是在門水平上,樣本之間差異卻不明顯[17]。卜東欣等利用平板計數法測定威百畝處理后土壤微生物數量,發現威百畝對土壤細菌先有一個抑制作用,然后再出現激活作用,最后再恢復到對照水平;而真菌在整個處理期內,都表現出抑制作用[18]。鄒小明等研究發現,高濃度的三唑磷對土壤細菌抑制后又具有促進作用,但對土壤真菌卻一直具有抑制效應[19]。殺線蟲劑對土壤中的微生物起促進作用的研究也有報道。時立波等研究表明,涕滅威刺激了土壤細菌繁殖[20];鄧曉等研究表明,辛硫磷對土壤中細菌有刺激作用[21]。本研究針對殺線蟲劑對山藥成熟期土壤細菌和真菌群落結構與組成的影響,通過高通量測序對其進行了研究,分析2種不同用藥方案對山藥成熟期土壤細菌和真菌在門、綱、目和屬等不同分類水平上的優勢類群。研究結果顯示,2種用藥方案對不同栽培模式下的山藥成熟期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大不相同,不僅提高了傳統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細菌和真菌的豐富度、均勻度及多樣性,也提高了淺生槽栽培模式下的土壤細菌群落均勻度和多樣性,但卻降低了土壤真菌群落的豐富度。不論是淺生槽栽培模式還是傳統栽培模式,2種用藥方案不會改變山藥土壤細菌和真菌的優勢物種組成,僅在不同物種的組成豐度上造成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