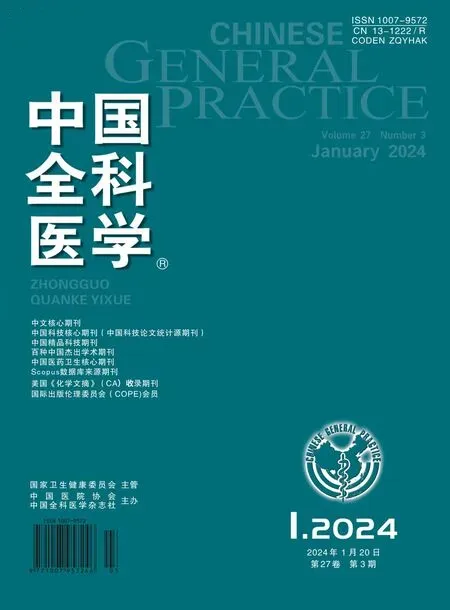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中老年認知功能影響的中介效應路徑分析
黃曉彤,王瓊,劉晨,侯曉春,許心蕊,吳炳義,楊曉*
1.261053 山東省濰坊市,濰坊醫學院護理學院
2.261053 山東省濰坊市,濰坊醫學院管理學院
認知功能是指人腦加工、儲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作為一項生理指標,與我國老年人口失能狀況有密切聯系[1]。認知功能障礙導致感知覺、記憶、注意、思維等受損,從而影響日常生活中的學習和決策能力[2]。由于認知功能障礙通常表現為漸進的過程,中老年人因增齡而成為認知功能障礙的高發人群。認知功能障礙不僅會影響中老年人的生活質量,還會影響家庭成員的心理健康,給整個家庭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此外,認知功能障礙還會對死亡率產生影響,認知功能下降迅速患者較認知功能正常的患者死亡風險高75%[3]。
認知功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社會經濟地位、行為生活方式、人口學因素等。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因素是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的獨立危險因素[4],也能通過影響個體社會活動[5]、心理狀態[6]等進一步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受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社會經濟因素,能夠顯著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
當前關于中老年認知功能的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多數研究基于橫斷面數據探討影響中老年認知的相關因素或基于縱向數據探討認知功能變化軌跡。隨著對生命歷程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中老年健康狀況可能與童年期經歷有關,研究多集中于童年逆境對晚年健康的影響[7]。關于中老年認知功能早期影響因素的研究集中于童年家庭內部因素[8],且多分析影響效應,較少關注多路徑的間接效應。因此,本研究基于生命歷程理論,探討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的影響效應及作用路徑,為改善我國中老年人認知功能提供研究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文數據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是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一項旨在通過跟蹤搜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變遷的社會跟蹤調查項目。樣本覆蓋25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目標樣本規模為16 000 戶,調查對象包含樣本戶中的全部家庭成員。根據本文所用數據和變量要求,主要變量來自2020 年的調查數據,但其包含的童年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信息有限,所以使用2010、2012年的童年信息根據個人ID 號進行1∶1 匹配。選取45歲及以上中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由于CFPS 2020 年數據主要通過電話隨訪,故有關認知功能的樣本量較少,刪除關鍵變量缺失的樣本,共獲取1 034 個有效樣本。
1.2 觀察指標

核心自變量為童年社會經濟地位。社會經濟地位常用的測量指標有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職業等。參考王慧敏等[10]的研究,將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使用童年家庭經濟地位自評、父母受教育水平、12 歲時戶口類型、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指數得分(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ISEI)5 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合成得到,其中KMO 檢驗=0.652,Bartlett's(巴特利特)球形檢驗<0.05。童年家庭經濟地位自評分值為1~5 分,分數越高表明童年家庭經濟地位越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分別為小學以下、小學、初中、高中/中專/技校/職高、大專、大學本科、碩士、博士,本研究對這些選項賦值為1~8 分;12 歲時戶口類型將非農業戶口、居民戶口賦值為1 分,農業戶口賦值為0 分;職業狀況根據國際標準職業分類編碼,轉換為ISEI,將其取值范圍依據25%、50%、75%分位數劃分為4 個階層:19~31、32~39、40~45、46~90 分,分別對應社會經濟地位的下層、中下層、中上層和上層[11],賦值為1~4 分。聚合為一個公因子作為連續性變量納入模型。
中介變量為成年期個體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和抑郁狀況。受教育水平采用受訪者已完成的最高學歷,選項分別為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中專/技校/職高、大專、大學本科、碩士、博士,本研究對這些選項賦值為1~8 分,分值越高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作為連續性變量納入模型。社會參與的指標選擇受訪者是否進行鍛煉、是否上網、是否為社會團體成員、是否政治參與,生成4 個虛擬變量[12]并通過加和處理。抑郁狀況采用流動中心抑郁自評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CES-D)進行測量,共包含8 個題目,其中“我覺得生活無法繼續”“我感到悲傷難過”“我感到孤獨”“我的睡眠不好”“我覺得做任何事都很費勁”“我感到情緒低落”,將答案“幾乎沒有”“有時候有”“經常有”“大多數時候有”賦值為0~3 分,“我生活快樂”“我感到愉快”進行反向賦分,將得分相加,賦值范圍為0~24 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狀況越嚴重。
本研究還將性別、年齡、城鄉、醫療服務利用、慢性病患病作為控制變量,其中使用醫療總花費的對數值作為醫療服務利用的替代變量。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采用描述性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相關性探討采用Pearson 相關性分析;影響因素的探討采用多重中介模型回歸分析。采用Hayes 編寫的SPSS PROCESS 宏程序執行基于Bootstrap 的模型81 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和檢驗,重復抽樣5 000 次,95% CI 不包含0說明中介效應顯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以下為復合式多重中介的操作模型(圖1)。公式中分別將M1、M2、M3、Y 作為結果變量,構建線性回歸方程。其中,X 為自變量童年社會經濟地位,Y 為因變量中老年認知功能,M1、M2、M3為中介變量,分別代表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抑郁狀況;iM1、iM2、iM3、iY為回歸方程的常數項;eM1、eM2、eM3、eY為方程的誤差項;a1、a2、a3、b1、b2、b3、d21、d31和c'為回歸系數。

圖1 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中老年認知功能影響的操作模型Figure 1 An operational model of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M1=iM1+a1x+eM1
M2=iM2+a2x+d21M1+eM2
M3=iM3+a3x+d31M1+eM3
Y=iY+c'x+b1M1+b2M2+b3M3+eY
2 結果
2.1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1 034 名中老年人的平均年齡為(62.33±9.89)歲,男性504 人(48.7%),女性530人(51.3%);城鎮居民460 人(44.5%),鄉村居民574 人(55.5%);患慢性病者270 人(26.1%),未患慢性病者764 人(73.9%)。其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得分為(0.000±0.797)分,個體受教育水平得分為(1.970±1.111)分,社會參與得分為(1.150±0.967)分,抑郁狀況得分為(5.960±4.681)分,中老年認知功能得分為(0.000±1.000)分。
2.2 相關性分析
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與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中老年認知功能均呈正相關(P<0.05);受教育水平與社會參與、中老年認知功能呈正相關(P<0.05);社會參與中老年認知功能呈正相關(P<0.05);抑郁狀況與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中老年認知功能均呈負相關(P<0.05),見表1。

表1 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抑郁狀況、中老年認知的相關分析結果(r 值)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education level,social participation,depression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2.3 多重中介模型分析
本研究在控制年齡、性別、城鄉、慢性病患病情況、醫療服務利用水平的基礎上,以童年社會經濟地位為自變量,將中老年認知功能作為因變量,個體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抑郁狀況作為中介變量進行多重中介模型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童年社會經濟地位正向預測受教育水平和社會參與(β=0.538,P<0.05;β=0.129,P<0.05);受教育水平正向預測社會參與、中老年認知功能(β=0.236,P<0.05;β=0.335,P<0.05),負向預測抑郁狀況(β=-0.397,P<0.05);社會參與正向預測中老年認知功能(β=0.064,P<0.05);抑郁狀況負向預測中老年認知功能(β=-0.019,P<0.05),見表2。

表2 多重中介模型回歸分析結果Table 2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mediated-effects model
路徑分析結果顯示,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的直接效應無統計學意義(95% CI=-0.022~0.129)。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和中老年認知功能中的中介效應有統計學意義(95% CI=0.141~0.223,0.001~0.019),分別占總效應的69.23%、3.08%。抑郁狀況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和中老年認知功能中的中介效應無統計學意義(95% CI=-0.001~0.017)。此外,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與中老年認知功能中的鏈式中介效應具有統計學意義(95% CI=0.001~0.017),占總效應的3.08%;受教育水平、抑郁狀況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與中老年認知功能中的鏈式中介效應具有統計學意義(95% CI=0.001~0.008),占總效應的1.54%,見表3、圖2。

表3 中介效應的顯著性檢驗Table 3 Significance tests for mediating effects

圖2 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中老年認知功能影響的結果模型Figure 2 An outcome model of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3 討論
3.1 受教育水平是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的資源路徑
本研究發現,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可以通過受教育水平直接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也可以通過受教育水平影響社會參與、抑郁狀況,進而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有研究表明,個體受教育水平與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密切相關[13]。父母受教育水平作為童年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測量指標,具有代際傳遞作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中老年人其父母能夠為子代提供優渥的教育資源,從而使子代獲得較高的教育水平[14],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中老年人在接受教育方面則面臨更多困難。受教育水平不僅會受到童年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還是個體獲得社會資源的重要條件,從而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產生正向影響。郭帥等[15]通過追蹤數據探究了教育與老年人認知障礙患病率變化趨勢的關系,結果與本文結果與之相似。高教育水平一方面能夠提高個體社會經濟地位,保障醫療衛生服務利用,另一方面也能通過改變思維方式,養成良好的行為生活習慣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產生影響。此外,也有研究發現,教育能通過增加控制能力與概念化能力等認知儲備[16],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產生影響。總之,受教育水平是中老年認知功能的影響因素,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與中老年認知功能中具有重要中介作用。
3.2 社會參與是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的條件路徑
社會參與是“積極老齡化”的核心要求。本研究發現,童年社會經濟地位通過社會參與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產生正向影響。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可能會限制成年后收入、時間及生產生活資料,導致社會交往條件缺乏,社會參與水平下降。國外研究發現,童年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社會團體參與有關,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中老年人,其社會參與率顯著低于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中老年人[17]。社會參與水平能夠正向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這與劉凌晨等[18]的研究一致。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一是社會參與能夠提高中老年人的個體價值感與幸福感,維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延緩中老年認知功能衰退[18];二是社會參與能夠幫助中老年人維持社交網絡,獲得社會支持,增強社會適應能力[19]。此外,史珈銘等[20]研究表明,社會隔離對老年認知功能具有負向影響,反面印證了社會參與對認知功能的保護作用。從上述分析可見,提高中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率能夠減輕生命早期經歷帶來的負面影響,保護中老年認知功能。
3.3 抑郁狀況是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的風險因素
本研究發現,中老年人自身抑郁狀況和受教育水平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的過程中具有鏈式中介效應。具體而言,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可通過受教育水平負向預測抑郁狀況,進而作用于中老年認知功能。抑郁狀況影響中老年人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是心理障礙的主要類型。既往研究表明,抑郁導致患者難以調控自身負面情緒,老年人有限的認知資源被強烈的情緒所占據,導致認知功能受損[21]。從生理機制來講,抑郁可能會導致記憶力、信息加工能力、決策等認知相關能力受損[22]。然而,抑郁與認知功能障礙之間的關系尚未明確,抑郁與認知功能障礙在臨床表現與病理機制中存在相似性。有研究認為認知功能障礙是重度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能夠顯著增加抑郁復發的風險[23]。此外,在本研究中,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抑郁狀況的影響受到個體教育水平的影響,可能因為受教育水平能夠提供經濟、醫療資源,抵抗抑郁狀況,這與CSAJBóK等[24]的研究一致。然而,本研究與上述文獻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抑郁狀況影響的直接效應上存在差異,可能由地區特異性引起。從上述分析可知,抑郁狀況是影響中老年認知功能的風險因素,改善中老年人的抑郁狀況,是提高中老年認知功能的重要環節。
本文基于以上分析結果提出如下對策建議:立足于全生命周期視角,聚焦童年期低社會經濟地位兒童,提高對童年期社會經濟因素的重視程度;倡導居民重視教育水平的作用,積極推進義務教育,促進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同時,積極開展心理測評,加強抑郁風險篩查,關注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政府應積極規劃建設適老化公共設施,滿足多樣化社會參與需求,提高中老年人社會適應能力。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疫情影響,數據庫中樣本多采用電訪隨訪,故文中老年認知功能樣本量較少;并且本文中所采用的童年變量屬于回顧性調查指標,不可避免的產生回憶偏倚;希望在后續的研究中,更加深入探討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的影響效應及路徑。
綜上所述,受教育水平、社會參與、抑郁狀況在童年社會經濟地位對中老年認知功能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可以立足生命周期視角,從個人、家庭、社會多個層面關注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提高中老年認知功能。
致謝:感謝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提供CFPS 數據。
作者貢獻:黃曉彤、王瓊、吳炳義共同負責文章的構思與設計;黃曉彤撰寫論文初稿;黃曉彤、劉晨進行數據收集和整理;侯曉春進行英文修訂;黃曉彤、許心蕊進行統計分析和結果分析;黃曉彤進行論文修訂;黃曉彤、王瓊負責文章質量控制;楊曉對文章整體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