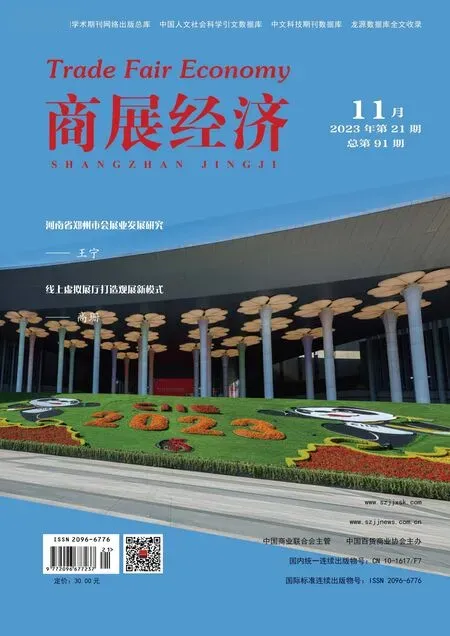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影響研究
鄧嘉琦
(南開大學 天津 300071)
1 文獻綜述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及經濟的迅速發展,文化消費逐漸成為現代經濟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當前,人類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升,文化消費的需求也不斷提高,以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在此過程中,文化消費將會成為社會進步與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因此,如何合理地實現居民文化消費水平提升是值得人們思考和探究的問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字技術與金融領域呈現出深度融合的趨勢,數字普惠金融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技術優勢,為精準有效的金融服務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同時對居民的消費意愿產生了深遠影響。
根據具體的研究成果,眾多學者普遍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張勛等(2020)、易行健和周利(2018)、鄒新月和王旺(2020)運用理論模型并結合實證分析,闡述了數字普惠金融對提升居民消費水平具有顯著效果;通過深入分析數字金融對農村金融需求的影響,傅秋子和黃益平(2018)發現,數字金融對不同農村群體的消費信貸需求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增長趨勢;涂穎清、萬建軍(2022)的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在提升中國居民消費水平方面發揮了雙重作用,即數字效應和普惠效應,尤其是在城鎮居民中,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效應更為顯著,而在農村居民中則相對較弱;江紅莉、蔣鵬程(2020)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消費水平的影響呈現出異質性,這是由于消費群體的差異、不同群體消費水平的差異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居民整體消費水平提升的同時,更加注重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這一點不容忽視。
此外,部分學者探究了數字普惠金融對消費水平影響的地域性差異。任文龍等(2019)的研究表明,通過提高金融發展效率,可以有效促進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的增長,擴大金融發展規模也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文化消費差異;根據南永清等(2020)的研究結果,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中部和西部地區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了積極的正向影響;從空間角度出發,任蓉等(2022)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呈現出異質性,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而數字化程度的直接效應則呈現出明顯的負向效應;據趙雪薇(2021)等的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在東部和西部地區對農村居民的消費升級產生了積極影響,但對城鎮居民的消費升級并未產生顯著影響。
雖然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水平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但對數字普惠金融與文化消費之間的直接關系的研究卻相對較少,更多地關注數字普惠金融對消費支出以及城鄉差距等方面的影響。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本文將數字普惠金融作為研究影響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關鍵變量具有極其重要的實際意義。
2 變量選擇與模型設定
2.1 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被解釋變量:居民文化消費水平(Cul),用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表示。
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fi),該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
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Gdp),用各省市人均生產總值表示;(2)政府行為(Gov),用地方財政文化旅游體育與傳媒支出表示;(3)文化產品與服務價格(Pri),用教育文化和娛樂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年=100)表示;(4)受教育程度(Edu),用各地區大專及大專以上人員占該地區常住人口的比例表示;(5)服務業發展水平(Ind),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例表示;(6)城鎮化水平(Urb),用城鎮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的比例表示。
樣本數據為2015—2020年我國31個省市(港澳臺地區除外)的相關數據,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見表1)。

表1 變量的統計描述
2.2 模型設定
借鑒張冰倩和毛海濤(2022)的研究,本文構建經濟模型如下:
式(1)中:α、β和γ為參數,i和t分別表示年份和省份;Clu為被解釋變量,即居民文化消費水平;Dfi為核心解釋變量,即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fi2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平方項;Z為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Gdp)、政府行為(Gov)、文化產品與服務價格(Pri)、受教育程度(Edu)、服務業發展水平(Ind)、城鎮化水平(Urb)。
3 實證分析
3.1 總體結果
如表2所示,三種回歸方式的結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總體來看,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文化消費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本文用Stata軟件進行Hausman檢驗后,檢驗結果的P值是0.0000,所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變量對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影響。為檢驗實證研究的穩健性,本文使用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例來體現各地區居民文化消費水平并重新回歸。固定效應模型中,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為0.0100,系數方向未發生變化,回歸系數大小也無明顯變化,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實證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2 全樣本回歸結果
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Dfi的系數顯著為正,而Dfi2的系數雖然在數值上趨近于0,但在1%的置信水平上是顯著為負的,說明數字普惠金融與文化消費水平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與文化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倒“U”型曲線也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前期對文化消費起到了帶動作用,而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不斷發展,在到達拐點后,居民文化消費水平也會隨之逐漸降低,但目前來看,數字普惠金融還是正向影響著文化消費水平,拐點還未出現。同時,在各控制變量中,只有政府行為(地方財政文化旅游體育與傳媒支出)在1%置信水平上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政府在文化發展方面的支出與居民的文化消費水平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文化市場的繁榮離不開政府的有力支持,文化消費的增長也離不開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持續關注和投入。
3.2 區域性差異分析
經過Huasman檢驗后,三個地區的P值分別為0.3169(東部)、0.2985(中部)、0.0522(西部),均大于0.05,所以對三個不同區域的實證研究皆應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如表3所示,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回歸結果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系數分別為0.0134(東部)、0.0209(中部);西部地區的回歸系數為0.0068,但結果并不顯著。

表3 分地區樣本的回歸結果
我國東部地區經濟蓬勃發展,文化產業相關市場繁榮,數字普惠金融與文化經濟相互促進,對居民文化消費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中部地區則與東部地區類似,兩者的系數都很顯著,但和東部地區相比,中部地區的系數略有增加。同時,政府在文化領域方面的支出對中部地區的文化消費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這兩個地區相對應的是,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金融發展相對滯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較低,與之相比,城鎮化水平對當地居民的文化消費產生的影響更為顯著。
4 結語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我國31個省份(港澳臺地區除外)的相關數據,實證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影響。結論如下:(1)總體而言,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文化消費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數字普惠金融與文化消費水平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且并未到達拐點;(3)數字普惠金融在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對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提升產生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在中部地區,這種促進效應更加顯著;(4)在我國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并未對居民的文化消費水平產生顯著的推動作用,與其相比,政府對文化消費的作用則更加顯著;(5)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行為、受教育程度、城鎮化水平對居民文化消費水平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本項研究有以下啟示:(1)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居民文化消費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促進金融平等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數字普惠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金融手段,不僅能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交易成本,還能為更多地區、更多群體提供金融服務,其在促進居民文化消費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因此,要進一步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讓更多地區、更多群體能享受到金融的發展成果,充分發揮其在促進文化消費方面的積極作用;(2)積極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中部和東部地區居民文化消費方面的推動作用,在確保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數字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推廣和應用,積極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文化產業的深度融合,增強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同時,隨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日益凸顯,應進一步加大對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建設的政策傾斜力度,以降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在空間上的不平衡程度;(3)政府行為對文化消費市場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既是發揮我國制度優勢的過程,又是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文化消費市場的調控者,其行為對文化消費市場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4)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文化產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文化消費升級、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數字普惠金融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為文化消費保持持續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此背景下,應繼續積極探索,不斷完善數字普惠金融體系,努力滿足不同地區、不同消費水平、不同文化程度的文化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的多樣化和精準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