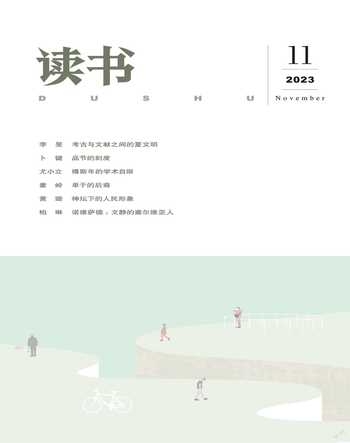單于的后裔
童嶺
如果我們今天出一道地理考題:“內蒙古希拉穆仁草原和西安有什么關系?”恐怕這超過一千公里距離的兩處地方,令當下的讀者難以產生直接的聯想。實際上,時間退回到公元六世紀上半葉,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六鎮之亂——北朝歷史上混亂程度最大、規模最大的叛亂風暴勃興之際,其風暴眼所在地,就包括了六鎮之一——武川鎮所轄的希拉穆仁草原。這次大規模的鮮卑王朝北部疆域的叛亂,卻不可思議地間接“孕育”出了中國史上以長安為都城的最輝煌的時代——隋唐帝國。
如果從“單于的后裔”——破六韓拔陵揭起六鎮反叛大旗的公元五二三年算起,到隋平陳的公元五八九年止,這一孕育過程可謂緩慢地延續了近七十年。其中,伴隨著它的不僅僅是一次又一次的“陣痛”,有時甚至是北中國全域的“劇痛”。溯源隋唐帝國核心層的政治性與民族性因素,六鎮之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基點,以此為基點打破了之前南北朝的動態平衡關系,接著撕裂了一個原先統一的鮮卑北魏。倘若單純從北魏王朝的視野來看,破六韓拔陵無疑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從這個“魔盒”中誕生了兩大巨頭:宇文泰(武川鎮鮮卑化的匈奴人)、高歡(懷朔鎮鮮卑化的漢人),他們將拓跋北魏撕裂為東、西兩個鮮卑政權,并沿著各自的軌跡奔騰向前。
鎮,這一由鮮卑人創設的、異于東晉南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到底是什么呢?公元四二七年,北魏拓跋燾攻下匈奴赫連氏的大夏都城統萬城之后,就在彼處設立了“鎮”,首領為“鎮將”。這是一種軍事與民政的混合體制度,并強調其軍事性。中古史籍中,廣義“北鎮”與“六鎮”的指代大體是一致的,而狹義“北鎮”僅指六鎮中的“懷朔鎮”。若以時間先后論,史籍中第一次出現“六鎮”是在《魏書·高宗紀》中,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詔書稱:“六鎮、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年谷不收。”這份詔書的頒布時間是太安五年(四五九)冬。但實際上,六鎮設置早在“魏主破降高車”時代就有了,這里的“魏主”,無疑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根據清儒沈垚《六鎮釋》研究,可知北魏從陰山山脈至河北省北部,從西至東依次設置了:一、沃野(今內蒙古五原北),二、懷朔(今內蒙古固陽南),三、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四、撫冥(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五、柔玄(今內蒙古興和北),六、懷荒(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縣北)。
六鎮,最初立意是用以拱衛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最西端是沃野鎮,最東端是懷荒鎮。其中沃野鎮的位置,唐長孺《北魏沃野鎮的遷徙》(載《山居存稿續編》,中華書局二0一一年版)一文認為在太和十年(四八六)與正始元年(五0四)有過兩次遷徙。以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六鎮鎮城的位置,多處于農耕區的最北界之上”(張文平:《北魏六鎮新論》,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5 輯)。六鎮之中,只有第六鎮在今天河北省的最北端張家口市張北縣。如果現在從北京北站坐火車“出塞”,火車穿越長城隧道之后,出了張家口,就可以明顯感受到不同于華北平原的草原地貌。其余五大鎮,則基本從西至東分布在今天內蒙古的巴彥淖爾到烏蘭察布之間,且大體都在陰山山脈的北面——也就是背靠陰山,防御來自蒙古大草原的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脅,拱衛鮮卑人的都城平城。
縱觀北魏中前期的歷史,六鎮的數字“六”并非恒定不變,譬如還有:御夷鎮(今河北赤城北)、高平鎮(今寧夏固原)、薄骨律鎮(今寧夏靈武西南。谷霽光用薄骨律替代懷荒,認為其是“六鎮”之一)。自從高車被北魏征服之后,六鎮的軍事目的主要是防衛柔然的侵襲。鼎盛時期的六鎮駐扎兵力,是北魏用于中原及南方兵力的兩倍以上。北朝民歌《木蘭辭》就是鮮卑將士在抵御柔然的大背景下誕生的。
既然六鎮是不同于州、郡等普通行政區域的特別軍事區,同時也是北魏帝國北方的前線基地,那么在“鎮”里面,具體居住著什么人呢?簡而言之,其中駐扎著:一、鮮卑族的嫡系子弟部隊,二、具有胡風的北方豪族漢人,三、投降北魏的部分高車、敕勒、南匈奴、羯等胡族武士。史料明確記載過:“緣邊諸鎮(六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征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齊書·魏蘭根傳》)這些可以控制與威懾內蒙古乃至北亞草原(長遠)的六鎮中,最初占據將帥層面的就是“國之肺腑”(鮮卑族人)與“中原強宗”,兵源層面則還有大量非鮮卑的胡族。就前兩者來說,出鎮六鎮在北魏早期是榮譽與地位的象征。第三種則是久經戈壁磨礪的戰士,尤其如高車族,是標準的全民皆兵的馬上勇士。他們即使去世了,也是在草原上掘坑,讓死者手持武器坐在里面,“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于生”(《魏書·高車傳》)。
六鎮鎮將、戍將與鎮民地位的轉折點是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四九四)春從平城遷都洛陽。南遷洛陽的鮮卑拓跋迅速地中原貴族化,抑或是傳統史書所說的“漢化”。他們逐漸遺忘了留在內蒙古荒原上的同胞們,而留在北方的部分鮮卑豪酋,政治上升途徑被洛陽中央政府徹底阻隔,在仕途和婚姻上不再被認為是清流。他們心懷怨恨的同時,又進一步加大壓榨欺凌六鎮的各族鎮民(當然也包括鮮卑族的貧民)。這樣以六鎮地區為中心,上上下下的矛盾越來越大。
吊詭的是,六鎮之亂的直接導火線,正是設置六鎮的初衷——防御柔然可汗入侵問題。自從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北亞柔然的實力也逐漸衰弱,幾乎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南侵,反而遣使向北魏朝廷求婚。正光年間,柔然發生可汗位爭奪的內亂,阿那瓌成為可汗之后,遣使內屬北魏,北魏孝明帝趁機冊封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雙方關系進一步緩和——相反,六鎮的存在意義就進一步下降。
正光四年(五二三)春正月,柔然地區發生天災,阿那瓌突然率眾號稱三十萬南侵,北魏派出所謂的精兵十余萬,由尚書令李崇、左仆射皇室元纂率領出征,結果卻無功而返。目睹這一切的六鎮之民,從此“意輕中國”——他們對于拓跋統治者不滿之外又加上了一層蔑視。實地感覺到火藥桶就要爆炸的北魏名臣李崇立刻上書,請求將北方軍事性過強的“鎮”改為民政性的“州”,然而當時未被采納。正光四年三月,沃野鎮的破六韓拔陵正式舉起了掀動整個歐亞大陸東部世界連鎖反應的起兵大旗(然而《魏書》與《北史》誤將其起兵年記成正光五年,如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國的形成》也誤從其說。但實際當以《周書》與《資治通鑒》的正光四年為準)。
破六韓拔陵,這位似乎是猛然“跳入”歷史敘述系譜的匈奴血統胡人,身上有著許多未解之謎。首先關于他的姓名,其姓三字《周書》與《資治通鑒》作“破六韓”,《魏書》作“破落汗”;其名為“拔陵”則大體無異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將“韓氏”歸為第三類“內入諸姓”,并云:“知破六韓氏即曾改韓氏之出大汗(步六汗)氏也。”
那何為“出大汗氏”?王仲犖《鮮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認為,這一胡姓的本名當為“步大汗氏”,即《魏書·官氏志》記載的“出大汗氏后改為韓氏”(載《?華山房叢稿續編》,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至于“出”字與“步”字的區別,晚清曾經任駐外蒙庫倫辦事大員、蒙藏總務廳總辦的大學者陳毅,在其名著《魏書官氏志疏證》云:“出當為步,篆書步、出形近,致訛。”(《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至于為什么把本姓步大汗“異譯”為破六韓、破落汗,王仲犖推測是北魏史書有意貶之。然而,“破六韓”抑或“破落汗”是否真的有貶義色彩?恐怕未必,至少到了周隋之際,還有一位匈奴人破六韓裒,深得楊堅信任,充當了楊堅的斥候騎士,在其奪權之后,幫楊堅完成了一個危險的任務——到鄴城喻旨給尉遲迥。《周書》即徑直寫為“破六韓”,并無“有意貶之”的含義。
上述疑惑,需要溯源到“破六韓”“破落汗”,他們都是“單于的后裔”。關于這一點,中古正統史書不會在述及破六韓拔陵時提及,因為這一事件的本質,無論是西魏北周還是東魏北齊,抑或到了隋唐,都將其視為“構逆”“為亂”(《北齊書》)、“反”“反叛”(《北史》),《北齊書·破六韓常傳》云:“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于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后人訛誤,以為破六韓。”具體來說,匈奴右谷蠡王于三國曹操時代內附,右谷蠡王的姓即為“潘六奚”,作為游牧部落的習俗,子孫及部落民皆以酋長之姓為氏。《北齊書》的作者是魏收,他作為六鎮之亂的“近代史見證者”,指出“破六韓”即“潘六奚”的音訛。這位破六韓常,與六鎮起義的破六韓拔陵是“宗人”,作為沃野鎮的匈奴破六韓氏豪強,得到了高歡的極大信任,此后在東魏北齊被追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簡而言之,“破六韓”這一支雖然在北魏末期成為戍邊鎮民,但不可否認他的祖先是匈奴的貴種。破六韓常的父親叫破六韓孔雀,即是破六韓拔陵起兵之后的重將之一,受破六韓拔陵封為平南王。他們都繼承了匈奴武士的驍勇善戰。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下冊》謂破六韓拔陵是“自從東漢以來就已加入鮮卑部落的匈奴人的后裔”。
為什么我要超越“匈奴人的后裔”而強調“單于的后裔”——這一似乎有些攀附北亞高貴血統的因素呢?因為在整個東漢至隋唐的歷史上,華北以及北亞草原爭衡的一條大線索就是:匈奴VS 鮮卑。雖然前者的實力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步下降,但在北亞諸多游牧民族的潛意識中,秦漢時代以來匈奴單于攣鞮氏的血統,依舊是最為尊貴的。故而五胡十六國第一位明確提出推翻晉王朝而獨立建國的,就是南匈奴貴酋劉淵;五胡十六國末期尚能和強大的北魏騎兵野戰對攻的,唯剩鐵弗匈奴赫連勃勃大夏政權。
破六韓拔陵所在的沃野鎮,在地理位置上為六鎮之最西端,在此鎮中的軍民,民族成分最為復雜。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薄骨律鎮的鎮將刁雍就有上表:“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薄骨律)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谷五十萬斛,付沃野鎮。”(《魏書·刁雍傳》)這是史籍第一次出現“沃野鎮”的記錄,同時這份記載支援沃野鎮的文獻中間,四個地方(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無一例外都是原來赫連勃勃匈奴大夏國的領地。
這位有著單于血統的匈奴猛士,首先忍受不了沃野鎮下屬高闕戍戍主的凌辱,先殺戍主,再殺鎮將而起兵——據千唐志所藏北魏書法名品《楊鈞墓志》,被殺的鎮將很可能就是楊鈞的麾下。據墓志,楊鈞的官職是“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大都督”,沃野鎮的鎮將與戍將均隸屬于楊鈞管轄,而楊鈞自己應該駐扎在懷朔鎮。
破六韓拔陵起兵之后,就立刻建元“真王”,我推測這一行為一方面是為了凝聚沃野鎮各族的中下層戰士,另一方面則徹底否定了拓跋北魏王朝的正統性。沃野鎮幾乎毫不費力就被破六韓拔陵占領,高平鎮的匈奴人赫連恩也立刻起兵,與高車族的酋長胡琛一起,響應這位單于的后裔,并攻下了高平鎮。隨后,壓抑著憤怒的胡漢鎮民,狂風暴雨一般繼續向西進攻,包圍了武川鎮與懷朔鎮。
關于武川鎮,因為誕生了此后西魏北周至隋唐的帝系而格外有名。它的遺址所在地,目前主要有三說:土梁城遺址、二份子城遺址、希拉穆仁城遺址。我曾經現場考察過這些遺址,這些位于陰山北面草原地帶的遺址附近,即便是今天,也是肥沃的農耕地,譬如武川縣的小土豆,實在是美味無比,說“味壓江南”一點都不為過。南北朝時期中國沒有土豆,但以今推古,六鎮設置之際,六鎮鎮民已經是胡漢混居,農耕與游牧并行,只有這樣才可能孕育出下一個時代偉大的統御集團。
至于懷朔鎮遺址,目前通說是白靈淖爾圐圙遺址,我在遺址現場的感受是,懷朔鎮明顯比武川鎮三個遺址大,長寬接近1500 米×1000 米,鎮城遺址內有河流經過,并發掘出佛寺。目前發掘的六鎮遺址,它們之間距離在五十至兩百公里以內,西部三鎮相距尤其較近,譬如從二份子城(武川鎮遺址之一)到懷朔鎮遺址,今天的內蒙古道路約七十公里,開車約一小時二十分鐘。從北魏的角度看,如有風塵之警,沃野、懷朔、武川之間可以互為掎角;然而從破六韓拔陵的角度看,他的匈奴族騎兵可以迅速向東占領三鎮。我在這幾處遺址上漫步,特別是走在希拉穆仁草原遺址上,天蒼蒼,野茫茫,身邊不時有一群馬跑過,牛羊在悠閑地吃草。遠處天際的云彩變幻莫測,會瞬間升起人類的渺小感與宇宙的浩瀚感。作為一位長期在南京大學課堂上講授五胡十六國及北朝文化史的江南人,我也瞬間明白了:內蒙古草原的六鎮之人,他們對于時間、對于生命、對于忠誠、對于共同體的榮譽感,是和北魏帝都的洛陽人,抑或南朝帝都的建康人截然不同的。
破六韓拔陵的戰士們由西向東殺赴過來,北魏派出宗室元彧為都督北討諸軍事,勇將賀拔勝從六鎮亂軍包圍之下的懷朔鎮率領敢死隊,大吼“我賀拔破胡也!”突圍至云中面見元彧,懇請他即刻出兵。但武川與懷朔還是落入了破六韓拔陵手中。元彧不得已與破六韓拔陵在五原會戰,結果北魏政府軍大敗。張金龍《北魏政治史》(甘肅教育出版社二00八年版)也指出:“懷朔鎮的陷落,使得北鎮形勢對北魏政府而言急轉直下。”另一方面,我特別想強調懷朔鎮也是破六韓部落民最多的一鎮,約有一萬多匈奴種的鎮民響應他們這位“單于的后裔”。因此,即便有賀拔勝這樣的北魏名將,也不可能收復懷朔鎮。上舉《楊鈞墓志》又云:“運屬橫流,覆舟反噬。鎮豎構逆,遂見圍攻。”講的就是懷朔鎮內外響應破六韓拔陵之軍,最終楊鈞力戰而死。由此,六鎮盡反,《資治通鑒》稱“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齊應他們的“真王”破六韓拔陵。北魏再次派出李崇為統帥,結果在白道與六鎮叛軍進行了慘烈的遭遇戰,對抗北魏大軍的主力,即是破六韓拔陵的沃野與懷朔二鎮有匈奴血統的鎮民。北魏政府軍第二次大敗,退回至云中。
經此二敗,“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于破六韓拔陵”(《資治通鑒》),敕勒一說就是高車的同種,其中西部敕勒的斛律部與叱列部的酋長如著名的斛律金等,都被破六韓拔陵封為王,斛律金家族將在此后東魏北齊的歷史上發揮巨大作用(魏斌:《斛律明月之箭》,載《讀書》二0二二年第一期)。北魏在軍事上無力征討六鎮之兵,于是想起李崇的鎮改州之策,派出《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作為大使,撫慰六鎮,但北上沿途全是叛軍,酈道元未能成行。
無計可施的北魏洛陽政府,居然轉向懇請柔然可汗去消滅六鎮反亂軍——這些本來被北魏用來防御柔然的北邊之民。柔然王阿那瓌立刻率領十萬大軍,自武川鎮殺向沃野鎮,聯合北魏政府軍,屢破破六韓拔陵。在孝昌元年(五二五)的六七月之間,廣陽王元淵的長流參軍于謹利用離間計,策反了敕勒的叱列部。在破六韓拔陵討伐叱列部之后,聯合柔然可汗三面伏擊他。英勇的破六韓拔陵兵敗被殺(一說逃亡,下落不明)。他的退場,正如他的登場一樣,好似當年冒頓單于的一支鳴鏑,迅速、猛烈而燦爛,然后消失在草原的盡頭。
狹義軍事上的六鎮之亂到此結束,但是,以鮮卑等胡族為主體的六鎮兵民二十萬,如何安置他們,是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這一問題隨后引起了更大的波瀾。六鎮之亂的初期,普通鎮民的生存問題與六鎮豪酋的榮譽問題同時占據了第一位,他們從“當時人物,忻慕為之”,淪落到被洛陽的鮮卑貴族鄙視的“代來寒人”。由此,催生了激烈的軍事行為。軍事行為本身,可能并不是六鎮胡族想做的,內在支配欲望也并非起兵的初衷,而是他們想要在既定的北魏政治體系中撕開一條裂縫,重新獲得生存與榮譽的空間。
一九九八年的迪士尼電影《木蘭》,其主題曲是《倒影》,由克里斯蒂娜·阿奎萊拉演唱,開頭幾句是:
Look at me ( 看著我)
You may think you see ( 也許你認為這就是)
Who I really am ( 真正的我)
But youll never know me ( 但你從沒有了解我)
北魏末年,柔然已經不再能構成對洛陽朝廷的本質性威脅,南朝也無意實質性北伐,至少表面上北魏可謂“當時四海宴清”,但正如歌詞所唱:But youll never know me(“但你從沒有了解我”)——假設北魏的歷史在沒有六鎮之亂的情況下繼續延長下去,洛陽朝廷很可能更加“南朝化”與“貴族化”。但“單于的后裔”破六韓拔陵扭轉了這一進程,他掀起的六鎮風暴在民族意義上是中古史上的匈奴與鮮卑“永恒”矛盾之再現;在政治意義上是邊疆鎮民與洛陽朝廷的矛盾之反映;而在“長時段”的意義上,六鎮之亂則是從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另一個完全相反的角度開啟了隋唐帝國的構建。
時間退回到六鎮之亂前整整三十年,孝文帝雖然決意遷都洛陽,其實他的內心還是放心不下代北六鎮。正式遷都前的幾個月,他出塞北巡。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懷朔鎮與武川鎮的土地,這一年,破六韓拔陵可能已經七八歲,而高歡只有兩歲,宇文泰則尚未出生。
“二0二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就是武川縣的大青山壩頂北魏祭祀遺址,我無法推測孝文帝在此祭天時禱告了什么,但北魏王朝此后顯然沒有按照他的禱告運行下去。
對于六鎮風暴的“單于的后裔”破六韓拔陵而言,他所倒影(Ref lect ion)或者說映射到中國中古史上的形象,無疑是多面而且復雜的,甚至在他消失之后,依舊有著巨大的歷史推動力。破六韓拔陵的年號叫“真王”,但到底“真正的我”(Who I really am)是什么?依舊是一個存在無窮魅力的中古文史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