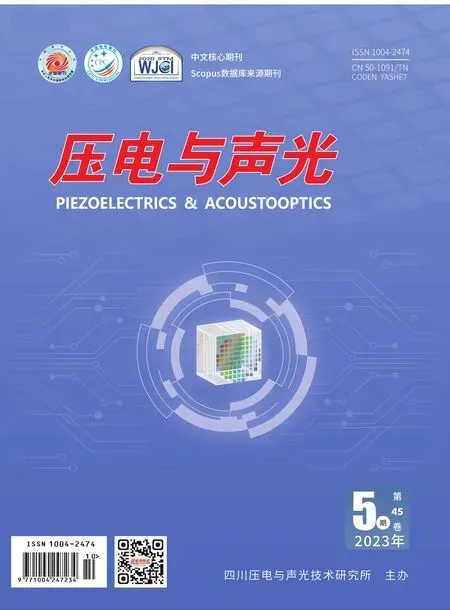基于HHT的光纖慣導系統級標定改進算法
顧生闖,蔡春龍,張 峰
(北京航天控制儀器研究所,北京 100094)
0 引言
光纖慣導已被廣泛用于飛機、汽車、艦艇等國防和國民經濟領域,其標定方法分為分立式標定和系統級標定[1]。系統級標定作為目前國內外的主流標定方法,許多學者將重點放在設計不同的慣性測量單元(IMU)編排路徑。Mark指出陀螺誤差參數與旋轉路徑相關,并據此設計了兩條正交標定路徑[2]。Lee采用系統級標定法辨識加速度計和陀螺的標度因子、安裝誤差角及加速計零偏,并設計了相應的標定路徑[3]。謝波等提出了一種多位置連續轉動標定方法,利用最小二乘估計,全面辨識出所有21個誤差參數[4]。但上述方法仍需借助轉臺、溫箱等設備,而溫箱壓縮機、轉臺電動機、實驗室環境等引起的隨機誤差均會對儀表的標定準確性產生影響。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提出了一種基于希爾伯特-黃變換(HHT)的高精度光纖慣導系統級標定方法。
1 慣性測量單元誤差模型
在光纖捷聯慣導系統中,IMU一般由3個光纖陀螺和3個加速度計組成。由慣性儀表引起的導航誤差占整個導航系統誤差的70%以上。根據誤差的來源,誤差可分為兩類:一是慣性儀表的器件誤差,主要包括零位、標度因數等誤差;二是慣性儀表的組合誤差,即慣性儀表3個敏感軸的不正交性和與本體安裝時的不準確性所導致的安裝誤差。考慮零位、標度因數及安裝誤差等參數,慣性儀表(以陀螺為例)一般建立如下數學模型:
Gc=G0+KgEgGr
(1)
其標量形式為
(2)

慣性儀表的標定可分為辨識和補償兩部分。辨識是通過已知的輸入信息和測得的輸出信息計算誤差模型的各項參數,而補償是通過算法(軟件程序)減小或消除誤差。由辨識模型可得到補償模型:
(3)

同理,加速度計的辨識和補償模型分別為
Ac=A0+KaEaAr
(4)
fb=Ar=(KaEa)-1(Ac-A0)
(5)
式中fb為加速度計補償后的輸出比力。
1.1 安裝誤差理論模型
光纖慣導IMU直接與載體相連,理論上慣性儀表的敏感軸、IMU基準軸、載體坐標軸三者完全重合。在實際應用中,IMU基準軸與載體軸基本完全重合,但陀螺和加速度計的3個敏感軸都無法完全正交,且慣性儀表和IMU基準軸也無法完全重合。由于不正交誤差和不重合誤差表達式相同,故將上述誤差統稱為安裝誤差。
圖1為光纖陀螺的安裝誤差示意圖。圖中OXgYgZg為陀螺的非正交坐標系,OXbYbZb為載體的正交坐標系,αij(i,j=x,y,z)表示b系i軸與g系j軸所在直線的夾角余角,且i≠j時接近于0°,i=j時約為90°,則載體坐標系到陀螺系的坐標變換矩陣即為陀螺安裝誤差,有

圖1 安裝誤差角示意圖
(6)
同理,加速度計安裝誤差為
(7)
1.2 慣性儀表標定誤差對導航性能的影響
捷聯慣性導航系統的誤差方程一般可表示為
(8)
(9)


(10)
式中i=g,a。將式(10)分別代入式(3)、(5)可得:
(11)
(12)
將式(11)、(12)代入式(8)、(9)式可得:
(13)
(14)
由式(13)、(14)可知:
2) 加速度計安裝誤差的標定誤差對導航的影響與載體比力fb有關。靜止時,加速度計輸出比力fb為重力加速度g;當載體相對慣性空間做變速運動時,加速度計安裝誤差的標定誤差也被放大。
2 系統級標定的一般方法
2.1 傳統系統級標定方法對比
目前國內外常用的系統級標定方法有兩種[1]:系統級標定濾波法和系統級標定擬合法。系統級標定濾波法以IMU誤差參數為狀態量,導航誤差為觀測量,通常采用卡爾曼濾波進行狀態估計[5]。其不再依賴于高精度轉臺和大理石平板,相較于分立式標定具有更高的標定精度,但計算量大,可觀性分析復雜,標定時間較長,且噪聲矩陣和狀態量的初值設置影響濾波的收斂性和收斂速度。系統級標定擬合法是通過數學分析的方式建立IMU各項誤差參數與導航誤差參數的解析關系,再通過最小二乘法擬合得到標定結果。該方法避免了卡爾曼濾波算法的相關缺點,同時具有計算簡單、不依賴高精度設備、標定時間短、標定精度高等優點[6-7]。
2.2 系統級標定擬合法
為了簡化推導過程,式(11)、(12)所建立的IMU誤差模型可簡化為
(15)
(16)

系統級標定擬合法的目的是通過導航速度誤差求解IMU誤差參數,記X為IMU的21項誤差參數組成的向量,其關鍵在于確定如下線性或近似線性映射關系:
(17)
或者確定如下線性關系:
(18)
為了充分激勵出IMU所有誤差參數,設計多位置轉動方案如表1所示。

表1 19位置轉動方案
系統通過18次轉動得到18組方程,每組方程推導過程類似且都包含對準、動態轉動、靜態導航過程,如圖2所示。選擇當地水平地理坐標系為天東北,以第一次轉動前后為例簡述推導過程(詳細推導可參考文獻[4])。

圖2 標定狀態示意圖
由式(8)、(9)的導航誤差方程出發,忽略牽連加速度的影響,可得:
(19)
每次轉動可得8個方程,18次轉動共得到144個方程,然后運用最小二乘法求得IMU所有誤差參數。
3 希爾伯特-黃變換在系統級標定擬合法的應用
3.1 傳統系統級標定擬合法的缺陷
傳統系統級標定將儀表所受環境噪聲視為白噪聲,直接選用儀表輸出信號通過系統級標定擬合法計算安裝誤差。而實際過程中,轉臺電動機、溫箱壓縮機等實驗室環境引起的隨機誤差具有非線性、非平穩特征,直接影響儀表的標定準確性,進而影響導航精度。
本文選用某型號光纖慣導,設計了在轉臺靜止和運行、溫箱靜止和運行等環境試驗,并對陀螺和加速度計的輸出信號進行頻譜分析,如圖3、4所示。

圖3 溫箱靜止、運行時陀螺輸出信號及其頻譜

圖4 轉臺靜止、運行時加表輸出信號及其頻譜
由圖3、4可知,由于外界環境引起的高頻噪聲導致慣性儀表輸出的原始數據包含諸多干擾信號(溫箱運行產生50 Hz的工頻干擾信號,轉臺工作時引入3.6 Hz的倍頻信號),并且不是傳統標定方法中假定的白噪聲,所以對原始信號進行濾波處理具有較大的意義。
3.2 希爾伯特-黃變換
希爾伯特-黃變換(HHT)是近年來發展的一種新的時間序列信號分析方法[8-9],其核心是經驗模態分解(EMD),把復雜的信號分解成若干個本征模態函數(IMF),再對IMF進行希爾伯特變換,得到每個IMF隨時間變化的瞬時頻率和振幅,最后求得振幅-頻率-時間的三維譜分布。由于EMD是自適應,故其分解快速有效;同時EMD是基于信號的局部變化特性,可用于非線性和非平穩過程分析。與頻譜分析方法(FFT)相比,HHT得到的每個IMF的振幅和頻率都隨時間變化,消除了為反映非線性、非平穩過程而引入的多余無物理意義的簡諧波。與小波分析方法相比,HHT具有小波分析的全部優點,在分辨率上消除了小波分析的模糊和不清晰,具有更準確的譜結構,因而HHT在分析非線性和非平穩過程中具有很高的應用價值[10-11]。
信號x(t)經EMD分解后生成了N個IMF信號分量,這些IMF分量的頻率成分依次從高頻到低頻分布,其中第1個IMF為最高頻部分,第N個IMF為最低頻部分。從IMF 篩選過程中可見,隨著篩分層數的增加,后篩分的IMF信噪比增加,因此,先篩分的IMF信噪比小于后篩分的IMF。對于所篩分的IMF分量,給定索引j,則{imfN>j}中信噪比高,而{imfN
假設有用信號y(t)被高頻噪聲信號z(t)干擾,得到新的信號:
x(t)=y(t)+z(t)
(20)

(21)
式中M為信號的總長度。
濾波的結果可用最小連續均方差(CMSE)作為評判標準[12]:
k=1,2,…,N-1
(22)
式(22)化簡得到:
(23)
則索引j的數學表達式為
(24)

(25)
以某型號光纖陀螺儀為例進行HHT“篩分”,結果如圖5所示。

圖5 EMD分解結果
由圖5可見,經過10次分解后,殘差變成單調函數,至此分解完成。此時信號x(t)可表示為
x(t)=[c1(t)+c2(t)+…+c10(t)]+r11(t)
(26)
完成上述頻率分解后,對信號進行重構,可有效濾除隨機噪聲信號。對不同層數的IMF求解CMSE,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不同層數的CMSE值
由圖6可知,當索引j=2時,IMF的CMSE值最小。另外,圖5中前兩層IMF的頻譜主要分布在高頻帶,而光纖陀螺的有用信號為低頻信號。綜上可認為前2層IMF為噪聲信號,而保留第2層以后的信號,由此進行重構后的輸出為
x(t)=[c3(t)+c4(t)+…+c10(t)]+r11(t)
(27)
綜上所述,慣性儀表的輸出一般是低頻信號,結合EMD分解頻譜中高頻隨機信號的分布和CMSE評判標準,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有效信號被保留,噪聲信號被濾除。
3.3 希爾伯特-黃變換優化系統級標定精度的機理分析
式(15)、(16)所建立的誤差模型是以儀表輸出理想值為基礎,而真實儀表輸出包含了高頻噪聲,且經頻譜分析發現噪聲幅值相對較大,其影響有以下兩點:

(28)

如3.2節所述,使用希爾伯特-黃變換的目的在于濾除原始儀表輸出中環境噪聲,確保系統級標定建立的誤差模型具有準確性,同時保證導航速度誤差與IMU誤差參數之間具有線性映射關系,然后才能通過最小二乘法進行擬合。
3.4 基于希爾伯特-黃變換的IMU誤差參數辨識
采用希爾伯特-黃變換分別對光纖慣導陀螺和加速度計輸出信號進行處理,然后利用系統級標定擬合法計算慣性儀表各項誤差參數。
首先,本文通過帶溫箱的三軸轉臺設計了19位置系統級標定試驗。其次,采用希爾伯特-黃變換對所得IMU數據進行濾波處理。其中,三軸陀螺輸出信號去除的IMF層數分別為2、2、3,然后重構得到新的陀螺輸出信號。光纖陀螺的原始信號和濾波后的信號如圖7所示。運用同樣的方法得到濾波后的加速度計信號,分別計算了三軸信號在濾波前后的均值,如表2所示。使用系統級擬合標定法計算IMU誤差參數,表3、4對比了濾波前后陀螺和加速度零偏變化。

表2 濾波前后加速度計信號均值

表3 濾波前后光纖陀螺零偏值

表4 濾波前后加速度計零偏值

圖7 濾波前后光纖陀螺信號
由圖7和表2可知,對陀螺和加速度計輸出信號進行濾波,信號中的高頻噪聲被濾除、慢變漂移趨勢被保留,同時濾波前后的信號均值相對于50×10-6g的加速度計未發生太大變化。由表3、4可見,希爾伯特-黃變換處理后的誤差參數得到一定程度的優化。
4 仿真分析與試驗驗證
為了驗證該方法的正確性,進行動基座導航試驗驗證。將光纖慣導及GPS接收機放置在導航車上,光纖慣導預熱15 min,對準10 min,以10 ms采樣周期采集1 h的慣導原始脈沖數據。
基于慣導原始脈沖數據,分別對以傳統算法和改進算法得到的誤差參數進行補償及仿真分析,同時以實時衛星導航數據作為基準,對比不同算法的導航結果,如圖8所示。為了避免試驗結果的偶然性,按照上述步驟進行3次試驗,試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跑車試驗結果對比

圖8 第一次跑車試驗結果
由圖8和表5可得:
1) 在動基座導航試驗中,慣導在直線行駛過程中,誤差發散較慢,與GPS解析出的位置基本重合;但當發生轉彎或掉頭等大動態運動后,位置誤差更快地發散,主要原因是動態過程中安裝誤差和標度因數標定的不準確性導致儀表誤差被放大,最終帶來更大的導航位置誤差。
2) 對于高精度光纖慣導,使用本文方法計算出的誤差參數更接近慣導的真實誤差模型。尤其在大動態運動中,模型參數準確性的提升,進一步提高了慣導導航位置精度。經過3次重復試驗,導航位置誤差相對減少約10%,證明了所述方法的有效性。
5 結束語
本文研究了光纖慣導誤差辨識技術,提出了基于希爾伯特-黃變換的高精度光纖慣導系統級標定改進算法。該算法能夠優化IMU數據,有效地去除了高頻隨機噪聲的影響,從而獲得更準確的IMU誤差參數。開展了動基座下多次導航試驗,試驗結果表明,1 h的動態導航位置誤差相對減少約10%,證明了該方法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