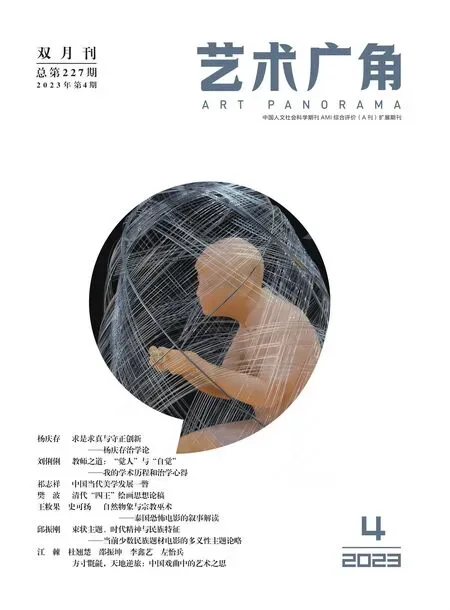在拐角處見
——說王雪茜《時間的折痕》
劉恩波
翻閱王雪茜的《時間的折痕》,如同走進作者心靈浪花的漩渦深處,跟著那一波又一波的浪,洗禮著文字記憶的潮汐。
不必諱言,王雪茜探入了精神歷史和文本脈絡之中,用自己特有的語調、口吻和言說方式,為我們打開了一道通向靈性閱讀的門窗。
那門窗連著街道,連著風景線,連著讀者的心。
或者說,雪茜的文字,是生命的相約,帶你到某個精神的拐角處,一下子見證了存在本身的折痕和光影。
赫爾曼·黑塞說:“世界上任何書籍都不能帶給你好運,但是它們能讓你悄悄成為你自己。”
也許,那個你自己,有時候是通過閱讀和理解別人才意外發現的。
對于我而言,看了雪茜的《尋找朝圣的方向》,就等于在她別致會意的字里行間,找到某處路標,某個驛站背景里的燈光。那是人類精神深處的折光。
《一個人的朝圣》是作家蕾秋·喬伊斯的心靈之旅的豐碩見證。某種程度上,雪茜的那篇讀書隨筆,也是引領我走進該書閱讀的踏板和過濾器。
茫茫人海中,喧嚷世間里,能夠接引你走向生命閱讀的文字和書畢竟不多。
當我走進《尋找朝圣的方向》,在雪茜用她靈感和心音交匯而成的書寫律動中,應該說發現了文學閱讀的一塊寶地——換而言之,這是精神生活的某個拐點和轉角,召喚著讀者前去尋找夢想的慰藉和依靠。
一天早晨一封信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那個叫哈羅德·弗萊的老頭兒,接到20 年未見的昔日同事兼朋友奎妮的告別信,她患了癌癥,并且正在走向生命最后一段日子的消息,讓他不能自持,他決定徒步去看奎妮——于是一個人,87 天,627 英里的路程,變成了這個平凡人最不平凡的傳奇歷程。
這是帶著信念和精神之光的奔走,不是旅行,也不是夢游。雪茜通過《世說新語》里王子遒雪夜訪戴的故事,還有杰克·凱魯亞克的傳世經典《在路上》的生命漫游的行跡,比照著說出了隱藏在哈羅德·弗萊行程背后的人生之道的奧義——“直視生存的悲劇性,通過張揚個體的悲劇精神來超越悲劇,從而達到對生命本真的體驗。”[1]王雪茜:《時間的折痕》,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248頁,第271頁,第22頁,第36頁。
也就是說,在雪茜提供給我們的精神閱讀的拐角處,她其實袒露了自己對于信仰、靈魂狀態乃至存在奧妙的某些深刻的領會和揭示。譬如,她以“救贖之旅”這個詞,洞悉、豐富了弗萊的步行,其實是去尋找信念和依托的內涵和意義。在她眼中,弗萊的朝圣之旅,同時也是夫妻關系的破冰之旅,是建構失去已久的親子之愛的紐帶和扶手,更是弗萊重新走進生活腹地發現另一個自己的身心修煉與整合。
走到貝里克,只要他在走,奎妮就會活下去,這構成了哈羅德·弗萊的內在支撐和源泉。雪茜說:“有時候你需要一個距離,才會看清真相,看清自己。”[2]王雪茜:《時間的折痕》,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248頁,第271頁,第22頁,第36頁。或許,我們都會在現實生活的某段時間、某個地帶、某種境遇里,迷失真我,偶爾又會通過特殊的救贖方式,把那個真我找回來。
雪茜將《一個人的朝圣》界定為關于勇氣、嘗試和生命不確定性的小說,她用一系列哲學、心理學、美學、精神分析等與之深度焊接的語態和情態表達方式,令人信服和具有延伸性地解剖了該書的架構、內涵、底蘊、形式,以及帶給讀者的精神凈化和感召作用。
正是借助這篇寫《一個人的朝圣》的妙文,我走進了雪茜那豐盈精彩的文字世界,發現她已經在那里開拓了屬于自己的文學疆土和精神邊界。
她的讀書隨筆集《時間的折痕》收入了十幾篇關于現當代世界文學經典的解讀文字,文風矯健灑脫,論述剴切得體,筆調里常常帶著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款款幽情脈脈神韻。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雪茜已經在閱讀和發現人類精神高峰的坐標里找到屬于自己的井泉的泉眼。這只要從她言說到的作家類型和作品的豐富性以及精彩程度上即可辨認出來。
《輕盈者的翅下藏著閃電》把視角對準了法國作家馬塞爾·埃梅的文學肌理和風格淵藪,在其中探尋其價值落點與精神走向。尤其難能可貴的還在于,她用了一節文字來比較埃梅與拉伯雷的血脈淵源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讀起來發人深省引人入勝:他們同是怪誕的現實主義的筆法,用夸張和諷刺解剖了人性深處的毒瘤,用笑聲祛除了命運的幽暗;另一方面,“拉伯雷的小說總體來說,格調明快,情緒樂觀,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天真憨厚。而埃梅的小說基調大都辛酸悲苦,他常寫失意者和下層人物,令人一掬同情之淚,作品顯得較為深沉悲愴。”[3]王雪茜:《時間的折痕》,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248頁,第271頁,第22頁,第36頁。
《時間的折痕與靈魂的印識》深入探討了愛麗絲·門羅的創作奧妙,從閱讀體驗、敘述視角、生命狀態(與馬爾克斯比照)、風格坐標等諸多處,找尋著通往她寫作之路的房間和走廊,街巷與拐角。“她用傳統的方式敘說故事,但用中斷、轉向、奇妙來表達發生的一切,她想讓讀者感到的驚人之處,不是發生了什么,而是發生的方式。她的敘述既從容飽滿,又有點午后陽光照射下的慵懶穿插和旁逸斜出,不真正熱愛她文字的讀者很可能與她失之交臂。”[4]王雪茜:《時間的折痕》,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248頁,第271頁,第22頁,第36頁。
雪茜讀門羅,讀得精細傳神,讀得既有路徑,又有竅門,真是風景這邊獨好的美妙讀解和探秘。她用莫比烏斯環的誘惑——永遠沒有出口的無限循環和埃舍爾繪畫難以找到出口和入口、不分上下的詭秘線條,來形容門羅作品的無限神秘性、敞開性和豐富性所在。
現代意味十足的小說已經背離或者說超越了傳統,它們不再因循因果律或者時間的線性敘事,而是鐘情于時空切割、主觀幻覺還有顛倒時序,似乎跟電影、繪畫乃至無調性音樂發生了密切的溝通。
雪茜視門羅為一個“內心的擴張主義者”,她小說的開頭和結尾都無章法可尋。如果用韓美林的說法,“藝術就是一筆下去,破它的七法八法”,以此來看門羅作品的框架結構和內在支點會是破迷開悟的點化之言。
“在門羅的小說中,時間空間都被扭曲、切割成一格一格的(像是碎布塊),然后她再隨心所欲地加以交叉重組,在下一個轉折之前,你無法預料到她將要寫什么,就像在一個新的轉角之前,你不知道會出現什么風景。”[1]王雪茜:《時間的折痕》,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46頁,第198頁。雪茜發現了門羅小說的精彩暗穴,在她眼里,只有這樣,門羅才回歸到文學異質敘事的本質——寬闊的、摸索的、模糊的、不確定的那種本性。
《故事》的作者羅伯特·麥基曾經別有見地區分過大情節、小情節和反情節三類人類故事情節模式。大情節,即傳統的戲劇化敘述,追求完整的因果律,因循時空高度合一的準則;小情節帶有散文化和詩化特征,故事走向相對游離自由;反情節則是打破了線索因果的專橫戒律,用閻連科的小說學講法,即是以半因果甚至零因果出場,徹底扭轉了人類想象力和審美力的終極疲勞。
或許以此來理解門羅的寫作門道,大概會有所助力吧。既然她說過“小說不像一條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那么我們走進其作品的錯雜無序,會是天經地義的享受。傳統的小說寫法死了,新意味新狀態的小說得以建立和誕生。
閱讀雪茜的讀書隨筆,你會覺得她的話題深刻有趣,議論縱橫捭闔,詞彩生動鮮活,這恐怕與她愿意選擇個人化個性化的生命體驗視角有關。
即以對塞林格別有會心的解讀來說,我覺得雪茜那篇《別在我唇上尋你的聲音》就是明顯的佐證。由于熱衷剖析引證塞林格的人確實太多了,該怎樣確立自己的閱讀法,對于每一位研究者都是不小的挑戰。
這一次雪茜故意屏蔽了塞林格的文學作品的敘事學視角,沒有像寫埃梅和門羅那樣通過精彩解剖其文本的蛛絲馬跡來印證經典性,而是用大眾傳媒與個性化作家的性格癥結的內在對抗的思路,厘清了簇擁在塞林格身上的世俗灰塵。
毋庸置疑,塞林格的遁世隱居幾乎構成了他生命史最令人為之著迷、困惑和茫然的部分。他作品的向心力和為人處世的離心力構成了二律背反,像是一首交響曲之中容納了極度錯位對峙的不和諧樂章。
《別在我唇上尋你的聲音》探入塞林格的性格暗礁之處,著意開掘其生命向度和價值觀的底座及其背景,讓我們了然塞林格之所以是塞林格的內在有機構成的可信度。
雪茜寫道:“在我最喜歡的塞林格的短篇小說《獻給愛斯美的故事——懷著愛與凄楚》中,那個叫查爾斯的小男孩總愛說一個謎語:猜猜看,一堵墻對另一堵墻說了什么?答案是:在拐角處見。”[2]王雪茜:《時間的折痕》,黃山書社,2021年版,第46頁,第198頁。
或許雪茜關于塞氏的探秘尋蹤,是在墻縫里找到了門,“凡墻都是門”,只是尋訪者要有足夠的耐力、思悟和信心。
首先,她發現戰爭創傷后遺癥帶給作者的終生困擾,稱之為“無法抹去的灼痕”。塞林格1944 年登上運兵船前往英格蘭,其后登陸歐洲,連續作戰11 個月。那無疑是肉體的創傷和日后精神撕裂的難以愈合的記憶痛點。海明威、約瑟夫·海勒、馮尼古特等西方大作家都飽受過戰爭陰影的遮蔽與傷害,于是有《永別了,武器》《第二十二條軍規》《五號屠場》等經典作品的深度印證。塞林格沒有以小說的形式強攻戰爭文學,也許他受到的磨礪和洗禮并沒有找到宣泄的通道和路口,倒是在其代表作《麥田里的守望者》中在主人公霍爾頓·考菲爾德身上,作者發出了反抗的微弱呼喊,盡管霍爾頓并非一個改變世界的戰士,而是一個游走在西方正統文化秩序之外的邊緣少年。
其次,塞林格的選擇是錯位式的,他對戰爭的指控轉為對戰后虛榮偽善的高度道德綁架化的主流社會,予以痛切憂思、指控、描繪和勾勒,用藝術呈現的形式投了反對票。其實,某種程度上塞林格就是考菲爾德,孤獨、無助、憂郁、叛逆、憤懣、不平……這一系列的氣質顯然造成了他后來的避世離俗傾向。用雪茜的話說,塞林格對隱私的狂熱的保護,加大了他的神秘感,而這也是大眾文化媒介即使在他隱退后,依然狂熱尋找他的因由。曝光和晾曬名人隱私,“以面目全非的方式供人消遣,遭人非議”,無疑構成了消費時代的總體精神癥候。
雪茜為我們嘗試解答的塞林格存在之謎,從一開始就找到了作家個人生活的聚焦點,即神秘和隱遁的內在需要,她用“內心的戰場也是地球上最孤獨的地方”來形容塞氏之所以把自己隱藏起來的根由。進而又結合作家家族影響、個人身世命運和性格傾向乃至契約式生存方式等諸多因素,圍繞著社會的獵奇出版和各種甚囂塵上的傳言輻射,和作家個人和家人之間的拉鋸戰,讓我們看到了文明機制里存在的機體病毒。
雪茜認同“在洶涌人潮中保有隱私是文明的標志”,而我們要想找到真正的塞林格,也只能在他的作品中,在那片孤寂而蒼涼的麥田里,去呼吸和感召人性和藝術的魔力。
塞林格,“在拐角處見”!
讀雪茜的文字,總覺得她是在攪動著作家血脈靈魂的冰與火,從那一聲一響、一動一靜、一張一弛中去領會歲月的滄桑和人性的冷暖。
探索過塞林格的墻,再來穿越特朗斯特羅姆的深淵,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事。那篇《每棵樹都是自己聲音的囚徒》就是關于特朗斯特羅姆詩歌旅程和精神奧義的富于個人才情的闡釋和解說。在這里雪茜調動了關于詩歌歷史、常識、信念和個性體驗的諸多學養,尤其是從生命的病理學角度切入詩人世界和詩意存在的隱痛和悖論之中,為我們燭照了那在深淵里掙扎、渴望、超越和救贖的靈性未泯的沖動與激情。
作為當代具有世界意義的詩歌巨匠,理解特朗斯特羅姆若不從他生命精神的淵源和文化坐標的譜系里去探入尋覓,恐怕很難發現其存在的端倪和入口。
雪茜的把脈問診從緣起階段就以“作家與心理危機”為基始為發端,通過探討中外詩人自殺的價值撕裂和斷裂現象,賦予詩歌和詩性以一種“哲學的超驗與生命的體驗相結合的微妙而令人顫悸的粘合力”,使語言的傾訴和詩意的表達變成“自由翻飛和俯仰無礙的飛行器”,于世俗和宗教之間自在穿梭。
有的詩人越過生死邊際,走向了存在的彼岸或者虛無,也有的遁隱蟄居于話語的故鄉,與死亡擦肩而過,而回返到精神探尋的深淵之處,踏歌而走,踏浪而行。特朗斯特羅姆無疑屬于后者。
應該說閱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就宛如用一把斧子鑿破凍結的冰川,其冷硬凌厲騰挪峭拔之風姿,綽約活現在眼前。從表面上看,那是詞與物并置的現實,實際上是生與死的對峙最后融解化合成了詩。
在雪茜筆下,特朗斯特羅姆深刻了悟了詩人之死的意義和價值,但他最終還是堅持活了下來,而沒有像策蘭、海子、川端康成等人那樣走向自絕和毀滅。雪茜從父愛的缺失、童年的孤寂、抑郁和自我放逐等視角還原了這位瑞典大師面臨深淵懲罰時的無以自拔的失措不堪,還有后來借助音樂和詩歌帶給自己救贖時的絕望中的希望。
讀雪茜寫特朗斯特羅姆小時候生活片段的文字時,譬如,有一次他和媽媽參加音樂會散場后意外走失的情形,覺得作者的確是以漣漪般的內心涌流攥住了被寫者的手。這讓我不禁想起自己閱讀伯格曼自傳《魔燈》、薩特自述《詞語》時的那種同等的面臨生活現場的抓握感——好的文字是在細節上覓取到人的存在狀態的魂魄的。
特朗斯特羅姆本來想成為作曲家,卻意外成為詩人,其職業身份是探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學者,這恐怕與他童年時經歷的一系列噩夢般的插曲有關。性格塑造命運,也注定與那些藕斷絲連的外部環境因素的細微影響脫不了干系。陽光背后陰影一直牽動著內心的撕咬。它構成了特朗斯特羅姆根深蒂固的詩意癥結。
概而言之,好的文學解剖和鑒賞會引發讀者的豐富聯想與延伸性的思維構建。
即如閱讀《時間的折痕》,體味作者從異質感個性化出發而帶給我們的心靈輸氧和文化傳導,玩賞那穿過時間湍流和歷史迷霧而蔚為壯觀的氣象,品覺她“探賾索引的私性筆觸”(于曉威語),確實會有一種走入寶山滿載而歸的踏實感和愉悅感。
可以說,雪茜這些充滿十足審美鑒賞意味的隨筆,是進入了文學本體內部的打撈與開掘,是跨越文學傳統迷霧和障壁的巡游和尋夢。她與筆下的作家作品聲氣相通,如影隨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窺其堂奧,點其命脈,勾勒出別樣的精神靈性畫圖。
《時間的折痕》構成了王雪茜的文本世界、詩性時空,更是她不斷出發的人生和藝術行走步履的薈萃與交集。她是一個孤獨的探尋者,將目光和視線定格在西方經典的幽邃之處,帶著屬于自己的信念、定力和熱切,去攀援一座座橫亙在文學史冊腹地或邊緣地帶的極峰。
而她的行文卻是那么晶瑩、剔透,散發著感召力和誘惑力。當年托·斯·艾略特曾經希望美好的文學鑒賞,要讓人聞到玫瑰花香味一樣帶著芬芳,我覺得雪茜的文字就有著與之相近的姿態和況味。
雪茜是探路者,也是猜謎者,最后愿意援引另一位大師谷川俊太郎的一句詩,“謎隨著年齡一起加深”[1]〔日〕谷川俊太郎:《谷川的詩》,田原編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534頁。作為本篇閱讀觀感的收尾。相信雪茜在勘測人類思想和精神之謎的路上會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