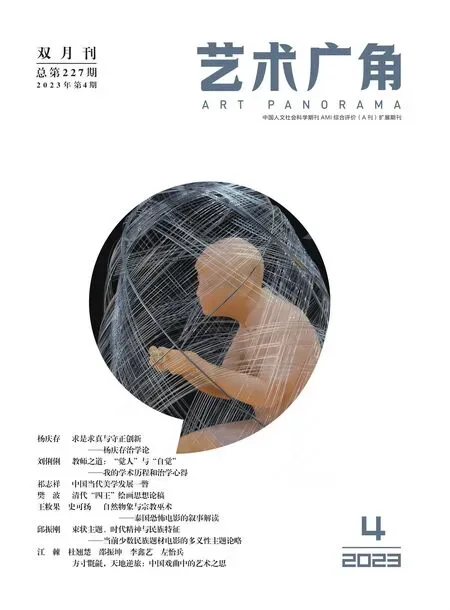試說石濤的“一畫之法”與“先天后天之法”
徐可超
石濤的畫作,世人莫不嘆服其神妙。至于何以有如此神妙之法,石濤也并非秘不示人,自著《畫語錄》以概說其要領。然而,《畫語錄》似乎頗涉玄遠隱微,令人莫測其奧義,歷來對之“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越說越糊涂”[1]吳冠中:《我讀石詩畫語錄》,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既然眾說紛紜而難得糊涂,我也想以己之淺見,妄置一喙,恐怕也只能再徒增一些糊涂罷了。
一、“庖羲一畫”
《畫語錄》之所以難懂,難就難在其中所謂“一畫之法”。明白了何謂“一畫”,《畫語錄》的通篇大義便基本上可以輕輕松松地弄明白了。而要明白何謂“一畫之法”,應該先弄明白“一畫”的出典。不知其典之所由出,實為“越說越糊涂”的原因。我以為,石濤所謂“一畫”最有可能不是個共名,而是個專名,即其義絕非“一點一畫”的“一畫”,卻是“庖羲一畫”。“庖羲一畫”的出典,遠可溯源于《易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2](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51頁。包犧(庖羲、伏羲)“始作八卦”,在古時被看成“人文”的開創(chuàng)、肇始。而石濤《畫語錄》開宗明義:“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3](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3頁。這里的“太古無法,太樸不散”,講的應該是“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zhì)民淳,斯文未作”,那么所謂“一畫”,講的應該就是“羲皇一畫”,而所謂“法”,講的應該就是“八卦”或稱“人文”之法,并非“天地”或稱“自然”之法。
在清代之前,人們對“天文”與“人文”、自然之法與人文之法還沒能區(qū)分開來,總是混淆為一。也就是說,那時人們從“天人合一”的觀念出發(fā),認為人文與天地萬物之文都是因“道”而塊然并生,其法一也。比如,南北朝時宗炳把畫中山水只看成畫外山水的具體而微者,作為畫外山水的替代品可臥游于其中,代表了清代之前的典型觀念。到了清代,開始有人對自然與人文稍作區(qū)分,如明末清初經(jīng)學家刁包在《易酌·序》中區(qū)分開了“畫前之易”與“畫后之易”,也就區(qū)分開了“太極”與“一畫”,從而認識到人文除了師法自然之外,作為“心畫”,又自有一套“由一畫而加之,至三百八十有四爻,易變易妙”的權衡、規(guī)矩、法式。刁包和石濤一樣,都是由明入清的遺民,刁包年長石濤三四十歲,因此石濤提出“一畫”之說,很有可能受到刁包《易酌》的啟發(fā),而其“夫畫者,從于心者也”之說,也與刁包“易,心畫也”之說是相通的。但石濤的觀點不單從畫理而且從哲理的角度來看,又要比刁包深入精微得多,所以石濤稱“一畫之法,乃自我立”,這絕非自夸——他在中國畫學史上確實具有一種不可否認的開創(chuàng)之功。
二、“一畫之法”
這種開創(chuàng)之功,首先在于石濤不但認識到自然與人文、自然之法與人文之法的聯(lián)系,也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區(qū)別,特別加以標示和闡發(fā)。對于石濤的“一畫”,有人認為當出于《老子》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有人認為當來自《易傳·系辭上》中的“太極”即“太一”。無論出于《老子》也好,來自《系辭上》也罷,“一畫”都被抽象地解釋為天地陰陽混沌未分時的元氣——用現(xiàn)代的哲學術語來說,就是宇宙的本體性與規(guī)律性。元氣化生天地萬物,那么畫家體認、參悟到元氣的化生之理,筆下自然就會化生不已。這種觀點的不當之處,就是和石濤之前的古人一樣,沒有認識到“太一”與“一畫”、自然與人文以及它們各自的化生之理是存在區(qū)別的。恰如伏羲以“一畫”類“太一”,然而這“一畫”絕非和“太一”一個模樣。乾、坤、巽、震、坎、離、艮、兌八個符號代表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然而這八個符號也絕非和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一個模樣。伏羲以八卦的生成變化,象征天地萬物的生成變化,然而八卦又自有一種內(nèi)在的生成變化之法,絕非天地萬物的生成變化之法。換言之,八卦尚有其自身的“義素”——最基本的是陰陽二爻——與“義素”之間搭配組合的規(guī)則。任何人文體系都具有其自身內(nèi)部的因而不同于自然的一些“義素”與“義素”之間由簡而繁、搭配組合、生成變化、易變易妙的規(guī)則。繪畫作為一種人文活動,傳寫世間萬象,發(fā)抒人之情性,但也不能直取世間萬象與情性發(fā)抒之法,還需遵照和創(chuàng)造繪畫本身之法。
從其語源來看,石濤的“一畫”既脫胎于“庖羲一畫”,就不是指宇宙自然的本體性與規(guī)律性,而是指與宇宙的本體性與規(guī)律性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藝術的本體性與規(guī)律性。石濤說:“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夫畫者,從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tài),終未得一畫之洪規(guī)也。”[1](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3頁。其中的眾有萬象及其“秀錯”“性情”“矩度”,都不是畫外之物,而是畫內(nèi)之象,在屬性上與畫外之物全然不同,雖由“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而得,又為人的心靈創(chuàng)生的精神之物。它們所構(gòu)成的世界,實屬于天地之外別開的一方虛構(gòu)的世界,一方靈奇的世界,一方藝術的世界。不明了這個藝術世界及其中萬有眾生的真正屬性,就無法深入其理而曲盡其態(tài),并使之化生不已,創(chuàng)造不息。
畫家吳冠中說:“石濤這個十七世紀的中國和尚感悟到繪畫誕生于個人的感受,必須根據(jù)個人獨特的感受創(chuàng)造相適應的畫法。這法,他名之為‘一畫之法’,強調(diào)個性抒發(fā),珍視自己的須眉。毫不牽強附會,他提出了二十世紀西方表現(xiàn)主義的宣言。我尊奉石濤為中國現(xiàn)代藝術之父,他的藝術創(chuàng)造比塞尚早兩個世紀。”[1]吳冠中:《我讀石濤畫語錄》,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吳冠中把“一畫之法”比作“表現(xiàn)主義的宣言”,而把石濤奉為“中國現(xiàn)代藝術之父”,這確實獨具慧眼,也毫不牽強。但僅是把這一提法的立足點落在“強調(diào)個性抒發(fā)”上,似乎還不夠周全,也不夠準確。因為“強調(diào)個性抒發(fā)”無論是在“一畫之法”還是在“表現(xiàn)主義”之前,都早已被中外許多藝術家所標持、高揚,所以我想對吳冠中的提法稍作一點補充。
或許可以這樣說,石濤“一畫之法”所包含的同樣道理,在西方要等到20 世紀初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誕生之后才被人注意。在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誕生之前,西方語言學一直認為,語言是對外部世界的一個模擬、命名的過程,語言中的諸多要素是和外部世界中的事物一一對應的,詞語的意義也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事物所賦予的。因此,語言內(nèi)部的結(jié)構(gòu)(詞語和詞語之間的關系)和它所指稱的外部世界是一致的。換句話說,語言本身并不具備獨自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比如“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這些詞語之間的關系,與它們所指的自然界中事物之間的關系是一樣的。而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則認為,語言具有其自身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也就是語言自成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個語素按照語法組織起來(能指)生成意義(所指)。這個意義不是直接相關于外部世界中的事物,而是直接相關于人的概念、觀念世界。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這一觀點的提出,不僅改變了語言學的歷史進程,也引發(fā)了語言之外包括藝術在內(nèi)的各個文化領域的一場觀念的革命。這場革命促使西方藝術由單純地崇尚自然——這個“自然”分為外在的和內(nèi)在的兩個方面,人本身的感受、情感是內(nèi)在的自然,所以“強調(diào)個性抒發(fā)”也是崇尚自然的一種表征——轉(zhuǎn)變?yōu)楦雨P注藝術自身的本體性與自律性,及對其內(nèi)部形式規(guī)律的探索,從而使西方現(xiàn)代藝術的發(fā)展獲得了新的路徑,并呈現(xiàn)新的風貌。其實,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觀念對于“古典主義”藝術觀念的巨大變革,并不在于以“表現(xiàn)”代替了“摹仿”,因為“摹仿”的觀念是要求藝術把人所感受、理解的世界表現(xiàn)出來,而“表現(xiàn)”的觀念是要求藝術把人對世界的感受、理解摹仿出來,所以從根本上說,“摹仿”與“表現(xiàn)”是一致的。由此來看,“現(xiàn)代主義”藝術觀念真正的革命性,就在于其對藝術之“本體”的發(fā)現(xiàn)與自覺。與西方現(xiàn)代藝術觀念與實踐的這一歷史發(fā)展狀況相比較,尤可看出石濤“一畫之法”的開創(chuàng)之功。確實,從石濤開始,中國畫的畫法、畫風、畫境得到了一種新的解放,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變化,顯示出這個貌似玄遠隱微的“一畫之法”對于藝術實踐所具有的特殊指導意義。
三、“先天后天之法”
“一畫之法”的實踐意義,首先在于它破除了以往的“法障”,這個“法障”就是把“先天之法”與“后天之法”混而為一,未加區(qū)別。石濤稱“吾道一以貫之”,其《畫語錄》也以“一畫之法”貫通各章。與他章相比,第一章“一畫”還僅可看作對“一畫之法”的一篇贊辭,而深入闡發(fā)“一畫之法”的含藏與妙用,其實是從第二章“了法”才真正開始的。
在“了法”中石濤說:“規(guī)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guī)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guī)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zhuǎn)之義。此天地之縛人于法,人之役法于蒙,雖攘先天后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為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1](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
我以為,要弄懂這段語錄的大意,關鍵就在于分清何謂“先天后天之法”,以及認明二法之間的關系。所謂“先天之法”,就是使天地之所以方圓而運行的“規(guī)矩”,也就是“自然之道”。而人稟受于天,應物斯感,抒發(fā)情性,在古人看來也莫非自然,同屬“先天之法”。這種“先天之法”是在人存在之先就已經(jīng)存在的,而在“天人揖別”之先不能被人所認識、把握,其原因就在于當時天人合一、同于大化,處于混沌未開的原始狀態(tài),尚未創(chuàng)設自身的“后天之法”。人必須憑借自身創(chuàng)設的“后天之法”——也就是各種人文之道,其始為“庖羲一畫”——才能“無端鑿破乾坤秘”。人創(chuàng)設了“后天之法”,卻不知“后天之法”為何物,而仍舊把它與“先天之法”擾攘不分,甚而把“先天后天之法”統(tǒng)統(tǒng)攘棄,以追崇某種天人合一、同于大化的所謂“境界”,這樣也就不能理解、掌握和運用“后天之法”,以鑿破、窺探并呈現(xiàn)“先天之法”。因此人不但要繼續(xù)為“先天之法”所束縛,而且要再次為“后天之法”所蒙蔽,處于一種不自由的狀態(tài),其實也根本不會達到天人合一、同于大化的所謂“境界”,這就是石濤所謂的“法障”。
唐代畫家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是千古不刊之宏論。其中的“造化”“心源”同屬于“自然之道”“先天之法”,都是繪畫必須謹遵之法理。然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既如此“造化”又如何可師?而“心猿不定,意馬四馳”,既如此“心源”又如何可得?所以說,要真正做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還必須另外具備一套師法與得法,而這套師法與得法就是石濤提出的“一畫之法”“后天之法”。畫家如不明了“一畫之法”,那么“外師造化”往往成了造化的徒役,“中得心源”就容易做了“心猿”的隨從。因此,“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一千古不刊之宏論,便有可能淪為一句束縛人的教條,一個蒙蔽人的“法障”。前人已知“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一法,卻不知如何才能達成此法之法。或者更恰當?shù)卣f,以往但凡卓越的畫家,不能不運用此法;不運用此法,就不能成為卓越的畫家。但這種運用還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未能明白地說出其中的道理,直到石濤才一語道破天機,把“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藝術觀念又提高了一個層次,使無意識成為意識,不自覺成為自覺。這一藝術的自覺,無疑會破除過去藝術領域中形成的種種教條、迷信,從而推動藝術活動的發(fā)展進步。
“一畫之法”,抽象地說是藝術的本體性與規(guī)律性,具體地說就是繪畫中的“筆墨”。正如石濤所說:“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2](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古人說話常用借代,這里是用“筆墨”代指繪畫藝術的形式與技法。對于形式與技法,石濤又論道:“墨受于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于人,勾皴烘染隨之。”[3](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這里采取了“互文見義”的句法,該句意思是說,筆墨受于天而操于人。天地萬物有陰晴寒暑之風貌,作為“形天地萬物者”的繪畫,就要以濃淡枯潤等形式隨之,這是說筆墨受于天;而要以濃淡枯潤等形式隨陰晴寒暑之風貌,又要以勾皴烘染等技法隨之,這是說筆墨操于人。因為繪畫的形式、技法是人操以“形天地萬物”的唯一途徑,所以石濤對之非常重視,《畫語錄》的許多章節(jié)文字也都是在探討這一“后天之法”如何習練、運用、借鑒、開新、提高與豐富。“石濤是四僧中畫路最寬、風格最廣的一位,因而其成就也最大。石濤作山水,通常用吸水性較強的生紙,再用濕筆,有時甚至將紙用水打濕后再畫,以此來表現(xiàn)云靄蒼茫的意境。他的山石做法,從大斧劈和長披麻演化而成,著筆雖較多,但脈絡清晰,來去交待十分明確,筆法剛?cè)嵯酀!保?]潘公凱等:《中國繪畫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頁。可見石濤畫作之所以神妙,與其筆墨之法的醇熟、變化、創(chuàng)新、豐富有著直接的關系。
在中國畫尤其是文人畫的領域里,有些人出于對莊、禪思想的誤解,鄙視筆墨之法,認為這只是“器”而非“道”,空泛地主張“無法之法”“妙在筆墨之外”,乃至于未“得魚”時先已“忘荃”,未“得兔”時先已“忘蹄”,以此遠慕“造化之工”。對此,石濤非常深刻地指出:“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為也,無法則于世無限焉。”確實,筆墨之法作為“后天之法”,如不運用得法,得心應手,就會限制、束縛人的天性與自由,使之不能巧奪天工。而沒有了法,也就沒有了這種限制、束縛。比如兒童畫畫,一派天真、無師無法、無拘無束,自然有一番天趣,而加之以師法約束,這番天趣便失掉了。但是,兒童畫雖存天趣,其內(nèi)涵與表現(xiàn)力畢竟是十分有限的,所以“無法”給人帶來的“無限”,辯證地看又是一種“有限”。蘇軾有言:“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而那種純?nèi)翁烊弧ⅰ安灰苑椤钡挠^點,其實也同樣是“見與兒童鄰”,是個“法障”,并不是“法”。石濤認為,不能因為筆墨之法具有有限性便棄之不用,而要突破這種有限性,非得在筆墨之法上淬煉研磨、拓展更新不行,只有這樣才能由“有限”而至于“無限”,從拘執(zhí)而達到自由,以奪天工之巧。所以他說:“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zhuǎn)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2](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第4頁,第5頁。
四、“搜盡奇峰打草稿”
石濤在其《畫語錄》中著力標持、探究“一畫”“筆墨”即“后天之法”,但這不僅不能表明他否認了“先天之法”的重要,反而可以表明他對“先天之法”的特殊重視,因為在他看來,“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3](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第4頁,第5頁。。
“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即天人、物我相感相生,這是“自然之道”“先天之法”。筆墨無論如何重要,相對于“先天之法”來說,也不過是借以表現(xiàn)、達至目的的“器”“具”。所以在石濤看來,唯恃“后天之法”,而荒棄“先天之法”,仍然未得繪畫藝術的真味。這個道理在“尊受”章中論說得更為深刻。“受與識,先受而后識也。識然后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識而發(fā)其所受,知其受而發(fā)其所識。”[4](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第4頁,第5頁。這里所謂“受”是指人稟受于天的“先天之法”,而“識”是對“先天之法”的進一步認識,以及反映與表現(xiàn)的方法,屬于“后天之法”。人必須借“后天之法”才能參悟并呈現(xiàn)“先天之法”,而在參悟并呈現(xiàn)的過程中,又必須確認“先天之法”的第一性與“后天之法”的第二性。非如此,則不能遵循、隨順“先天之法”,以權衡、變化“后天之法”,反而要被“后天之法”所拘限,“不過一事之能,其小識小受也”。因此石濤提出的“尊受”,就是確立“先天之法”的第一性原則,此為“一畫之法”中的又一妙義。“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強而用之,無間于外,無息于內(nèi)。《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1](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5頁,第7頁,第7頁。只有“尊受”,才能促使藝術家在繪畫實踐中勤力于“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并不斷摸索、探究如何“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方法,從而使“后天之法”與“先天之法”相合為一,達至化境。
石濤特長于山水畫,所以他從自己的山水畫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出發(fā)現(xiàn)身說法,最能闡明“尊受”與“筆墨”如何統(tǒng)一的要旨。在“山川”章中,他說:“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zhì)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zhì)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于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zhì)與飾也。”[2](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5頁,第7頁,第7頁。山川是繪畫表現(xiàn)的對象和內(nèi)容,要畫好山川,首先必須認識、把握其作為自然物之中所包蘊的“乾坤之理”,即其規(guī)律性,然后才能運用“筆墨之法”予以表現(xiàn)。“乾坤之理”與“筆墨之法”的關系是“質(zhì)”與“飾”的關系,如孔子所說的“繪事后素”。“繪事”(飾)是在“素”(質(zhì))之后,所以“質(zhì)”與“飾”的關系其實是一種先與后的關系。這種先與后的關系并非一種孰重孰輕、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一種先后相隨、缺一不可的關系。只有以“后天之法”隨“先天之法”,才能達到心手合一、物我相齊的審美高度。
繪事不是“質(zhì)”,而是“飾”,是“文”,即一種審美與藝術活動。審美與藝術既不是主觀的,也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與客觀的統(tǒng)一,“一畫之法”正包含著這一審美與藝術的基本規(guī)律、原則。在畫家的審美與藝術活動中,首先離不開對客觀自然對象的觀照,然而這種觀照絕非一種單純物理性的觀照,所以石濤說:“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jié)云萬里,羅峰列嶂,以一管窺之,即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即可參天地之化育也。”[3](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5頁,第7頁,第7頁。如果把自身與對象分裂開來、對立起來,而從自身的管見來外在地觀察對象,對象就不能成為審美與藝術的對象,而畫家也就不能發(fā)現(xiàn)并把握對象中潛在的審美與藝術因素。因此必須按照“一畫”這一審美與藝術的態(tài)度和方法,投身于對象當中內(nèi)在地體驗對象,才能發(fā)現(xiàn)并把握對象中潛在的審美與藝術因素及其生成變化的規(guī)則。
石濤一生的山水畫創(chuàng)作都可謂在實踐著“一畫之法”,而又分為“山川脫胎于予”和“予脫胎于山川”先后兩個階段。“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于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4](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8頁。原標點經(jīng)筆者修正。
畫家早年,“未脫胎于山川也”,當然處身于山川當中,與山川為一體。這時畫家也并不是把山川當作徒具“形”而沒有“神”的“糟粕”,使山川與自身分離因而在自身之外私藏其形神。因此,畫家能夠深切體驗到山川形神之豐美,而不吐不快,好似“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于是畫家操筆運墨,山川的形神便由筆墨傳寫出來,好似“山川脫胎于予也”。經(jīng)過如此這般審美藝術活動,多年之后“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物我的界限便滌除一空。如果說在前一階段,畫家的創(chuàng)作還是“以形寫神”,那么這一階段便是“以神馭形”,即“搜盡奇峰打草稿也”。以往對于這句名言,人們更多重視其中的“搜盡奇峰”四字,而“打草稿”三字卻未獲深解,我覺得其實后三字才是該句的關鍵、精要所在。“打草稿”說明畫家“搜盡奇峰”之所得,僅是他定稿之前的素材,畫家需要駕馭這些素材以傳寫山川之形神。畫家“搜盡奇峰”,卻并不按照奇峰本來的樣子來描繪,而是按照藝術本身的規(guī)律、原則,對其重新組織、安排、結(jié)構(gòu)。這樣傳寫出的形神,就不只是山川的形神,同時也是畫家自己的形神。也就是說,畫家通過傳寫山川的形神而傳寫出自己的形神,好似“予脫胎于山川也”。當“山川脫胎于予”之時,畫家與山川主客一體,但對這一關系,畫家還不夠自覺,所以是“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到“予脫胎于山川”之時,畫家對于自身與山川的統(tǒng)一關系已經(jīng)完全自覺。這種自覺,使得畫家的藝術創(chuàng)作進入了更為自由的狀態(tài),也達到了更為高妙的境界。
《畫語錄》的一些現(xiàn)代標點本,在“山川脫胎于予也”和“予脫胎于山川也”之間用逗號標點,而在“予脫胎于山川也”與“搜盡奇峰打草稿也”之間用句號點斷,使“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于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為一句,而“搜盡奇峰打草稿也”自成一句。這樣標點恐怕不合文法,而影響了句義的明暢,讓人難于理解。一句語義不明,也會使得《畫語錄》許多章節(jié)乃至整部都讓人難于理解。比如俞劍華先生說過:“古今學術書籍,故意用艱深文字以炫耀博學而實掩蓋淺陋的著作,為數(shù)甚多。可惜石濤也犯了這個毛病,不是在講畫法,而是在做文章;不是在做文章,而是在耍筆頭;不是在耍筆頭而是在變戲法。原意本想用這種方法增加著作的價值,但結(jié)果卻大大減少了著作的價值。有很多人想讀‘畫語錄’,但都打不破文字這一關,不是半途而廢,就是束之高閣。假使石濤能用普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淺出,說明高深的道理,使人易學易知,我想它在藝術界的地位和影響,一定比現(xiàn)在大得多。”[1]俞劍華:《石濤畫語錄研究》,(清)道濟著,俞劍華標點注譯:《石濤畫語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版,第105頁。而我覺得,其實《畫語錄》絕非以艱深文淺陋,卻正是用古人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淺出地說明高深的道理。它之所以讓今人難于理解,關鍵在于今人對它的標點、注釋還遠不夠精嚴,還存在許多的問題。由此深感在古代畫論、畫史的研究中,首先必須打通文字這一關。而要打通文字這一關,決不可希求古人用今人易曉的文字來書寫,只能通過今人自己的努力,去完成通曉古人文字這項非常枯燥且艱辛的工作。因此文獻的整理、校點、訓釋、考證等基礎工作,在古代畫論、畫史研究中至為重要,缺之不可。如果不做好這項基礎工作,就難免要以今人自以為是的某些抽象哲理去強解古人,甚而把自己之不通妄加到古人頭上,以之為古人之不通。這樣,古人苦心得來的道理,便不能為今人心領神會。而做好做足基礎的文獻工作,古代畫論、畫史研究中的許多難點、疑點自然就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