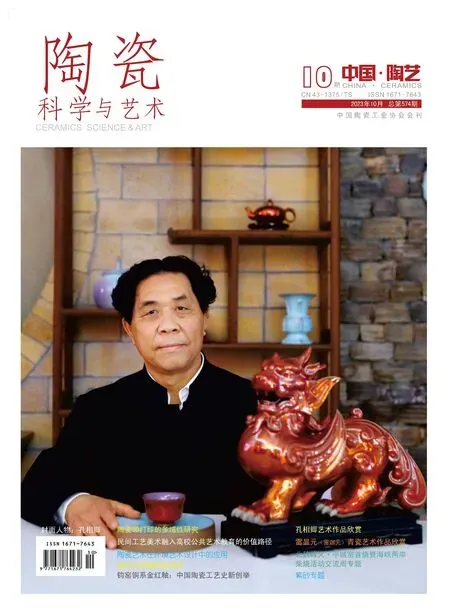淺析紫砂壺《梅竹雙親》的造形設計與內涵意義
馮志浩
梅花,不僅美麗還有著高潔的風尚。王安石贊其“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唯有暗香來”;陸游以梅花自喻,一首“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的詩,讓人心生敬佩;特別是一句“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更是激勵了多少中國人艱苦奮斗,勇往直前。竹子,不僅風雅還有著堅毅的品行。徐庭筠贊其“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云去也無心”;蘇東坡就說得很直白了,“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劉禹錫以《庭竹》自擬“露滌鉛粉節,風搖青玉枝。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依”,道出了君子如竹不隨風逐流,無論身處何處均可自立清高的人生格局。
這樣的梅花與竹子,已經不僅僅只是讓人觀賞的植物了,而是成為象征著精神品格,民族氣節的文化符號,備受人們推崇。它們經常出現在文人墨客的書畫中,比如擅長寫竹、畫竹的鄭板橋,以梅詩、梅畫聞名于世的王冕等。梅與竹雖然不同屬性,卻有著相同的精神品行,所以,在傳統的中國畫中生出了竹與梅相會于一幅畫中的繪畫形式,這樣的內容題材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做“梅竹雙親”。這樣的藝術形式既有了梅的美,又有竹的雅,既有竹之清,又有梅之潔,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不僅常常出現在中國畫中,也出現在了紫砂壺的創作中。隨著紫砂文化的發展,紫砂壺已經不再只是飲用器皿,而是像詩歌書畫等領域的藝術一樣融入了作者的情感秉性,傳遞了作者的價值觀、人生觀,是具有文化屬性與文化價值的藝術品,所以紫砂壺的創作常常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靈感且以這種獨特的手工藝術的形式反映中國的文化觀。極具中國文化象征意義的梅和竹是常見的紫砂素材,以梅花為題材的經典壺式有梅樁壺、梅花周盤壺、梅報春壺等,以竹為題材的傳統壺式有竹段壺、竹節壺等,而《梅竹雙親》將梅與竹這兩種元素融于一壺,以求達到疊加的美感呈現與加倍的情感表達。

紫砂《梅竹雙親》這樣以梅和竹為元素的創作理念由來已久,史上有不少的紫砂匠人都有嘗試過此類壺形,可以說是紫砂“束柴三友”壺系列的分支之一。“束柴三友”是將梅、竹、松三者合一,后來也就有了梅與竹、梅與松、竹與松這樣的兩兩組合,所以《梅竹雙親》也算是傳統的壺式之一了。但是做為手工藝術,歷代紫砂匠人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模式與藝術風格,即使是同一個壺式在不同的手藝人手中也會生出不同的風格,比如曼生石瓢與子冶石瓢,雖以石瓢為結構框架,卻呈現了完全不同的造型藝術,本文的《梅竹雙親》也是一樣。在同樣以梅與竹為素材的造型中延續了梅與竹的情感表達,在傳承了梅竹一壺的創作理念的基礎上,融入了自己的藝術風格,為大家呈現了不同的紫砂《梅竹雙親》壺。
這把《梅竹雙親》的造型迥異于其他同類型的壺,特別是壺身呈圓柱型,表面光潔素雅,配以較大的壺口,像一只紫砂杯,如此便有了極佳的實用性。壺把、壺嘴、壺鈕都是以彎曲的梅樹枝為形制,蓋面上有從壺鈕處胥出的梅花,在蓋面上盛然開放。無論是枝干的彎折還是梅花的刻繪,都追求著自然的形態,特別是細節中的處理,比如枝干上的樹癭,蓋面上的花瓣,都以非常細膩的技法刻畫得極為形象生動。竹元素的應用非常巧妙,以花器中貼花的技法呈現在壺身上,枝葉自然伸展,立體生動。因為梅花表現得比較紛繁,所以竹元素就以較少的筆墨呈現出來,這樣就有了繁而不亂、疏密有序的和諧美感。繽紛炫麗是花器的一大美學特征與造型優勢,而這件《梅竹雙親》卻選擇了通體一色的本色花器的藝術形式,希望在不借助顏色表達的情況下仍然能以純熟精細的工藝呈現自然之象,希望受眾不被炫麗的色彩沉迷,而是專注到梅與竹的風骨,感受到作品中旺盛的生命力和堅毅不屈的精神力量。
這把《梅竹雙親》,沒有炫麗的色彩,沒有紛繁的造型,但是在這壺中好像看得到白雪皚皚中,凌寒深處里,那紅色的梅花傲然,那翠綠的竹子挺立,聞得到那清冽的梅香,感受得到那竹的堅毅,這就是這把《梅竹雙親》壺的造形設計與內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