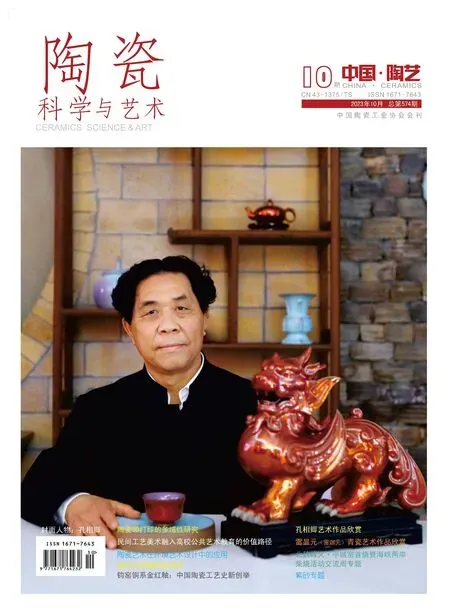淺析紫砂作品《風花雪月》的創作
史俊超
喝酒用酒壺,喝茶用茶壺,特別是在講究生活品質與情調的當代,更是有專門的酒器、專業的茶器。而“風花雪月”這件作品卻將這兩種器皿融為一體,以紫砂的形式做了一把酒壺形式的茶壺,這也是這件作品極為獨特的造型特征。究其創作之源,就要說一說中國的茶文化與酒文化的各自發展與相伴相生了。
酒壺與茶壺,本就是飲用器皿中同源的東西,酒壺早于茶壺出現,中國人很早就開始飲酒,商周時期的酒壺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茶壺發展較晚是因為唐時才開始出現并形成飲茶的習氣,這時候才有了用于盛茶的茶壺。那時的茶壺材質主要還是瓷器,其形制之源本就是借鑒了酒壺的造型,只不過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這兩種器皿的造型逐漸有了分化進而形成獨屬于酒壺與茶壺的不同的美學特征,特別是茶文化的發展迅猛,自然出現了各種具有宜茶性與觀賞性的飲茶器皿,如此發展,酒器與茶器的造型特征也就越發不同,所以《風花雪月》這件作品的酒器造型就更顯獨特了。
《風花雪月》造型上的獨特還在于選擇了酒器中“執壺”的造型。中國的酒文化博大精深,酒壺發展至今已經幾千年了,樣目繁多,明清是酒器發展的高潮,造型多樣,追求精美,其中尤以執壺為尚。巧合的是,明清時期也是紫砂壺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的紫砂壺也在追求著造型上的創新、工藝上的精致,要不怎么說茶酒之源妙不可分呢?以酒壺為創新之靈、造型之源的《風花雪月》,因為這樣注定的緣分在眾多的酒壺造型中選擇了執壺的樣子為形制。當然,選擇執壺造型的原因不僅僅在于它們在發展史上的緣分,更在于“執壺”是酒壺中非常鮮明的存在,是酒壺造型發展的巔峰象征,執壺一出現,我們就能想到酒壺,想到酒,從而深化酒與茶融于一壺的造型深意與情感主題。
茶與酒融于一壺,不僅是造型上的交織,更是兩種文化在情感上的交織。中國有兩大文化,引無數文人墨客競折腰,即茶文化與酒文化。太多的文人墨客為之寫詞作賦,酒有韋莊嘆:“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岑參的“人生大小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李煜也有“一壺酒,一竿身,快活如儂有幾人”,何況是嗜酒如命的詩仙李白,一生作酒詩無數,杜甫更是直言:“李白斗酒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他們就真的只是貪圖美酒嗎?歐陽修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茶有王重陽之詠“烹罷還知何處去,清風送我到蓬萊”,也有元稹“香葉,嫩茶。洗盡古今人不倦,將至醉后豈堪夸”之頌;錢起的一句“竹下忘言對紫茶,塵心洗盡”更是道出了茶文化中修身養性之精髓。酒與茶看似矛盾的兩種東西,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茶友之意不在茶,殊途同歸中有了茶與酒的交融,“松花釀酒,春水煎茶”“一杯濁酒笑紅塵,半盞清茶淡貧生”,特別是蘇軾的一句“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道出了文人墨客執著于茶酒的人生,風花雪月,肆意瀟灑。

《風花雪月》不僅有酒文化與茶文化交融的浪漫人生的追求,還有對細節、對美的追求,這也是紫砂壺藝創作精益求精的體現。主要表現在兩點:其一,鋪砂裝飾。鋪砂是紫砂裝飾的一種,以“珠粒隱現,光閃奪目”為人贊嘆。《風花雪月》的壺身表面如滿天星辰,單單這四個字,已是風花雪月般的極致的浪漫。其二,陶刻裝飾。壺口處刻了一圈如意符號,如意是非常典型的吉祥元素,在中國有著家喻戶曉的群眾基礎,寄寓著事事如意的祥瑞之意;壺身上刻了一圈回字紋紋飾,這種紋飾因為像漢字的“回”字,所以被稱為回字紋,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器上,后來作為青銅器的裝飾而流行起來,因為其形回環反復、延綿不斷,所以有了“富貴不斷,福運連綿”的說法,逐漸從裝飾上升到文化層面,廣泛地出現在民風民俗中,是祥瑞文化的元素符號之一。這把《風花雪月》上面的壺口與下面的壺身均采用了陶刻的吉祥紋飾作為裝飾,且在位置上、內容上、形式上都起到了相互呼應的藝術效果,如此,不僅有了造型上和諧統一的美感,在情感上也為這件作品增加了一些祥瑞的氛圍。
當茶與酒遇到紫砂,碰撞出了新的火花,《風花雪月》這把壺以最直觀的造型直率地呈現了茶與酒的交織交融,這不僅是造型上的融合,也是精神上的契合,酒的醉人,茶的清醒,半醉半醒半浮生,亦真亦假亦過客,人生,不過風花雪月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