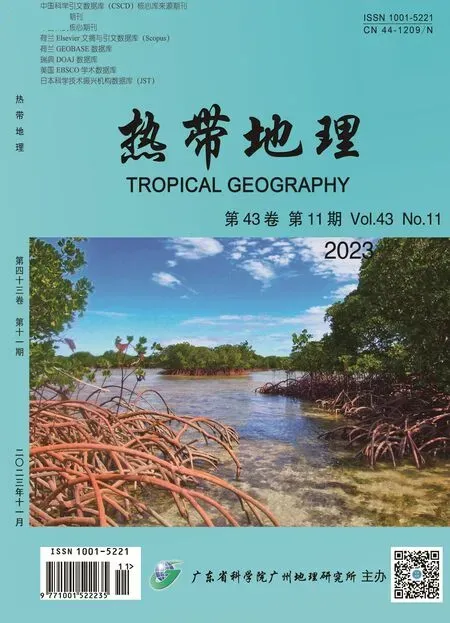基于扎根理論的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與綜合評價
黃穎敏,付 曉,曹小曙,廖 望
(1. 江西理工大學 a. 建筑與設計學院;b. 土木與測繪工程學院,江西 贛州 341000;2. 陜西師范大學 西北國土資源研究中心,西安 710119)
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改革開放以來,在非均衡區域發展戰略下,我國出現了與世界上類似的“核心-邊緣”的區域空間格局(Harvey, 2007)。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的重要共識(樊杰 等,2018;鄧祥征 等,2021)。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并試圖加快特殊類型區域的振興發展(馬詩萍 等,2020;黃穎敏 等,2023)。革命老區作為典型的特殊類型區域,在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為中國革命做出重大犧牲和貢獻(易筱雅 等,2021),但受自然環境和戰爭創傷等因素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是典型的欠發達地區(曹小曙 等,2018),已成為影響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短板之一(張明林 等,2020)。2012 年以來,國務院先后出臺了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陜甘寧、左右江、大別山、川陜等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規劃,在加快革命老區振興發展上取得了顯著成效(韓廣富 等,2019)。在成功經驗的基礎之上,2021年,國務院繼續出臺《關于新時代支持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1),希望進一步加快推動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然而,由于中國區域類型多樣,構建一套適用于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成為了促進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提。
當前,國內外對于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基礎。與國內高質量發展相類似,國外發達國家也提出了相應的發展理念與指標體系。如美國發布的《美國各州新經濟指數報告》(Atkinson et al.,2017)、歐盟的2020 戰略(European Commission,2010)、韓國的綠色增長戰略(Jones et al., 2011)以及日本的新增長戰略(日本經濟產業省,2009)。雖然各國提出的背景迥異,但指標體系存在一定共性,均強調了創新、產業轉型升級、生態環境保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改善。近年來,國內對高質量發展的研究逐漸增多,以經濟學和地理學視角為主,形成了系列成果(魏敏 等,2018;方創琳,2019)。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的指標體系經歷了從單一指標,如人均GDP(陳詩一 等,2018)、全要素生產率(賀曉宇 等,2018;Zeng et al., 2022),向多元綜合指標評價的創新(李金昌 等,2019;張軍擴 等,2019)。學者們圍繞高質量發展理念,基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個維度,構建了新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開展了實證研究(馬海濤等,2020;Pan et al., 2021)。
總體而言,國內外對高質量發展理念及相關指標體系均存在廣泛而深刻的探討,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1)忽視了不同區域類型發展的階段性與資源稟賦差異性特征;2)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相混;3)雖有學者將研究單元下移至縣域尺度,闡述了縣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并提出相關指標體系,但實證相對較少(王薔 等,2020);4)由于地域性特征,有學者發現國內學術界對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地方政府的高質量發展績效考核體系未能有效結合(黃順春 等,2020)。本研究在國家高質量發展理念的基礎上,結合革命老區地方實踐和地域特色,基于扎根理論,試圖構建出一套適用于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對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進行縣域尺度的綜合評價,以期為加快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與科學貫徹高質量發展理念提供一定的政策啟示。
1 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理念的內涵
高質量發展理念提出以來,政府和學界從不同視角闡釋了其內涵。政府認為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內涵是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大發展理念,并落實在地方發展的實踐當中。學界認為高質量發展主要是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結構和動力(張軍擴 等,2019)。然而,在具體地域的高質量發展研究中,還需要依據地方實踐與地域特色對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做進一步闡釋。本研究認為在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中應將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作為核心動力,把縮小區域與城鄉差異作為協調的主要對象,將綠色生態作為發展的優先手段,在開放下增強城鄉與區域要素流動與循壞,以高質量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目的。相較于沿海發達地區,革命老區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經濟社會與城鄉發展已取得較大的進步,但高質量發展仍面臨嚴峻的挑戰,尤其是生態資源和紅色資源的挖掘仍需進一步強化。對于革命老區縣域而言,其高質量發展應以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并重,在數量和質量上融入5大發展理念,最終整體實現有機統一發展(袁曉玲等,2019)。
2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2.1 指標體系構建思路
縣域作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是國家全面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空間載體,也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點和難點區域。本研究的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思路為:1)基于現有的指標構建存在的問題,提出指標構建原則;2)運用頻數分析法、對比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以及專家咨詢法對指標進行篩選;3)基于扎根理論的三級編碼過程,建立指標的層級結構,并對指標體系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4)最后,編碼歸納出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及內涵(圖1)。

圖1 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邏輯Fig.1 Logic of construc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2.2 指標體系構建原則
基于當前指標體系構建存在的不足,本研究將遵循以下原則:1)系統性傳導原則。縣域高質量發展在結合縣域特征與發展訴求的前提條件下,應與國家、省、市保持一致,形成系統性傳導的發展格局。指標選取時縣域應遵從更高層級系統的高質量發展指標,加強指標體系構建的頂層設計;2)結果導向性原則。高質量發展是過程,但評價針對的是其結果,所以,指標體系當更加注重納入結果類的指標;3)地域性原則。指標體系構建應當體現地域特色,增加地域特色指標,支持差異化和有特色的縣域高質量發展。
2.3 指標體系篩選方法
本研究構建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所采用的篩選方法主要包括頻數分析法、對比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和專家咨詢法。1)頻數分析法是指將文獻中獲取的指標進行數學統計,選擇其中出現頻數較高的指標作為核心指標,并且在此階段剔除過程與投入指標(黃順春 等,2020)。2)對比分析法由2部分組成:一是將獲取的高質量發展核心指標與地方實踐指標進行比對,取兩者的并集;二是將研究區域與其他地域進行比對,基于地域的資源稟賦,發現地域特色,從而選取縣域高質量發展指標、地方實踐指標以及地方特色指標。3)文本分析法是指將現有的指標進行理論定義,選擇符合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指標。4)專家咨詢法是通過對本領域的專家進行咨詢,對指標進行調整。最后,確立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庫(陳向明,2015)。
2.4 基于扎根理論的指標層級結構建立
本研究在一般性評價指標的基礎上,試圖從國家高質量發展指標、地方實踐和地域特色3個維度構建新的評價指標體系。但是,實現這一目標所涉及的指標體系維度和結構尚不明晰,所以有必要采取具有理論探索性功能的研究方法,從指標含義的角度出發,對指標層級結構進行理論建構。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作為一種能從數據分析中發現研究理論的質性方法(Corbin et al., 1990),可有效解決本研究的指標層級構建問題。扎根理論在心理學、教育學以及社會學等學科得到廣泛應用(李克東 等,2011;陳向明,2015),該方法被逐步應用在構建評價指標方面(張天問 等,2014;李巧巧 等,2022),方法的科學性已得到有效驗證。扎根理論通過“一級編碼—二級編碼—三級編碼”3個關鍵步驟,由下而上建立指標層級間的邏輯關系。其中,一級編碼是將原始指標按照其定義進行概念化和范疇化;二級編碼是將一級編碼形成的范疇進行歸類和集聚,并形成主范疇;三級編碼是將所有的范疇提取到一個核心范疇,構建新的理論概念的過程。
2.5 理論飽和度檢驗
理論飽和度檢驗是指通過扎根理論已經構建了完整范疇的評價指標體系,即使再增加指標也不會產生新的范疇的過程(陳向明,2015)。為此,需將事先預留的指標庫與構建的指標進行比對,如果其定義包含在所形成的核心范疇中,且各主范疇之間也未形成新的因子,則表明所要構建的評價模型已達到飽和,可以停止加入新的指標。若出現新的范疇則繼續添加指標,重復上述步驟直至模型中的核心范疇和主范疇達到飽和為止。
3 實證研究
3.1 研究區概況
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老區經歷了多輪的國家政策支持(張明林 等,2020)。作為原中央蘇區的核心部分,2022年,國務院批復贛州、閩西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范區建設方案(以下簡稱‘示范區’)。示范區地處江西省、福建省和廣東省邊界,包括贛州、三明、龍巖3個地級市,共有37個縣級行政單位(圖2),國土面積81 365.11 km2,其大部分位于偏遠貧困地區和三省交界地區。根據全國“七普”數據(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22)和江西、福建2省2021年統計年鑒(江西省統計局 等,2021;福建省統計局 等,2021),截至2020 年年底,示范區GDP 總量為9 218.29 億元,人口總量1 418 萬人,人均GDP 6.5萬元,仍低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自2012年國家實施新一輪的革命老區振興政策以來,示范區經濟社會與城鄉高質量發展成效明顯,選取贛州、閩西革命老區作為研究區域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圖2 贛州、閩西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范區Fig.2 Location of demonstration areas in Ganzhou and West Fujia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3.2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主要由7部分構成:1)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2019—2021 年《贛州市統計年鑒》(贛州市統計局 等,2019—2021)、《三明市統計年鑒》(三明市統計局 等,2019—2021)、《龍巖市統計年鑒》(龍巖市統計局 等,2019—2021),以及縣市2018—2021 的社會經濟統計公報;2)專利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3)基礎地理信息數據來源于國土調查成果共享應用服務平臺公布的三調數據①https://gtdc.mnr.gov.cn/shareportal#/special/statisticalReport;4)2019 年碳排放數據和電力消耗數據分別來源于ODIAC 官方網站②https://db.cger.nies.go.jp/dataset/ODIAC/、figshare③https://figshare.com網站,并在最終計算時除以2019年縣域GDP,保證數據的時間可比性;5)高新技術企業數量來源于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網站④http://www.innocom.gov.cn/;6)紅色文化數據來源于中紅網以及江西省、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廳;7)生態環境數據來源于江西⑤http://sthjt.jiangxi.gov.cn/、福建⑥https://sthjt.fujian.gov.cn/2省生態環境廳、市(縣)生態環境局官方網站。部分缺失數據采用市域均值或相鄰年份均值和相鄰年份代替。
3.3 指標篩選
3.3.1 基本指標的選取 本研究首先以國家、省、市、縣各級政府“十四五”規劃中的目標指標作為參考,同時綜合學術界基于全國尺度(張軍擴 等,2019;李金昌 等,2019)、區域尺度(徐輝 等,2020;汪俠 等,2020)、省域尺度(魏敏 等,2018)、市域尺度(Pan et al., 2021)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選取了425個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備選指標。其次,縣域高質量發展還具有多元性特征。在上述兩方面的基礎上,重點參考了縣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文獻(劉玉 等,2012;劉湘輝等,2013;王薔 等,2020),從中選取155 個備選指標。初步形成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庫,共計580項指標。
指標初步篩選中,由于高質量發展應當更加關注結果類指標,首先剔除了反映投入、消耗的指標,如“固定資產投資額”“教育經費投入”等(李金昌 等,2019);其次,對指標進行頻數處理以及理論分析。將頻數≥2 的文獻指標作為核心指標,將頻數為1的作為備用指標,并通過理論分析逐一對指標進行釋義。在進行編碼前,先定義原始指標,定義的規則為:指標定義以參考文獻中的指標原始定義為主,若沒有出現定義,或者多篇文章中定義存在差異,則重點參考指標在多數文章中的共識性定義。此外,對某些內涵相近或者具有包含關系的指標進行疊加處理,如“污水處理率”“垃圾污水處理率”,本研究將其頻次進行加和,統一命名為“污水處理率”;最后,通過專家咨詢法對部分指標進行調整,選擇更加符合實際的指標。
3.3.2 地方實踐類指標的選取 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應與縣域發展階段性特征和資源稟賦相適應,以及與地方政府推動高質量發展實踐相結合。本研究主要參考江西省和福建省2020 和2021 年度高質量綜合績效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以及贛州、閩西革命老區各縣(市、區)2020年高質量發展綜合考核評價方法,選取地方高質量發展共性指標⑦選用2020和2021年的兩年的江西省、福建省高質量綜合績效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高質量發展實踐具有連續性和動態性,即2021年的指標是在2020年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選取兩年的具有動態性特征,能夠反映地方政府的高質量發展關注點。。
通過專家咨詢、查閱地方文件內的指標設置含義并與核心指標對比,剔除與核心指標在定義上重疊的部分。最終,確定5個地方實踐指標為“鄉村振興”“學前教育發展狀況”“營商環境”“實際利用省外資金”“森林覆蓋率”。鄉村振興對應的指標釋義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農林牧副漁產值”,學前教育發展狀況對應“學前教育教師數量與學生數量比值”,營商環境對應“人均新注冊企業數量”,實際利用省外資金對應“實際利用省外資金與GDP的比值”,森林覆蓋率對應“森林面積與國土面積的比值”。
3.3.3 地域特色指標的選取 結合《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支持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意見》《“十四五”特殊類型地區振興發展規劃》和《贛州、閩西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范區建設方案》等國家級政策,江西和福建2省近年頒布的革命老區振興相關政策,本研究認為革命老區在紅色文化傳承、紅色旅游、紅色文化保護以及紅色主題教育等方面具有區別于其它區域的顯著特征。因此,從紅色文化的數量、影響力、革命教育功能以及與其它旅游資源的協同能力方面切入(鄒建琴 等,2021;王釗 等,2021;朱媛媛 等,2021),最終確定3 個革命老區地方特色指標,即贛閩2 省公布的“省級以上革命文物”“紅色旅游人數”“紅色旅游收入”⑧最初確定的地域特色指標中,“300 處紅色經典旅游景區”“經典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數量”“A 及以上紅色旅游景點”,與贛、閩2 省公布的“省級以上革命文物”具有極高的相似性,經比較,“省級以上革命文物”數據更全面、更具代表性,最終確定使用“省級以上革命文物”數據替代上述3項指標。。基于上述指標選取原則與方法,最終確立本研究基于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共計40 項指標(表1)。

表1 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一級編碼范疇化Table 1 Categorization of first level cod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of counties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3.4 編碼過程
3.4.1 一級編碼 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個人主觀因素對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在進行編碼時盡量選擇原始指標定義所涵蓋的信息命名。通過范疇化過程進一步對指標作篩選,最終得到27 個一級編碼范疇(見表1)。
3.4.2 二級編碼 首先,把高質量發展理念內涵融入指標體系二級編碼過程中。其次,結合近年來國家公布的關于全國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規劃,以及贛州、閩西2個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范區建設方案的具體要求,提取其中的公共部分作為二級編碼依據。最后,結合革命老區的地域特色和地方實踐需求,對一級編碼階段的27個范疇按照其內涵進行歸類和集聚,最終形成7個范疇,分別為“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城鄉協調”“民生福祉”“生態文明”“內外開放”和“紅色文化”(表2)。

表2 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及其權重Table 2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and its weight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創新環境、創新產出和勞動產出是創新發展的重要方面,而土地產出則以地方政府的“畝均論英雄”標準為導向,并與科技創新推動集約化發展相契合,因此將其整合為創新驅動。產業結構、經濟規模、經濟穩定性、經濟效率、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客觀屬性,而財政保障體現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物質保障的功能,因此將其整合為經濟發展。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是破除城鄉二元化差異,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路徑,同時也要確保鄉村在中國糧食安全和耕地安全中的“壓艙石”地位,因此將城鄉差異、鄉村振興、安全保障整合為城鄉協調。教育狀況、人均受教育年限、社會就業、醫療保障體現基本公共服務在教育、就業、醫療3個方面,是國民幸福的基本保障,因此將其整合為民生福祉。空氣質量、綠化環保、能源產出、污染排放分別與防范大氣污染攻堅戰、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對應,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將其整合為生態文明。國內貿易、交通設施完善性、營商環境、經濟開放是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的重要方面,因此將其整合為內外開放。紅色文化存量和紅色經濟屬于紅色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是助力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優勢資源和特色產業,故將其整合為紅色文化。
3.4.3 三級編碼 本研究以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為核心范疇,編碼歸納出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內涵: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包括7 個維度,各個維度之間定位清晰,且彼此依存,互為反饋。1)創新驅動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動力,應促進技術升級,推動革命老區現代化產業體系建立,加強產業的競爭能力;2)經濟發展是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目標,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基礎;3)城鄉協調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應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推進鄉村振興,為城鄉協調發展樹立樣板;4)民生福祉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應提高居民的幸福感、獲得感,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5)生態文明是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載體,使其在全國或區域發揮生態功能區的重要作用;6)內外開放作為重要抓手,提供對外交流通道,讓革命老區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一體化等國家重大區域戰略;7)紅色文化是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的特殊要求,作為紅色文化的發源地,應注重紅色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講好紅色故事,提高紅色文化影響力。上述7個維度協同發展,最終使革命老區形成紅色文化繁榮、生態美麗宜居、特色產業興旺、人民生活富裕的高質量發展格局(圖3)。

圖3 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邏輯Fig.3 Logic diagram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revolutionary old area counties
3.4.4 理論飽和檢驗 通過對原始指標中處理后留下的頻數為1 的200 條指標進行“刪除—定義—編碼”過程,將其與核心范疇中的7個維度進行比對,發現指標仍在現有的范疇中,未出現新的主范疇。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構建的高質量發展指標模型已達到飽和。
3.5 實證檢驗
為檢驗本研究構建的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適用性,對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采用極差標準化法進行指標間的歸一化和同向處理,利用熵值法計算各指標權重,具體見表2所示。
1)各二級指標對高質量發展影響具有一定差異性。在二級指標中,創新驅動維度(0.280 7)的權重值最高,這表明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差異更多來源于創新驅動,即創新產出、創新環境、土地產出和勞動產出4個方面。改善縣域創新環境,提升創新產出,加快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進而促進縣域勞動產出,在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中最為關鍵。其次,經濟發展維度(0.168 3)的權重值也相對較高,這表明現階段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應當繼續以經濟增長為主,應做大做強經濟總量,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城鄉協調維度(0.167 1)的權重值位列第3,這表明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應注意縮小城鄉差異,推進鄉村振興,保障糧食和耕地安全,積極推進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建設,進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生態文明(0.034 5)維度的權重值最低,說明革命老區縣域內部生態文明維度的發展水平相差較小,尚未體現足夠的潛在驅動力。
2)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差異性特征(圖4)。首先,省域之間具有差異性,贛州革命老區示范區的高質量發展水平(0.277 5)總體低于閩西革命老區示范區(0.340 1),得分較低的7個縣均位于贛州。第二,贛州、閩西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區相對較少。2020年,示范區的高質量發展平均得分為0.31,處于平均水平以上的縣域有17個,約占總體縣域個數的46%。其中,章貢區的得分最高,為0.545 6,第二為新羅區,得分為0.508 0,僅有上述2個縣域的高質量發展得分超過0.5。

圖4 贛州、閩西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范區縣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ies of the West Jiangxi and Fujian Demonstration Areas
3)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呈現“核心-邊緣”圈層的空間特征(見圖4)。在空間上,示范區內形成較為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具體而言:贛州市的章貢區、龍巖市的新羅區以及三明市的梅列區、三元區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區,在空間上離散分布,其周圍的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而江西、福建2省的省域邊界地區則集中分布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域,形成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塌陷帶。究其原因,市轄區往往擁有較好的基礎條件,往往形成市域增長極;與之相反,示范區內發展水平較差的縣域往往位于山區,自然條件相對較差,交通不便,難以獲得發展機會。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本研究在系統梳理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以及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運用扎根理論,構建了基于地方實踐視角下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邏輯框架,并選取了贛州、閩西革命老區高質量示范區進行評價指標體系適用性測評,可為地方政府與學界構建高質量發展績效考核評價體系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高質量發展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主要研究結論有:
1)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是以新發展理念為依據,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革命老區縣域的高質量發展應涵蓋紅色文化保護和傳承、經濟發展規模增長和結構優化并重等內容。
2)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由“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城鄉協調-民生福祉-生態文明-內外開放-紅色文化”7 個維度所形成,各個維度之間定位清晰,且彼此依存,互為反饋。
3)通過評價指標體系在贛州、閩西高質量發展示范區的實證研究發現,創新驅動是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差異的重要來源,而生態文明在現階段對于高質量發展尚未體現足夠的潛在驅動力。同時,示范區內縣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內部差異性顯著,在空間上呈現“核心-邊緣”圈層空間結構特征。
4.2 討論
本研究的研究價值主要在于:1)提供了一種新的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思路,雖然現有的文獻對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已有較多的成果,但大部分是基于對高質量發展內涵的理解,缺少從地方政府高質量發展實踐、資源稟賦的視角切入。基于現有研究,從地方政府和地域特色這一“下”的視角切入和國家戰略需求這一“上”的要求出發,采用上下結合的方式構建本研究的評價指標體系,為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標提供了新的思路,將地方政府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納入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增加了“鄉村振興”“學前教育發展狀況”“營商環境”3項地方高質量發展實踐指標,在注重指標普適性的同時,也體現國家的戰略目標,并針對革命老區縣域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差異,增加了“紅色旅游人數”“紅色旅游收入”“省級以上革命文物保護得分”3項反映革命老區地域特色的指標。2)突出了研究單元對指標體系的影響,即依據國家戰略中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鄉村振興和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發展戰略,綜合學術界在縣域尺度上的城鄉融合、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等方面的研究,在進行理論編碼時,將縣域尺度的協調發展重點定位在“城鄉協調”維度。3)在把握現有的高質量發展核心內涵的同時,延伸出新時代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內涵,豐富了現有的高質量發展內涵。在實踐應用上,雖然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相對滯后,但紅色文化卻是其顯著區別于其他區域的發展優勢,是推進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遇。與此同時,省域邊界的縣域雖然高質量發展得分低于非省界縣域,但生態文明維度卻高于非省界地區。因此,未來發展過程中,在政策支持上,應更應關注省域邊界的縣域,例如建立異地生態補償機制,發展生態旅游,將生態優勢轉化為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驅動力。
未來可開展的工作:1)將本文構建的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實踐推廣,增加指標的實用性。2)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是一項不斷發展變化的復雜工程,因此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也具有多維性和動態性特征。未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積極采取大數據采集等多種研究方式,識別革命老區縣域高質量發展時空演進規律,進而長期檢測和修正完善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