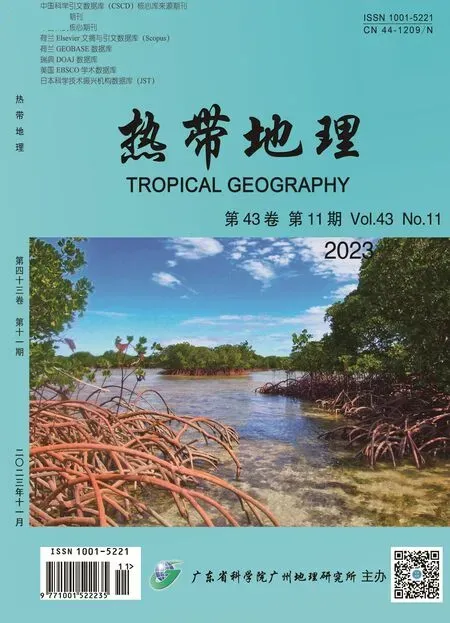老年旅游到老年旅居:基于畢生發展控制理論的邏輯新論
劉 斌,許 磊,陳 浩
(安徽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合肥 230036)
大眾旅游時代,旅游已經成為居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密切關聯著人生的不同階段(Smith et al.,2017)。退休后的老年人,大多擁有相對豐富的自由時間和可支配收入,因此可以更加靈活地選擇旅游方式,成為旅游市場中最為活躍的群體之一(Nielsen, 2016; Elivis et al., 2021)。在諸多老年旅游方式細分中,旅居具有生活性、舒適性等諸多優勢,日益受到中國老年群體的關注(劉昌平 等,2017;王金蓮 等,2019)。旅居原指前往外地或外國居住生活,該詞義融合了異地性和生活性,符合國內新近發展起來的流動現象,流動包括候鳥式流動、異地養老式流動以及“第二居所”等,與旅游流動范疇相一致(孔令怡 等,2017;王海濤,2019;王金蓮 等,2019)。上述旅游流動形式既具有一般旅游定義的時空與活動特征,又貼近日常生活內容,日常與旅游交融的旅游方式,有別于傳統休閑旅游方式,由過往研究可知,老年人是其主要參與群體(趙松松 等,2021)。然而,針對融合且復雜的老年旅居現象,目前缺少整體認識與辨別,不僅現有概念與現象間關系繁雜重疊,同時新現象仍在持續涌現,亟需構建一個合理的框架加以統籌,以避免未來概念間的矛盾和沖突問題持續加劇,以及未來出現明顯的旅居概念濫用。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2個方面:
一是在概念指向上有重合。旅游研究中的旅居突出了旅游者的意義,不具備生產屬性(趙松松等,2021),并且在目的地呈現基營式的流動特點(程豪 等,2021),具有旅游和日常休閑生活的融合特性(王金蓮 等,2019)。基于以上共性,以不同的時空流動形態或目的地類型來理解,并冠以某某旅居的淺顯描述,形成了候鳥旅居、第二居所旅居、養老旅居以及鄉村旅居等諸多旅居概念(孔令怡 等,2017;王金蓮 等,2019)。然而,第二居所旅居同樣可以發生在鄉村、城市等不同空間并以養老為目的。候鳥和養老旅居也具有較高的重合性,養老旅居的研究者認為該概念兼容了候鳥和度假的養老方式,所涉及的空間包括第二居所、療養基地、田園鄉村和養老社區等(王海濤,2019);而鄉村旅居概念則更加寬泛,其他3種形式都可以發生在鄉村(Cheng et al., 2020)。
二是在動機展現上相類似。不同于一般的觀光旅游,旅居更追求在目的地的舒適體驗(趙松松等,2021),總結現有研究發現,實現這種舒適體驗主要有物質環境與心理環境2個層面來源。在物質層面,因為居住地的不利環境和個人身體因素等,促使他們尋求更為舒適的氣候與自然環境,其中,以出現在海南、廣西等地的候鳥、第二居所旅居等最為典型,呈現強烈的舒適性遷移動機(孔令怡 等,2017;王金蓮 等,2019;趙松松 等,2021);另外,鄉村旅居研究中還認為鄉村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吸引條件(程豪 等,2021),但目的地環境要素是多重的,其共同指向身體上的健康與舒適動機。心理環境層面,因為離家可以增強旅游者尋求快樂的程度以及降低遵循規范和履行責任所帶來的壓力,有利于維護現有的社交網絡、發展新的社交網絡以及改善不利情緒,滿足社交與情感發展等動機(Alen et al., 2015),但這些是所有旅居都存在的特點。
總的來說,現有研究多突出某一區域旅居的時空表現特點,導致觀察過于淺顯,且常受限于對某種旅居行為的單一探討,容易忽視老年人完整的內在動機心理。從老年人完整的生命歷程看,旅居只是所有行為中的滄海一粟,老年人花費精力和時間參與旅居活動,不僅有當下的短期動機,還呈現整體的積極意義,同時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旅居的老年人將持續進行有利選擇與行為控制,這與畢生發展的理念相一致(曹鈺舒 等,2012)。據此,本研究嘗試結合畢生發展理念,引入其核心的畢生發展控制理論(life span theory of control),選擇從更高層次的發展視角解讀老年旅居。因此,這并不是一個實證性的分析,而是試圖將老年研究、旅游研究通過畢生發展思維深度關聯。本研究主要有2個目的,一是探索老年旅居統籌辨析方法,體系化重塑現有概念知識;二是依據統籌分析結果,更加系統地認識老年旅居,并嘗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
1 理論引入:以畢生發展控制理論重讀老年旅游
1.1 旅游可以是畢生活動
正如亞伯拉罕·馬斯洛(2020)對動機復雜性的認識:“一個帶有動機的行為可能起到一種渠道作用,通過這個渠道,其他意欲得以表現自己”。老年人對旅游的追求看似為意識中對出游的渴望,但背后包含了復雜多樣的動機。這些動機的根本都深刻表達著老年人發展或調整自我的需要(Moal-Ulvoas, 2017)。諸多關于旅游與福祉的探討都認為,絕大部分旅游行為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個人福祉和發展(Cooper et al., 1993)。因此,拋開每次旅行的單獨意義,從整體上看,老年人一生的全部旅游行為可被看作是自我發展目標的一種長期表現。每次出游,表面上看是一次次的孤立行動,但其只是在深層需求目標下,表現為不同時空和不同形式而已。
人們對自我的發展是畢生的,這是Baltes(1987)畢生發展觀的核心內容。大部分旅游行為呈現出對個體的發展驅動作用,因此旅游是否也可能是畢生的事情?而現實確實對此有所彰顯。首先,旅游行為本身具有時間貫穿性,在Pearce 等(2005)提出的旅游生涯梯度理論中,證實了旅游在個人生命中的跨時間特性,認為旅游者會依據出游經歷的累積而變化,去追求更高層次的滿足,每一次旅游相互之間可共同構成連續和有機的整體。其次,旅游的結果也可以跨越時間,旅游經歷在人生記憶中有重要作用,一次非凡的旅游經歷令人難忘,它們在個體的人生中可以被當做積極的錨定事件,成為回憶時刻,其主要作用包括:對個人身份的形成和維持;構建重要的家庭生活里程碑;發展家庭與社會關系;及產生重訪動機等,這對普遍出現記憶隆起(memory bump)的老年人來說意義顯著(Tung et al., 2011)。最后,旅游的目標同樣如此,對部分老年人來說,旅游還具有實現夢想與補償過往的作用,尤其是年輕時期受條件限制導致的旅游缺失;Hsu 等(2007)對中國老年人出游動機進行研究,發現實現年輕時期未成行的旅程成為老年人重要的出游動機之一,出游目標在人生中形成延續。
旅游行為、結果與目標的時間貫穿性表明旅游至少在發生、效能和動機上呈現一定程度的畢生屬性。而日益繁多的旅游形式還可以為不同文化、人生階段和需求的人群找到“行動”的意義。現如今的旅游早已不是古代士大夫階層的一次寄情山水或者西方工業革命后的一次英法包價旅游等所能概括的,人們旅行的范圍早已超出了“美景”的限制,從簡單的快樂到幸福的促進乃至精神的超越都可以在旅游的意義中找到答案(Smith et al., 2017)。這表明旅游不僅可以貫穿人生的某些時段或時刻,甚至可以有力量地橫跨整個人生階段,使旅游者實現不同層次的滿足。
1.2 老年旅游是畢生控制的體現
在畢生發展觀的影響下,心理學家Heckhausen發展出畢生發展動機理論(motivation development of life span theory),該理論認為大多數人都在塑造自己的積極人生,并根據自己的認知和判斷追求長期目標,同時擺脫那些無法實現的目標(曹鈺舒等,2012)。盡管旅游也可能導致一些不利于個體的行為產生,如放縱酗酒,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旅游都與長期自我發展的目標有關,包括自我實現、美好生活與精神發展等方面,能否去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是目標達成能力的體現,雖然有利他主義的志愿者,其旅游是出于幫助社區發展的目標,但其根本依舊是旅游者個人的自我實現,從一個有意義的經歷中收獲幸福(Smith et al., 2017)。
在畢生發展動機理論認識中,目標達成的能力在與具體活動形成連接時,是受到控制的,并進一步形成畢生發展控制理論,其中的控制包括初級控制和次級控制,可以分為2個辨識維度,分別是目標(外部世界-自我)和過程(行動-認知),理論認為目標中指向外部世界的行動都是初級控制,目標中指向內部自我的認知活動都是次級控制,其中初級控制具有優先性,而次級控制是對初級控制存在難度時的促進或緩解(Heckhausen et al., 1995;李曉東 等,2002;王大華 等,2002)。從上述理論視角看,老年旅游可以被解讀為老年人為實現長期自我發展的目標而去參與旅游活動(初級控制),并且優先采取初級控制即參與旅游,而不是直接調整自己的心態和認識(次級控制)等,這也是旅游的意義所在,以改變環境來獲得更好的自己。
事實上,并不是所有指向外部的行動都能夠輕易實現。老年旅游需要資源與目標保持一致性(Gabru? et al., 2022),很多時候可能會面臨系列阻礙,如老年旅游的實現會受到包括時間、資金、身體、技能以及家庭等諸多因素的影響(Crawford et al., 1991),屆時,旅游行動的初級控制與次級控制之間形成一種控制策略。Heckhausen等(1999)提出了一個二維的初級控制和次級控制策略的最優化模型(model of optim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在模型中,一個維度是初級控制和次級控制,另一個維度是選擇和代償,它們組成4種控制策略,分別是:選擇性初級控制策略,指為實現目標直接投入資源;代償性初級控制策略,指尋求外部資源和技術的幫助,以老人和小孩使用較多;選擇性次級控制策略,指個體內部世界增強對目標的堅持,即意志力的投入;代償性次級控制策略,指減少目標達成失敗帶來的消極影響(單玲玲等,2008)。
以老年旅游作為目標行動內容,會形成4種表現(圖1)。在控制策略下,老年人出游行為在付諸實施時,受個體條件和不同出游形式難度差異的影響,會產生不同表現。1)在能力完全足夠時,可直接付諸出游行動,不用采取代償性初級控制。2)在面臨個體內部能力不足時,包括時間、資金以及出游經歷等限制,采用代償性初級控制,包括尋求他人幫助或其他舉措。3)在初級控制的資源條件達成后,還可能面臨意志力投入的問題,對于老年人來說,身體機能的衰退是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Crawford et al., 1991),尤其在面臨出游行動可能帶來的旅行疲勞和身體風險時,無論是選擇性還是代償性初級控制都很難解決,屆時,選擇性次級控制介入,意志投入有助于提高個人對達成出游行動的承受力,如提高對身體不適的容忍度。4)如果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都不能夠為出游行動提供有力支持時,老年人通過實施代償性次級控制來抵抗不能出游可能帶來的心理不適,包括放棄目標、向下比較(與不如自己的他人比較)或歸因偏見(將不能成行的原因歸結為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等(李艷華 等,2001)。

圖1 老年旅游行為的控制策略Fig.1 Control strategy of elderly tourism behavior
依據以上的控制表現,老年旅游存在以下特點:1)不同旅游形式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資源投入需求。老年人的旅游形式日益繁復多樣,對個體而言,對資源的投入要求也不盡相同,如高端的長途度假往往意味著更多的時間、金錢以及出游技能的投入。2)對身體不適的容忍是老年人需面臨的主要意志投入項,盡管當前老年人健康水平不斷提升,但身體機能的下降是年齡增長的必然趨勢,相對其他年齡段,老年階段的身體感知更為深刻,所以老年人時常在超越身體和過分關注身體的矛盾之間徘徊。旅游的流動特性會讓老年人身體的不適感格外凸顯,需要他們采取更多的意志力以超越身體(Sch?llgen et al., 2012)。3)老年人的意志投入力度會因為不同的旅游形式而呈現差異,一次長途遠游和一次周末的近郊鄉村度假,對老年個體來說,前者產生身體不適的可能性相對更高,而為了達成遠游的目標,有時必須調整自己。
總的來看,意志投入和資源投入需求是構成老年人出游行為控制的2個關鍵要素,是控制視角下解讀老年人旅游行為的核心。一方面凸顯了老年人旅游行為中身體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將形式復雜多樣的老年旅游納入到統一框架下重新分類,個體旅游的畢生發展變化能夠在核心投入要素上形成直接反映。
2 框架提出:老年旅游類型劃分的資源-意志投入框架
2.1 框架提出
基于上述控制策略中意志投入和資源投入的作用效果,構建反映老年旅游的“資源-意志”二維框架。將資源投入以R(Resource)代指,意志投入以W(Willpower)代指。資源投入依據基本且必要投入的相對大小,將其劃分為較大投入(RH:High)和較小投入(RL:Low);意志投入則依據必要性,將其劃分為必要投入(WN:Necessary)和一般投入(WG:General)。在二維劃分的基礎上,根據旅游系統的主要構成,以及旅游者投入主要集中在通道和目的地的特點(吳必虎,1998),將個體的單次出游過程劃分為路途、目的地2部分。對于可能存在多個目的地的房車旅行、長途自駕、騎行等旅游方式,依然可以這樣劃分,將一次行程的全部路程和目的地統籌區分,同樣涉及路途和目的地2個部分。如Viallon(2012)研究的歐洲老年人的房車旅行,他們的資源和意志投入主要在路途中,而在目的地時,他們主要依托自己的房車休閑,很少參觀景點且產生的旅游消費相對較少,因此,對目的地的資源和意志投入都不明顯。
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資源主要指滿足旅游過程中基本生活和游憩需要的時間、資金等,對于購買奢侈品等非基本必要投入不列入其中,資金投入的相對大小主要依據大眾游客的平均消費水平,如中國國內旅游人均每次消費自2019 年起便達到900~1 000元左右(董紅玉,2023),但沒有絕對標準,且不包括極端個例,如美國富豪貝索斯的太空之旅對他來說可能算是大的資源投入,而平常的一次海外旅行只是較小的花費,但對大多數人而言,這卻很可能是一次投入較大的旅行。關于意志投入,老年人主要指向身體,而年輕群體意志投入的指向可能是不同的,這有待其他研究的探索。關于資源投入中最為核心的時間和資金等,在路途部分,時間和資金呈協同關系,但如果發生時間和資金投入不對等情況,則以具有突出表現的因素為主,如廉價且時間長的長途火車旅程,將其判定為較小資源投入,較高花費但時間短的航空旅程,將其判定為較大資源投入;而在目的地部分,從整體的目的地階段看,時間投入的比較意義已基本被隱藏,或許只可能在某個節點上產生時間投入的比較感,如排隊,因此在整個目的地階段資源投入比較的主要對象是資金因素,而且目的地停留時間與花費是密切聯系的(Anantamongkolkul et al., 2017)。
2.2 老年旅游類型劃分
依據以上劃分,綜合考慮路途和目的地的資源與意志投入,在理論上存在16 種旅游行為模式(M1~M16)(表1 中以黑色方塊標注),這16 種模式在當前豐富的旅游行為表現中基本都能找到相應的實踐,以老年旅游者為范本,如M1(RLWN·RLWN),所展現的是路途中資源投入少,但要求必要的意志投入,在目的地也同樣如此,據此可以判斷,其路途資源投入少,但接近難度較大;在目的地同樣花費較少,但是目的地體驗有必要投入身體意志,這類旅游行為可能是老年人的一次短途騎行運動之旅或者一次長途的廉價低消費旅游。每個模式所能代表的旅游行為可能是多樣的,而且因為意志投入針對內容不同,對于不同年齡階段的人群來說會有不同意義。

表1 資源-意志投入框架下的16種老年旅游行為模式及舉例Table 1 Sixteen tourism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elderly and exampl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source-willpower input
1)路途部分。從旅游組織的一般表現來說,長途旅游活動一般需要更高的資源投入且更容易出現身體疲勞,短途的旅游活動基本代表更少的資源投入以及不容易出現身體疲勞,因此,其在模式列表中形成M5~M8(RHWN) 的一般長途旅游和M9~M12(RLWG)的一般短途旅游。除此以外,還存在一些不同表現。如,M1~M4(RLWN)的資源投入少,但是身體勞累可能性大,主要存在2種可能:一種是短途的運動之旅,如騎行,其資源投入少,但是身體勞累程度高;另一種可能是長途的廉價旅游,距離長,時間長,舒適度差,身體勞累可能性大。M13~M16(RHWG)表現為資源投入大,需要的意志力投入小,也可能存在2種情況:一種是長途的舒適旅游,如郵輪出游形式;另外還可能是高端的長途旅游,雖然路程長,但速度快,舒適度高,如高端航空旅游。
2)目的地部分。一共出現4種狀態,其一,資源投入較小且必須付諸意志投入的較小投入(指資源投入)勞累狀態(RLWN),可能是休閑類運動或廉價旅游所造成的身體不適體驗。其二,需要較大資源投入且必須付諸意志投入的較大投入勞累狀態(RHWN),可能是高端的戶外運動或連續的觀光活動造成的身體不適等。其三,資源投入較小且意志投入一般的較小投入舒適狀態(RLWG),可能是較短時間的一般休閑觀光或較經濟的旅居等。其四,資源投入較大但意志投入一般的較大投入舒適狀態(RHWG),可能是中高端的度假活動。
通過將接近目的地和在目的地的過程整合,可劃分為短途運動或長途廉價旅游、一般長途旅游、一般短途旅游以及長途舒適旅游或高端旅游4種類型,體現了接近目的地的方式和在目的地的活動狀態區分,展現老年旅游中控制與體驗感受的關系。
3 框架應用:老年旅居的分類及未來研究思考
3.1 老年旅居的類型劃分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將老年旅居的對應模式進一步縮小,集中為M7、M8、M11、M12共4種。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住宿類型、不同的目的地距離與老年旅游者的停留時間之間存在關聯,更遠距離和更穩定的居住場所,其停留的時間也越長,反之更近的距離和更自由的居住場所,停留時間則相對較短(Alen et al., 2014)。異地所關聯的更穩定的居所和更長時間的停留,意味著更大的資源投入,反之則相對較小。這樣在距離、目的地資源投入和居住穩定性上可形成綜合考量。結合對應的4種模式,可以形成新的老年旅居表現類型劃分,分別是“大投入-長旅途”老年旅居、“大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小投入-長旅途”老年旅居以及“小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圖2)。

圖2 資源-意志投入框架下老年旅居類型劃分Fig.2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es of elderly sojour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sources-will input
“大投入-長旅途”老年旅居(類型1):該類型主要表現為前往較遠地區進行候鳥旅居、第二居所旅居、養老旅居等,以購買或租賃的固定住宅為載體(保繼剛 等,2018),考慮到旅程不易,停留時間相對較長,需要購買或租賃房產等,且由自己照料基本生活,所以在目的地的投入較大(黎莉 等,2015)。
“大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類型2):該類型旅居主要分布在城市周邊的郊野或鄉村,老年人前往近郊或鄰近常住地的其他區域等購買或租賃房產,資源投入較大。但因為距離相對較近,往返便捷,因此停留時間長或短的均有,主要表現為第二居所旅居、養老旅居(包括產權式養老酒店、養老社區)等(Gallent et al., 2000)。
“小投入-長旅途”老年旅居(類型3):屬于候鳥和養老旅居中經濟型選擇,一般依托較為經濟的旅游酒店、農家樂或者廉價的民宅等,沒有穩定的居住場所,如中國的廣西北海地區(李文放,2020)。此外,也有依托房車在目的地長期停留,但這種模式在國內較少,國內房車旅行目前普遍流動性較強(劉斌 等,2021)。該類型旅居一般在目的地投入相對較小,只為滿足住宿、餐飲等基本需求,且場所與地點選擇相對自由,受與目的地距離的影響,停留時間也相對較長。
“小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類型4):這種類型的老年旅居一般不依托固定居住設施,目的地和居住場所選擇相對自由,投入相對經濟,受較近距離影響,出游時間相對較短。目前這種現象在國外還未找到類似的參照,國內對該類型也還沒有形成具體認識。鄉村旅居(rural stay)提出的概念中有對這一類型的部分描述(Cheng et al., 2020)。
第二居所旅居、候鳥旅居、養老旅居、鄉村旅居等概念與以上4個類型相關聯(圖3)。第二居所概念對應類型1與2,突出第二居所的較大資源投入特點,2 種類型主要區別在目的地距離的遠近。候鳥旅居概念與類型1 和3 對應,突出候鳥旅居對較遠距離差異性環境的選擇特點,同時存在在目的地有相對固定居所和相對經濟的自由居所2種選擇差別。養老旅居因為突出養老生活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其界定時間一般為在目的地停留1 個月及以上(黃璜,2013),因此其住所位置相對固定,但場所類型不固定,可以是類型1 和2 的固定居所養老,也可以是類型3 的遠距離、長時間的經濟型養老。鄉村旅居概念主要依據旅居的城市-鄉村的場景變化內涵界定,強調鄉村空間中旅居所形成的特性和吸引力(Cheng et al., 2020),但當第二居所旅居、候鳥旅居、養老旅居等發生在鄉村時,同樣可以稱之為鄉村旅居,這一概念涵蓋范圍更加寬泛,與4種老年旅居類型都有所關聯。
4)訓練方式、手段及步驟:在該項目中,以“任務驅動、自主探索”為主要教學方法,運用情境設置、問題導向、自我探索、任務、小組競賽、成績展示。在活動過程中穿插相關訓練活動和情景面試環節,結合材料案例分析和個人感悟。

圖3 4種旅居類型與現有老年旅居相關概念的關系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r types of sojourn and existing main concepts of sojourn
3.2 老年旅居類型的比較
3.2.1 老年旅居類型間的表現差異 老年旅居即是一種出游方式,也是老年生活的一部分。老年人一般會持續參與旅居(王海濤,2019),時空環境變化讓老年人在日常居所與旅居目的地之間形成了生活場景的反復切換與生活狀態的持續交替。依據在目的地資源投入狀況和路程不同形成的4種老年旅居類型中,既展現場景切換的區別,也體現生活狀態交替的差異(表2)。

表2 場景切換與狀態交替比較Table 2 Compare scene transitions and state transitions
在場景切換層面。類型1更加強調場景的差異性,并愿意為之投入較多的精力和資金,包括氣候差異、城鄉環境差異以及居住場所的差異等,整體場景切換難度較大,要求較高。類型2更加突出異地居所及環境的品質性,通常以城市周邊的鄉村第二居所、養老地產為依托,需要投入較多的資金,整體場景切換要求較高。類型3同樣追求場景差異性,但受到消費能力或消費意愿的影響,更加注重外部的氣候以及環境差異,對居所要求不高,且不具有固定性,但長距離會導致空間切換需要付出較大精力。類型4主要表現為城-鄉空間的切換,追求貼近鄉土生態環境,同樣受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的影響,不選擇長期持有異地固定居所的產權,與日常居所之間通勤距離相對較近,需要的資金和精力投入程度一般。
在狀態交替層面。以居家日常生活狀態為原點,4種老年旅居類型會形成4種不同的異地狀態表現。類型1中,日常居所和旅居目的地之間形成一種同質生活狀態的平移交替,老年人努力在兩地之間保持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性的一致性(段圣奎 等,2021)。類型2為日常生活狀態與旅居狀態交替,在旅居目的地存在超越生活狀態,付出較大的資金成本,追求優于日常的理想生活狀態(Gallent et al.,2000),是區別且獨立于日常居家生活之外的一種向上的狀態交替。類型3 與1 具有相似性,追求環境差異性,但受到遠距離和低資源投入的影響,依托的是相對廉價的租賃房屋或經濟的服務接待設施,只能保證基礎生活水平,較難達到與居家一致的生活狀態(李文放,2020),形成一種向下的狀態交替。類型4具有很強的休閑性和靈活性,與居家生活之間更容易形成空間、心理和社交方面的密切聯系,既不顛覆日常生活方式,又具有逃避日常居家勞務活動的優勢(Cheng et al., 2020),類型4是日常居家生活的靈活拓展,與居家生活之間形成千絲萬縷的連接交替。
3.2.2 老年旅居類型間的參與差異 受到4種類型在場景切換和狀態交替差異的影響,老年人的參與難度、社交關系的維持發展以及對旅居目的地的選擇都會有所區別。
首先,在老年人的參與難度上。國內外研究證實,老年群體在退休后有機會獲得更充裕的個人時間和自由的經濟條件,但這并不是完整的現實(Fleischer et al., 2002)。受到中國“責任倫理”文化的影響,不少老年人退休后成為兒女生活的重要助力,包括幫助照顧孫輩甚至是照顧工作繁忙的子女等,老年人依然面臨著明顯的時間約束(Hsu et al., 2007),導致可承受遠距離、長時間旅居的老年人相對有限,而老年人的身體會進一步約束老年人選擇較遠距離的旅居,如類型1和3的旅居。此外,中國老年人整體養老收入相對有限,類型1 和2 資金投入相對較大,也限制了大部分老年人的參與。但類型4的近距離和低投入特征,為經濟條件一般、時間相對緊張和身體素質較差的老年人提供了實現旅居的機會,大幅度降低了參與門檻。
其次,在老年人社交關系維持與發展上。社交參與是老年人重要的活動形式(Ryu et al., 2015),并帶有顯著的情感特性,一方面,老年人在選擇社交對象時,偏向于較為熟悉和具有一定情感基礎的人群,另一方面,社交能帶來豐富的情感體驗(肖健 等,2013)。4 種老年旅居類型間存在不同的參與門檻,不僅意味著不同的個體參與難度,對偏向結伴出游的老年人來說(周奇美 等,2018),還關乎他們的游伴選擇。類型1、2 和3 參與難度較高,容易受到不同個體間的時間、經濟和身體等因素差異影響,縮小了他們在原來熟悉的社交群體中選擇旅居游伴的范圍,提升了選擇難度。因此,他們一般以固定群體為結伴對象,主要為配偶或者其他親屬,在異地的社交情感類型較單一,這意味著他們可能需要在旅居目的地擴展新的社交圈,但這并不輕松,容易出現社會融入困難以及與家鄉社交網絡缺乏聯結等問題(李雨潼 等,2018)。而類型4 的低門檻,意味著老年人可以更容易維系發展包括親朋、好友、老同學等各種社會關系,組成結伴旅居隊伍,有利于緩解老年人旅居的人際限制,并獲得超出家庭社交圈的其他情感。
最后,在對旅居目的地的選擇上。類型1 和3付出了較多的精力或資金,選擇遠離居住地開啟異地生活時光,主要因為受到某些常住地或近距離目的地難以獲取因素的吸引,如溫暖氣候、更加獨特的自然生態條件,甚至是一些具有身體治愈性的康養因素等。類型2則是以較多的資金投入換取超越日常的生活狀態,盡管目的地的選擇可能是近距離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目的地一定是經過仔細挑選的,從已有經驗看,他們常位于城市邊緣的風景度假地或鄰近常住地風景秀麗的鄉村地區(吳悅芳 等,2012)。類型4 擁有較近的距離和較少的投入,意味著在基本餐宿條件上趨向于經濟或廉價水平,不會對目的地形成過高的期待。在控制視角下,類型4讓老年人在舒適性和經濟性上實現平衡,既保障了基本的舒適體驗,又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其中以農戶自建房改造的農家樂或中低端民宿為代表,是降低資源投入的關鍵(Cheng et al., 2020)。針對類型4,老年人期待程度低、鄉村接待設施易改造,因此類型4 的旅居目的地選擇面更加寬泛,給更多鄉村提供了機會。
綜合來看,類型1 與2 具有一定的參與難度,呈現較為顯著的“精英”色彩,但在龐大老年人口基數上,該群體的數量依然可觀,仍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類型3的參與難度略低于類型1和2,但在目的地選擇上仍具有較明顯的限制,滿足市場需求的可選區域相對有限。相對而言,類型4場景切換簡單便捷,參與難度較低,對老年人群體和區域的覆蓋度都較高,具有明顯的普惠性。
3.3 未來研究思考
老年旅居參與方式日益多樣,但當前針對該內容方向的研究相對匱乏。現有研究中,老年旅居更多被視為一種旅游流動背景,以探討第二居所旅居以及候鳥旅居的社會融入問題、鄉村旅居的鄉村發展問題、養老旅居的產業經濟問題等,忽略了老年旅居本身(劉斌 等,2023)。
隨著老齡人口規模的持續攀升,中國提出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發展針對銀發人口的旅游經濟是宏觀趨勢。在老年旅游市場被同質化認知的過去和當下,旅居是目前國內為數不多能夠表現出顯著適老性的旅游形式。其能夠與觀光旅游、休閑旅游、度假旅游等有機融合,與這些旅游的主要產品實現資源、渠道和效益的共享,而不必單獨建設一套獨立的旅游目的地系統。老年旅居突出的適老性優勢,能夠彰顯老年人的獨有需求,包括更加舒適的行動安排,更加休閑放松的活動內容等;還能讓老年人追尋更適合自我的體驗和意義,而不是不隨著大眾客流去體驗俗套而泛濫的旅游經歷。對地方而言,旅居與區域其他旅游產品之間的共享優勢,可以讓更多的地方以較小的成本,吸引規模龐大、消費力不俗且有利于平衡目的地季節性的老年旅游消費群體。
適老性造就了獨特的行為動機、表現以及體驗意義,與地方旅游發展融合,推動著旅居空間的變化。基于此,本文認為未來回歸老年旅居研究可以從行為、主體和空間3 個視角切入,形成對行為、動力和空間及其互動結果的探討,主要研究思路框架見圖4所示。

圖4 老年旅居研究框架Fig.4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elderly sojourn
1)老年旅居行為研究可以突出對行為特征的把握,發現老年旅居行為的具體共性以及不同類型間的差異,發現促成這些行為特征的主體和空間影響因素,區分在不同空間、時間和細分群體上的行為特征表現,尤其是持續參與過程中所形成的行為連續性變化,歸納行為特征的形成機制。
2)老年旅居動力研究可以結合老年人行為心理,探索老年旅居體驗的老齡價值和意義,以畢生觀念思考老年旅居對老年人的整體意義,將旅居置于老年生活的有機組成,并與積極老齡化理念相結合,以此考察老年旅居所形成的“真實的”情感意義、幸福價值等,挖掘老年旅居持續發生的生活場景切換和狀態交替行為的根本動力與具體動機表現。
3)老年旅居空間研究可以關注具體地方在響應老年旅居行為需求時的變化過程,綜合思考與比較不同類型旅居場所的地方差異,總結地方響應的模式、路徑以及優化調整的機制,分析旅居空間在老年人心中的地方形象認知及其構建機制,探求不同旅居類型所需要的要素體系與層次,為地方提供更具實踐指導意義的成果。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引入畢生發展控制理論,提出了新的老年旅游類型劃分框架,并將其應用到老年旅居的統籌辨析中,主要得出以下結論:1)旅游是一個受到畢生控制的活動,老年旅游中資源和意志投入是2個關鍵的控制要素;2)依據資源投入大小和意志投入的必要性形成對老年旅游行為模式的新解構,體現老年人在出游決策時對身體意志以及所需資源的不同控制策略;3)相比于老年旅游,老年旅居者的行為模式更加聚焦,在目的地的意志投入必要性有所降低,但目的地的資源投入呈現“精英化”和“大眾化”的區分,路途階段的資源與意志投入則隨路途遠近增減,形成由目的地投入大小和路途遠近所區分的4種老年旅居類型;4)4種老年旅居類型分別為“大投入-長旅途”老年旅居、“大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小投入-長旅途”老年旅居以及“小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與旅居目的地生活場景形成聯系,體現了老年人對不同異地旅居生活狀態的渴望,促使他們選擇不同參與難度、社交關聯以及目的地的旅居,同樣體現老年人對行為的控制。
總體而言,老年旅游的類型劃分和老年旅居類型的統籌辨析是一個知識的建構過程,本研究以演繹方式實現遞進式探討,所得出的結論具有理論和現實2方面的重要意義。從理論視角看,整體過程循著理論引入—關鍵框架—框架應用—概念析出的持續收攏流程,形成了類似三段論的邏輯思路,構建了具有統籌性的分類框架,為未來研究奠定了一定的認識基礎,提供了關鍵方向。本研究與畢生控制理論相結合的創新性研究視角,為解讀當前持續豐富和變化的旅游行為及現象等探索出一種可以模式化分析的手段。從現實應用視角看,本研究從基礎層面探討了老年旅居的不同行為特點和需求差異,對于指導地方提供相應服務產品、統籌資源等具有實踐意義,使地方能夠更好的服務老年群體,提升老年旅居的幸福感與獲得感;同時還有利于指導地方差異化地發展老年旅居經濟,促進老年旅居銀發經濟價值潛力的釋放和老年人個體的積極發展,助力地方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
本研究將畢生發展控制理論引入到老年旅游和老年旅居的研究中,但重點是對老年旅居形成統籌認識,期待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未來一方面是針對老年旅居,可以在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基礎上,通過豐富的實證分析,優化完善老年旅居研究體系。另一方面,回歸到老年旅居的積極老齡化貢獻上,進一步延伸老年旅居的研究視野,針對老年旅游,目前已有研究從主觀幸福感、福祉、積極老齡化以及生活滿意度等多個視角理解老年旅游行為的積極價值,但更多被局限在從家到旅游地的單向行為體驗中,未來可以嘗試增加探討旅居地向居家場景切換和交換過程,探討對回家的積極貢獻,將老年人日常生活與老年人旅居生活統籌考慮;此外,現有研究對旅游“控制失敗”的探討極少,而這種控制失敗如成功一樣的常見,如社會比較(與周邊他人)造成的挫敗感和失落感等,需要如何去理解和調節,是否是引發相關補償性旅居的原因,是否會引起不同旅居類型間的替代和轉化等?這些在畢生控制的認識下,不應該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