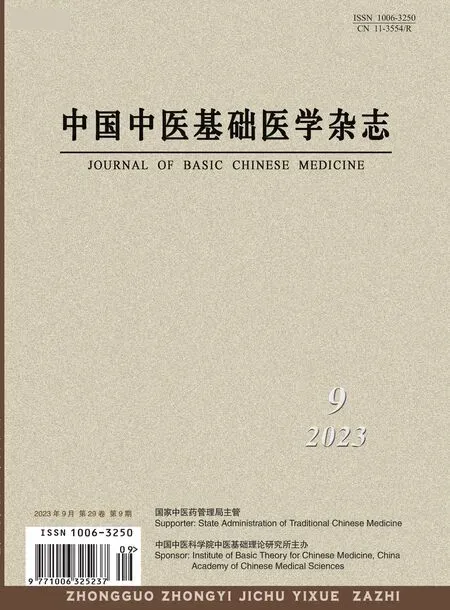“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新解?
高宴梓,張立平,于智敏△
(1.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北京 100700;2.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700)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出自《禮記·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1]。古今學者對本文的解釋,僅限于“三世”一詞,鮮有結合“不服其藥”全面探究者。現對其含義進行新的解析。
1 “三世”內涵考辨
對“三世”內涵的理解是完整準確詮釋此命題的關鍵。作者認為,“三世”包括“三世之學”“三試之驗”和“三圣之道”三個層面的含義。
1.1 三世之學
“三世”指祖孫三代,強調世醫家傳的重要性。東漢鄭玄對《禮記》作注曰“三世,自祖至孫”[2]。《周禮訂義》引鄭節卿言“古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懼其不精也”[3]。“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突出強調了這些行業特征;嚴陵方氏有言“醫之為術,茍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4]?史家之贊孫思邈曰“夫人之身出必有處,處非得已,貴為世補”[5]。通過父子間“親炙”這種傳承方式,掌握獨門技法,通過臨床實踐增強信心,凝練專業方向,實現從量的積累到質的提升。
“三世”即“三世之書”,強調讀醫書的重要性。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在鄭玄注基礎上進一步作疏曰“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2]。史崧為《靈樞》作序時提出“夫為醫者,在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為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醫者也”。《慎疾芻言》亦云“一切道術,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漢唐以前之書,徒記時尚之藥數種,而可為醫者”[6]274。張志聰引程伊川語“醫不讀書,縱成倉、扁,終為技術之流,非士君子也”[7]。
師承亦是傳遞“三世之學”的重要途徑。“古之學者必有師”。《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長桑君乃以禁方傳扁鵲,淳于意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針灸大成》引《玉龍歌》云“七般疝氣取大敦,穴法由來指側間,諸經具載三毛處,不遇師傳隔萬山”[8]。師承是對“親炙”的補充與修正,可避免《傷寒論·序》所謂“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的弊端。
“三世之學”核心在“學”。后人總結的“徐大椿閱書五千卷,葉天士拜師十七人”詮釋還是“學”,只不過前者重視讀經典,后者側重參名師。《醫經允中》云“況得心應手之妙,有父不得傳之于子者,道在典籍而非篤好以善之,雖十世奚益?故不惟其世,惟其學矣”[9],明示讀醫書、承家傳、拜名師三者關系。張志聰《侶山堂類辯》分析“簪纓世胄,士之子而恒為士”的家學原因,在于“能讀三代之書”“又能讀書好學”,故能“世代相傳”[7]。
1.2 三試之驗
三試之驗是對“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補充深化,包括臨床經驗的總結、方藥的體驗和失敗教訓的反思。藍田呂氏曾言“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4],道盡“三試之驗”緣由。
中醫乃致用之學,需要臨床實踐檢驗。《左傳》說“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辭》指出“九折臂而成醫”;徐大椿認為“醫之為道,全在身考”[6]238,他們均強調了臨證的重要性。明代宋濂《贈醫師葛某序》對“三世之書”作出闡釋“脈訣所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10]。
醫者臨證必深諳藥性,如此方能心有定見,用藥有準。清代談金章《誠書·凡例》中說“醫之知藥性,猶主將之識兵,必明順逆險阻,而后戰勝攻取”[11]。《藥性賦》曰“藥有溫熱,又當審詳”[12];《醫宗必讀》載“寒熱溫涼,一匕之謬,覆水難收”[13]。《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載“夫濟時之道,莫大于醫;去疾之功,無先于藥……未諳體性,妄說功能,率自胸襟,深為造次”[14]。以上諸論均強調于此。
對失敗的教訓引以為戒也是“三試之驗”的重要內容。元代羅天益《衛生寶鑒》有“藥物永鑒”三卷,凡25篇,專門介紹藥誤所致的不治案例,喻世明理,當為避免醫誤藥誤之龜鑒。
1.3 三圣之道
三圣之道又稱“至道”,指伏羲、神農、黃帝之道,是中醫的最高醫道與醫術境界。《素問·王冰序》有言“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這是對“三圣之道”的高度概括。
三圣之道是醫者追求的最高境界。《軒岐救正論》言“明良之工,世不常出,直超儒仙千仞而上之矣”[15]。《素問·氣交變大論篇》言“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足見體悟至道之高之難。“三世之學”與“三試之驗”是登堂入室體悟至道的門徑。
《傷寒論·序》記載的“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等名醫事跡,彰顯的就是“三圣之道”。明代趙獻可《醫貫》“有醫術,有醫道。術可暫行一時,道則流芳千古”[16]是在診療技術、處方用藥上對“三圣之道”的升華。
2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探析
2.1 句型分析
本文是雙重否定句。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反正·虛實》的定義是“一句之中,上下兩次用否定詞,就含有肯定的意思”“雙重否定或者加強肯定,口氣更加堅決”[17]。以此類推,本句表述為“醫必三世,方服其藥”于理亦通,但用此句式表達不足以突出其警示作用!
2.2 內容解析
本文有兩層含義:一是直觀判斷醫生水平高低的重要參考。服,信也。《管子·正》言“能服信”[18],表明醫生水平夠高,才容易得到患者的信任而心悅誠服地服藥。當然,此語的提出有具體的語言環境,通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體現“慎物齊”[2]思想。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周易·無妄第二十五》言“勿藥有喜”等,表達的是同樣意思。所以,患者服藥之前從“三世”角度對醫生醫術進行評判不無道理。
二是明確了德藝雙馨醫師所需具備的職業經歷與基本條件。《東醫寶鑒》概括其中緣由為“蓋謂學功須深故也”[19]。“學功須深”言簡意賅,寓意深遠,其中蘊含專業知識的學習、長時間臨床的熏陶浸潤以及家族獨特技藝的傳授等。《漢書·藝文志》言“有病不治,常得中醫”[20],實在是有感而發;孫思邈曰“寧可不服其藥,以任天真,不得使愚醫相嫉,賊人性命,甚可哀傷”[21],誠屬經驗之談。《靈樞·史崧序》言“不讀醫書,又非世業,殺人尤毒于梃刃”,則是對此進行的高度概括。
3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踐行路徑
《素問·王冰序》中說“將升岱岳,非徑奚為?欲詣扶桑,無舟莫適”,提示欲達目標需要路徑與條件。“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是中醫人才培養路徑,是“體三圣之心,窮三世之理,則道乃可明;明三圣之道,守三世之法,則病無失治”[9]的踐行路徑。
3.1 參三世之學讀十年書登堂入室
讀書重在明理。《本草新編》言“人不窮理,不可以學醫;醫不窮理,不可以用藥”[22]。《醫鏡·蔣序》亦曰“觀夫醫之為道,全憑邃識在心,輝燭病理,審悉幽隱,酌和湯味。顧醫之上者,理于未然,其次在毫毛間”[23]。而且,醫理精微,非淺嘗能至,須經三世之學的積累與實踐。王叔和《脈經·序》亦言“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在心易了,指下難明”[24]。
臨證貴在心悟。清代俞根初《通俗傷寒論》言“讀書無眼,病人無命”[25]。《醫門棒喝·田序》言“凡讀書貴能信,尤貴能疑。信則有定識而無所游移,疑則分別決擇衷于至是”[26]。王孟英曾感慨“第有學無識,雖博而不知反約,則書不為我用,我反為書所縛矣”[27]。蕭京《軒岐救正論》指出“世間業醫者……非專守河間之法,則偏執丹溪之書,訕李東垣獨理脾胃,吠薛立齋每重命門,不曰傷寒專門,則云雜病獨科,求其始會其全,由博入約者,無有也”[15]。
問道貴參名師。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指出思辨的具體方法為“事貴師古,尤貴與古為新,方能使醫學日有進步。愚愿有志學醫者,既于古人著作精心研究,更當舉古人著作而擴充之,引申觸長之。使古人可作,應嘆謂后生可畏,然后可為醫學嫡派之真種子,而遠紹農軒之傳也”[28]。《醫鏡·蔣序》又曰“醫理精微,淺師難學;醫宗博浩,庸師莫殫”[23]。
3.2 經三試之驗臨千百證胸有成竹
臨床經驗需要實踐積累。中醫臨床療效源于一病、一證、一法、一方、一藥的診治經驗與心得體會,是在取得若干鮮活的診療經驗基礎上凝聚出的學術閃光點與提煉出的思想精華,這些寶貴的經驗是保證診治疾病胸有成竹,藥到病除的關鍵。王充《論衡·別通》言“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29];山陰陸氏亦言“三世相傳,意之所不能察者察矣。世云,老醫少卜”[4]。《世醫得效方·王充耘序》載“語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醫何以貴世業也?謂其更嘗多,而險危劇易皆得之耳聞目見,較之臆決嘗試者,得失何啻倍蓰”[30]。
臨證還需明辨藥性物性。《重陽立教十五論·合藥》言“藥者,乃山川之秀氣,草木之精華。一溫一寒,可補可泄,一厚一薄,可補可托”[31]。《圣濟經·藥理篇·權通意使章第四》言“物各有性,性各有材,材各有用。圣人窮天地之妙,通萬物之理,其于命藥,不特察草石之寒溫,順陰陽之常性而已”[32]。
療效的取得在于有維有守。《尚書·說命》言“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33]。對于患者服藥后出現的眩暈、頭目昏花等反應,到底是服藥后身體機能調動的正常現象還是藥不對癥而引起的副作用?醫者最初并無確切把握,還需請求師長的點撥與指正。
此外,醫者在臨證過程中遇到的其他疑惑,亦需師長的解答,以利于自身更好更快地成長。在此過程中,中醫學由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其學術思想和臨證經驗均已足夠成熟,可稱其為一個系統性和完整性的學術體系。
3.3 入三圣之道參詳變易神用無方
心悟啟微尋道。實現理與術合,道與法會,直契本心。清代醫家程鐘齡指出“心悟者,上達之機;言傳者,下學之要”[34],強調悟性的重要。具體而言,三圣之道在于參詳變易。孫思邈說“若夫醫道之為言,實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里。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諭”[35]。
以意為之悟道。《太平圣惠方·序》言“夫醫者意也。疾生于內,藥調于外,醫明其理,藥效如神,觸類而生,參詳變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36]。如此,方能達到三圣之道的境界。清代石壽棠《醫原》中說“以心醫心之法,乃是最妙上乘”[37]。《素問·八正神明論篇》言“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云,故曰神”。
神用無方證道。《治嘉格言》記載“不藥之益壽丸”,足為典范,“足柴足米,無憂無慮;蚤完官糧,不驚不辱;不欠人債起利,不入典當門庭,只消清茶淡飯,自可益壽延年”[38]。《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載“繇是醫者必須舍短從長,去繁就簡,卷舒自有,盈縮隨機,斟酌其宜,增減允當,察病輕重,用藥精微,則可謂上工矣”[14]。張介賓《類經·自序》載“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斷流之水,可以鑒形;即壁影螢光,能資志士;竹頭木屑,曾利兵家”[39]。如此,則隨心所欲即是方。
《周易·系辭傳上》載“神無方而《易》無體”。明代李梴《醫學入門》載“善用方者不執方,而未嘗不本于方”[40]。明代吳昆《醫方考·方時化序》言“無方而有方,有方而無方,其斯大醫之門,蹈道之徑也”[41]。清代喻嘉言《醫門法律》載“始于用方,而終于無俟于方,夫然后醫之道成矣”[42]。如此,方可神用無方,醫道乃成。
4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意義
《素問·氣交變大論篇》言“善言天者必應于人,善言古者必驗于今”。因此,探討這個中醫傳承理論命題的意義,古為今用,以服務于當代中醫的守正傳承與創新發展。
4.1 為患者擇醫提供指導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實際上是患者擇醫的一種心理習慣,是對經驗之醫的信任。患者在面臨生死之困時,選擇合適的醫者對其來說是最為重要的。晉代楊泉《物理論》言“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43]。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包含醫生的身份資質與品牌字號,以“三世”為標準選擇醫生,今天看來也是無可厚非的。
4.2 為人才培養指明路徑
中醫人才培養應遵循自身發展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探索能將學院教育和師承培養相結合,通識教育和專長教育相結合的中醫人才培養新路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作為提升中醫藥人才能力素質的路徑,有必要研究完善并賦予全新的內涵。其中,“三世之學”強調醫師所應具備的學識和視野;“三試之驗”強調醫師所應具備的感悟和經歷;“三圣之道”強調醫師所應具備的層次和境界,是其核心。
4.3 為學術傳承提供決策
傳承是中醫傳遞思想、方法、技能的重要形式[44]。古代中醫學術傳承主要包括家傳和師承兩種模式,或為親炙,或為私淑,二者對古代中醫學術傳承與發展發揮同等重要的作用。兩者方式有別,途徑各異,但關鍵節點和核心要素則一,涵蓋在“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中:既重視家學,又重視參師;既強調讀書,又強調診病;既重視理論,又重視實踐;既保持學術的延續,又主張納新。這種融體悟與心悟于一體的傳承范例,可為中醫學術傳承要素篩選提供決策支持。
5 結語
中醫強調“傳承精華,守正創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意蘊諸此。裘慶元在《三三醫報》創刊宗旨中提倡的“醫者須讀三世之書,求三年之艾,方能三折其肱”[45]為具體方法,《醫學辯害》所論“醫不止于三世,而其書又奚止于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46]。可謂一語中的,當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