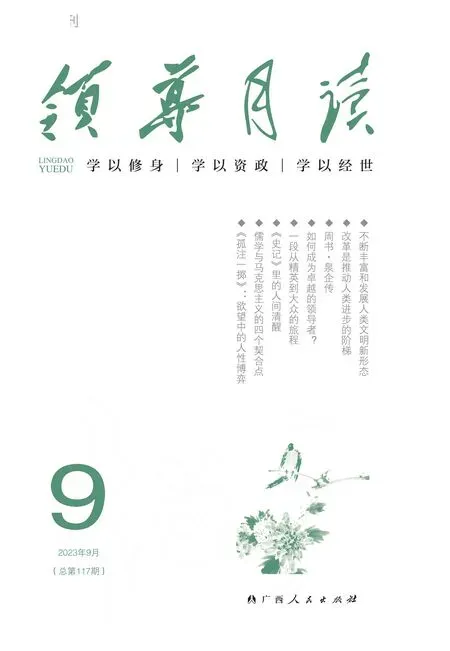發展經濟要尊重經濟規律
秦 朔
從政府到社會,盡管發展經濟、強信心都很努力,但形勢不容樂觀,原因是什么?除了人口的結構性變化、全球增長乏力和地緣政治影響,以及收縮性政策造成的“合成謬誤”等等,我認為中國經濟的壓力之源,在于較為普遍的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又和GDP優先目標下的政府行為相關,即過于重視投資拉動,而對產出的效率、效益缺少應有的重視。由于需求側的勞動者保障不充分,遭遇困難時的直補也很有限,所以一旦增速下行,居民但求自保,節儉過日子,導致供給過剩更為嚴重。
投資由負債驅動。負債并不可怕,只要能帶來有效回報。但我們很多地方的投資,要么空空蕩蕩,要么產能同質化,企業打價格戰,打得收入和納稅都不達預期,又導致政府稅源不足,只好進一步舉債,這又使負債率越來越高。
資源配置是經濟學的最基本問題。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太急于出成績,把經濟發展當成造房子,說幾天造好就幾天造好。
事實上,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的成長是有規律的,有的可以快一點,有的恰恰需要慢一點,就像不同植物的成熟期都不一樣。硬要快出成績,恨不得一個季度招商引資就上臺階,半年就有一批企業投產,一年就大見成效,這是不符合規律的。
新華社最近有一篇調研,反映部分地方政府為爭項目加碼招商政策,互挖存量企業,“招商內卷”“超常規優惠”等問題,認為這種“血拼”內耗不利于發展。有的地方的受訪干部說:“自從上馬了大項目,財政幾乎被掏空。”這種情況的本質,還是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急于求成。
產業調整和升級要漸進而行,不能過于主觀化。一個產業,只要市場需要,依法合規經營,就不應該被經常性地干擾。如果基礎消費、基礎產業(如房地產)都失靈了,很多高精尖也會失去用武之地。
很多官員的眼睛都在往“高處”看,往“別處”(別人在做什么)看,而不是往下看,往眼前看。一看到高大上的,就眼睛發亮,拿出各種優惠條件。而對腳下的土地,對現有的經濟形態、就業形態,對在市場經濟的自然肌理里長出的東西,往往看不上、看不起,不是想著怎么幫他們就地提高,而是想著如何關停并轉。
我們的資本市場說要搞注冊制,其實還有很多窗口指導,對一般制造業和食品等消費行業都是低看一眼,A 股似乎已經不需要、不歡迎這些東西了。殊不知,那些高大上的科創題材,真能為投資者創造價值的未必很多,而老干媽、農夫山泉這樣一目了然的消費品公司,難道就和高質量無緣了?
最近重讀新發展理念的有關論述,感到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理念中,協調做的是最不夠的。其余四個理念易于理解把握,但如何協調?對各地政府來說,我認為協調發展的一個緊迫要求,就是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基礎產業之間要平衡發展,不要簡單化地做高下之分,而要盡可能地包容,充分考慮到現有產業的內在邏輯、成長脈絡,再進行恰當的優化。大量傳統產業/基礎產業還是地方的“現金牛”,也不用政府投入,何必在新興產業的增量并沒有真正起來的時候,就先漠視起存量來了呢?
最近我去了歐洲幾個國家,西班牙、匈牙利、奧地利、德國等,也去了日本,感覺和多年前去的樣子沒有多少變化,但運轉很正常。因社保、醫保完善,老百姓也很安心。所以,在存量經濟為主和經濟增速不高的情況下,也有發展的模式。相比之下,我們把大量資源投到基建中,社保、醫保特別是農村、農民工的保障相對欠缺。
前幾年我在德國一些公司考察工業4.0,最觸動的是他們的工廠是百年工廠,100 多年了還是同一個地方,不斷改造升級,一直到今天的4.0。這才是對資源的善待,才是他們最牛的地方。最怕的是一直另起爐灶,一直攤大餅,直到把資源耗到不可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