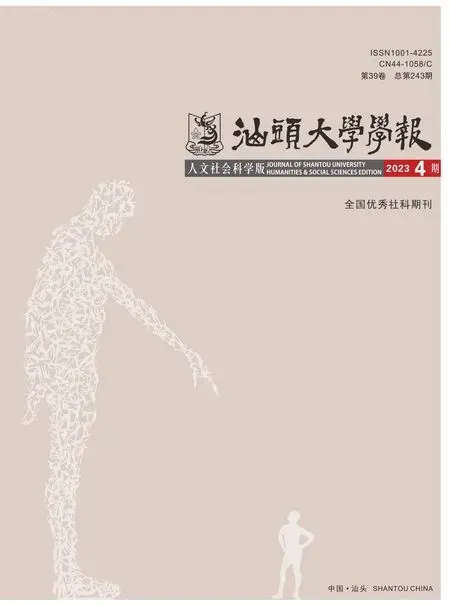約瑟夫·康拉德《吉姆爺》中的敘事判斷
陳祎滿
(西北大學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吉姆爺》(Lord Jim,1900)講述了海員吉姆在一次航行中,遇到海難置乘客于不顧棄船逃跑,隨后獨自接受審判,繼而被西方社會拋棄,前往東方成為英雄的故事。在《吉姆爺》中,“帕特納號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是小說的中心事件。在“帕特納號沉船事件”中吉姆因違背了水手的職業準則接受審判,在“布朗事件”中,吉姆以自我犧牲獲得了他所重視的榮譽,他的行為被敘述者反復評價,伴隨敘事進程的展開,讀者對吉姆產生了多維反應。學界傾向于對《吉姆爺》進行倫理闡釋,揭示小說倫理道德的復雜性。有學者指出吉姆在東方世界進行精神懺悔[1]100,認為“吉姆的靈魂只有在偏遠山區才能得到拯救。”[2]120也有研究者認為《吉姆爺》講述了一個英雄主義的夢,肯定了友情和互惠的價值[3]33,表現出康拉德普遍偉大的道德愿景[1]102。若執著于對《吉姆爺》的中心事件進行倫理評價,則難以窺見小說的審美價值,援引詹姆斯·費倫的敘事判斷可以從人物的闡釋判斷、敘述者的倫理判斷以及讀者的審美判斷三方面厘清文本極具闡釋價值的多義性,審視小說在敘事倫理、敘事形式上的交融。
當代敘事學理論的重要學者詹姆斯·費倫認為,敘事會建立自發前進運動邏輯的方式,這一進程邀請讀者參與其中[4]147。費倫據此區分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敘事判斷:“闡釋判斷(將某事視為X而不是Y 的決定),倫理判斷(關于構成人物活動價值、敘述者活動價值以及作者活動價值的決定),美學判斷(關于敘事總體質量和具體質量的決定)。”[5]28其中,闡釋判斷是對事件性質的判斷,倫理判斷是從道德角度進行的判斷,而美學判斷是對敘事質量作出判斷。這三種判斷存在于小說故事層面與小說的敘事交流之間,且這三種敘事判斷或是互相影響,或是相互交融。康拉德在小說中使主人公、敘述者以及讀者圍繞吉姆行為做出諸種敘事判斷,在賦予文本多義性的同時,也構成推動小說敘事進程的動力。此外,費倫指出文本中存在四種“倫理取位”(ethical positions),可簡單概括為:人物的“倫理取位”、敘述者的“倫理取位”、隱含作者的“倫理取位”以及“有血有肉的真實讀者”的“倫理取位”[6]23。《吉姆爺》中敘述者與受述者,隱含作者與理想讀者,真實作者與讀者之間在涉及到知識、判斷、價值、信仰上均有所分歧。主人公、敘述者圍繞“帕特納號”和“布朗事件”的不同判斷使小說充滿不確定性,故事的不確定性和讀者對“確定性”的本能追求,在文本中構成充滿張力與活力的辯證關系推動小說敘事進程,實現小說在敘事形式和敘事倫理上的交融和暗和,構成具有豐富意蘊的敘事美學。
一、主人公的闡釋判斷:被迫逃逸與直面死亡
《吉姆爺》以主人公吉姆對朋友馬洛的講述復現小說的中心事件,吉姆通過回憶性講述闡釋自己的舉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吉姆是帕特納號船上的大副,擁有成為航海英雄的理想,在帕特納號的一次航行中,船只發生大面積漏水現象,危機之時,船員們置乘客于不顧棄船逃生,在事后的審判中,只有吉姆出席了庭審,被吊銷了航海執照。吉姆只得前往東方重新開始生活,成為備受尊崇的“吉姆爺”。海難發生時吉姆看到船上的鐵板即將被破開,整條船將被淹沒,船上的救生船數量也根本不夠所有的乘客逃生,這種情況下叫醒乘客只能是增加更大的恐慌。此時的吉姆六神無主,正在他眩暈苦惱之際看到其他船員準備逃生,隨著船長的喊叫聲,他懵里懵懂地跳上了救生船。
吉姆在對馬洛的講述中,不斷強調自己跳船時無意識的狀態和跳船之后的懊悔。吉姆多次重復跳船的細節,指出自己顫抖著站在甲板上,滿腦子都在想著“八百個人,七條小船”[7]117。混沌的他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選擇了逃跑,是當時情況的危急和其他水手的引誘與迫使讓他最終做出了跳船的選擇。他也反復強調自己醒悟過來后內心的煎熬與懊悔:“我當時但愿能死掉……我仿佛跳進了一個無敵深洞……”[7]198吉姆竭力想通過自己的語言描述出當時那種混亂而又真實的場面,試圖重現那一刻他內心的煎熬,以這種方式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企圖得到傾聽者的理解和寬容,以消解內心的痛苦與折磨。吉姆在對馬洛的講述中,反復強調自己跳船時和跳船后的心理狀態,強調自己內心的掙扎與痛苦。費倫指出:“同一行為會引起多種判斷,人物行為本身包含人物對自己的判斷。”[8]9吉姆將自己跳船的行為解釋為無意識的和被迫的,消解了棄船逃生行為的不道德性。
如果說吉姆在“帕特納號”事件中展現出了人性的軟弱,那么在“布朗事件”中直面困境,慷慨赴死則是他修復創傷的重要行為。吉姆被西方世界拋棄后,來到斯坦因在土著部落帕圖森的貿易站工作,他因斯坦的推薦獲得了頭人多拉明的信任,憑借自己的智慧摧毀了惡棍警察長的軍事營地,建立了自己的營地,受到當地人的認可,建立了自己的王國,成為了受人尊敬的吉姆爺。白人海盜布朗入侵后打破了他理想的生活狀態。起初入侵的海盜布朗被頭人的兒子丹·瓦利斯制伏關押起來,吉姆在與布朗交談后出于對受難白人的同情釋放了布朗。但布朗脫困后對部落進行了反擊,攻擊并槍殺了丹·瓦利斯。吉姆失信于帕圖森人民,面對自己給部落帶來的重大傷害,吉姆沒有逃避,他來到頭人多拉明面前,沒有任何的猶豫與遲疑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面對與吉姆有相似遭遇的布朗,吉姆選擇給布朗一次機會。反觀吉姆在西方世界的遭遇,即便他接受了懲罰也未曾得到任何人的原諒,導致他只能來到帕圖森重新開始。吉姆對布朗的釋放是與過去自己的和解,第一次面臨生命的選擇時,他被迫逃生后飽受精神的折磨,當再次選擇時他堅定地維護生命。他也并未因自己被白人社會拋棄就心生怨懟,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為布朗做擔保。最后在面對自己的決策失誤時,他也堅定地選擇了放棄一切奮不顧身地履行責任,直面死亡以彌補自己在帕特納號事件中的軟弱,他也從一個逃避責任的海員變成了一個擁有堅定剛毅氣質的英雄,修復創傷后的吉姆成為了大英帝國的英雄。
吉姆的行為包含對其理想信念的闡釋。吉姆的棄船逃跑是無奈之舉,之后作為船員代表出席庭審并被吊銷執照,是他對自己罪責的承擔,從而使他棄船逃跑的罪行減輕甚至變得可以理解。吉姆在布朗受困時呈現的友好善良以及在布朗反擊后承擔責任的勇敢堅毅,吉姆最終為自己信仰的英雄主義和普遍性倫理法則而死,成長為道德意識極強,擁有社會責任感和男子氣概的英雄。
二、敘述者的倫理判斷:社會棄兒與土著英雄
敘述者是小說重要的敘事動力,康拉德擅長通過不同的敘述聲音使作者以及讀者的道德立場復雜化。在敘事活動中,人物的言語行為參與敘事話語的建構[9]150,《吉姆爺》中敘事者的多聲音對話呈現出不同的倫理取位。熱奈特指出所有承擔敘述職能[10]180的人物都可以稱為敘述者,同時將敘述者的職能分為五類:講述故事、講述話語結構、敘述情境功能,回憶證實功能,以及敘述思想。依照熱奈特的分類,將《吉姆爺》中敘述者的功能進行區分,以更清晰地辨別敘述者的倫理取位。《吉姆爺》中馬洛是承擔講述故事職能的敘述者,與此同時小說中諸多人物擔任了敘述者的不同職能,對主人公吉姆進行評判,在小說中形成了多聲部、復調式的對話結構,以豐富小說的敘事判斷。小說中敘述者的判斷與吉姆對自己的評判產生分離,多種人物的不同立場的互相交織,形成了故事層上的不穩定性,而多種敘事聲音的不確定性推進了小說的敘事進程。
馬洛是小說主要的敘述者,康拉德以其對吉姆的不確定性判斷建構了不可靠敘述話語。布斯指出,敘述者的言行與作品的表意不一致時,敘述者是不可靠的。馬洛對吉姆事件的敘述,是通過轉述吉姆的回憶性講述和他對事件的評判構成,但他的判斷充滿不確定性。在法庭中關注吉姆是因為他想看一個罪犯被逮個正著的后果,馬洛一開始認為帕特納號案件船員違反職責是不道德的,將吉姆視為罪犯。但他見過吉姆后發現吉姆身上的氣質明顯與另外兩個海員的氣質不同:“吉姆在外表上是那種給人良好印象的傻瓜。”[7]146從這里他開始對這個罪犯有了好感。之后吉姆講述了自己痛苦迷惑的經歷后,馬洛將吉姆視為同類并理解他的行為,導致他對吉姆做出不同的倫理判斷,認為吉姆善良且看起來不像是罪犯。正如他指出:“吉姆想盡辦法使我搖擺不定,我承認這一點……那原因很模糊,很沒意義。”[7]184馬洛對吉姆行為做出的闡釋判斷使其認為吉姆從道德上可以被接受,但馬洛又在之后與吉姆的交談中對其道德品行進行質疑。馬洛對吉姆的倫理判斷不斷反復,吉姆對自己內心的反復懺悔最終使馬洛接受了吉姆的行為,將其視為可憐的迷失青年,并幫他推薦工作重新開始生活。馬洛在知道吉姆在帕圖森成神又因布朗事件被消解神性后感慨道:“吉姆是一個無名的征服了名聲的人,在他崇高的自我主義的示意和召喚下掙脫了一份妒忌的愛的臂膀。”[7]445馬洛指出吉姆雖以生命踐行了承諾獲得了名聲,但他的死亡終是自私的,自我的出于對名譽的追求,吉姆最終也未能逃脫浪漫主義的束縛。馬洛的判斷在敘述中不斷變得模糊和不可靠。
馬洛對吉姆的判斷始終是含混的,康拉德以此消解了馬洛作為小說的重要講述者所代表著的絕對權威。敘述者馬洛對吉姆進行報道、闡釋和評價,讀者根據馬洛的報道認定馬洛是最能理解吉姆的人,然而“馬洛在探索關于吉姆的真相時,消解了二元對立,暗示了他解釋的不確定性”[11]202,但是馬洛對吉姆的闡釋和評價都是不確定的。直至小說的最后,吉姆死亡時馬洛也對此發出了疑問:“他滿意了沒有——相當滿意了沒有,現在,我想知道。”[7]445主要敘述者馬洛的不可靠敘述增加了小說的敘述張力。
布斯指出,在戲劇化的敘述者中,除了敘述代言人外,還有旁觀者[12]172,康拉德借助敘述者馬洛之口傳遞小說中旁觀者的判斷,在人物參與情節進程的同時形成對吉姆的多元倫理判斷。首先在船員的世界中,吉姆被認為是一個在危急關頭棄船逃跑的背信棄義的人。水手們對吉姆的闡釋判斷依據的是吉姆作為水手的實則行為,大部分水手沒見過吉姆不了解他,但他們聽說帕特納號事件后,便在茶余飯后指責他們行為的不道德。與此相對,也有可以理解吉姆行為的白人敘述者。作為吉姆案件陪審員之一的布萊利爾船長認為對吉姆的審判是一種折磨,他認為那些有道德瑕疵的審判者批判吉姆的行為極度虛偽,他想要出錢資助吉姆逃跑。布萊利爾認為當自己處在吉姆那樣的絕境,也不一定會做的比他好。布萊利爾深知作為一個船長必須要對船只負責,但是作為一個人他也有著對生的渴望,這是個體對生命的本能欲望。布萊利爾認為吉姆的選擇是對生命的渴望,可以被理解,所以他對吉姆的行為做出了正面的倫理判斷。馬洛的朋友斯坦因在聽說吉姆的經歷后表示:“我非常理解,他很浪漫。”[7]278斯坦因認為吉姆是一個浪漫的人,這種浪漫正好與斯坦因的追求相契合,于是他推薦吉姆去他在帕圖森的貿易站工作,給了吉姆重新開始的機會。
敘述者馬洛指出“帕圖森以傳說賦予吉姆以超自然的力量”[7]324,吉姆被帕圖森人視為神一般的人物。吉姆來到帕圖森后,他的事跡總是被神化,他一個人能背兩門炮上山,在與阿里警長斗爭中的勝利奠定了他在帕圖森人心目中的地位,村民們非常信賴他,將他的話奉為金科玉律。帕圖森人對吉姆的判斷是從神話他的行為開始,他們將吉姆利用滑輪運送炮彈的行為解釋成他具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頭人多拉明和他的兒子丹·瓦利斯也對這種力量深信不疑。海盜布朗在見到吉姆時就指出他是一個因為犯了錯而藏匿在這里的人,稱他和自己一樣都是侵略者,并且他在這里撈到了不少的好處,而吉姆嘴上所提到的責任與村民們無辜的生命都是借口,布朗認為吉姆跟自己是一路人,只是他運氣好,先到了這里,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吉姆的妻子珠寶與忠實的仆人唐·伊塔姆,在吉姆為了實現自己的承諾而堅決赴死的時候,他們更多的是不理解。珠寶在得知布朗的血腥復仇后,想讓吉姆立馬逃跑,但是吉姆并沒有聽她的,甚至吉姆在做決定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過珠寶的想法,對于唐·伊塔姆來說更是這樣。珠寶和唐·伊塔姆對吉姆是帶著怨恨的,在吉姆死后,被斯坦因收養的珠寶指責吉姆虛偽[7]393以傳達自己的怨氣。珠寶無法理解吉姆的行為,只能看到他的自私與無情。
敘述者馬洛在對吉姆故事的講述過程中,也承擔了轉述者的職能,轉述了其他旁觀者的看法,康拉德以此使敘述者的講述變成不可靠敘述,進而影響讀者的判斷。讀者通過敘述者對吉姆的判斷后對吉姆的認識是愈發模糊與不確定的。對于吉姆的棄船逃生,馬洛與白人世界都對他進行了不道德的倫理判斷,但同時馬洛、布萊利爾以及斯坦因又從對其行為的闡釋判斷上理解了他,正是這些不一致的敘事判斷影響了讀者在對吉姆的判斷。除此之外,布朗、珠兒、唐·伊塔姆對吉姆在闡釋判斷和倫理判斷上的否定,也使讀者陷入了對吉姆的復雜的思考,讀者在理解敘事時,首先要判斷人物的判斷究竟是否合理,在這闡釋判斷的基礎上做出倫理判斷,最終做出對小說敘事的審美判斷。
三、讀者的審美判斷:單向接受與雙向對話
《吉姆爺》的命名使讀者以對吉姆進行篤定認知的接受預期進入文本,作者康拉德借助主人公、敘述者、旁觀者對吉姆的多種評價混淆讀者的判斷,文本的不可靠敘述使讀者的闡釋判斷和倫理判斷錯綜復雜,從而突顯文本的審美藝術功能。費倫認為一部敘事作品中至少有兩個平行的敘述層次,即敘述者主導的故事層面和隱含作者主導的講述層面,援引費倫的敘述層次有利于厘清讀者的敘事判斷。《吉姆爺》的敘述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由敘述者馬洛講述關于吉姆與帕特納號和帕圖森故事的被講述層面,另一個是由康拉德作為隱含作者所建構和構想的層面,即講述馬洛講述的故事。《吉姆爺》的讀者在敘述者的講述中對吉姆進行單向的闡釋判斷和倫理判斷,在與康拉德的互動中對作品進行審美判斷。
在敘述者的講述中,吉姆的復述使讀者陷入一種不確定性判斷中。吉姆認為自己棄船而逃是無奈之舉,并且敘述者馬洛從闡釋判斷的基礎上對吉姆做出了可以諒解的倫理判斷,同時其他人物的議論分錯也使棄船的不道德變得不確定,本來是一件吉姆失責的事件,因為吉姆出于對生命原始欲望的沖動而陷入迷茫,讀者在此陷入了充滿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現代倫理[13]157的困惑中,查爾斯·泰勒指出現代性帶來了極端個人主義[14]1-10的隱憂。20 世紀末的英國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工業化發展帶來的貧富懸殊使階級矛盾和社會不平等現象頻現,資本主義的發展滋生個人主義,康拉德以吉姆棄船逃生的失責行為喻指英國社會迭出的不道德現象。此外,康拉德還通過多重敘述者對同一事件的不同判斷,從敘述藝術的層面指出吉姆并非極端的個人主義者,而是在個人主義和英國偉大傳統道德間踟躕的徘徊者,以引導讀者做出不同的倫理判斷。
康拉德在講述“帕特納號”的故事中消解了吉姆道德上的失誤,呈現出人性的相對性和道德模糊性,贏得讀者的同情與理解。小說中吉姆以及多位敘述者對吉姆行為進行的倫理判斷和闡釋判斷,影響了讀者對吉姆的判斷,正如費倫所說:“人物的闡釋判斷與倫理判斷相交織,讀者不同種類的判斷也自然會相互交融。”[15]27事實上,人物的闡釋判斷涉及的是吉姆的行為所涉及的道德責任,讀者需要對人物的判斷做出闡釋性的判斷,也就是說,讀者需要判斷吉姆對自我行動的辯護是否合理。
在這一事件中,康拉德在小說中有意引導讀者消解吉姆行為的不道德。首先,康拉德抹黑譴責吉姆跳船行為的事件評論者。指責吉姆棄船跳海行為的評論者是虛偽的法官和道聽途說的水手,康拉德在庭審現場使法官的無理與虛偽暴露無遺,而那些將此事當成茶余飯后的談資更是胡謅亂說。其次,康拉德借助馬洛將吉姆形象與其它兩個船員的形象比較,指出吉姆的長相并不像罪犯。讀者在對事件并未完全了解后,就被吉姆重復的話語迷惑認為他的棄船之舉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最后,在讀者了解了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道德敗壞和吉姆被誘惑的無意識行為后,康拉德再指出其實帕特納號最終并未沉沒,恐怖的海難與八百朝圣者命喪大海的局面并未出現,吉姆的行為并未造成大的災難,而這一切都與獨自站在審判席上可憐又無辜的吉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吉姆與罪犯的格格不入,引發了讀者的同情與憐憫,使讀者對吉姆的行為做出可以理解的闡釋判斷。
在“布朗事件”中,康拉德暗示讀者對吉姆慷慨赴死的崇高性產生懷疑。吉姆直面承諾死在多拉明槍下,他認為這是自己取得非凡成功的時刻。但康拉德通過馬洛之口消解吉姆為諾言而死的英雄性,馬洛在吉姆英勇赴死后說道:“吉姆是在他崇高的自我主義的示意和召喚下掙脫了一份妒忌的愛的臂膀。”[7]445這句話直指吉姆的個人主義。吉姆的妻子珠寶和他忠實的仆人唐·伊塔姆面對吉姆絲毫不顧及他們感受的自私感到無盡的痛苦,帕圖森百姓也對他生出無盡的失望,吉姆爺的神性光輝逐漸暗淡,康拉斯似乎有意在消解吉姆為承諾赴死的崇高性,暗示是吉姆的精神失落使他最終走向直面死亡。此時對吉姆來講是唯一可行的路,而這條路無關道德的崇高性與英雄主義的實現。吉姆直面死亡并不是為民族或群體做出的巨大犧牲,而是以犧牲的姿態踐行自己的承諾,成為個人主義英雄,吉姆試圖以此去彌補自己在道德的缺陷,以實現精神世界的完滿。
康拉德通過馬洛對吉姆的不確定判斷,引導讀者參與文本的接受,在對中心事件進行闡釋判斷、倫理判斷,感受20 世紀末英國社會道德困境的同時,接受小說由不確定性帶來的藝術張力的審美召喚。康拉德似乎在向讀者暗示,吉姆既不是一個道德上完滿的英雄,也不是一個十足的壞人,他身上的缺陷具有普遍性。吉姆認為自己的慷慨赴死能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拯救,實現人生價值,但馬洛對此提出了疑惑,這也是康拉德在小說中提出的疑問。康拉德在小說中借斯坦因之口說道:“人很神奇,但不是杰作。”可以說,康拉德無意塑造一個英雄形象,而是通過彰顯人性的弱點,呈現人性的復雜性及道德的相對性。這種復雜性在“吉姆爺”的命名上就有所體現,有學者指出,“神”隱喻著一種神性的光環[16]163,代表著英雄和浪漫主義,而“吉姆”隱喻了一個普通人。實際上這種復雜性也與康拉德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質疑有關,在19 世紀理性與科學大行其道的情況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同時康拉德也繼承了浪漫主義精神傳統,因此在康拉德的作品中,總是呈現出理性主義與浪漫理想的矛盾交織,這種交織呈現出來的不確定性正是康拉德對19 世紀盛行的理性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思。文明社會的道德法則戕害了人性的自由,強者和完人的社會理想毒害了像吉姆這樣看重名譽的年輕人,使他們無法正視自己的道德缺陷。正是出于這樣的敘述目的,康拉德通過多位敘述者的不同講述,使讀者陷入了多維關系網,以此展現了生活世界的多層次性,利用吉姆對自己行為的判斷與各位敘述者站在不同倫理取位上對吉姆做出的判斷,使讀者對吉姆的倫理判斷陷入一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的彰顯,使讀者更關注吉姆對人生的體驗。正像昆德拉曾提到的:“小說在于提供了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對性和道德模糊的力量。”[13]160正是小說中這種偉大的力量引導讀者去關注人物的生存境遇與情感價值,體會人應遵循的道德原則的“例外情形”[13]4,觸摸個人的生命感覺,而不是去尋求一種善惡分明的道德原則,這也是小說書寫的重要取向。
結語
康拉德在《吉姆爺》中通過多種敘事聲音進行繁復的敘事判斷,完成了小說敘事對倫理、形式和審美的要求,實現了自己和敘述者的雙重目的。在故事層面讓讀者陷入不確定性與確定性的張力與活力中,完成對文本的接受,同時在講述層面讀者可以充分參與文本獲得愉悅的閱讀體驗。馬洛對吉姆的判斷,影響了讀者對康拉德敘述目的的判斷,讀者由此對吉姆的行為進行反思,做出自己的倫理判斷,這樣康拉德與讀者建立的關系就不是一個單向、簡單直接的給予和判斷關系,而是讀者在馬洛的講述中不斷對吉姆的行動進行闡釋判斷、倫理判斷。康拉德邀請讀者與他合作理解馬洛的講述,讀者只有在做出闡釋、倫理判斷之后才能實現對小說的審美判斷。由此,讀者會反思康拉德對整部小說的設計,重審敘述者和小說中諸人物對吉姆的判斷,進而對小說的敘事質量做出積極的審美判斷,正如費倫指出:“同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相比較,使讀者參與同解決敘事形式問題緊密相連的復雜的倫理判斷,是更大的成功。”[15]30同時“吉姆以充滿負罪感的反英雄形象,使《吉姆爺》成為現代小說的誕生之作。”[17]29康拉德以多種敘事聲音的參與充分調動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在思考人性的同時實現豐富了小說的審美意蘊,使之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經典之作。
詹姆斯·費倫提出敘事判斷后,并未指出明確的實踐路徑,研究者在應用的過程中,常將敘述者、人物以及讀者的闡釋、倫理、審美判斷融為一體。本文嘗試分開論述《吉姆爺》中人物的闡釋判斷以及敘述者的倫理判斷,同時在讀者的審美判斷中論述諸種敘事判斷的關系,以更好地厘清《吉姆爺》的現代主義文學特色,為敘事判斷理論提供了一種更清晰的闡釋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