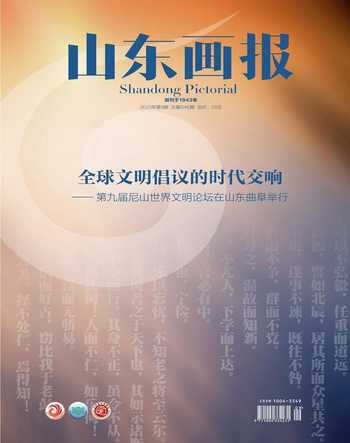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完善漢籍存藏,促進文明互鑒
張媛媛 李瀟雨

“漢籍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布,是域外文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主和積極的選擇,是多元文化視角下人文交流互鑒的直接體現。合璧工程著眼于保存歷史,見證文明,強調世界眼光和中國關懷,既可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促進國際漢學研究的創新性發展,也可從域外文明對中華文化的自主選擇中發掘世界文明的共通性,實現中華文化價值的現代轉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交匯繁榮。”
這是全球漢籍合璧工程首席專家鄭杰文在第九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講話。漢籍合璧工程的意義重大而深遠,他和團隊在做的事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已經年逾古稀的鄭杰文,為了漢籍合璧工程,常常四處奔波。從尼山歸來的他,因為身體有恙,住進了醫院。在病房里,他依然記掛著工作,電話不斷。
鄭杰文與漢籍合璧的故事要追溯到十三四年前。那時以文史見長的山東大學想在教育部的十年規劃(2010-2020)中有所貢獻,就召集了專家學者開會共議。“我們決定做‘子’部書的研究,初衷很簡單,就是認為學界缺少這方面的研究。”令他想不到的是,這僅僅是個開始,更深入的研究還在等著他。
2010年起,山東大學開始實施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對境內外現存子部漢籍開展系統整理研究。2013年11月,基于子海項目的成功經驗,山東大學提出“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的設想,將漢籍整理、研究的范圍,由子部擴大到經、史、子、集四部;將合作對象由東亞擴展至全球,全面實現中國大陸缺藏漢籍珍本的再生性回流。
雖然漢籍合璧工程的設想早在2013年就被提出,但畢竟“茲事體大”,需要多方的支持與配合。“經前期一系列論證和規劃,2018年11月,我們正式啟動國家重點文化工程全球漢籍合璧工程。”
目前,漢籍合璧工程已調查境外1988家藏書機構,正在開展其中554家藏書機構所藏漢籍的編目工作,已目驗編纂36萬部境外中華古籍的版本目錄。鄭文杰和團隊的工作并不是簡單的幾個數字能衡量的。“我們的編目工作很煩瑣、很復雜,有些藏書機構編目不仔細,只是記錄了何時何地收藏了這本書,并沒有記錄書的實際年代與內容。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只核對他們的編目找出我們沒有的,還需要做一些更細致的工作。” 一些海外藏書機構對日均借閱數量有限制,團隊成員經常一天往來奔波幾個小時、多次換乘公共交通工具,才能看到四五種漢籍。而且國外各藏書機構的影印費用也不一,個別十分昂貴。
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團隊從編纂的境外中華古籍版本目錄中發現了1900多種中國大陸缺藏的珍稀漢籍,并復制回歸1600余種。”但編目及回歸并不是他們工作的終點,他們還需進一步精選學術價值高、內容完整、學界亟須的古籍,通過標點、校勘等形式開展整理工作,對境外中華古籍的存藏、流布及影響開展學術研究。目前已有140種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境外漢籍正在或完成了整理工作。
2022年秋,在“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山東展區,“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相關成果吸引不少參觀者駐足。從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發現的系統總結16世紀初中國冶鐵技術的《鐵冶志》孤本,到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清代舟山詩人陳慶槐所著《借樹山房詩草》稿本;從俄羅斯藏宋代刻本《淮南鴻烈解》,到英國所藏記錄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福次咸詩草》稿本……這些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古籍,屬于中國大陸著錄未見或缺藏的珍貴版本和品種,在全球合璧工程團隊的努力下,回歸到它們的誕生地,為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提供助力。
漢籍流散境外,唯有“合璧”,才能揭開中華文化的“整幅畫卷”。盡管困難重重,但鄭杰文及其團隊向前的腳步從未停止。保存歷史、見證文明,他們任重而道遠。(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