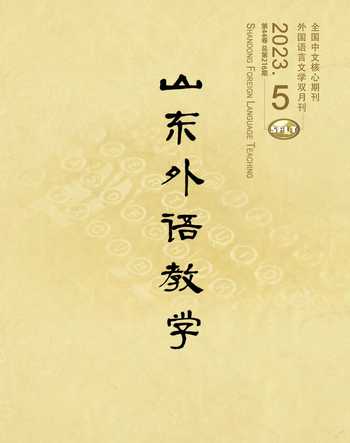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現狀、趨勢與前沿
羅少茜 荀慧



[摘要] 本研究以文獻計量軟件Citespace為研究工具,對近20年(2001—2021)發表于CNKI和WoS核心合集中的相關文獻進行量化分析和可視化呈現,描述國內外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現狀和焦點,同時追蹤發展趨勢,捕捉研究前沿。分析結果顯示,國內外發表均呈現逐年增長勢態,國外研究覆蓋范圍較廣、內容較多,可以為國內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提供有效借鑒。此外,該領域的研究表現出任務類型日趨多樣,任務相關變量逐漸豐富,研究方法呈現跨領域、跨學科交叉,研究對象群體廣泛四個層面上的發展趨勢。通過分析,本文提出未來國內研究可以關注綜合性任務、計算機線上任務、任務模態、任務重復、任務投入度、低齡學習者群體、個體差異等新問題,開展更多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創新性研究。
[關鍵詞] 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文獻計量;趨勢;前沿
[中圖分類號] H319[文獻標識碼] A[文獻編號] 1002-2643(2023)05-0039-10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Research at Home andAbroad(2001-2021): Current Status, Trends and New Frontiers[JZ)]
LUO Shaoqian XUN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TBLL) published in CNKI and Wo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2001-2021). By using Citespace, the bibliometric software, this study outline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indicated the trends and new emerging topics in this field. It concludes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ublished in this field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almost year by year at home and abroad. Four developmental trends are detected: the diversity of task types, the variation of task-related variables,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extensiveness of research participants. New frontiers driven by each trend are also identified, including integrated tasks, computer-mediated tasks, task modality, task repetition, task engagement, young learner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end, we call for the researchers at home to carry out more innovative studies with localized characteristics in TBLL.
Key words: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bibliometrics; trends; frontiers
1.引言
近二十年來,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理論和實證成果頗豐,研究熱度日益提升。根據Gilabert等(2016)的觀點,學界關注任務語言學習領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1)任務可以幫助學習者注意到語言的形式和意義,并將其儲存在記憶中,從而促進其中介語體系的發展和完善;(2)通過任務的設計,我們可以引導學習者發展自身語言表現的特定維度,促進他們語言能力的均衡發展。因此,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紛紛從與任務相關的不同角度出發,試圖發掘二語學習者的語言發展潛勢(邢加新、羅少茜,2016)。然而,由于任務本身涉及的因素復雜,研究角度繁多,所以有必要對該領域的研究進行全面梳理,以窺全貌。
為了準確描述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現狀和焦點,追蹤發展趨勢、捕捉研究前沿,本文以文獻計量軟件Citespace為研究工具,對近20年來(2001—2021)發表于中國知網(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WoS(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相關文獻進行量化分析和可視化呈現,以期為國內該領域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提供借鑒,從而開展更多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創新性研究。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兩個問題:(1)近20年來,國內外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呈現什么樣的態勢?研究焦點包括哪些內容?(2)該領域國內外研究的發展趨勢如何?有哪些研究前沿問題?
2.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有兩處,國內期刊來自CNKI,國外期刊來自WoS核心庫。通過CNKI庫內檢索發現,國內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約起始于2001年。為掌握國內研究全貌,我們檢索了CNKI數據庫內發表于2001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期刊文獻, 來源類型包含北大核心、CSSCI、EI、SCI和CSCD。搜索題目關鍵詞為“任務”的中文期刊文獻,學科選擇“外國語言文字”。經過標準化、去重處理以及后期人工閱讀篩選,剔除有關任務型教學理論和書評等非實證研究類文章,最終獲得文獻116篇。同樣,我們檢索了同時段WoS核心庫收錄的期刊文章,使用“Task”為題目關鍵詞,研究領域設置為“Linguistics”,文獻類型限定為“研究論文”,文獻語種選擇“英語”。經過手動剔除明顯不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獻,最終生成有效文獻1576篇,并將上述兩組文獻分別導入Citespace軟件運行處理。文本處理關鍵詞來源參數選擇為 “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DE)”,關鍵詞類型選擇“Noun Phrases”,其余為默認參數。
3.研究結果與分析
以下將會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梳理:國內外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發文量、高頻被引文獻、高頻關鍵詞共現、高頻關鍵詞突現年份、關鍵詞聚類。筆者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綜述梳理,歸納該領域研究的發展趨勢以及最新的學術增長點。
3.1 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現狀
總體來看,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發文數量大體呈逐年遞增的趨勢(見圖1),國內外學者對該領域的關注和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從共引文獻的角度看,盡管國內的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起步較晚,發展緩慢,但在一定程度仍順應了國際上的發展趨勢。根據國內外共引次數排列前5的文獻統計結果,以Robinson(2001)為代表的“認知假說(Cognition Hypothesis)”和“任務復雜性三角框架模型(Triadic Framework of Task Complexity)”對國內外學界影響較大,已發表文獻有較多的共引(見表1)。另外,雖然共引文獻各不相同,國內為Foster & Skehan(1996),國外為Yuan & Ellis(2003),但可以看出任務準備也是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熱衷探討的話題之一。
在Citespace得出的關鍵詞頻次列表中合并相同的詞,并剔除二語、外語、前人研究等相對較寬泛的高頻詞,表2歸納了國內外排列前十位的高頻關鍵詞。通過對高頻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表3得出了國內外各五組關鍵詞聚類,每組各四個關鍵詞。
3.2 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焦點
基于以上數據分析結果,結合相應文獻梳理,可以總結出:近20年來,國內外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三個方面:任務復雜度、任務準備以及任務表現的測量。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在Citespace數據分析結果中,詞匯習得相關研究呈現為焦點,但通過文獻綜述發現,雖然很多詞匯研究在題目、關鍵詞和摘要中都涉及“任務”相關的概念術語(如任務難度、任務類型),但英漢匹配、單詞聽寫、造句等活動在這類研究中被視為“任務”,與本研究的研究視閾不符,因此將詞匯附帶習得、投入量假設焦點予以剔除。
3.2.1 任務復雜度
以Skehan為代表的“有限注意力模型”(1998;2009)和以Robinson為代表的“認知假設”(2001)兩種觀點間的爭議方興未艾,是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熱點問題(陶娜、王穎,2022)。據統計,國內的任務復雜度相關研究有4篇關注口語表現,7篇關注寫作表現(其中2020至2021年占6篇)。因此,任務復雜度對寫作表現的影響是近年來國內學者研究的重點。國內研究涉及任務復雜度與任務難度、工作記憶容量的交互效應,以及與其他理論視角的結合,包括復雜動態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靳紅玉、王同順,2021)。從任務復雜度的調節上看,國內學者一般基于Robinson(2001)的“三角框架模型”,選擇一個或兩個變量調節任務的認知復雜程度。其中,探討最多的是“+/-元素數量”,其次為“+/-推理需求”。還有部分研究根據Robinson(2001)的模型制定了測量工具,從多個維度具體評估了不同任務的復雜度(如張煜杰、蔣景陽,2020)。相比之下,國外任務復雜度的研究數量較為龐大。一方面,國外研究會調節更多的任務復雜度變量;另一方面,它們還積極探究復雜度與其他關鍵概念的交互效應,包括任務重復、任務驅動型動機、反饋效能等(Khatib & Farahanynia,2020)。另外,與國內研究對象全部集中在高校學生群體相比,國外研究的參與者在年齡、語言水平、語言學習背景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和多樣性。
3.2.2 任務準備
根據Citespace的分析結果,任務準備關鍵詞突現于2018年,其熱度延續至今。在準備類型的選擇上,國內研究關注任務前的策略性準備,包括教師對語言結構和語言點的講解、學生單人或小組形式的自行準備(如劉兵、尉瀟,2019)。研究者還探究了準備活動的相關因素對學習者二語表現的影響,例如,有/無準備,準備時長,準備行為的差異(如戚焱、吳鈺迪,2020)。相比之下,國外研究者探究的策略性準備條件較為全面和豐富,包含教師引導下的對子準備、小組準備,以及學生自行單人準備、對子準備、小組準備等多種形式(如Aubrey et al.,2020)。他們還積極探究任務預演以及任務重復對二語表現的獨特作用,并且對有壓力和無壓力的在線準備探討頗多(如Panahzadeh & Asadi,2019)。值得指出的是,部分國外研究依托多模態在線交際技術,探究了二語線上文字聊天、3D多用戶虛擬環境等不同交際語境下,任務準備對二語表現的影響(如Chen,2020)。
3.2.3 任務表現的測量
任務完成的成功與否、效果如何,關鍵要看學習者的任務表現。復雜度、準確度、流利度是衡量和評估學習者任務表現的三個重要維度(Skehan,1998)。研究者不但根據自身對各個構念的理解,制定并完善測量方法和度量指標,而且還積極開發相應測量維度的自動分析軟件,如“Coh-Metrix”(McNamara et al.,2014)和“二語句法復雜度分析器”(Lu,2010),這有效助力了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深入和發展。除了從語言形式的層面測量任務表現,國外研究還關注意義層面的評估,例如通過分析“觀點單位(idea units)”來測量任務表現的命題復雜度(Vasylets & Marín,2021),對比母語和非母語者任務表現的功能與交際適恰性、話語及語用特征等(Nuzzo & Bove,2020)。此外,國外研究還聚焦語言表現之外的其他任務表現,包括手勢使用及其功能、任務交際中的一語使用情況、注意力和關注焦點,以及語言形式片段(language-related episodes)等(如Xu & Fan,2021)。鑒于此,未來研究在完善和開發語言表現測量指標和方法的基礎上,還可以聚焦在功能、意義層面對語言表現不同構念的評估,以及任務完成過程中的其他表現。
3.3 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趨勢與前沿
根據Citespace的數據分析結果,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任務類型、任務相關變量、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四個方面。在綜述相關文獻的基礎上,下文將闡述這些方面的發展趨勢,并指出不同趨勢推動下的研究前沿。
3.3.1 任務類型日趨多樣,綜合性、計算機線上任務成為新焦點
通過總結已有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中的具體任務,我們發現隨著二語習得領域關注點的變化,任務的具體類型逐漸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傳統的任務類型中,敘事任務是探索最多的任務類型(Hu,2018)。隨著交際性、互動性和真實性的外語教學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信息差任務和拼圖任務等交際任務已成為專家學者樂于探討的任務類型。與此同時,學界開始關注真實任務的復雜多樣性,并意識到整合多種語言技能為學習者語言發展提供的潛在機會。研究表明,在過去的十年里,綜合性任務已然成為新時期二語習得研究中的重要任務類型(Zhang et al.,2022)。同時,科技的發展不僅變革了語言學習及教學方式,也為二語任務類型的開拓創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以計算機為媒介的線上任務通過多模態模擬共現的形式來呈現任務相關元素,徹底打破了傳統任務的媒介局限,也是近年來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領域頗具發展前景的突現關鍵詞(Tang,2020)。
3.3.2 任務相關變量逐漸豐富,任務模態、任務重復、任務投入度值得探究
任務相關變量的全面化極大豐富了該領域的研究內容,不僅包括任務內部的橫向層面,還拓展到了任務與任務間的縱向層面。除了上文所總結的焦點關鍵詞之外,國外研究還出現了相對較新的任務名詞組合。這些組合其中一部分是有關相同任務、相似任務、不同任務之間的組合排序問題,如任務轉換(task switching); 另一部分涉及關鍵概念的重新闡釋,如任務就緒度(task readiness)。其中,任務模態(task modality)、任務重復(task repetition)和任務投入度(task engagement)是近年來本領域頗具潛力的前沿突現關鍵詞,值得國內外學者深入探究。
首先,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需要聚焦任務模態的差異性。當今世界具有全新的、快速變化著的技術空間,全球化進程更加速了這種技術空間的變化。這些技術能夠允許人們參與全新的和更令人興奮的交際活動,它打破時間、空間和身份維度的局限,豐富了信息傳遞和人類交際的模態。因此,任務模態的呈現形式更加靈活多樣,包括多種模態元素的組合編碼。任務的產出模態也不僅是口語(對話和獨白)和書面語兩種傳統產出模式,還包括線上文字聊天、線上語音聊天、PPT制作與匯報展示等。隨著技術的發展和世界的變化,我們需要不斷審視領域內的理論框架,并及時做出調整,才能適應在實體教室、網絡平臺和現實世界學習語言的實際情況。不同的任務模態是否會影響任務的認知復雜程度,從而改變其基本概念的建構,包括Skehan(1998;2009)和Robinson(2001)的相關假設; 學習者在不同模態下完成任務是否會經歷不同的心理過程(既涉及認知層面,又涉及情感態度層面),從而進一步影響他們的語言表現;如何對不同模態下的任務進行排列組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引導學生“聚焦形式”等,上述問題都有待學者進行深入探究。
其次,任務重復對二語表現的影響也是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領域的前沿問題。Bygate于2018年出版的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Task Repetition一書引起了學界探究任務重復的興趣。研究結果表明,學習者首先關注任務完成過程中的意義傳達,隨后在重復任務中,才會將重點轉移到監測和選擇恰當語言形式的層面。因此,任務重復能幫助學習者將注意力轉移到語言的形式上,加快語言知識和技能的程序化和自動化進程(Lambert et al.,2017)。基于其有效性結論,學界可以將任務重復探討的關注點從“是否需要”轉移到“在什么條件下進行”,不僅可以聚焦任務重復的具體操作方式,如重復的間隔時長、重復的次數、不同任務搭配的重復模式等;還可以探究任務重復與其他介入手段搭配組合對學習者任務表現的影響,比如重復之前或之后介入教師顯性教學、重復中教師不同形式的糾正性反饋、重復后的產出轉寫等。需要指出的是,相關研究必須在方法描述中清楚區別任務重復和任務預演兩個關鍵概念,其區別在于學習者是否被告知會進行重復任務(Bui & Yu,2021)。另外,該領域研究最終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個關鍵性問題,那就是任務重復的效果能否轉移并擴展到新任務中,而目前能夠回答該問題的實證研究較為少見。由于任務重復涉及一個或多個任務的復現,所以學習者對重復完成任務的態度、積極性和投入程度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Bui & Yu,2021)。
最后,任務投入度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前沿關鍵詞。投入度越來越被認為是學習者成功完成任務的關鍵因素之一,它可以從認知、行為、社會、情感四個維度進行解讀。認知投入度表現為學習者的內在努力,如在互動中主動提問問題等;行為層面則體現在完成任務的時長和產出數量上;社會投入度是學生參與互動的意愿程度,可以通過反向溝通或者互動關系體現;情感投入則呈現學生在任務中的主觀體驗(Lambert et al.,2017)。由此看出,任務投入是一個多維、復雜和動態的構念,涉及因素較多。有關任務投入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嘗試回答有哪些任務特征,在什么情況下會讓學習者保持、增加,抑或減少、放棄投入等問題;另一方面還可以追蹤學習者投入度的縱向動態發展過程(Hiver et al.,2021),以及探討何種干預措施將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任務投入度等問題,例如糾正性反饋、任務重復等(Nazemi & Rezvani,2019)。
3.3.3 研究方法呈現跨領域交叉,神經成像技術的應用潛力巨大
在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領域中,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使用日益多樣化。研究范式通常涉及聚焦一個或多個任務相關變量,以探究其對學習者在復雜度、準確度、流利度各個構念上的任務表現的影響。數據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相關性分析、回歸分析、差異顯著性分析、聚類分析和元分析等(如Pang & Skehan,2021)。為了提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質性研究方法在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結構式訪談、焦點小組訪談、刺激性回憶和有聲思維等。此外,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還積極尋求與其他領域的交叉,出現了諸如語篇分析法、基于語料庫的分析法、鍵盤追蹤和眼動等方法。雖然目前神經成像技術(如核磁共振)在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中的應用較少,但鑒于其在二語習得其他領域的表現,利用核磁共振技術觀察學習者在執行任務過程中的認知心理活動具有巨大潛力(Révész,2021)。總之,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已經超越了學科固有的研究范式,為解決領域內具體的研究問題,積極尋求和嘗試最優化和最科學化的研究方法。
3.3.4 研究對象群體廣泛,語言障礙人士、低齡兒童、個體差異亟待關注
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參與者涉及范圍廣泛,包括一語、二語和外語學習者,同時也包括雙語及多語使用群體。在年齡層面上,研究對象涵蓋了成年人、大學生、中學生、低齡學習者、幼兒等不同年齡階段。基于對國外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的分析,我們發現國外研究者還借助任務,積極探尋能夠恢復帕金森、兒童失語癥、發育性失讀癥等患者生理語言功能的相關途徑。另外,自2018年以來,低齡學習者作為國外研究的突現關鍵詞,在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中持續受到關注,成為近年來備受重視的研究對象群體。然而,在國內研究中,對上述群體的研究尚屬少見。隨著二語習得領域對個體差異關注的逐漸增加,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亦呈現出關注學習者個體因素及其獨特發展潛力的趨勢。研究者試圖解析個體差異如何可能導致不同的任務表現,進而產生不同的語言發展潛力,以及個體差異可能如何影響任務相關變量的有效性等問題。國外研究中涉及的關鍵詞包括:學習者的任務體驗、任務表現檔案、個體創造力、學習動機等(如Pang & Skehan,2021)。除了進一步探究上述關鍵詞,國內學者還可以聚焦學習者在任務完成過程中的執行力、負面情緒、二語使用焦慮、對語言模糊的容忍度等問題。
4.結論
任務型語言教學的理論基礎具有多元性,涉及教育學、心理語言學、教育技術學與二語習得等多個學科領域,呈現出明顯的跨學科特點。回顧過去二十年,在國內外學術領域,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主要立足于認知心理學視角,積極探索與其他新學科、新視角的交叉融合,不斷拓展研究范圍,至今仍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本文基于對近二十年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量化分析,同時進行相應的文獻綜述,以期彌補現有研究方法所導致的分析結論具有寬泛性、一般性的缺陷,進一步明確領域內亟待解決的具體研究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鑒于本研究旨在探討任務型語言學習實證研究,因此在文獻檢索階段,盡量剔除了任務型教學的相關文獻。然而,教學研究與學習研究本身實際上是難以嚴格割裂的,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因此,未來研究可以著眼于任務型語言教學和學習研究的整體發展趨勢,探討更多尚待開發的前沿課題。
參考文獻
[1]Aubrey, S., C. Lambert & P. Leeming. The impact of first as opposed to second language pre-task planning on the content of problem-solving task performance[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20, 26 (5): 867-892.
[2]Bui, G. & R. Yu. Differentiating task repetition from task rehearsal[A]. In N. Sudharshana & L. Mukhopadhyay (eds.).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C].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1. 119-137.
[3]Bygate, M.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Task Repetition[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8.
[4]Chen, J. C. The effects of pre-task planning on EFL learners oral performance in a 3D multi-user virtual environment[J]. ReCALL, 2020, 32 (3): 232-249.
[5]Foster, P. & P. Skehan. The influence of planning and task type on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6, 18 (3): 299-323.
[6]Gilabert, R., R. Manchón & O. Vasylets. Mode i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BLT research: Advancing research agendas[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6, 36: 117-135.
[7]Hiver, P., H. A. Al-Hoorie, P. J. Vitta & J. Wu. Engagement in language learn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20 year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definitions[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21. https://doi.org/10.1177%2F13621688211001289.[2022-10-04]
[8]Hu, X. Effects of task type, task-type re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criteria on L2 oral production[A]. In M. Bygate (eds.).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Task Repeti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8. 143-169.
[9]Khatib, M. & M. Farahanynia. Planning conditions (strategic planning, task repetition, and joint planning), cognitive task complexity, and task type: Effects on L2 oral performance[J]. System, 2020, 93: 1-12.
[10]Lambert, C., J. Kormos & D. Minn. Task repet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cessing[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17, 39 (1): 167-196.
[11]Lambert, C., J. Philp & S. Nakamura. Learner-generated content and engagement in second language task performance[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7, 21 (6): 665-680.
[12]Laufer, B. & J. Hulstij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construct of task-induced involvement[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 22 (1): 1-26.
[13]Lu, X. Automatic analysis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10, 15 (4): 474-496.
[14]McNamara, D. S., C. A. Graesser, M. P. McCarthy & Z. Cai. Automated Evaluation of Text and Discourse with Coh-Metrix[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Nazemi, M. & E. Rezvani. Effects of task familiarity and task repetition on Iranian EFL learners engagement in L2 oral performance[J].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9, 1 (4): 45-56.
[16]Nuzzo, E. & G. Bove. Assessing functional adequacy across tasks: A comparison of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written texts[J]. EuroAmeric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s, 2020, 7 (2): 9-27.
[17]Panahzadeh, V. & B. Asadi. On the impacts of pressured vs. unpressured on-line task planning on EFL students oral production in classroom and testing contexts[J]. Eur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9, 5 (3): 341-352.
[18]Pang, F. & P. Skehan. Performance profiles on second language speaking tasks[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1, 105 (1): 371-390.
[19]Prior, A. & B. MacWhinney. A bilingual advantage in task switching[J]. 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10, 13 (2): 253-262.
[20]Révész, A. Exploring task-based cognitive processes: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and challenges[J]. TASK, 2021, 1 (2): 266-288.
[21]Robinson, P. Task complexity, task difficulty, and task production: Exploring interactions in a componential framework[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 22 (1): 27-57.
[22]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Skehan, P. Modeling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complexity, accuracy, fluency, and lexis[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9, 30 (4): 510-532.
[24]Skehan, P. & P. Foster. The influence of task structure and processing conditions on narrative retellings[J]. Language Learning, 1999, 49 (1): 93-120.
[25]Tang, X. Task-based interactional sequences in different modalit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computer-mediated written chat and face-to-face oral chat[J]. Applied Pragmatics, 2020, 2 (2): 174-198.
[26]Vasylets, O. & J. Marín. The effects of working memory and L2 proficiency on L2 writing[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21, 52: 1-14.
[27]Xu, J. & Y. Fan. Task complexity, L2 proficiency and EFL learners L1 use in task-based peer interaction[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21.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11004633.[2022-10-03]
[28]Yuan, F. Y. & R. Ellis. The effects of pre-task planning and on-line planning on fluency, complexity and accuracy in L2 monologic oral production[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3, 24 (1): 1-27.
[29]Zhang, P., J. Fan & W. Jia. Assessing L2 integrated writing self-efficacy: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J]. Assessing Writing, 2022, 54: 1-18.
[30]黃燕. 檢驗“投入量假設”的實證研究——閱讀任務對中國學生詞匯記憶的影響[J]. 現代外語, 2004, (4): 386-394.
[31]靳紅玉, 王同順. 任務復雜度、工作記憶容量與二語寫作表現——學習者能動性的作用[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21, (3): 102-113.
[32]劉兵, 尉瀟. 任務組織方式對在線英語寫作任務準備和產出的影響[J]. 中國外語, 2019, (6): 67-74.
[33]戚焱, 吳鈺迪. 準備時間及任務條理性對中國英語學習者口語詞塊產出的影[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20, (4): 1-9.
[34]陶娜, 王穎. 外語寫作任務復雜度對語言形式注意和修改效果的研究[J]. 山東外語教學, 2022, (5): 67-76.
[35]吳旭東. 學習任務能影響詞匯附帶習得嗎?——“投入量假設”再探[J]. 外語教學研究, 2010, (2): 109-116.
[36]邢加新, 羅少茜. 任務復雜度對中國英語學習者語言產出影響的元分析研究[J]. 現代外語, 2016, (4): 528-538.
[37]張煜杰, 蔣景陽. 任務復雜度對二語寫作復雜度和準確度的影響[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20, (4): 49-54.
(責任編輯:孫炬)
收稿日期:2022-10-29;修改稿,2023-08-25;本刊修訂,2023-09-16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科技創新2030-“腦科學與類腦研究”重大項目“中國學齡兒童腦智發育隊列研究”(項目編號:2021ZD020050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羅少茜,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任務型語言教學、語言測試、二語習得。電子郵箱:sqluosheila@bnu.edu.cn。
荀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任務型語言教學、二語習得。電子郵箱:xunhuimillie@163.com。
引用信息:羅少茜,荀慧.任務型語言學習研究的現狀、趨勢與前沿[J].山東外語教學,2023,(5):3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