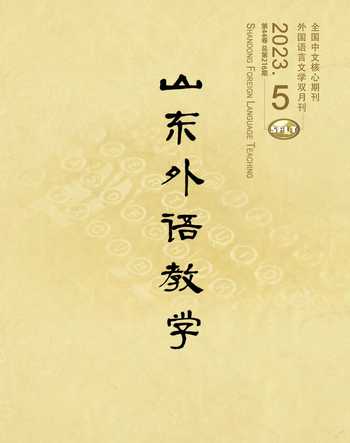拉各斯的誘惑
杜志卿 張燕
[摘要] 賽普瑞安·艾克文西的長篇代表作《城市中的人們》和《賈古娃·娜娜》把尼日利亞舊都拉各斯描寫成既是自由、平等和充滿機遇的理想之地,又是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墮落之地,生動體現了作家對拉各斯愛恨交加的矛盾情感。兩部小說的城市書寫雖延續了歐洲城市小說中城鄉對立的主題,但對鄉村和宗教的救贖力量持保留態度。在作家眼中,城市里的人們追逐物欲和肉欲滿足,在墮落中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即使傳統的鄉村生活和來自西方的基督教也無法為他們提供救贖力量。艾氏對城市的矛盾情感反映了他對獨立后尼日利亞何去何從的迷茫以及男性至上的性別歧視意識。
[關鍵詞] 艾克文西;《城市中的人們》;《賈古娃·娜娜》;拉各斯;城市書寫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獻編號] 1002-2643(2023)05-0080-10
The Allure of Lagos: Urban Narrative in C. Ekwensis People of theCity and Jagua Nana[JZ)]
DU Zhiqing1,2 ZHANG Yan1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1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age of the city Lagos in Cyprian Ekwensis best-known novels, People of the City and Jagua Nana. These two works depict Nigerias former metropolis Lagos both as a dreamland full of equality, freedom and opportunities, and as a corrupt place shorn of morality, which impressively reflects Ekwensis ambivalent love-hatred attitude toward the city.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Ekwensis depiction of Lagos in the two novels extends the motif of city-country dichotomy prevalent in European city writings. However,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authors of city writings, Ekwensi is pessimistic about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the country and religion. In his view, people in the city have degenerated in the satiation of their desires for sex and material profits so much that neither the traditional country life nor the Western Christian belief can be their salvation. Ekwensis ambivalence in his urban narrative reveals his sexism, as well as his bewilderment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newly independent Nigeria.
Key words: C. Ekwensi; People of the City; Jagua Nana; Lagos; urban narrative
1.引言
早期尼日利亞的英語小說常把故事背景設置在前殖民時期或殖民初期的鄉村,鮮有對與奴隸貿易和歐洲殖民相伴相生的現代城市進行書寫。圖圖奧拉(A. Tutuola)的《棕櫚酒酒徒》(The Palm-Wine Drinkard,1952)和《我在鬼林中的生活》(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1954)、阿契貝(C. Achebe)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和《神箭》(Arrow of God,1964)以及阿馬迪(E. Amadi)的《妃子》(The Concubine,1966)莫不如此。賽普瑞安·艾克文西(Cyprian Ekwensi,1921-2007)被譽為尼日利亞“城市小說之父”,是最早把筆鋒對準城市生活的尼日利亞作家。雖然他早期不少作品將背景設置在鄉村,但其重要作品如《城市中的人們》(People of the City,1954)(以下簡稱《城》)、《賈古娃·娜娜》(Jagua Nana,1961)(以下簡稱《賈》)、《伊斯卡》(Iska,1966)以及《賈古娃·娜娜的女兒》(Jagua Nanas Daughter,1986)等都把故事背景設置在尼日利亞舊都拉各斯(Lagos)。與阿契貝及其他作家不同,艾克文西的自我定位是不為“藝術而藝術”的通俗小說家。他聲稱,“在我們的社會中,作家不可能為藝術而寫作,因為有許多刺痛良心的問題存在”(qtd. in Dogon-Daji, 2016:10392)。他強調自己不是那種文學形式主義者,更感興趣的是“能直擊普通人看得出的事實的核心”(qtd. in Oti-Duro, 2015:43)。
雖然艾克文西將自己定位為通俗小說家,但不少學者都認為他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典作家。珀維(John Povey)和帕爾默(Eustace Palmer)是重新發現這位作家的重要學者,他們認為,如果評論者能看到艾克文西作品的社會關懷,就能更好地欣賞其文學價值(Ola, 1985:48)。尼日利亞著名文學評論家伊曼尤紐(Ernest Emenyonu)認為小說《賈》在西非英語文學的發展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Tariq, 2004:210)。 帕里(J. Parry)甚至認為《賈》可以比肩阿契貝的《瓦解》和圖圖奧拉的《棕櫚酒酒徒》(Emenyonu, 1974:79)。目前我國學者對艾克文西的研究尚未有效地開展,僅對他的創作生涯、主要作品進行過較為具體的介紹(顏治強,2019:132-148)。本文將深入分析這兩部作品中人物在城市空間中的生活體驗,旨在凸顯作家矛盾的城市觀,并揭示獨立前后尼日利亞人民從鄉村走向城市的過程中所遭遇的辛酸和迷茫。
2.夢想與欲望之城:令人愛恨交加的拉各斯
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城市總是有著矛盾的情感,文學作品中的城市書寫也大抵如此,常給人一種愛恨交加的印象(徐剛, 2010:66)。艾克文西的城市書寫也不例外。正如勞倫斯(Margaret Laurence)所言,艾克文西對拉各斯的城市情感“是分裂的”:他熱愛城市,所以能把拉各斯寫得栩栩如生,但他又不斷批判“城市的貪婪、冷漠、欲望以及腐敗”(qtd. in Okonkwo, 1976:34)。在艾克文西筆下,拉各斯表征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城市里較好的基礎設施能使居住者過上與鄉村完全不同的生活。《城》中的大比特麗絲(Beatrice I)毫不避諱告訴主人公桑果(Sango),吸引她到拉各斯的正是以“車、傭人、高級食物、體面的衣服”為代表的新生活方式(Ekwensi, 1969:72)①。這也是弗雷迪(Freddie)拋棄其顯赫的酋長之子身份來到拉各斯的主要原因。
拉各斯是一個以自由和開放著稱的城市。在19世紀50年代,拉各斯的人口有一半是前奴隸(Boostrom, 1996:63)。1866年尼日利亞首次人口普查表明,該市的居民除了來自本國各地不同族群,還包括1826年至1835年間從塞拉利昂的“自由鎮”(Freetown)遷移過來已獲得自由的奴隸,以及從葡萄牙前殖民地巴西遷來的那些獲得人身自由的約魯巴奴隸(Folola & Salm, 2004:275-276)。《賈》中,南希(Nancy)的父母就是從“自由鎮”遷至拉各斯,但他們在這座城市里沒有受到任何歧視。艾克文西筆下的拉各斯可謂不同種族、部族和文化的融合之地。《城》中所描寫的“普語俱樂部”(The All Languages Club) 是一個崇尚平等、自由以及部族融合的公共空間。它的創建人“想要朝著世界統一邁出實際的一步”(42),希望創建一個能讓操各種語言、來自不同階層的人互相了解的空間。或許是由于這種跨族群的平等理念深入人心,《賈》中來自尼日利亞各地的人們在拉各斯都使用洋涇浜英語。小說敘述者借主人公賈古娃之口說,拉各斯人之所以說洋涇浜英語是因為人們“不想要太多讓人想起部族或習俗那些令人尷尬的東西”(Ekwensi, 1979:5)。正是拉各斯這種自由、平等的氛圍讓《賈》中賈古娃相繼與弗雷迪、泰沃戀愛,并促成了《城》中若干青年男女的跨國戀情。
在艾克文西筆下,拉各斯還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實驗地。尼日利亞首個政黨“尼日利亞國家民主黨”就是在拉各斯成立(Folola & Salm, 2004:33)。《城》寫道,這座大城市里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團體和政黨,它們為了去殖反帝的共同目標——為尼日利亞人自己決定“能掙什么錢;吃什么食物;什么時間點睡覺;看什么電影”而戰(56)。在拉各斯,除了成立政黨和團體,人們還通過各種報刊雜志自由表達政治觀點和立場。尼日利亞最早的現代報紙,如《拉各斯標準報》《英裔非洲人報》《尼日利亞先鋒報》等都是在拉各斯創刊(Folola & Salm, 2004:33)。在真實的歷史中,這些報紙以對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敏感以及大膽的揭露而著稱。艾克文西本人當過多年的新聞記者,深知報紙的政治力量(Riche & Bensemanne, 2007:41)。《城》中桑果供職的《西非知覺報》(West African Sensation)就是一份關注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報紙。作為該報的法制新聞記者,他常對一些社會問題進行大膽的揭露并提出辛辣的批評。他對東格林斯煤礦危機事件的報道曾讓該報在全國熱賣。更重要的是,他的報道使各部族的政治家們紛紛放下分歧,團結起來與制造煤礦危機的英國殖民政府作斗爭。總之,尊重個性自由和倡導民主政治的拉各斯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吸引賈古娃到拉各斯的正是那種男女平等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拉各斯的女性可以“和男人一樣在辦公室里上班”,也可以“跳舞、抽煙、穿高跟鞋和窄腿褲”(Ekwensi, 1979:167)。
在歐洲的城市書寫中,城市常是欲望和物質主義的代名詞。在《城》和《賈》中,處于新舊秩序轉型期的拉各斯也是充滿物欲、肉欲的墮落之地。拜金主義操控著人們的生活,人們擠到城里往往是想“通過更快的手段掙到錢”(Ekwensi, 1979: 6)。對金錢的病態渴望致使城市里的人們道德淪喪。正如艾克文西所言,獨立之前的尼日利亞“城市居住者沒有選擇,由于經濟壓力,他們不得不昧良心”(Nganga, 1984:282),在拉各斯不斷上演著丑陋的“劇場秀”(154)。女性由于生活在社會底層,只能靠出賣肉身獲取金錢,《賈》中的賈古娃和《城》中的大比特麗絲莫不如此。在拉各斯,窮人還常以詐騙和搶劫為生。為了過上奢侈的生活,《城》中的愛娜冒險行竊,貝約不惜出售假藥,《賈》中的丹尼斯從事搶劫的勾當。更可怕的是,這些人從不為自己那種“只在乎瞬間的快樂”和 “孤注一擲”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愧(Ekwensi, 1979:124)。相比之下,有錢人的道德淪喪也觸目驚心。拉基德雖已腰纏萬貫,但為了掙更多的錢也常常不擇手段——他曾讓人假扮警察扣押盜賊從軍隊里盜得的贓車,不費吹灰之力就發了一筆橫財。而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溫文爾雅的政客更是有過之無不及,他們背地里常為了金錢而玩弄政治、草菅人命。艾克文西認為,尼日利亞獨立后的政府官員尤其是第一共和國的政客與小丑無異(Nganga, 1984:283),他們眼里只有權力和金錢,一旦身在高位就會把為大眾謀福利的承諾都拋到九霄云外。《賈》寫道,弗雷迪從英國留學歸來后并沒打算報效祖國,而是馬上投身于大選并伺機斂財;而在泰沃大叔這個老政客眼里,政治除了能滿足他的權力欲和虛榮心之外還帶來巨額的灰色收入。見錢眼開的他認為“人命一文不值”(Ekwensi, 1979:155),企圖擋住其財路的政敵弗雷迪就被他設局謀殺。總之,如艾克文西本人所說,拉各斯猶如阿里巴巴故事中四十個大盜窩藏贓物黃金的洞穴,任何知道咒語的人都可以進去自取想要的寶貝,但有時貪婪會讓人不知不覺中了芝麻的圈套,下場就像阿里巴巴的兄弟一樣(Emenyonu, 1974:29)。
城市里的物欲和肉欲似乎是孿生姐妹。艾克文西筆下的拉各斯不僅物欲橫流,也是肉欲肆意流淌之地。有學者指出,現代城市人因為視覺而神魂顛倒,城市里的一切都能被轉化成為各種可以采集的景觀。在城市里,由于視覺比嗅覺、味覺、觸覺、聽覺更具優勢,身體僅被簡化為外表,而身體的其他多重知覺則被邊緣化(厄里, 2008:158)。女人身體給人的視覺印象尤為容易被轉化為色情景觀。賈古娃就經常穿著暴露,在各個公開場合把身體的性誘惑力發揮到極致。“熱帶風情”俱樂部的姑娘們也在這座“現代的超級性交易市場”(Ekwensi, 1979:13)里放縱自己。《城》中除了賈古娃這類風塵女子,普通已婚和未婚女性也在“普語俱樂部”撩人的音樂聲中訴說著自已的原始肉欲:“一聽到桑果演奏的音樂,(她們)就放下手中的毛線活或針線活,抖動她們的屁股、腰肢和胸脯,……而那些還沒找到男人的姑娘會在愛慕她們的男人面前以一種誘人的方式扭動著屁股”(Ekwensi, 1979:7)。毫不夸張地說,整個拉各斯就像一個原始肉欲恣意流淌的城市。
在艾克文西筆下,女性的墮落是城市欲望的重要表征。在拉各斯,似乎沒有適合女性的正當職業,那里似乎也沒有打壓性交易的法律。在“熱帶風情”俱樂部生意不好的時候,女人們就肆意在街上攬客。賈古娃首次踏上拉各斯的土地時就被一個皮條客收留并被轉手給一個英國男子當情婦。作家或許想以這種夸張的表現方式說明拉各斯女性的集體墮落。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他的城市書寫中出現大量將女人欲望化的身體意象。也正是這種“對女性不加掩飾的解剖”導致一些宗教和女性組織對《賈》進行猛烈的抨擊(Emenyonu, 1974:78)。
伊曼約努指出,艾克文西善于描寫城市里人們如何運用自身的天賦及后天習得的能力來操控他們的生活和環境——他們未能實現生活目標的根本原因并非充滿敵意的命運或他們同胞的惡行,而是他們自身的缺陷(Emenyonu, 1974:13)。奧比艾奇納(Emmanuel Obiechina)則認為,與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曼哈頓中轉站》(Manhattan Transfer,1925)相似,《城》里的人物由于城市生活的種種壓力而走投無路,甚至到了否定他們主體性的地步(Dunton, 2008:71)。筆者贊同上述觀點。對金錢的迷狂以及對肉欲的本能追逐常使城市中的人們喪失理智和尊嚴。在《賈》中,艾克文西用自然主義的手法呈現拉各斯人狂野的生活:對金錢的追逐使賈古娃仿佛變成追逐獵物的母獅,在拉各斯這個“天然的棲息地”伺機追捕獵物;那些與賈古娃一起瘋狂揮霍青春的姑娘們常在那個絕佳的狩獵地點——“所有進城及出城道路的交匯點”等候她們的獵物(Ekwensi, 1979:106)。漢斯(Z. Hans)和希爾福(H. Silver)認為,在艾克文西的城市書寫中,“人物雖是活的,卻劣于造就他們的環境”(qtd. in Dunton, 2008:70)。不言而喻,在拉各斯,對肉欲和物欲的追求致使人們喪失了主體性,淪為城市動物,而拉各斯這個非主體性的存在卻如奇拉姆(D. Killam)所言,“扮演了人物的角色,控制、界定、組織而且經常摧毀居民的生活” (qtd. in Dunton, 2008:70)。這個追逐金錢和肉欲的城市注定會毀滅人性:《城》和《賈》中的重要人物“都是毫無成就的個體”(Obiechina, 1975:103),而且都一一命喪拉各斯。賈古娃雖沒有死在城里,但在那失去了用身體換來的所有錢財。桑果也同樣一事無成,沒有實現在拉各斯出人頭地的愿望。伊曼約努認為,這兩部小說中各種人物的悲劇性遭際表明,艾克文西在小說中“既是原告,又是陪審團,他的《大憲章》中只有一句話,罪惡的代價是死亡”;這些死亡同樣也說明拉各斯儼然是“小說中的惡棍” (Emenyonu, 1974:43),“每年(要)吞噬許多無辜的生命”(149)。這兩部作品顯然隱含了作家對欲望之城的倫理批判:拉各斯并非普通民眾逐夢的理想之地!
3.從城市到鄉村:尋找救贖的力量
從《城》和《賈》的故事情節中,不難看出城鄉的差異與對立:城市只要結果,不在乎手段,為達目的人們可以不擇手段;城市充滿混亂、腐敗和墮落,因此道德與法律幾乎無用武之地。而鄉村仍保留著較強的是非觀,傳統的倫理道德觀依然是人們生活的根基。在《賈》中,艾克文西通過人們對待身體尤其是女性身體的不同態度來折射城鄉的差別及對立。在鄉村,女性裸露身體比較常見,并無太多的性暗示,男性在觀看時通常不會有色情的聯想,因為 “在這一部分的世界里占上風的是自然,裸露并不是什么稀奇事”(Ekwensi, 1979:71)。然而在城市里,女性的身體往往已被客體化,通常就是肉欲的代名詞。因此,從未到過拉各斯的桑果母親給兒子寫了許多信讓他當心城市生活。在桑果母親眼里,城市充滿邪惡。為了預防墮落的城市女性對兒子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她在鄉下挑選了一個“來自好人家的正經姑娘”艾莉娜當他的未婚妻(8)。純潔、無邪的艾莉娜可謂鄉村姑娘的典范,她被精心地保護在一個“看不到世界的邪惡,只談論美德和純真”(82)的鄉村修道院里。久居城市的桑果見到純真無暇的艾莉娜時便“因自己的城市背景而詛咒自己”(83),覺得自己的身體“必須要實施某種凈化處理”(82)才能配得上她;修道院純潔而寧靜的氛圍一度讓他覺得自己是個罪人,看不到“得救的希望”(83)。
城鄉對立是英國乃至歐洲城市書寫中的重要母題。艾克文西的城市書寫似乎沒有偏離這一經典母題,但他筆下的城鄉對立主要是通過兩性關系的描寫展示出來,而且城市的罪惡更集中體現為女性的性墮落。在《賈》中,賈古娃在離開家鄉奧戛布(Ogabu)之前接受了其父為她安排的婚事,她“想安頓下來,做個賢妻”(Ekwensi, 1979:167)。但她最終還是抵擋不住城市新生活的誘惑而前往拉各斯成了風塵女子,完全把自己變成欲望的奴隸。實際上她對精神生活沒有興趣,而且也沒有足夠能力去理解諸如“白人帝國主義在尼日利亞終結的個人記憶”這樣的討論內容。《城》中大比特麗絲也是城市墮落女子的典型代表,為滿足虛榮和欲望,她不惜成為男人們的玩物,最后病死在拉各斯。或許作家就是想以她的死亡來隱喻女性墮落而遭受的懲罰。賈古娃雖未客死他鄉,但失去了所有的財物以及當母親的機會,最終不得不離開拉各斯又回到鄉村。與此不同的是,桑果是誘惑良家婦女性墮落的城市男性,他“完全拒絕鄉村生活、傳統價值及其內在美”(Emenyonu, 1974:39),但他卻未遭受任何懲罰,反而還獲得了作家的同情,被看做是受“妖婦”愛娜引誘的受害者(151)。艾克文西甚至通過不太可信的“情景劇方式”(Emenyonu, 1974:43),讓桑果心儀的對象小比特麗絲的男友出車禍而死,從而使他得以順利和她結婚,如愿以償留在本不愿離開的拉各斯。小說《賈》中也是女性在拉各斯受到誘惑而墮落,男性卻能自如應對城市里的聲色犬馬,在作家眼中,似乎只有女性才需要遠離城市,接受鄉村生活的保鮮。因此,可以說他在該小說中進行了城市—鄉村之間的“空間性別化區分”,把城市空間的主導權交給男性并按他們的意圖來描繪,女性只能囿于傳統角色。這種空間話語權力的分配是福柯所指的“通過移植、分配、劃界、對領地的控制以及一些領域的組織等策略構成了某種性別地理政治”(Riche & Bensemanne, 2007:44),體現了作家明顯的性別偏見傾向。
從墮落的城市回到傳統的鄉村,洗心革面、重整道德秩序是18世紀前期英法文學城市書寫的慣用模式(陳曉蘭, 2014:103)。那時城市文學中凈化的力量主要來自宗教和自然。按照萊切和本賽曼的看法,賈古娃在鄉下的父親身為神職人員,這一細節安排絕非偶然。從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看,城市象征著罪惡,而優美的鄉村則代表著善,是上帝用神性創造出來的。因此,他們將賈古娃從鄉村到城市之旅理解為她從善向惡的墮落過程,而她從城市又回到鄉村則是一場救贖之旅(Riche & Bensemanne, 2007:39)。不過應當看到,鄉村的新宗教,即西方的基督教并不能成為賈古娃的救贖力量,因為當她從拉各斯回到家鄉時,她的牧師父親已經去世四天,她已沒有機會接受父親的宗教勸導。巴蘭迪亞(G. Balandier)在《歧義的非洲》中指出,比起尼日利亞其它城市,拉各斯更像是由英國人建立的城市(Dunton, 2008:70)。從本質上講,艾克文西在書寫拉各斯這座欲望之城的同時也把批判的筆鋒指向英國的城市文化,因為拉各斯畢竟是英國殖民文化的產物。
小說《賈》在情節上與法國著名作家左拉的《娜娜》(Nana, 1880)頗為相似,兩位女主人公還名字相同,因此有論者認為《賈》受到左拉的《娜娜》的影響(Nganga, 1984:281)。在左拉筆下,美麗的大自然喚起了妓女娜娜對美好事物的感知和羞恥感,也喚醒了她的母愛,使她懂得了愛情并最終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而得到了救贖(陳曉蘭, 2014:140)。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拯救了賈古娃?我們發現,與左拉筆下的娜娜被大自然所拯救不同,艾克文西筆下的賈古娃·娜娜是在回歸鄉村老家及傳統的生活方式之后才開始過上有尊嚴的新生活。她似乎在提及兒時生活時才幡然悔悟自己在城市里的墮落,后悔自己忘記了“在奧戛布自由而簡單的生活”(Ekwensi, 1979:178)。拉各斯踐行的是英國城市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其居住者卻無法安居樂業。筆者認為,艾克文西讓賈古娃回歸鄉村或許還隱含了他這樣的觀點:傳統的非洲價值觀并沒有奴役非洲女性,奴役非洲女性的是西方殖民文化,它把非洲女性變成欲望的客體和消費主義的奴隸。作家讓賈古娃回歸鄉村或許源于想讓她重新“贖回”在城市中因西方殖民文化奴役而失去的尊嚴。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賈古娃在城市里一事無成卻能在鄉下過上體面的生活,完成自我實現。
在艾克文西眼里,非洲人如果忘記鄉村老家,放棄傳統的價值觀,就會失去自我,永遠沒有歸屬感。他曾在訪談中說,“沒有一個真正的非洲人會忘記他的家。他總是想著某一天會回家。……如果一個人想要找到生活的方向,家譜是最重要的”(Nganga, 1984:282)。在其《非洲作家的兩難處境》一文中,他進一步指出,讀者可以在他的小說中清晰感受到其非洲思想背后的心理以及作為他小說源泉的哲學和文化模式(Lindfors, 2010:175)。賈古娃在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往復演繹了一種環形的生命軌跡。謝爾頓(Austin Shelton)認為,這一環形生命軌跡展示了“非洲性的環形原則”,暗示她重新回到其非洲傳統并得到了升華(qtd. in Lindfors, 2010:175)。換言之,賈古娃通過這種“本體論上的撤退”獲得了心理上和哲學上的充實進而得到救贖:她不僅在鄉村實現了其在城市中無法實現的當母親的夢想,而且她還“被置于奧戛布神祇般的地位”(Emenyonu, 1974:91)。
非洲作家傾向于將社會的部分變化視為個人的文化身份從完整到分裂、迷失的變化,他們認為個人可以通過堅持傳統或回歸傳統所認可的行為來“重獲自我的完整性、行為的正確方向以及應有的嘉許”(Emenyonu, 1974:91)。但必須指出,艾克文西對鄉村的救贖力量并未持樂觀態度。或許這也是他在《城》和《賈》中對鄉村著筆不多的重要原因。艾克文西的一生都在城市里度過(Nganga, 1984:281)。奧貢喀沃也指出,與阿契貝、阿馬迪、恩瓦帕等作家不同,艾克文西出生的環境、早年的生活以及職業生涯使他無法系統獲取有關鄉村傳統的第一手資料(Okonkwo, 1976:34);他認為艾克文西對鄉村生活著筆較少是因為他對尼日利亞傳統鄉村生活缺乏了解。筆者不太贊成這一觀點。艾克文西雖生長在城市,但他父親是頗受歡迎的口傳表演者和著名的說書人(Emenyonu, 1974:70),一生都在傳承尼日利亞傳統。正是受到其父的影響,他才萌發了文學創作的熱情。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城市里,但在業余時間總會到農田幫忙、喂養家里的山羊或看他父親雕刻或割棕櫚酒(Emenyonu, 1974:47)。艾克文西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創作的小說都將背景設置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他在這兩部小說中對鄉村著墨較少或許是源于他對以鄉村為代表的尼日利亞傳統文化的態度。與阿契貝和阿馬迪不同,艾克文西并不具有濃厚懷舊主義情緒,也不向往鄉村牧歌情調。對他而言,尼日利亞傳統鄉村社會的瓦解不可避免,他甚至期待那種缺乏雜交影響的鄉村舊模式的消亡(Okonkwo, 1976:34)。 因此,他在《城》和《賈》中用較少的筆墨來描寫鄉村及其傳統文化,或許只是想把它定位為非洲女性逃避西方文化奴役的避難所而已。
事實上,讀者可以從《城》中桑果對鄉村和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賈》中賈古娃的鄉村經歷中清楚地感受到艾克文西本人“在徹底的西化以及回歸非洲傳統之間來回搖擺的態度”(Lindfors, 2010:175):盡管桑果在返回鄉村期間到修道院探望未婚妻艾莉娜,并被那里純潔的氣氛所感染而突然懺悔,但小說的敘述者告訴我們,當他看到純潔而笨拙的艾莉娜時,絲毫沒有要娶其為妻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回來的路上他突然意識到,艾莉娜曾是一種激勵他遠離墮落城市誘惑的力量,但“現在他感覺這種推動力已經消失”(83)。桑果的想法表明,鄉村的純真已無法對抗城市的墮落。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他在結婚之際想象艾莉娜的鄉村生活時,心里“夾雜著局促不安、喜悅和悲傷之情”(157)。其實在艾克文西筆下,遭受西方殖民文化圍剿的非洲鄉村傳統文化今非昔比,其純潔性已受到嚴重挑戰:在《賈》中,賈古娃在離開家鄉去拉各斯之前就和村里多名男子有染,她不檢點的行為雖然受鄉村倫理道德制約,但她本人卻很難踐行傳統道德理念。傳統鄉村生活于她而言并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另外,雖然她在城市里撞得頭破血流之后又回到鄉村重新開啟新生活,但假如她沒有得到泰沃大叔留給她的那筆不義之財,也是不太可能過上有尊嚴的獨立生活。由此可以較清楚地看出艾克文西矛盾的城鄉觀:鄉村雖在一定程度上是逃避城市邪惡的避難所,但其傳統的價值觀念已很難對抗城市文化的侵襲。柯林斯指出,阿契貝等作家對獨立后尼日利亞的未來流露出灰心喪氣和無所適從的困惑(Collins, 1969:65)。筆者認為,上述那些細節或多或少也折射出艾克文西本人關于新尼日利亞何去何從的困惑:盡管英國殖民者給尼日利亞城市帶來了一些改變,但人們卻深受西方殖民者物質至上以及享樂主義思想的影響,不知如何去創造一種適合自己的新生活。
4.結語
艾克文西被譽為“現代非洲文學中的查爾斯·狄更斯”(Riche & Bensemanne, 2007:37),是“當代的記錄者”(Okonkwo, 1976: 33)和“成功的社會現實主義作家”(Tariq, 2004:225)。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艾克文西的文學地位不斷上升,其作品的經典價值日益彰顯。有論者甚至稱,“五十份政府報告都沒有他的小說如《城》等告訴讀者那么多有關西非的情況”(Emenyonu, 1974:1)。艾克文西曾指出,小說家應是一面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的“鏡子”(qtd. in Emenyonu, 1974:125)。事實上,尼日利亞獨立前夕許多人都陶醉于“鍍金的國家形象”(Emenyonu, 1974:2),但他作為一位通俗作家卻能較客觀描寫“拉各斯的暴力、欲望、混亂、殘忍以及各種壓力”(Ola, 1985:52) ,生動地展現殖民語境下尼日利亞社會的真實風貌。薩特曾言,“作家有責任將小說視作一種反思歷史、改變現實處境的不朽力量”(轉引自程彤欣、劉白,2023:92-93)。如果說阿契貝、索因卡聚焦的是尼日利亞受過教育的少數精英人群的命運,那么艾克文西最關心的則是城市里普通民眾的生活百態。他坦誠直面轉型期尼日利亞社會的各種社會政治和道德問題,“雖然他沒有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帶著極大的同情對其進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Emenyonu, 1974:11)。艾克文西對拉各斯這座城市愛恨交加,其城鄉觀不乏矛盾,表露了他對尼日利亞何去何從的迷茫,但其城市書寫體現了當代尼日利亞的現實主義圖景,無疑反映了非洲知識分子努力尋求歷史根基、思考現代文化和表達自尊的努力,“邁出了(非洲)文化解放的第一步”(Emenyonu, 1974: 122)。另外,我們看到艾克文西之后有越來越多的尼日利亞作家把目光投向城市,投向拉各斯,作為非洲城市書寫的先驅者,艾氏自然功不可沒。
注釋:
① 以下出自該著引文僅標明頁碼,不再詳注。
參考文獻
[1]Boostrom, R. Nigerian Legal Concepts in Buchi Emechetas The Bride Price[A]. In M. Umeh(ed.). Emerging Perspective on Buchi Emecheta[C].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6. 57-93.
[2]Collins, H. Amos Tutuola[M]. New York: Twayne, 1969.
[3]Dogon-Daji, U. M. Thematic 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of Cyprian Ekwensis Novel The Burning Gra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6, 6(11): 10388-10395.
[4]Dunton, C. Entropy and Energy: Lagos as City of Words[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08, 39(2): 68-78.
[5]Ekwensi, C. People of the City[M].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1969.
[6]Ekwensi, C. Jagua Nana[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9.
[7]Emenyonu, E. Cyprian Ekwensi[M]. Ibadan: Evan Brothers, 1974.
[8]Folola, T. & S. Salm. Nigerian Cities[M].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04.
[9]Lindfors, B. Early West African Writers: Amos Tutuola, Cyprian Ekwensi and Ayi Kwei Armah[M].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10.
[10]Nganga, B. An Interview with Cyprian Ekwensi[J]. Studia Anglica Posnaniensia: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984, (17): 279-284.
[11]Obiechina, E. Culture,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the West African Nove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Okonkwo, J. I. Ekwensi and Modern Nigerian Culture[J].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1976, 7(2): 32-45.
[13]Ola, V. U. Cyprian Ekwensis ISKA Revisited[J]. UTAFITI: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1985, 7(1): 48-52.
[14]Oti-Duro, N. A. The 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Novels of Cyprian Ekwensi: A Study of Jagua Nana, ISKA and Jugua Nanas Daughter[D]. Kwame Nkrum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15]Riche, B. & M. Bensemanne. City Life and Women in Cyprian Ekwensis The People of the City and Jagua Nana[J]. Revue Campus, 2007, (8): 37-47.
[16]Tariq, G. G. Traditional Change in Nigerian Novels: A Study of the Novels of Tal Aluko and Cyprian Ekwensi[D]. Sri Krishnadevaraya University, 2004.
[17]程彤歆, 劉白. 以幻想演說歷史:科爾森·懷特黑德《地下鐵道》中的非洲未來主義書寫[J]. 山東外語教學, 2023,(1): 85-94.
[18]陳曉蘭. 性別·城市·異邦:文學主題的跨文化闡釋[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4.
[19]約翰·厄里. 城市與感官[A]. 汪民安等主編. 城市文化讀本[C].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155-163.
[20]徐剛. 1950至1970年代農村題材小說中的城市敘述[J]. 文藝理論與批評, 2010,(6): 66-72.
[21]顏治強. 論非洲英語文學的生成:文本化史學片段[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9.
(責任編輯:翟乃海)
收稿日期:2023-03-01;修改稿,2023-09-05;本刊修訂,2023-10-05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項目編號:19ZDA296)、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與歷史語境下的尼日利亞英語小說研究”(項目編號:13BWW06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杜志卿,碩士,教授。研究方向:英語族裔文學、非洲英語小說。電子郵箱:chrisduzq@163.com。張燕,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語女性文學、非洲英語小說。電子郵箱:sallyzhang7206@163.com。
引用信息:杜志卿,張燕.拉各斯的誘惑——艾克文西《城市中的人們》和《賈古娃·娜娜》的城市書寫[J].山東外語教學,2023,(5):8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