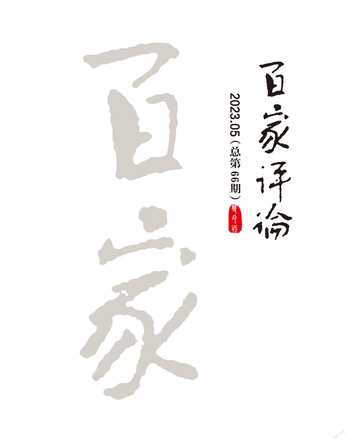高原之巔的扎西德勒
趙月斌
內容提要:《雪山大地》借助兒子的口吻為扎根在高原的“父輩們”樹碑立傳,同時也是偉大的父輩們用生命寫下的一部蕩氣回腸的創業史。小說極盡虔誠的敘述姿態讓我們看到了極具奉獻與犧牲精神的父親母親,亦使整個文本呈現出濃郁的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作家所張揚的“理想主義”,為他的作品賦予了一種宏闊的張力,就像雪山回應大海,讓我們聽到了叩擊心靈的寂靜之聲。
關鍵詞:雪山大地 理想主義 凡間英雄 好藏族人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大概這是詩人艾青最為膾炙人口的詩句,正像該詩題目所說《我愛這土地》,人們通常都會熱愛自己的故鄉,而詩人作家往往更具有濃重的戀地情結,他們不厭其煩地書寫著基于某一地域的前塵往事或美麗鄉愁,把一個“郵票大小的地方”變成了引人矚目的文學空間。楊志軍無疑也是這樣一位非常熱愛故土家園的“戀地”作家——他的幾乎所有作品都在書寫自己生活的地方:假如他不曾在青海度過半生,大概就沒有《無人區》《環湖崩潰》《大悲原》《藏獒》《伏藏》《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巴顏喀拉山的孩子》等荒原、藏地系列,假如他后來不曾定居山東青島,或許我們也看不到《你是我的狂想曲》《最后的農民工》這類青島故事。西北高原和沿海都市已經成為楊志軍最具標志性的敘事場域,這兩種極具反差的地理環境之所以能讓他縱筆馳騁,當然與作家的生命歷程密切相關,正因有了由西北到沿海的空間跨越,他的作品似乎天然地產生了一種宏闊的張力,就像雪山回應大海,讓我們聽到了叩擊心靈的寂靜之聲。
具體到《雪山大地》,這部剛剛榮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僅看題目即可知道,楊志軍依舊在續寫他的藏地詩篇,接著只看正文第一句話,又會發現,他仍舊是在講述父輩的故事:他要汲取“生活的原色”為扎根在高原的“父輩們”樹碑立傳。《雪山大地》中的漢族干部“強巴”,既是敘述人的“父親”,是小說的主人公,更是在作者的高原故鄉巍然屹立的靈魂人物。他與《藏獒》中所寫的父親“漢扎西”構成了互為映襯的鏡像關系,也是作家對其“父輩”給予的更深層次的挖掘和塑造。楊志軍自言:“我是天生的理想主義者,這個不可救藥,所以,我也比較喜歡寫這種氣質的作品。”a他還把《雪山大地》與另兩部作品合稱為“理想主義三部曲”,讓“理想主義”的光芒穿透紙背,與點點星辰同明相照。足可見“理想主義”之于他,并非只是一種凌虛高蹈的個人姿態,而是一種踏踏實實的創作追求,他以《雪山大地》書寫父輩的生命史,更以父輩們“永不放棄的愛念”回答了“人應該怎樣做才能稱其為‘人。”
一、“我”與父輩們的神話世界
“我想我已退休,不再是校長,有的是時間,為什么不寫出來呢?”b這是《雪山大地》最后一句話。因此,從開頭第一句話“父親住進桑杰家的帳房純屬偶然”c開始,整個小說文本都可看作“我”(江洋)的回憶錄:回憶“我”的父親母親、姥爺姥姥以及“我”和同輩們——前后三代人——經歷的時代發展和“山鄉巨變”。若按照江洋正常的退休年齡推算,小說起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大概跨越了半個多世紀。在五十多年的時間里,以三江源地區所在地玉樹藏族自治州為地理原型的阿尼瑪卿州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里原本是藏族頭人角巴德吉所屬的沁多部落,雖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直接由部落變成了人民公社,但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幾乎都還停留在原始的游牧時代,以父親為代表的“紅漢人”(第一批黨政干部),就是在這樣一個原始部落開啟了一代人的“創世紀”。他們建起了第一所學校、第一所醫院,開辦了第一家商店、第一家超市,蓋出了第一座樓房,讓牧民變成了市民,不僅吃上了蔬菜,跳起了廣場舞,而且用上了煤氣、電腦、智能手機,讓他們趕上了被落下二十年都不止的現代化進程,直接進入了與內地人同步的“神話世界”——原本貧窮落后的阿尼瑪卿草原成了“中國最美草原”,三代人接力營建的沁多城成了“高原最佳景觀城市”,“父輩們”靠著樸素的信念和“愛的速度”,開創了天堂一般的“理想國”。所以,從故事層面上看,《雪山大地》完全可以概括為一部創城記,同時也是偉大的父輩們用生命寫下的一部蕩氣回腸的創業史。
如果把《雪山大地》看作一部虛構的史傳,那么它的傳主就是強巴,與雪山大地同在的漢族干部強巴支撐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強巴傳”。所以,這部采用第一人稱敘述的作品主人公并不是“我”,而是“我”的父親強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雪山大地》延續了《藏獒》所采用的全知型第一人稱,在“我”講述父輩們的故事時,往往突破了第一人稱的視角限制,把“我”變成了無所不知的說書人。因此小說中的“我”不像《堂·吉訶德》中的“我”那樣只是單純的敘述者或作者的代言人,也不像《孔乙己》中的“我”那樣只是一個起到穿針引線作用的影子人物,《雪山大地》中的“我”是作為主人公的兒子、作為一個配角,講述作為主角的父親的一切。這樣,就把父親放置到了相對客觀的全知視角中,既弱化了“我”的主觀色彩,突顯了“父親”作為一號人物的重要地位,又讓敘述者保持一種本然的回憶狀態,以后知后覺的方式獲得言說的自由。作為兒子對父輩的回憶,小說的敘事語態盡顯謙卑和虔誠,表達了對父輩一代的緬懷和崇敬。這種假托于兒子的敘事姿態,讓我們看到了有如圣徒圣女的父親母親,亦使整個文本呈現出濃郁的頌圣色彩。再加上前置于每一章開頭以及夾雜在文本中的大量頌詩,更是這種頌圣體的直觀表現。在風也唱著“扎西德勒”的頌圣氛圍中,作家筆下的“雪山大地”便是護佑天下蒼生的神性空間,父輩們注定了要抵御蠻荒走向一個幾無瑕疵的神話世界。
二、“好藏族人”
盡管小說刻意淡化、簡化甚至模糊了半個多世紀發生的歷史事件,有時只用“在那個艱難苦澀的歲月里”d、“這是一段荒涼的歲月”e來籠統帶過,但是父輩們遭遇的一場場苦難卻是無法回避的。所以《雪山大地》的背景就不只是自然環境和歷史原因造成的貧窮落后,更有接踵而至的“不可抗力”帶來的苦難時世,父輩們的命運注定要和這樣的現實膠著在一起,不得不受其牽累、戧害,又不得不與之周旋、對抗,哪怕最終成了無辜的替罪羊,成了自身難保的“泥菩薩”,也要做一個“真正的藏族人”。按照草原上的習慣,“好藏族人”是正面的褒獎,“不是藏族人”則是負面的貶抑。小說里的父親剛一出場的時候,不僅說得一口流利的藏話,“連表情都成了地道的藏族人”。這位“吃糌粑已經吃了好幾年”,“藏化”得和藏族人沒什么兩樣的漢人干部,只是缺了個藏族人的名字。所以,原為部落“頭人”的公社主任角巴,為他取了一個藏名,叫強巴。小說主人公“我”父親——從此就以強巴為名。通過后文可知,小說的敘述人“我”叫江洋,但是父親的原名,甚至姓氏,從未出現,他認同了這個尊貴的藏族名字,至死都叫強巴。
藏語中的強巴,指的是藏傳佛教中的強巴佛(漢地佛教中的彌勒佛)。梵文“彌勒”意譯即為慈氏、慈愛。正因如此,當父親接受了“強巴”這個名字的時候,也意味著接受了藏族人角巴對他寄予的厚望,讓他一輩子都是心存慈悲的“好藏族人”。所以,強巴的一生也可以說是致力于做一個“好藏族人”的一生:在角巴成為替罪羊面臨牢獄之災的時候,他挺身而出代為受過,哪怕是受了處分丟了官職;在陷害過他的老才讓命懸一線時,他又不計前嫌,先后兩次救其性命;在老才讓恩將仇報,制造了牽連多人的“強巴案”時,他卻自投羅網,主動充當了負刑下獄的“首犯”;而在參與保護草原生態、推動城市建設等有利于民生大計的決策部署的時候,他還能主動團結老才讓,把好事辦好。這位彌勒佛一樣的“藏族人”,從一開始到牧區蹲點,到后來實行“大包干”帶領牧民致富,最后又致力于環境保護,要把變壞的草原變回去,不管是當干部,當校長,還是做牧民、做商人,好像,他傾其一生,只是要做一個“好藏族人”,好像,他就是為雪山大地而生的。在他臨死前,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在心里敬畏雪山大地,跟朝拜是一個樣子的,所以不光是今天,我時時刻刻都在朝拜,說到底,工作就是朝拜,需要虔誠,還需要一絲不茍。”f這是強巴阿爸不經意留下的遺言,他就死在把工作當朝拜的路上:“坐下來的父親再也沒有起來,直到幾分鐘后離世而去,都還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望著圣潔的雪山。”g活著“一絲不茍”,死也“端端正正”,這位“好藏族人”無愧于強巴這個未來佛的名字,他把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雪山大地。
再來看“我”母親,苗醫生。這位省醫院的女曼巴,來到缺醫少藥的藏區縣城,從無到有把機關診所擴建成了縣醫院,還要到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別離山創辦麻風病醫療所,結果反被誣為“投機倒把”,父親強巴獲刑入獄,苗醫生也成了逃犯,只好躲進與世隔絕的醫療所,專心救治被遺棄的麻風病人。雖然后來冤案得到平反,苗醫生卻沒能重獲自由——她也染上了麻風病菌,最終死在了親手創建的醫療所。醫術高明的苗醫生,一向被牧民當作“活菩薩”,她和強巴一樣,的確堪稱救苦救難的“菩薩”,最后也如強巴一樣,把生命獻給了她所致力的“工作”。無疑,苗醫生也是無愧于雪山大地的“好藏族人”。
至于土生土長的藏族人角巴德吉——小說中干脆非常直白地說他“古道熱腸,肝膽照人”——當然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好藏族人”。他原本是沁多部落的世襲頭人,解放后不但順應政策主動把部落改造成了公社,而且善于發揮進步頭人的影響力,屢屢幫著強巴解憂困,渡難關,無論是辦學校、搞經營,還是建醫院、護草原,都有他出錢出力想辦法,強巴之所以做成好多不易做成的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角巴的功勞。這一個重情重義、顧全大局的“好藏族人”,最終也被雪山大地收走了——為了給陷于風雪的牧人探路,他掉進了深不見底的雪淵。
此外,才讓哥哥也是作家著力塑造的“好藏族人”之一。這個藏民后代被強巴阿爸收養后便離開了牧區,在城市長大,并到美國留學,后又回來擔任副市長,效力于強巴阿爸的建城搬遷計劃。可惜就在即將大功告成之際,他卻猝死在辦公室里——死于黎明。就像角巴爺爺、強巴阿爸和苗苗阿媽一樣,第三代“好藏族人”才讓哥哥也以最后的犧牲回報了雪山大地。就像小說所寫,三代人前赴后繼留下的精神資源已經“變成了空氣,變成了雨露,變成了花朵的種子,播撒在了人們的心里,年年月月都在綻放。”h大概,這也是作家苦心營造的一種“理想主義”。
如果再加上為救強巴而死的賽毛(桑杰的妻子,才讓的生母),為了保育院的孩子被狼吃掉的姜毛(角巴的妻子),在火災中為救人而死的央金(角巴的二女兒),為大家操勞一生最終走失的姥姥,以及差不多裸捐出了全部積蓄的桑杰阿爸和卓瑪阿媽(角巴的大女兒),以強巴和角巴為代表的漢藏兩家人無疑構成了“好藏族人”的巨幅群像,即使不算走失的姥姥,這兩家三代人先后竟有六人不幸罹難犧牲,他們生生死死都像雪山大地一樣圣潔,他們就是雪山大地最完美的象征。
綜上可見,為了表現“好藏族人”之好,《雪山大地》極力塑造了一批大公無私、不畏犧牲的凡間英雄,在敘述者不吝贊美的浪漫回憶中,“父輩們”幾乎就是神話一樣的存在,即便他們沒有說過什么豪言壯語,沒有超凡脫俗的過人之處,卻都像登上了以雪山大地為背景的神圣舞臺,似乎每個人的動作對白都表現得無可挑剔,哪怕他們不經意揚起了塵埃,那塵埃也會自帶光芒。《雪山大地》就這樣寫成了一部凡人神話,作家所謂的理想主義,大概就是這樣:知其不可而為之,知其不可奈何而勇猛前行。
三、老才讓和盜馬賊之歌
《雪山大地》可以說是一部“好藏族人傳”,不過也有個別次要人物“不是藏族人”。比如一直和強巴作對的老才讓,強巴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卻幾次三番痛下黑手,甚至把強巴送進了監獄。在小說的前半部,這位藏族干部依仗手中的權力排除異己、尋私謀利,完全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反面”人物,簡直“不是藏族人”,但是到了小說后半部,這個原本大肆破壞草原生態的人,卻和強巴走到了一起,轉而變成了保護草原的人,最后終于和眾多對手、政敵和解,甚至把酒言歡。“不是藏族人”的老才讓,似乎也在雪山大地的感召下轉化成了“好藏族人”。或許小說有意回避了具體的政治背景,所以從人物的行為看,老才讓的許多表現都顯得莫名其妙,好像前半生只是為了壞而壞,后半生又為了好而好,這樣一個本來可能更復雜的人物,最終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兩面人。
再如盜馬賊秋吉,不僅是令人痛恨的強盜,還是背負了三條人命的殺人犯,這種死有余辜的壞蛋當然“不是藏族人”。可是老才讓卻將他保護起來,因為他不光有探尋金礦的本事,還能馴出黑妖馬,把牧民的馬匹引誘得不知所蹤。尤其可恨的是,他還盜走了草原上最好的馬——日尕,它是強巴最為鐘愛的坐騎。但是這樣一個壞人,最后卻做了一件有“功德”的大事:他培養妖馬,引誘日尕,再讓日尕領著馬群去往不為人知的宗宗盆地,竟是為了保護阿尼瑪卿草原,使牧民們不再養馬為患。對于這件“功德”,強巴亦為認同,但是他的殺人之罪卻是無法抹除的。小說沒有把他寫成嗜血的惡魔,而是揭出了他殺人的原由:因為那家人想要圖財害命,他才把毒酒倒到了對方碗里。當然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辭,不過從他最后的自殺,多少也能看出這個強盜身上或許還存有“好藏族人”的成分。盜馬賊喝多酒時唱了幾句歌:
我偷拿搶奪的禍害人知道,
我半夜三更的憐憫天知道,
我是夾巴窩里出色的強盜,
我也曾祈求雪山大地關照。i
這個過場人物盡管微不足道,卻有可能是小說中最接近真相的人。也只有在講述一個人所不齒的盜馬賊的時候,敘述者才可能放下頌圣的負擔,在雪山大地的背影里發現生動的顏色。
最后再引述一段話:
人身上最難懂的就是臉上橫七豎八的皺紋,但是父親的皺紋我們都懂,那是跟雪山和草原一樣自然而然的褶子,是為了母親為了所有人的刻痕,是“人”的標記。j
這部近六十萬字的小說大概就是為了寫好一個“人”字,作家把這個“人”字寫到了雪山大地的褶皺里,寫到了故土家園的歷史記憶中。為什么這個“人”字如此巍峨如此肅穆?因為偉大的父輩們永遠站在高原之巔。
注釋:
a張嘉:《楊志軍:人要有“翅膀”,才可能破土而出》,《北京青年報》2023年03月07日。
bcdefghij楊志軍:《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672頁,第2頁,第39頁,第267頁,第658頁,第658頁,第672頁,第608頁,第6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