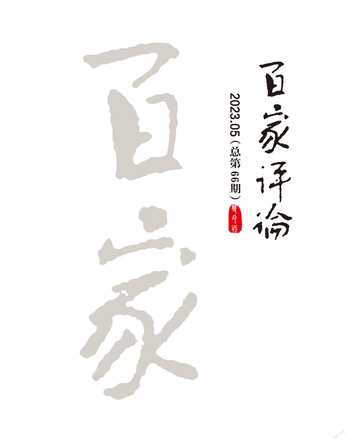論《河灣》的家族“秘史”、時(shí)代“病癥”與精神“藥方”
叢新強(qiáng)
內(nèi)容提要:張煒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河灣》重新講述半島歷史、半島故事和半島人的生存,融家族苦難史、時(shí)代變遷史、個(gè)人精神史于一體。主人公洛珈和傅亦銜都面對(duì)著家族所遭遇的巨大“冤屈”,并爭(zhēng)取著屬于自己的絕對(duì)“申訴”;與此同時(shí),無(wú)孔不入的“厭倦癥”、“胃口太大”的“急躁癥”、疏而不漏的“網(wǎng)絡(luò)癥”又嚴(yán)重侵襲著時(shí)代生活;一路走來(lái)的世俗之愛(ài)和精神之愛(ài)都不可靠,回歸萬(wàn)物自然的“河灣”才能確立生命的依靠。究其根本,《河灣》自始至終關(guān)注著所謂“異人”和如何居于“潮流之上”的核心命題。
關(guān)鍵詞:《河灣》 家族史 “厭倦”癥 “河灣”精神
“人這一輩子就像一條河,到時(shí)候就得拐彎。”a張煒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河灣》在半島歷史、半島故事和半島人的書(shū)寫中,重新揭示家族“秘史”,敏銳表現(xiàn)時(shí)代“病癥”,竭力探尋精神“藥方”。從愛(ài)情到家族,貫注著綿延不絕的“冤屈”與“申訴”;從歷史到現(xiàn)實(shí),呈現(xiàn)著“厭倦”“急躁”與“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病癥;從愛(ài)的依靠到自然的回歸,顯示出“愛(ài)”的不可靠與“河灣”精神的重建。這部作品提供了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肌理、歷史之問(wèn)、時(shí)代之思和信念之辨,代表了張煒創(chuàng)作的新探索、新高度和新境界。
一、“冤屈”與“申訴”的家族“秘史”
《河灣》從“訪高圖”及其“怪人”“異人”等“高人”的獨(dú)特生活狀態(tài)寫起,從主人公傅亦銜和洛珈的隱而不彰的婚姻關(guān)系入手,切入愛(ài)情與家族的牽連和糾葛,并重新展開(kāi)對(duì)于家族“秘史”的敘事。“關(guān)于家世,那些痛楚的歲月,只能如數(shù)堆積在原處。……一路奔波至此,所有的屈辱和遭遇,只不過(guò)為了有一天能夠?qū)π膼?ài)的人從頭訴說(shuō)。”b對(duì)于洛珈和傅亦銜而言,雙方都面對(duì)著家族所遭遇的巨大“冤屈”,并爭(zhēng)取著屬于自己的絕對(duì)“申訴”。
作為傅亦銜至親至愛(ài)的戀人和愛(ài)人的洛珈,本身就是謎一樣的存在,之所以如此的一個(gè)重要原因顯然來(lái)源于洛珈的家族“秘史”。洛珈出身紳士世家,一個(gè)血腥之夜改變了家族的命運(yùn);而殺人如麻的匪兵卻走向了歸順之路,致使“區(qū)長(zhǎng)”陷入極大的痛苦。“區(qū)長(zhǎng)”特別清楚那支土匪在半島上打家劫舍、欺辱百姓、奸淫擄掠的種種惡行,所以他要為紳士的女兒寫出長(zhǎng)長(zhǎng)的申訴書(shū),并呼吁釋放清白無(wú)辜的女子,“她身負(fù)沉冤,她深遭不幸,她有功且有大用”。c由于不斷地進(jìn)行申訴,雙方被作為“多余的人”;由于相濡以沫,雙方最終也走到一起。本來(lái)?yè)碛懈锩巴镜摹皡^(qū)長(zhǎng)”,因此而被逐出城區(qū),成為郊區(qū)老師。他繼續(xù)申訴,無(wú)非證明一點(diǎn):“紳士一家是無(wú)辜的、有功的、善良的,而被那支土匪隊(duì)伍殘害的一家人、任何人,不僅無(wú)罪而且應(yīng)該得到保護(hù)。”d然而,辯護(hù)的證據(jù)越有力越有效,受到的懲罰越嚴(yán)酷越多樣。他們被監(jiān)管,掃大街、搬垃圾、修破廟、住窩棚。無(wú)論什么處境,一直寫那份永遠(yuǎn)不可能完成的申訴書(shū),直到不在人世的那一天。這是洛珈的冤屈的身世。開(kāi)明有功的外祖父母和年幼的舅舅遭遇匪兵的殺害,父母遭遇不公正的對(duì)待,申訴不止的父親付出生命的代價(jià),這一切都郁積于洛珈的內(nèi)心深處。而制造“冤屈”和“不義”的肇始者,卻搖身變?yōu)椤皻w順”和“正義”的革命者。繼續(xù)申訴的使命仿佛天然地落在洛珈這里,而且已經(jīng)變得更加艱難。
承接著父親的西西弗斯式的生命“申訴”,洛珈的尋根究底式的邏輯“申訴”發(fā)生在她和不無(wú)情感的繼父之間。盡管位高權(quán)重的繼父對(duì)自己和母親的保護(hù)與關(guān)心不容置疑,但洛珈的“申訴”仍然沒(méi)有停止,并逐步把造成“冤屈”的源頭和對(duì)象指向繼父本身。當(dāng)年繼父參加的游擊隊(duì)伍在混亂的戰(zhàn)爭(zhēng)中,其實(shí)難辨是非曲直,也無(wú)所謂正反立場(chǎng),但是戰(zhàn)爭(zhēng)的結(jié)果卻涇渭分明。在與繼父保持距離的交往中,洛珈不得不正視的一個(gè)問(wèn)題是:“繼父和親生父親以及母親經(jīng)歷的是同一個(gè)半島上的戰(zhàn)爭(zhēng),結(jié)局卻正好相反。”e都是同一個(gè)時(shí)空的經(jīng)歷,為什么有的改弦易轍、雞犬升天,為什么有的冤屈深重、申訴無(wú)門。這不僅是洛珈個(gè)人的疑問(wèn),也是家族命運(yùn)的轉(zhuǎn)折,更是歷史存在的迷思。洛珈探究的結(jié)論非常明確:自己的外公外婆和舅舅是被繼父所參加的在半島山地打游擊的小部隊(duì)所殺害的。所謂的“土匪”“游擊隊(duì)”“小部隊(duì)”等,僅僅是不同的稱呼而已,實(shí)際上并無(wú)二致,或者退一步說(shuō),他們之間互相聯(lián)系。更進(jìn)一步,在深入的檔案查閱和浩繁的文獻(xiàn)勘察基礎(chǔ)上,洛珈和繼父通過(guò)書(shū)信的方式繼續(xù)追究“冤屈”的來(lái)源和“申訴”的理由。在洛珈看來(lái),包含剿匪、起義、收編的一場(chǎng)場(chǎng)戰(zhàn)斗和村莊里發(fā)生的屠殺,連接起來(lái)就是半島的昨天。尤其那場(chǎng)可怕的劫掠的實(shí)施者,甚至比大股敵人都更殘忍。在繼父那里,他承認(rèn)匪兵的存在,并把這段歷史定性為“糊涂賬”。“戰(zhàn)爭(zhēng)年代,風(fēng)頭一變番號(hào)也變,有槍就是老大,有武器就能拉桿子,一年里出了十五個(gè)草頭王。但總歸邪不壓正,他們幾年后全都完了。”f然而,勝利者的“糊涂賬”,在受害者那里卻無(wú)比清晰。盡管繼父明確表明自己的正義立場(chǎng),但也無(wú)法否認(rèn)戰(zhàn)爭(zhēng)年代的紀(jì)律嚴(yán)明也只是相對(duì)而言,因?yàn)榇婊畈攀鞘滓獑?wèn)題。既然為了存活,那么不擇手段也就難以避免。在洛珈看來(lái),繼父極有可能是十五個(gè)土匪強(qiáng)人中的一分子,只不過(guò)幸運(yùn)地走向了“光明”。繼父對(duì)此直言不諱:“頑抗到底,死路一條;棄暗投明,既往不咎。”洛珈則繼續(xù)追問(wèn):“既往如果血債累累,也不咎?”g繼父對(duì)此回復(fù)延宕,言不及義而言他。歷史的關(guān)鍵點(diǎn)其實(shí)也在這里,看似正當(dāng)?shù)暮戏ǖ睦碛桑贿^(guò)是逃避審判的借口,更是進(jìn)一步掩蓋事實(shí)和抹煞真相的手段。
洛珈對(duì)繼父的提問(wèn)一直持續(xù)到對(duì)方去世。“那個(gè)血腥的山村之夜讓她失去了外公外婆舅舅三位親人,她與他們從未謀面,卻是他們的血緣后人。但母親是親歷者目擊者,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一直認(rèn)為,直到現(xiàn)在也認(rèn)為,母親是在一個(gè)特殊的年代里被迫嫁給他的。她想得還是簡(jiǎn)單了,以為這樣不僅可以救我們母女倆,還可以完成父親的遺愿,會(huì)替她轉(zhuǎn)呈那些申訴。她根本不知道,她嫁給的人如果就是被申訴的一伙呢?”h盡管繼父最終沒(méi)有給出明確答復(fù),也或許無(wú)能為力,但其中的真相已經(jīng)漸次呈現(xiàn),甚至已經(jīng)大白于天下,只是無(wú)法直面而已。在繼父的隊(duì)伍正式歸屬“光明”之前,他們都是殺人魔王的一員,每一個(gè)都難辭其咎,每一個(gè)都難逃罪責(zé)。在母親看來(lái),繼父更加明白“冤屈”之后的“申訴”的難以達(dá)成甚至適得其反,所以他要做“申訴”的終結(jié)者。不僅終結(jié)事件中的自我經(jīng)歷,也要終結(jié)事件中的歷史痕跡。“他說(shuō)世上有個(gè)奇怪的道理,那就是一般的冤屈和是非可以申訴,黑白分明的大冤屈是無(wú)法申訴的。”i一般的小“冤屈”經(jīng)過(guò)“申訴”后,不僅不能否定歷史,反而進(jìn)一步鞏固了歷史;但是黑白分明的大“冤屈”經(jīng)過(guò)“申訴”后,不僅可能否定歷史,甚至進(jìn)一步顛覆了歷史。而洛珈所“申訴”的正是后者,也就注定有始無(wú)終。在嗜血的年代,所謂的參與者、勝利者和規(guī)劃者,如今都已經(jīng)時(shí)過(guò)境遷,甚至積壓了無(wú)法言說(shuō)的關(guān)于自己和他人的罪惡。面對(duì)“冤屈”的明確制造者與清醒和解者,究竟申訴什么又如何申訴?即便“無(wú)法申訴”,也要保存完整的記錄;即便“無(wú)法申訴”,也不能“不作申訴”。這是生命的自由和無(wú)法剝奪的權(quán)利,這是生命的尊嚴(yán)和必須出具的“正名”。在此,“申訴”的過(guò)程已經(jīng)超越“申訴”的結(jié)果,而具有獨(dú)立的價(jià)值和神圣的意義,“申訴”本身就是對(duì)于“冤屈”的明證。盡管遺忘意味著背叛,但也意味著放下,總要有個(gè)了結(jié),“申訴”本身也是“冤屈”的了結(jié)。
無(wú)獨(dú)有偶,洛珈經(jīng)由長(zhǎng)輩所遭遇的“冤屈”和“申訴”,在傅亦銜那里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共鳴。這不僅成為二人情感依存的內(nèi)在基礎(chǔ),也成為激發(fā)后者寫作家族傳記的動(dòng)力。因?yàn)楦狄嚆暯?jīng)由長(zhǎng)輩所遭遇的“冤屈”和“申訴”,不比洛珈來(lái)得輕松甚至更為嚴(yán)峻。“我出生于一個(gè)不幸的、蒙受冤屈的、為民族進(jìn)步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家族;我的父親母親以及外祖父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有的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為尋一條生路,我不得不在少年時(shí)代背井離鄉(xiāng),浪跡整個(gè)半島。”j與洛珈相似,傅亦銜同樣經(jīng)歷著家族的“苦難史”。
對(duì)傅亦銜來(lái)說(shuō),本就郁積于心的家族“秘史”,在與洛珈的情感互通中被重新激發(fā)出來(lái)。“洛珈關(guān)于母親、親生父親和繼父的復(fù)雜經(jīng)歷深深震撼了我。但我的家族、我自己,一切都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一部血淚史、奮斗史、世紀(jì)傳奇,這樣講也許毫不夸張。”k二人的家族故事顯然有著內(nèi)在的交織,固有的“冤屈”和“申訴”同樣需要感同身受的觸動(dòng)和心有靈犀的引領(lǐng)。他人的歷史和苦難一定與自己有關(guān),那些白流的鮮血并非廉價(jià),那些無(wú)端的死亡不可漠視,更不用說(shuō)本就屬于自己的血緣來(lái)路了。傅亦銜的命運(yùn),天然地連接著外祖父和外祖母、父親和母親,并由他們所決定。外祖父是一位中西醫(yī)術(shù)兼?zhèn)涞牧坚t(yī),因?yàn)榕c教會(huì)醫(yī)院的頻繁往來(lái),而成為虔誠(chéng)的基督徒,同時(shí)還熱情地參與同盟會(huì)的革命活動(dòng)。抗戰(zhàn)開(kāi)始后,面對(duì)既合作又爭(zhēng)奪的各路土匪和異族隊(duì)伍,外祖父勉強(qiáng)維持診所而積極投身抗戰(zhàn)事務(wù)。因?yàn)橥练岁?duì)伍與外敵的勾結(jié),外祖父遭到伏擊,把生命獻(xiàn)給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業(yè)。即便抗戰(zhàn)結(jié)束也沒(méi)有迎來(lái)太平,反而進(jìn)入更大的混亂。顯然,外祖父的犧牲構(gòu)成傅亦銜家族“冤屈”的緣起。而父親的不幸也與此有關(guān),在他冒死完成重托之時(shí)卻陷入局中不得解脫直至死亡,這就帶來(lái)了更加深重的“冤屈”。在抗戰(zhàn)最為緊張的膠著階段,抗敵戰(zhàn)區(qū)的一位重要人物落入嗜血成性的悍匪“半島王”之手。為營(yíng)救此人,父親臨危受命。憑借著過(guò)人膽識(shí)和生死不顧,父親把這位大名鼎鼎的“仁公”成功營(yíng)救。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父親也受其思想影響,兩人結(jié)下深厚情誼,可謂生死之交終生難忘,并按照“仁公”的辭行邀約而決定追隨“仁公”的革命之路。也正是在尋找“仁公”的革命歷程中,父親遇到外祖父和母親的救助,使得家族的命運(yùn)融為一體。父親一直在跑路,從關(guān)外到關(guān)內(nèi),從直隸到港城,本來(lái)追尋革命理想?yún)s遭遇始料未及的災(zāi)難。不僅本家叔叔被冤死,而且自己還要面對(duì)審查者的懷疑和審訊。父親的辯護(hù)絲毫無(wú)效,隨著事態(tài)的進(jìn)展,處境更為嚴(yán)峻。正如審訊者所表明的,“一些敵偽人物和其他隱匿的敵人,都先后鎮(zhèn)壓了,你屬于哪一批還說(shuō)不準(zhǔn)。”l非但不能認(rèn)定有功,反而面臨殺身之禍,為自己辯污已經(jīng)刻不容緩:“他從頭說(shuō)怎樣找到‘半島王,怎樣突破三道防線;怎樣周旋和營(yíng)救;怎樣抵達(dá)抗戰(zhàn)區(qū);怎樣與‘仁公約定關(guān)外。”m并且,找到珍藏的“仁公”照片作為實(shí)證。但事與愿違,照片恰恰是審訊者的首長(zhǎng),也就意味著從來(lái)沒(méi)有什么“仁公”了。無(wú)數(shù)人冒著生命危險(xiǎn)營(yíng)救出來(lái)的“仁公”竟然無(wú)影無(wú)蹤,還有什么比這樣更加荒誕不經(jīng)?父親的“冤屈”,只能寄希望于“仁公”的出場(chǎng)。顯然這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不僅鬢發(fā)斑白,而且還被發(fā)配興修大型水利工程。母親的提醒樸實(shí)無(wú)華,卻一語(yǔ)中的:“‘仁公不仁!你拼死拼活找他,差點(diǎn)丟了性命,他倒藏在暗處不吭一聲。”但是父親再次正色:“如果他已經(jīng)犧牲了呢?”n父親不敢承認(rèn)母親的說(shuō)法,寧愿尋找其他的借口。因?yàn)檫@已經(jīng)不僅僅是活下去的希望,更是“冤屈”和“申訴”存在的依據(jù)。否則,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犧牲者的生命價(jià)值到底何在?豈不陷入巨大的虛無(wú)而永無(wú)解脫的可能。
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是,“仁公”非但并未犧牲,反而成為矚目的首長(zhǎng)。與洛珈的繼父一樣,“仁公”同樣需要終結(jié)此前的歷史。不僅讓本來(lái)極其簡(jiǎn)單的問(wèn)題變得更加復(fù)雜多變,而且直接置當(dāng)事者生死于不顧甚至置之死地而絕無(wú)后生的可能。顯然,這是巨大的錯(cuò)位和不對(duì)等。所以即便被發(fā)配遠(yuǎn)行做苦力,父親仍然懷抱單純的希望,甚至清醒地自欺地活著。盡管再也沒(méi)有力氣上路,只能喝一碗糊糊躺著鑿山,但仍然堅(jiān)持爬起來(lái)尋找“仁公”,這是精神活著的現(xiàn)實(shí)理由。與此同時(shí),“我”也被迫一并走上了艱難的人生之路。結(jié)果可想而知,其實(shí)母親的話已經(jīng)揭示了真相。《河灣》的最終,傅亦銜放棄官場(chǎng)機(jī)會(huì)而選擇回歸“河灣”,根本上來(lái)看與此有關(guān)。他要在“河灣”寫出自己的家族紀(jì)事,寫出自己的“冤屈”和“申訴”。其中不僅是傳記材料,更是苦難記錄;不僅是一篇遲到的寫作和文字,更是一份留存的“心念”和“心證”o。
對(duì)于洛珈和傅亦銜來(lái)說(shuō),他們的選擇和堅(jiān)持并非執(zhí)迷不悟,因?yàn)椤笆郎纤械谋晃耆韬捅粨p害者,都迫切需要自潔自證”p。如果說(shuō)洛珈式的“冤屈”和“申訴”是尋找肇事者,而肇事者卻無(wú)法直面;那么傅亦銜式的“冤屈”和“申訴”則是尋找證明人,而證明人卻選擇背叛。總而言之,兩者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相大白的“懸案”。如果說(shuō)前者隱藏著巨大的歷史秘密,那么后者可以說(shuō)隱藏著巨大的人性秘密。當(dāng)然兩者之間相互關(guān)聯(lián),但畢竟也各有側(cè)重。在這個(gè)意義上,《河灣》通過(guò)洛珈和傅亦銜這樣一對(duì)愛(ài)人所依存的兩個(gè)家族的時(shí)代遭際及其命運(yùn)走向,尤其是貫穿其中的“冤屈”和“申訴”,而揭示出歷史的本來(lái)面目和人性的深層面相。在文學(xué)意義上,也可以認(rèn)為,這是作家的心結(jié)郁積之所在,只有說(shuō)出來(lái)和寫出來(lái)才能有所緩解,其實(shí)也正是文學(xué)精神的獨(dú)特品質(zhì)之所在。
二、“厭倦”“急躁”與“網(wǎng)絡(luò)”的時(shí)代“病癥”
顯然,傅亦銜和洛珈都在窮其一生地質(zhì)詢著歷史的荒謬邏輯,并試圖揭開(kāi)謎底。但終究無(wú)法擺脫歷史的魔咒,只能將謎底的可能性公之于眾。幾乎同步,他們又切身面臨并感受著現(xiàn)實(shí)的嚴(yán)峻考驗(yàn),試圖著手解決或者超越身置其中的時(shí)代“病癥”。對(duì)他們和我們而言,“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和“歷史”案件同樣迫切而重要。
首先是無(wú)孔不入的“厭倦癥”。像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所意識(shí)到的時(shí)代病癥“媚俗”一樣,張煒在《河灣》中明確表達(dá)并分層辨析作為一種時(shí)代情緒的“厭倦”。“‘厭倦,一切都始于它并終結(jié)于它。終點(diǎn)是令人懼怕的,那往往要伴隨暴力和狂躁,是難以承受的巨大痛苦。‘厭倦一般不可避免,它的令人恐怖之處就在這里。這是不言而喻的。本來(lái)一切都好好的,都還可以,可是‘厭倦已經(jīng)悄悄來(lái)襲了。于是人們用各種方法抵抗‘厭倦,總是收效甚微。盡管如此,這種實(shí)驗(yàn)和嘗試還要一代代進(jìn)行下去,哪怕付出血的代價(jià)。無(wú)一例外的是,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會(huì)‘厭倦,包括對(duì)抗‘厭倦的方法,它本身也會(huì)‘厭倦。這才是最為可怕的,無(wú)以療救的。”q“厭倦”已經(jīng)成為普遍性的存在,這里包含了“厭倦”的緣起、癥狀、過(guò)程、方法、效應(yīng)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切實(shí)的體驗(yàn)感。這是作家的敏銳,也是眾人的盲點(diǎn),尤為值得重視。傅亦銜的好友余之鍔,因?yàn)閰捑肓藱C(jī)關(guān)生活而辭職,如其所言:“每天都活在語(yǔ)言的固定搭配中,如果說(shuō)這種日子是在考驗(yàn)人的耐心,還不如說(shuō)正在考驗(yàn)人的道德。”r因?yàn)椤皡捑搿保嘀姾吞K步慧夫婦改行經(jīng)營(yíng)旅游公司;因?yàn)椤皡捑搿钡牟豢杀苊猓麄冇指男薪?jīng)營(yíng)“河灣”;及至后來(lái)的婚姻變故,也仍然不排除其中的“厭倦”因素。而天然淳樸、寬厚樂(lè)觀、任勞任怨的蘇步慧的悲傷離世,也讓“心靈的港灣”蒙上了令人質(zhì)疑的色彩。余之鍔離開(kāi)河灣,蘇步慧離開(kāi)人間,只留下無(wú)盡的悲嘆。曾經(jīng)同樣都是機(jī)關(guān)工作,余之鍔和蘇步慧極為重視家庭生活,而傅亦銜和洛珈則極為重視愛(ài)情生活。與前者相比,后者最為擔(dān)心的是愛(ài)情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于是努力尋找防止“厭倦”的方法。看起來(lái)特別有效的“隱婚”“距離”“預(yù)約”“隱私權(quán)”“書(shū)面語(yǔ)”“儀式感”“把戀愛(ài)進(jìn)行到底”等等,似乎成功防止了“厭倦”,但卻走向另一個(gè)極端,那就是“愈加熾烈地燃燒”s。既然已經(jīng)確認(rèn)了“厭倦”的永恒性,那么這樣的試驗(yàn)也已經(jīng)有了結(jié)果,盡管不容置疑其中忘我無(wú)私的真愛(ài)的存在。“厭倦”成為“愛(ài)”的敵人,傅亦銜最終走向“河灣”,不僅出自對(duì)于職業(yè)生涯的“厭倦”、對(duì)于家族使命的勇敢承擔(dān)和對(duì)于摯友二人的永遠(yuǎn)懷念,也不可排除對(duì)于愛(ài)情狀態(tài)的“厭倦”、對(duì)于家庭生活的無(wú)力承擔(dān)和對(duì)于“河灣”精神的再度重建。
其次是“胃口太大”的“急躁癥”。似乎與“厭倦癥”直接相對(duì),“急躁癥”也是異常鮮明的時(shí)代表征。在《河灣》中,主要表現(xiàn)在“異人”何典對(duì)于蘇步慧“心病”的治療。“就是急躁,有時(shí)想什么就急得不行,坐立不安。”t不僅蘇步慧如此,其實(shí)包括“我”在內(nèi)的哪一個(gè)又能例外呢?總是慌慌張張,安定不下來(lái)。時(shí)代的變化轉(zhuǎn)嫁成個(gè)體的焦慮,“急躁”也就在所難免,終究又屬于欲望的呈現(xiàn)。如蘇步慧所親身體會(huì)到的,“心急也是胃的問(wèn)題,平時(shí)說(shuō)‘胃口太大,就是恨不能把什么都一口吞下,太急了怎么成。要細(xì)嚼慢咽,一點(diǎn)一點(diǎn)來(lái),耐煩一些啊,就好了。”u如果說(shuō)蘇步慧的“急躁”還是單純的,那么他人的“急躁”就復(fù)雜多了,“時(shí)代猝不及防地走到了這一步,相當(dāng)大的一部分人忙得腳不沾地,幾乎沒(méi)有時(shí)間休閑、愛(ài)和閱讀,甚至沒(méi)有時(shí)間胡思亂想”。v然而,五花八門的犯罪信息和事實(shí)卻在這個(gè)時(shí)代大量出現(xiàn)。究其根源,一如“異人”何典在夜色里發(fā)出的感嘆,“不停地追逐交配和不擇手段地追逐財(cái)富,其實(shí)一樣無(wú)聊。”w傳統(tǒng)世界的時(shí)空已經(jīng)大大地被壓縮,迅速轉(zhuǎn)化為“物”和“欲”的外化。我們所“急躁”的也已經(jīng)不再是“需要”,而是“想要”。
再次是疏而不漏的“網(wǎng)絡(luò)癥”。相對(duì)于“厭倦癥”和“急躁癥”,“網(wǎng)絡(luò)癥”恰恰是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特色表征。看起來(lái)無(wú)所不能的“科技”,解決不了所有問(wèn)題而且?guī)?lái)更大問(wèn)題。不僅“理想主義”值得反思,再加上“物質(zhì)主義”和“縱欲主義”的流行,網(wǎng)絡(luò)亂象層出不窮,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發(fā)展和希望越來(lái)越充滿懷疑。這個(gè)時(shí)代的“光速”,總是讓人始料不及,最為直接的載體就是手機(jī)。“誰(shuí)想把自己的日子搞亂,只一部智能手機(jī)就夠了。”x這里并非危言聳聽(tīng),而是反思警醒。本來(lái)作為服務(wù)于人的工具,結(jié)果卻成為統(tǒng)治人的枷鎖。所謂“雙刃劍”的過(guò)程,總是收到“單刃劍”的效果。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人相互擾煩,總也沒(méi)有清凈安寧;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信息擁堵,又難以規(guī)避謠言風(fēng)氣。“一方面是知識(shí)爆炸,另一方面又出奇地?zé)o知;充斥頁(yè)面的荒謬浮淺乃至顛倒黑白太多,許多時(shí)候那些似是而非無(wú)聊臟丑之物呈蜂擁之勢(shì)。”y網(wǎng)絡(luò)傳播的后果更為嚴(yán)重,卻又無(wú)力改觀、無(wú)可挽回。《河灣》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癥”的揭示和批判,一方面來(lái)自作者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和作家的生命體驗(yàn),另一方面又為尋找“河灣”提供了前提條件,同時(shí)延伸出“高人”和“異人”到底如何居于“潮流之上”的價(jià)值判斷。
《河灣》毫無(wú)保留地陳列出“厭倦”“急躁”“網(wǎng)絡(luò)”等系列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和時(shí)代病癥,隱含著對(duì)于生活世界及其人的生存的多方位思考。如果不能超越于此,必將陷入海德格爾所謂的“雜然共在”。人人都在互相參照,互相效仿,互相異化,互相磨滅個(gè)性,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因而最終都成了一種失去主體精神的“常人”。而“常人”的習(xí)性和行為,又成了每個(gè)人無(wú)師自通、默默遵守的“公共意見(jiàn)”。因此,“這樣的雜然共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別和突出之處的他人則又更其消失不見(jiàn)了。在這種不觸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況中,常人展開(kāi)了他的真正獨(dú)裁。常人怎樣享樂(lè),我們就怎樣享樂(lè);常人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怎樣閱讀怎樣判斷,我們就怎樣閱讀怎樣判斷;竟至常人怎樣從‘大眾中抽身,我們也就怎樣抽身;常人對(duì)什么東西憤怒,我們就對(duì)什么東西‘憤怒。這個(gè)常人不是任何確定的人,而一切人(卻不是作為總和)都是這個(gè)常人,就是這個(gè)常人指定著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z
《河灣》中也一再感嘆,從出生到現(xiàn)在結(jié)識(shí)形形色色的人,“可是那些能夠擊中心弦、讓人深感訝異的生命個(gè)體,卻似乎從來(lái)沒(méi)有出現(xiàn)過(guò)。他們總是大同小異,不僅衣著和言行是這樣,即便是最偏僻的心之角落也似曾相識(shí)。”如此而已的“常人”狀態(tài),又何談所謂“高人”“妙人”“異人”?可見(jiàn)《河灣》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批判,是為了更為高遠(yuǎn)的追求,也正與如何居于“潮流之上”的理想不謀而合。一個(gè)人僅憑突出的個(gè)性都不能稱為“異人”,何況這個(gè)時(shí)代普遍存在著的“常人”呢?在作者看來(lái),高遠(yuǎn)的人格追求,完全可感可知可以具體把握。“那必須是極為內(nèi)在的稀有品質(zhì),既有異能特技、超凡脫俗的恪守,還要樸實(shí)無(wú)華。咋咋呼呼的夸張和表演恰恰與真正的‘高人和‘異人背道而馳。”也正如這里的表述一樣,真正的生命意義無(wú)不在于樸實(shí)無(wú)華的形式必須承載深刻透徹的內(nèi)涵。如何達(dá)到這一境界,通過(guò)“愛(ài)”的渠道與“河灣”的建設(shè)是否可行?
三、“愛(ài)”與“河灣”的精神“藥方”
在《河灣》中,其實(shí)傅亦銜的家族故事本身就有《獨(dú)藥師》中的故事背景。張煒在長(zhǎng)篇小說(shuō)《獨(dú)藥師》中,圍繞“養(yǎng)生”“革命”和“愛(ài)欲”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展開(kāi)敘事,并將最終的生命選擇指向“愛(ài)欲”。正是在尋求突破“愛(ài)欲”的過(guò)程中,養(yǎng)生世家第六代傳人季昨非逐步超越了根深蒂固的前輩觀念:“遭逢了這樣的亂世,人真正可做的事情、最有意義也是最緊迫的事情,就是養(yǎng)生”。進(jìn)而深刻地意識(shí)到,“人在這樣的世道其實(shí)還有一件值得好好去做的事情,就是愛(ài)。”而且,他從另一面證實(shí)了自己的猜測(cè):父親因?yàn)槭プ類?ài)的母親,也就不再致力于養(yǎng)生。“如此看來(lái),一個(gè)人沒(méi)有了愛(ài)就會(huì)焦躁峻急,然后極易鋌而走險(xiǎn)浪擲生命。”沒(méi)有了愛(ài),“養(yǎng)生”也就失去了意義。
在長(zhǎng)篇非虛構(gòu)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中,如果說(shuō)野物為代表的自然萬(wàn)物具有神性的話,那么外祖母本身就是一種愛(ài),而且是一種博愛(ài),“在外祖母眼里,小動(dòng)物們?nèi)呛⒆印薄M庾婺概惆椤拔摇背砷L(zhǎng),也在陪伴野物成長(zhǎng)。在這種陪伴的過(guò)程中,“我”認(rèn)識(shí)世界,認(rèn)識(shí)自我,接受自然的饋贈(zèng),接受社會(huì)的教育,最終也學(xué)會(huì)了愛(ài)。可以與《我的原野盛宴》相提并論,在另一部非虛構(gòu)杰作《愛(ài)的川流不息》中,張煒再次強(qiáng)調(diào),愛(ài)恰恰是對(duì)于“痛苦”“恨”“陰郁”“悲傷”等負(fù)面情緒的超越。當(dāng)愛(ài)上升為不可抗拒的“愛(ài)力”的時(shí)候,就會(huì)產(chǎn)生無(wú)私的愛(ài),終究“有愛(ài)的人才有無(wú)數(shù)的糧食”。一切都是因?yàn)椤皭?ài)”,即使愛(ài)非所愿,也要在所不辭。《愛(ài)的川流不息》的最后篇章是“川流不息”,不禁發(fā)出反向追問(wèn),“如果所有的愛(ài)都有一個(gè)悲涼的結(jié)局,還敢愛(ài)嗎?可是沒(méi)有愛(ài),為什么還要生活?生活還有什么意義?那只能是折磨,一場(chǎng)連一場(chǎng)的折磨。我們不要那樣的生活。”
到了《河灣》中,“愛(ài)”繼續(xù)作為解決“厭倦”“急躁”“網(wǎng)絡(luò)”病癥乃至“冤屈”歷史的根本力量。在這里,首先是生活的世俗之愛(ài),其次是純粹的精神之愛(ài)。
在世俗之愛(ài)方面,以余之鍔和蘇步慧的婚姻為代表。他們性格互補(bǔ),夫唱婦隨,擅長(zhǎng)經(jīng)營(yíng)家庭氛圍,并且兩人分工清楚:“男的負(fù)責(zé)思想,而女的唯一要做的、終生都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愛(ài)他。”他們不斷地籌劃、搬家、跨界,希望擺脫概念化的生活,追求清新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力求躲避一天到晚的“喧鬧”,尋求“能夠生長(zhǎng)的地方”,最后移居偏遠(yuǎn)的“河灣”,似乎找到了終極的歸宿。然而恰恰在這片充滿“理想主義”的“河灣”,他們面臨著新的虛妄,正如洛珈所指出的,“所有擺脫了喧鬧的人,最后都會(huì)陷進(jìn)另一個(gè)泥潭。”果然,余之鍔變得精神沮喪、身體瘦削,蘇步慧變得失眠恍惚、身體病重。尤其是那個(gè)迷惑蘇步慧的虛假表演的歌手“小木瀾”,“掛著羊頭賣狗肉”地把夫妻二人的“河灣”生活推向絕境。在傅亦銜看來(lái),這是一場(chǎng)噩夢(mèng):河灣渾濁,石屋坍塌;在余之鍔眼中,“河灣對(duì)她是一場(chǎng)浪漫,對(duì)我是一場(chǎng)苦役。回頭看看,好像今生最大的成就,不過(guò)是栽活的那三棵樹(shù)。”在蘇步慧那里,則是萬(wàn)劫不復(fù)的心病,是愛(ài)而不能的崩潰,是走入絕境的哀傷,無(wú)藥可醫(yī),無(wú)醫(yī)可治,只能將自己永遠(yuǎn)留在河灣。“我”的至真摯友余之鍔和蘇步慧,曾經(jīng)無(wú)比令人艷羨,而今傷痕累累地訣別,世俗之愛(ài)的中斷仿佛只是時(shí)間。
在精神之愛(ài)方面,以傅亦銜和洛珈的隱婚為代表。為了規(guī)避可能發(fā)生的“厭倦”,他們未雨綢繆,雙方刻意保持一種隱而不彰的兩性關(guān)系。在洛珈這里,因?yàn)樽陨斫?jīng)歷的特別和平庸婚姻的懼怕,她找到了“愛(ài)情保鮮法”:“分開(kāi),彼此獨(dú)立,和而不同,相敬如賓;一生熱烈、真摯、渴望。”因?yàn)榫芙^袒露,所以拒絕傾聽(tīng),而是把一切留給未來(lái),甚至漫長(zhǎng)的一生。在傅亦銜這里,卻想成為對(duì)于愛(ài)人的“傾聽(tīng)者”和“訴說(shuō)者”。“我在凄苦的人生之路上備受冷落,一度是最孤單的人。我對(duì)所有的愛(ài)護(hù)都心懷感激,并用加倍的愛(ài)去回報(bào)他們。”既然如此,對(duì)于愛(ài)人洛珈就更加明顯。可見(jiàn),洛珈眼中的“愛(ài)”是距離,傅亦銜眼中的“愛(ài)”是無(wú)間。盡管二人同病相憐,也愛(ài)意綿綿,但終究不是同路人。況且,傅亦銜總是不斷想起朋友以前講過(guò)的那個(gè)苦追麗人一生、最后下場(chǎng)凄慘的不幸之人,尤其記住了深受刺激的那句話:“結(jié)了一輩子婚沒(méi)有老婆”。相對(duì)于余之鍔的主動(dòng)的人生,傅亦銜清醒地意識(shí)到自己的被動(dòng)的人生,再加上家族使命的召喚和摯友夫婦的變故,即毅然而然奔赴“河灣”。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傅亦銜的女上司作為官場(chǎng)和機(jī)關(guān)的代表,其同學(xué)德雷令作為商場(chǎng)和資本的代表,為傅亦銜和洛珈的生活提供了環(huán)境參照,但終究又產(chǎn)生了不同的影響。最后,傅亦銜選擇離開(kāi)機(jī)關(guān)的束縛并投入“河灣”的懷抱,而洛珈則進(jìn)入資本的場(chǎng)域并陷入其中的循環(huán)。至此,純粹的精神之愛(ài)同樣遭遇中斷。
憑借著“愛(ài)”一路走來(lái),結(jié)果“愛(ài)”的世俗和純粹卻都不可靠。回歸動(dòng)物、植物、農(nóng)作物,回歸萬(wàn)物自然永恒的“河灣”,仿佛才是人生去處,才能確立生命的依靠。這是“創(chuàng)作主體”和“對(duì)象主體”的共同的探索,也是“接受主體”的應(yīng)有的思索。當(dāng)然,全心全意、竭盡所能地選擇“河灣”的余之鍔“失敗”了;那么,前赴后繼、再接再厲地進(jìn)入“河灣”的傅亦銜能夠“成功”嗎?恐怕這也是接下來(lái)需要追問(wèn)的問(wèn)題。盡管在傅亦銜看來(lái),洛珈具備“高人”或“異人”的特質(zhì),但她卻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高人”或“異人”,倒是傅亦銜本人卻極有可能實(shí)現(xiàn),雖然他并不自知自覺(jué)。可以想象,在“河灣”的重建中寫完家族史的傅亦銜是如何成為“異人”和“潮流之上”的人。如其所言,“‘異人是擁有自我的人,他們不在潮流之外,也不在潮流之中,而在潮流之上。”在此,《河灣》提出的所謂“異人”和如何居于“潮流之上”的核心命題合二為一、融為一體。進(jìn)而言之,構(gòu)成《河灣》并貫穿“河灣”之緣起和終結(jié)的“訪高圖”上的形象再度成為參照的典型:“他們避世獨(dú)處是因?yàn)橐伎己吞幚韽?fù)雜的內(nèi)心問(wèn)題,但并不意味著糊涂。跟隨潮流是俗眾,淹沒(méi)潮流會(huì)丟失,而在潮流之上,就會(huì)有更開(kāi)闊的視野,那才是‘高人。”同步延伸而論,這部小說(shuō)從開(kāi)篇的善畫(huà)“訪高圖”和其中的“河灣”意境到結(jié)尾的回歸“河灣”場(chǎng)景和再畫(huà)“訪高圖”,形成自我的閉環(huán)結(jié)構(gòu),不僅是“文本”的需要,也是“河灣”精神的強(qiáng)調(diào)。
結(jié)語(yǔ)
文學(xué)總是在一定程度上透視著或者折射著作家的經(jīng)驗(yàn)廣度和體驗(yàn)深度。一個(gè)人或者一個(gè)家族的外傷可以修復(fù),甚至修復(fù)得更加完美無(wú)缺;但是一個(gè)人或者一個(gè)家族的內(nèi)傷卻永遠(yuǎn)難以修復(fù),甚至越修復(fù)越殘缺。即使隨著時(shí)間推移也無(wú)能為力,有時(shí)候自欺欺人的直接擱置或者干脆漠視也不失為權(quán)宜之計(jì),但又何其艱難。在《古船》的最后,抱樸好像在傾聽(tīng)一種聲音,見(jiàn)素還聽(tīng)到了另一種聲音。“見(jiàn)素終于聽(tīng)到了。那是老磨在嗚隆隆地轉(zhuǎn)著,很像遙遠(yuǎn)的雷鳴。這就是鎮(zhèn)上老人常常講起的那種聲音——老人們講那些背井離鄉(xiāng)的人,比如下了關(guān)東的人,半夜里爬起來(lái)都能聽(tīng)得見(jiàn)故鄉(xiāng)的老磨聲,嗚隆嗚隆的。可是見(jiàn)素此刻仿佛還聽(tīng)到了另一種聲音,河水的聲音;看到了那條波光粼粼的寬闊河道上,陽(yáng)光正照亮了一片桅林。”歷經(jīng)脫胎換骨,“古船”重新出海。在《九月寓言》的結(jié)尾,追隨挺芳出走的肥、火中涅槃的寶駒趕鸚,歷經(jīng)滄桑而獲得生命的更新。“親愛(ài)的肥你再不要泣哭,我已經(jīng)無(wú)數(shù)次地吻去了你的淚水。親愛(ài)的肥,緊貼在我身上吧,這樣一路、這樣一生!我們逃出來(lái)了,我們?nèi)フ易约旱纳睢G魄疲瑫r(shí)代真的變了,我們?cè)俨挥孟衲愕南容厒兡菢樱嗄_穿過(guò)野地。我們乘車——看著一片片的莊稼在窗外飛閃。看看,多好的紅薯地,望不到邊……你最后看一眼就可以把它忘掉了。真的,因?yàn)槟銢](méi)有什么可以牽掛的了,你是沒(méi)爹沒(méi)娘的孩兒。”……“無(wú)邊的綠蔓呼呼燃燒起來(lái)。大地成了一片火海。一匹健壯的寶駒甩動(dòng)鬃毛,聲聲嘶鳴,尥起長(zhǎng)腿在火海里奔馳。它的毛色與大火的顏色一樣,與早晨的太陽(yáng)也一樣。‘天哩,一個(gè)……精靈!”個(gè)體的命運(yùn)轉(zhuǎn)換也是幸存和希望的所在,同時(shí)構(gòu)成民族的悲劇、毀滅和新生的“寓言”。
張煒的創(chuàng)作豐厚而深刻,擺脫了不同的潮流而走出了一條獨(dú)樹(shù)一幟的自我超越之路,在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共時(shí)性和歷時(shí)性存在中顯示出不同凡響的稀有價(jià)值。《河灣》和其前期的《古船》《九月寓言》等經(jīng)典之作一樣難分難解,融家族苦難史、時(shí)代變遷史、個(gè)人精神史等全部關(guān)懷,反映了對(duì)于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國(guó)家與民族、家族與個(gè)體、時(shí)空與人性等各種依存關(guān)系的深刻思考和切實(shí)把握。就整體而言,張煒的創(chuàng)作所隱含的作家復(fù)雜的主體意識(shí)與作者自覺(jué)的文化立場(chǎng)仍然有待于繼續(xù)探究和深入辨析。
注釋: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張煒:《河灣》,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60頁(yè),第27頁(yè),第51頁(yè),第52頁(yè),第72頁(yè),第75頁(yè),第76頁(yè),第77頁(yè),第79頁(yè),第60頁(yè),第103頁(yè),第160頁(yè),第161頁(yè),第163頁(yè),第102頁(yè),第61頁(yè),第21頁(yè),第23頁(yè),第25頁(yè),第194頁(yè),第195頁(yè),第286頁(yè),第308頁(yè),第90頁(yè),第135頁(yè),第31頁(yè),第92頁(yè),第29頁(yè),第176頁(yè),第220頁(yè),第321頁(yè),第10頁(yè),第43頁(yè),第219頁(yè),第110頁(yè),第110頁(yè)。
z[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shí)間》,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1987年版,第156頁(yè)。
張煒:《獨(dú)藥師》,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頁(yè),165頁(yè)。
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頁(yè)。
張煒:《愛(ài)的川流不息》,山東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頁(yè),第151頁(yè)。
張煒:《古船》,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頁(yè)。
張煒:《九月寓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頁(yè),第339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