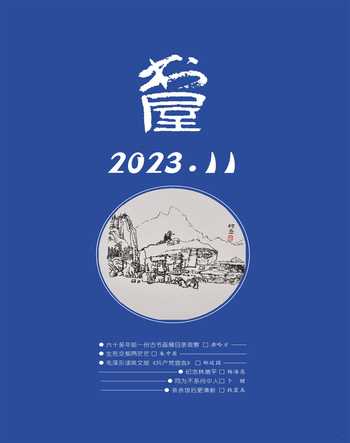唐吟方:“面貌有自己的味道”
薛原
人往往最后活成了自己原來不希望成為的自己。這話忘記是誰說的了,原話也未必就是我記得的這樣,但意思大差不差。或許活成油膩的中年人都不是當年青蔥少年所希望的。經過多年的人生歷練,還能讓自己保持原來的“面貌”是件不容易的事,說好聽點,是不忘初心;說不好聽的,則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或者說頑冥不化、固執己見。其實,固執己見也是一種可貴的品質,譬如唐吟方就是典型的例子。
唐吟方的固執和“一意孤行”體現在他日常生活里的點點滴滴,尤其體現在他的書畫篆刻上。我喜歡讀他的畫,也喜歡讀他寫在畫邊上的閑話。自畫自書,自刻自話,是唐吟方的功課,也是他藝術生活的日常呈現。唐吟方是誠實的,這種誠實體現在他對待自己的創作上。譬如他說,一幅畫完成后,常常覺著這兒或那兒不舒服,改畫幾乎成了日常。當然百分之九十九的畫作毫無懸念被改壞,碰運氣自己認為改得更好的當然也有,雖然在別人看來仍是廢紙。他以自己畫的《翁嫗江干行吟圖》為例:“之前畫面右邊濃密的樹葉畫得過輕,顯得沒分量,漸次加重,以期和那個又粗又黑的樹干情調相合。筆在紙上點染時既擔心落墨太重畫面悶了,又怕下筆太輕不見分量,筆拿在手上真有點‘濕手捏干面——左右不是,而我本性又粗魯直率,不肯小動作太多……還好,最后呈現的樣子總算是平靜祥和的,畫面意蘊也是我要的那種,頂頂要緊的是畫的面貌有自己的味道。”
這段“閑話”有總結,有自謙,有調侃,有得意,還有得意忘形后的狂言:“頂頂要緊的是畫的面貌有自己的味道。”這句話其實道出了唐吟方的心語,或說是他的藝術態度。“有自己的味道”正是唐吟方的作品的面貌,他的書畫與眾不同,自出一路。就像他的為人,看似平靜隨和,卻有著獨持己見、一意孤行的倔強和剛毅。
其實,只要一說到唐吟方這個名字,我就想起了那句“南朝人物晚唐詩”。南朝人物和晚唐詩并列,其實也是一種心境,散淡的人生況味和淡淡的悲秋情致糅合在文人的風骨里。當然,還想到他的畫:疏散山林、曠靜湖水,一樹柳枝、幾叢修竹,點綴幾枚《世說新語》里的人物,即便是野山抱琴,也是一副不管不顧、絕塵而去的灑脫模樣……
唐吟方的畫是不入時流的。他畫的人物,寬袍大袖,遺世獨立,即便是三三兩兩地漫步于湖畔山林,也透露著滿臉桀驁不馴的神態——盡管他畫的那些人物往往都一個面孔,五官也朦朧成一種神情。唐吟方的畫也很難討時人喜歡,他畫的人物,不管是春色里折柳,還是山路上尋芳,沒有半點時人的影子,那種姿態,那種傲然,在當下是尋找不到的,而是滿紙《世說新語》里穿越千年的風景。
唐吟方是固執的,固執己見的性格尤其體現在他的畫上。他畫的這些寬袍人物已經成了他繪畫的一種符號,一種屬于他個人的獨特標志。在這點上,也可以看出他屬于那種一根筋走到底的人,任憑窗外風云變幻,獨自躲進小樓耕耘著自己的一方田園。那個寬袍大袖的畫中人,決絕地走進山林深處,似乎就是他自己的化身。
在唐吟方的身上看不到對潮流的迷信,也看不到對一些熱鬧場合的向往。在他的生活里,所謂的時尚“主流”不是他的選擇。他所關注的往往是被“正史”忽略的,或說是被遮蔽的,或說是未被認識到的。其實,唐吟方更是自信的,這種自信不是畫地為牢,也不是自大傲世,而是獨自守在自己的“邊緣”里,但又是“霸悍”的,這種霸悍體現在他的創作態度上。他的畫一直延續著這種已成他繪畫“定式”的風格,就像一個打磨銅鏡的手藝人,每天打磨著自己的淡淡的生活。之所以用銅鏡來比喻唐吟方的繪畫,還是因為在今天,一面打磨得再精細的銅鏡,也已經不是生活里的必需品了。工業流水線已經為我們的生活生產了豐富的必需品。為“無用”的手藝,為“無用”的繪畫,這其實也是唐吟方的自信所在。
生活中充滿了“有用”,像是有一條無形的鞭子在驅趕著人們去追逐“有用”的生活。于是唐吟方創作的這種“無用”也就更凸顯了活著的獨特滋味。其實,生活是需要有一點特殊的滋味的,這也是藝術的價值所在。唐吟方的畫大多是小畫,冊頁、扇面、窄窄的條幅,在不大的天地里,描繪他眼里的山林、湖畔、田園……但尺幅千里,小中見大,有著遠離塵世的深邃和廣博。
這句“南朝人物晚唐詩”其實還有上句,合起來就是:“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體現出一種心境和對待歷史與現實的態度,也體現了一種對文化人生的理解與向往。正好可以用來形容唐吟方其人其畫給我的印象。
就像唐吟方寫的《雀巢語屑》《新月故人》《藝林煙云》等書一樣,唐吟方的畫和他的字也是“個色”一路,看上去就和他這個人一樣:瘦骨嶙峋,高視闊步。他喜歡畫的更多是尋常蔬果日常餐飯,譬如他畫蘿卜青菜、藕節柿子、南瓜榴梿、大餅油條、粽子燒賣,呈現在紙上的還是飽滿的文人趣味,總有一點不甘于平庸的超脫與淡然,筆底藏不住的仍是那點舊時文人的心境。譬如他畫南瓜,一橫一豎,題曰:溫老暖貧。畫里畫外,他所守望的還是那點浸入骨子里的傳統文化的筆墨情懷。
至今仍清晰記得多年前第一次讀三聯書店出版的逯耀東的《寒夜客來》一書時,突然看到書里選用了唐吟方的畫當插圖,大為驚喜。但又感到出乎意料,因為唐吟方的畫個性鮮明,不是那種為談飲食的文章而特意畫的插圖。但細細一想,又覺得非常貼切,這樣豐富而又獨特的書,自然要有這樣有個性和內涵的插圖。《寒夜客來》是逯耀東繼《肚大能容》之后的又一本談中國飲食文化的隨筆集,書中旁征博引,追溯飲食淵源;作者文思典雅,學養與才情并茂。其筆下的飲食故事多有一份真切而醇厚的歷史滄桑感。書中的插圖,雖然不是應文特制,卻在文字的閱讀之外,豐富了此書的內容。
某日,唐吟方在微信朋友圈貼了一張圖片:一張折疊式的小飯桌,配文曰:“有桌一張,可疊可開,疊則成片,開則成桌。桌面不大,可容書二三。可以吃飯,可以搭腳,可以打盹,三四友來,還可打牌。諺云:桌不在大,能用便行。大了也沒用,我只占一角。”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他的性情和為人為文為畫的態度,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或說他的創作談。
唐吟方性格耿直,不人云亦云,用他自己的話說,一些據說特別紅的書家不知為什么他一直喜歡不起來。他坦承:“發覺自己的趣味真的很頑固。有個老朋友說我堅持浙江趣味海寧趣味,也有人說我頭腦不夠活絡,跟不上時風,但我固執以為有些個風氣,別看他是九層樓臺,很巍峨的樣子,大約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可以預見是雷峰塔轟然倒塌的結局。”
即使對一些譽滿天下的名家名人,唐吟方也堅持自己的評價。例如他談現在已經被書法界公認為大家的徐生翁,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赴紹興拜訪沈定庵先生時,才知道徐生翁這個名字,后來因為他的老師沈紅茶先生與生翁先生是畫友,就格外關注徐生翁。他當時在沈先生家看了徐生翁的墨跡,還有徐生翁年譜油印本,還看到沙孟海、陸維釗先生的題跋。沈先生提到他去杭州請沙老題生翁臨的一頁漢隸,沙老并不喜歡生翁字,但題跋文字并沒有直接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陸先生好像也表達了“成年人為什么要學兒童寫字”之類的話。
唐吟方說,他看不出徐生翁的高明之處,只覺得寫得很怪,但也得到了一種啟示,字原來還可以這樣寫。后來接觸了不少史料,如鄧散木1949年前跑到紹興去拜訪徐生翁,拿著徐生翁的字去請教蕭退庵,結果為退庵稱好。鄧于是撰文吹噓徐生翁的神妙,并引起好友唐云注意特地去紹興求字。唐吟方說他相信鄧散木雖然在上海寫了文章,但以上海文藝界當時的傳統,大概不會產生影響。
唐吟方說,他是徐生翁“身后名”的見證者,如果沒有沈定庵先生的執著,大概不會有徐生翁今天的“名滿天下”。當然,徐生翁的名氣與新時期挾新書風快速崛起的那批書家有關,更得力于時風的推波助瀾。唐吟方筆鋒一轉,說他不看后來仰慕者寫的徐生翁,常有預設的立場,你能企盼他能寫出歷史經緯上真實存在過的“徐生翁”?勾勒出的多半是供在神壇上的“徐生翁”。
再如他談當下的西泠印社:杭州西泠印社湖濱營業廳,如今依舊高懸著沙孟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寫的匾額“翰墨千秋”。大師駕鶴西歸,留下的墨跡猶新。二十世紀的風景漸漸遠去,二十世紀的印壇人物還在沉浮飄搖,曾經的煊赫終究歸于平靜,大師也罷,名家也罷。在梳理了一個世紀中國印壇工細和豪放兩種不同風格的篆刻路數的脈絡之后,他感嘆一個世紀的滄海桑田,留給印壇的只是極窄極窄的空間。留名歷史的大概只有少數,大多數注定會被埋沒……從事藝術的人若想不被埋沒,就要在這個狹窄的空間里拿出自己的作品獨自叩門,至于能否成功,則在于自己的造化。
讀書、寫作、書畫、篆刻、院子里勞作,構成了唐吟方的日常生活。就像一位書友所說:“筆不論枯與潤,紙不計短與長,養在舊日風雅里,雀巢吟其方。”墻邊竹影和破土的春筍,既構成了他的紙上畫面,也寄托了他的文人情思。幾叢芭蕉,數棵櫻桃,裝點了他鋪在案上的舊紙頭——他的枯筆殘墨間流淌的還是早已飄散無蹤的江南文人舊夢。
唐吟方的確是骨子里浸透傳統舊夢的文人,但又不是循規蹈矩泥古不化,而是有著當代探索的氣息,或說他自己的面貌。就像他在完成篆刻《南湖煙雨》之后所寫:“不過也知道自己是個不太有工匠精神的人,刻著刻著就會走神,弄些牛頭野叉的東西……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部有軌電車,當軌道鋪設好后,每天閉著眼睛開呀開呀……幾十年如一日……可惜天生是勞碌命,總是在東尋西找,尋找所謂的有意味的形式,其實在這個地球上你還能揪著自己的頭發飄到月球上?”他的視野是開放的,也關注民間,并非只是盯著廟堂和學院里的“學術”,例如他刻《春酒無深巷》,之所以治此印,他說:“那年參觀一個長沙窯展所見詩句,這是唐代底層老百姓的歌詠,關于酒的,很喜歡,移刻石頭上。”
唐吟方的生活是藝術化的,或說藝術融入了他的生活,他的創作遠離當代書畫界的主流,屬于在主流之外,邊緣的邊緣,但卻在四季的輪替里有著自己傲世獨立的精神,既感受著窗外的季節,也紓解著自己內心的波瀾。譬如他刻《江山風月》,初看此印,不由想起梁啟超的集聯:“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但在唐吟方的筆下,卻話鋒一轉:“已覺天氣涼。今日立秋,強推鈍刀刻頑石。印石石丁縱橫,行刀崎嶇,刻成自視,斑駁歷落,居然微有鈍丁前輩意,個中消息,不堪與專刻富貴石之大小名家言之,唯常刻劣石輩知之。惜此情不常也,恨恨!昔人言山水渾厚,得江山之助。拙印獨得劣石之助。”話里話外,別有滋味。
唐吟方畫中的人物當然是他的臆造,但卻有著魏晉“竹林七賢”時代的影子,當然,他的人物絕少那種魏晉人物的酒后瘋癲,更多的是陶淵明歸隱南山的閑散平和。在他看來,“前人的山林,今人的城市”。閉門就是深山,就像他說:他常常覺得完整的林和靖固然找不到了,林處士的影子總還留在許多讀古書的人身上。有些人總指責部分有林處士情結的人太裝,他倒覺得對于今人的林處士情結不宜過分以“潔癖”視之。有總比沒有好,至少證明這個社會是有包容力的。他的這段話可以看出他雖孤傲但并不“潔癖”,待人處事有知人閱世的容忍。
唐吟方畫外的“閑話”往往意蘊豐富,也耐人尋味,譬如他畫喇叭花,題曰:“連續三天尋訪朝顏,實不滿足白石筆下梅郎家的名種。白石當然清楚朝顏的物理特性,可我不知道,花三天時間反復觀察,終于探知一二。試畫一稿,不過朝顏那種英氣逼人的藍我是望塵莫及的。”當然,唐吟方也是與時俱進的,偶爾也畫當下的人物,但必然也是借題發揮,例如他在畫當下“時裝”人物之后題曰:山水有靈,若見畫家每每古冠今戴,必言“時間停止了”,故寫一二時裝人物縱情山水間。
唐吟方當然不是避世的“隱士”,只是不屑與所謂的書畫界的主流為伍,譬如他寫與古人的對話:“夜夢趙撝叔先生:……聽說我身后出了不少角色?我唯唯諾諾:是是。趙先生說:你倒跟我說說。我就把書上看過的姓名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人還不少哩。我說:只要有場子,為歷史獻技的人總不會少的。趙先生又問:依你看,這些成名人物怎么樣?我敬謝不敏,并再三說明自己連看客都稱不上,只是百年間的過客、糊涂蟲而已。趙先生捋捋胡子,緩緩道來:當年我攀交了不少大人物,他們也很幫我忙,到處說項,還湊錢幫我到一個窮地方當知縣,雖然如此,畢竟還不是一路人,我眼下就想聽聽你這個小人物說說。唉,趙大人您是出世早了,要是在今世,趕上文藝大發展,以您才情大概就不會這樣受窮受苦了……”
唐吟方是有態度的,也是自信的,這種自信體現在各個方面。他曾說,有人說只寫一體不是書法家,他倒是覺得成不成家是次要的,盡量吃透一體是重要的,一體都顧不上,貪多又何益。寫字以老實為本。所謂老實,筆送到,墨落實,又能盡力盡意,“光這幾個字就夠我一輩子硯田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