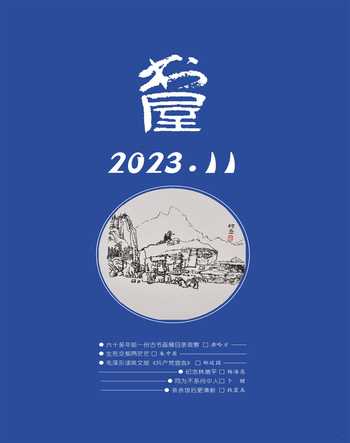“書止于顏魯公”
顏湘君
唐乾元元年(758),顏真卿滿懷悲慟寫下《祭侄贈贊善大夫季明文》(本文中簡稱《祭侄文稿》),此稿歷經一千二百余年,現典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為其限展級的鎮館之寶,是中國書法國寶級珍品。《祭侄文稿》不僅是書法藝術,更以其忠烈之氣深深感染和激勵著后人。
《祭侄文稿》是歷代鑒藏家、書法家爭相收藏賞鑒的作品,從印章、跋文來看,它是一件傳承有序的書法真跡。
顏真卿《祭侄文稿》書于乾元元年,歷二百余年而為宋初李士衡觀察所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傳承淵源。根據宋代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載:“顏魯公真跡,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侄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皆有石本……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宋史》有《李仕衡傳》,“李士衡”作“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進士及第,歷任京兆鄠縣主簿、邠州通判、度支員外郎、荊湖北路轉運使、給事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等,終同州觀察使知陳州。
北宋宣和年間,《祭侄文稿》被內府收藏,著錄于《宣和書譜》。《宣和書譜》二十卷為徽宗命文臣編纂內府所藏歷代法書而成,著錄歷代書家一百九十七人,作品一千三百四十四件,每種書體前都有敘論,敘述各種書體的淵源、發展情況;次為書法家小傳,記載作者生平,遺文軼事,并評論其書法的特點、優劣;最后是列御府所藏的作品目錄。卷第三“正書一”列舉唐代書家中就有顏真卿,評價為:“惟其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書之大雅,豈不宜哉!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云,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概也……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缺,不忍棄也。其為名流所高如此。后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燕尾,僅乃得之,曾不知‘以錐畫沙之妙,其心通而性得者,非可以糟粕議之也。嘗作《筆法十二意》,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今御府所藏二十有八。正書(按:六種):《旌節敕》……行書(按:二十二種):《爭坐前帖》……《祭侄季明文》。”《宣和書譜》明確著錄了內府收藏顏真卿二十八件書法作品中就有行書《祭侄文稿》。
元代,《祭侄文稿》先后歸于曹大本、鮮于樞和張晏。
山東鄆城人曹大本(字彥禮),生卒年不詳,宋末元初人。有學者根據元代虞集和吳澄為曹彥禮《運氣考定》所作之序、虞集《道園學古錄》、崇禎版《鄆城縣志》收入的曹大本《七十二賢畫像記》等材料考證,曹大本在元世祖至元時曾在杭州游歷,至元二十二年(1285)自杭州返回家鄉鄆城,曾指導鄆城縣尹劉彧改繪文廟內七十二賢畫像,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至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前后在大都為國子監教授。曹大本平生好收藏,曾藏有顏真卿《祭侄文稿》、柳公權《易賦靈寶經》等名家法書。曹大本與鮮于樞交好,同為元初期著名的書法家和收藏家,兩人常有共同賞鑒書法藝術作品之活動。《祭侄文稿》后部有兩處鮮于樞的題跋,都寫作“東鄆曹大本彥禮”。其一:“唐太師魯公顏真卿書《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書第二,余家法書第一。至元壬午春得于東鄆曹大本彥禮,甲申錢塘重裝,丙戌六月鮮于樞記。”另一處跋較長:“右唐太師魯國公書祭侄季明文稿。按《宣和書譜》載,內府所藏魯公書廿有八,此其一也。宣、政小璽及天水圓印遺跡隱然尚存。至元癸未,以古書數種易于東鄆曹彥禮,甲申來杭重裝。戊子十月九日,鮮于樞拜,手書。”元世祖至元年間(1264—1294),至元壬午為1282年,癸未為1283年、甲申是1284年,戊子是1288年。
按鮮于樞跋文所述,鮮于樞是以數種古書從曹大本手中換來的,視若珍寶,稱為“天下行書第二”。縱然鮮于樞愛如珍寶,奈何他去世后不久,《祭侄文稿》歸于張晏。張晏二跋《顏真卿祭侄文稿》,行楷,書于元大德七年(1303),首跋:“《宣和書譜》顏真卿《祭侄季明文》,知在錢塘,傳聞數年。辛丑歲,因到江浙,得于鮮于家。諸公聚觀,以為在世顏書中第一。”又跋:“世傳顏書凡見八本:《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頓首夫人帖》今在秘書監,《馬病帖》《允南母告》《昭甫告》今在田師孟郎中家,《太子太師告》在一豪貴家。此《祭侄季明文》今在余家。住京師,嘗會諸賢品題,以為告不如書簡,書簡不如起草。蓋以告是官作,雖端楷終為繩約,書簡出于一時之意興,則頗能放縱矣。而起草又出于無心,是其心手兩忘,真妙見于此也。觀于此帖,真行草兼備三法。前宋名重當時,宣和嘗收,后為庸功剪去印記。今于歲字傍猶有天水圓印痕跡,其幾于淹沒者數矣。向往錢塘,始獲見焉,既歸于予,喜不能寐。東坡有云:‘書止于顏魯公。亦予平生收書之志愿永足矣。大德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忠宣后人、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兼樞密院判張晏敬書于端本堂西勸學齋。”1302年,鮮于樞去世,次年《祭侄文稿》歸于張晏家。
明代徽商溪南吳氏和王氏先后也收藏過《祭侄文稿》。明代中期以后,徽商財力巨大,賈而好儒,汲汲于刻書藏書,對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傳播有卓越的貢獻。徽商形成了諸多名門望族,素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之說,“徽州八大姓”是指“新安十五姓”中的前八姓,即程、汪、吳、黃、胡、王、李、方八大姓。溪南吳氏和王氏就位列其中。
清初許弘勛布政使曾經得到《祭侄文稿》,交付給自己的幕僚徐介錫。因與徐介錫同宗的關系,徐乾學以高價購得真跡。徐乾學(1631—1694),字原一,號健庵,昆山(今江蘇昆山)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尚書等。徐乾學得到《祭侄文稿》后,寫下了一篇詳細的跋文以溯源、詮釋和評價這件書法珍寶:“顏魯公《祭侄季明文》真跡向為溪南吳氏收藏,后歸王氏。許布政弘勛得之,以付其幕官徐介錫。介錫與余有宗人之分,重價購焉,驚喜累日……后段書體益復激昂,忠憤勃發,神氣震蕩。公千古第一種人物,亦擅千古第一種書體。余衰年薄祜,何幸獲此重寶,因考史傳同異證其文義,而以臆見題識其后。子孫其永寶諸。康熙三十三年夏五月徐乾學謹題。時年六十有四。”
徐乾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獲得了他視為“重寶”并希望子孫后代“永寶”的《祭侄文稿》,但后人辜負了他的期望,這件重寶很快成為王鴻緒的藏品。王鴻緒(1645—1723),初名度心,中進士后改名鴻緒,字季友,號儼齋,別號橫云山人,華亭(今屬上海金山)人,清代官員、學者、書法家。王鴻緒精于鑒賞,工書法,對書畫研究很有造詣,是當時公認的書畫鑒定權威。他得到《祭侄文稿》后,在上面鈐下了諸多的鑒藏印章。
王鴻緒去世后,其長子王圖煒(字彤文)將《祭侄文稿》贈與伯父王頊齡(1642—1725)。王頊齡是清代著名文學家,晚號松喬老人。康熙十五年(1676)中進士,歷官日講起居注官、四川學政、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等。王頊齡寫下了激動的跋文:“魯公祭侄文真跡,昔在大司寇徐健庵先生所見之,后歸叔弟儼齋,又見之。其流傳始末考訂證據詳著于諸跋中,不待再贅一辭矣。惟是魯公忠義光日月,書法冠唐賢,片紙只字,足為傳世之寶。況祭侄文尤為忠憤所激發,至性所郁結,豈止筆精墨妙,可以振鑠千古者乎!從子彤文,知余素好古跡,寓書贈余,余暮年得此,如獲瑰寶。書此數語,以示子孫,當世世珍藏,與天地同不朽也。雍正二年十一月十日,松喬老人王頊齡謹識于燕山邸舍,時年八十有三。”又跋:“按唐肅宗乾元元年戊戌,至今皇帝雍正二年甲辰,凡九百六十七年。魯公此書,閱歷已及千載矣。非魯公之忠孝友義,足以感格天地,書法之雄奇變化,至于超神入圣,安能數經兵燹,而紙墨完好,神采煥然若是乎:意必有神物護持,故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也。為之驚嘆無已,爰志數語,以著其流傳之永久云。松喬老人同日載題。”
數十年后,《祭侄文稿》真跡被王氏后人賣與鹽商,鹽商重利,再賣,《祭侄文稿》遂歸于內府所藏。乾隆皇帝丙午(1786)御筆《顏真卿〈祭侄文稿〉記》備述詳情:“內府所收顏真卿真跡凡四,入石渠寶笈者一(真卿書建中三年朱巨川告身),待續入者三(真卿自書告身卷,又書建中元年朱巨川告身卷,又裴將軍詩卷),別有一爭座位帖似屬贗,鼎列之石渠次等不以為珍也。茲乃得其《祭侄季明文稿》真跡,批閱一再,嘆其一家舍身盡節而為其君者如不知也。又嘆其經千年滄桑之變而故紙宛存,誠有所謂神物呵護者也……此卷之顯晦流傳,王頊齡、徐乾學論之詳矣,茲不復贅。獨是二人者,皆本朝世家,亦當叮嚀其子弟善守希珍矣。今其子弟不能守而鬻之鹽商,搉鹽者從而貰之以登之內府。撫卷三嘆,知忠烈之可以永存而聲華之未必恒保,更思時有忠烈之臣則其世必多喪亂之事,是可畏之甚也。且此數卷獨非宣和書譜中所有之真跡乎,其輾轉流落民間又將六百余歲矣,然則弆此卷于禁中,胥足以為殷鑒之警,是不可不記。乾隆丙午孟秋月御筆。”
清朝覆亡后,《祭侄文稿》為國民政府所有,終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祭侄文稿》自寫成后經歷了一千二百余年曲折艱難的歷史,它的流傳經歷不僅可以從各處跋文中追尋到,而且還能從中國歷代鑒藏家們在上面鈐下的一個個鮮紅的印章中找到歷史證據。
按元代張晏跋文所言,《祭侄文稿》“前宋名重當時,宣和嘗收,后為庸功剪去印記。今于歲字傍猶有天水圓印痕跡,其幾于淹沒者數矣。”現在可見的都是元、明、清三代的印章,這些印章又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帝王印章,主要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印章最多,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太上皇帝之寶”“古希天子”“古希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壽”“御書房鑒藏寶”“宜子孫”“三希堂精鑒璽”“石渠寶笈”“乾隆御覽之寶”等。嘉慶皇帝有“嘉慶御覽之寶”,末代皇帝溥儀有“宣統御覽之寶”“宣統鑒賞”“無逸齋精鑒璽”。
第二類是私人收藏家印章。寶物為我所有,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以花樣繁多的鮮紅印章表示對寶物的所有權。此類印章最多的莫過于鮮于樞、張晏、徐乾學、王鴻緒、王頊齡。
第三類是鑒賞者印章。他們有機會過眼藏品,又能在寶物上留下千秋姓名,也興致勃勃,以鈐蓋印章表示自己曾經看見過、欣賞過藏品。有些鑒賞者未能留下印章,僅有文字記載,如周密、屠約、王圖炳等。
在《祭侄文稿》一千二百余年的收藏、傳播史中,那些留存下來的跋文和印章生動地表達了人們對它的由衷熱愛和景仰,也記錄了它的遷徙。歷經世易時移的動蕩,無數的寶藏被毀,《祭侄文稿》卻越過“紙壽千年”的困境成為中國書法文物至寶。那一個個鮮紅的“世所希有”“子孫寶之”“宜子孫”的印章讓人們不禁感喟,先賢的忠烈之氣與書法之妙確乎可以震古爍今!